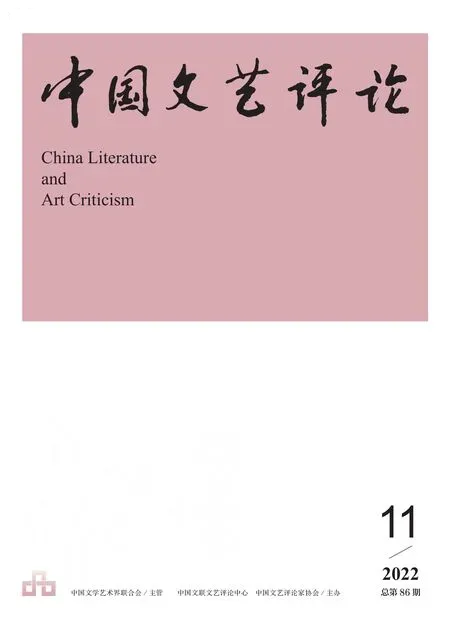明確的是非 熱烈的愛(ài)憎
——訪文藝評(píng)論家鄭伯農(nóng)
■ 采訪人:許 瑩

鄭伯農(nóng)簡(jiǎn)介:1937年生,福建長(zhǎng)樂(lè)人。1951年進(jìn)入中央音樂(lè)學(xué)院附屬中學(xué),1962年畢業(yè)于中央音樂(lè)學(xué)院音樂(lè)學(xué)系。歷任中央音樂(lè)學(xué)院教師、中央戲劇學(xué)院兼職教師,文化部政策研究室干部,中國(guó)文聯(lián)研究室理論組組長(zhǎng)、研究室負(fù)責(zé)人,《文藝?yán)碚撆c批評(píng)》常務(wù)副主編,中國(guó)作家協(xié)會(huì)黨組成員、《文藝報(bào)》總編輯,中國(guó)作家協(xié)會(huì)全國(guó)委員會(huì)委員、名譽(yù)委員,中國(guó)社會(huì)主義文藝學(xué)會(huì)會(huì)長(zhǎng)、名譽(yù)會(huì)長(zhǎng),中華詩(shī)詞學(xué)會(huì)常務(wù)副會(huì)長(zhǎng)、代會(huì)長(zhǎng)、名譽(yù)會(huì)長(zhǎng),《中華詩(shī)詞》主編。1958年開(kāi)始發(fā)表文章,部分作品被翻譯到國(guó)外。著有《鄭伯農(nóng)文選》四卷(含文論、詩(shī)詞、詩(shī)論)等。
一、音樂(lè)評(píng)論界的學(xué)徒與新星
許瑩(以下簡(jiǎn)稱(chēng)“許”):您的第一愛(ài)好是音樂(lè),1951年您進(jìn)入中央音樂(lè)學(xué)院附中學(xué)習(xí)大提琴,1962年畢業(yè)于中央音樂(lè)學(xué)院音樂(lè)學(xué)系,能否回顧下您的學(xué)子生涯?
鄭伯農(nóng)(以下簡(jiǎn)稱(chēng)“鄭”):1951年春,我初進(jìn)京,偶然從報(bào)紙上看到一則招生啟事,說(shuō)是中央音樂(lè)學(xué)院成立附屬中學(xué),要招第一屆學(xué)生。我酷愛(ài)音樂(lè),征得父母同意后,于1951年夏天前往天津參加附中考試,當(dāng)時(shí)報(bào)考的人很多,一共錄取了16個(gè)人,其中就包括我。我所在的班叫“五一班”,和我同班的有著名鋼琴家劉詩(shī)昆、鮑蕙蕎等。在附中學(xué)習(xí)的第一年,大家一律都要學(xué)鋼琴,到了第二年分專(zhuān)業(yè)時(shí),我學(xué)了大提琴,教我拉琴的是王友健老師,他是院長(zhǎng)馬思聰?shù)男【俗印?/p>
時(shí)任中央音樂(lè)學(xué)院副院長(zhǎng)、中國(guó)音樂(lè)家協(xié)會(huì)主席呂驥醞釀著在中央音樂(lè)學(xué)院成立音樂(lè)學(xué)系,專(zhuān)攻音樂(lè)理論評(píng)論、音樂(lè)史研究等。他的學(xué)生也是他的部下黃翔鵬,在我初三那年進(jìn)入附中當(dāng)教務(wù)長(zhǎng)。他是我的啟蒙老師,講課很有吸引力,對(duì)我影響很大。我上到高二的時(shí)候,黃老師找我談話,希望我能搞音樂(lè)理論,并袒露了中央音樂(lè)學(xué)院要成立一個(gè)音樂(lè)學(xué)系的想法。黃老師是個(gè)全才,西方音樂(lè)他懂,民族音樂(lè)他也很精通。記得第一次上課,他一上來(lái)就教了我三十多首民歌,其中有的我熟悉,有的我不熟悉,他讓我把這三十多首民歌都背下來(lái),我很快就背會(huì)了。
黃翔鵬老師讓我搞音樂(lè)理論,也是考慮到家庭環(huán)境對(duì)我成長(zhǎng)的影響。我父親是杭州地下黨,解放前我們和他不住在一起,因?yàn)樗奶庯h零,有時(shí)候還會(huì)被通緝。全國(guó)解放后,父親奉調(diào)從杭州前往北京,參加《學(xué)習(xí)》雜志的創(chuàng)辦和編輯工作。后來(lái)《學(xué)習(xí)》雜志社的很多人被調(diào)到《紅旗》雜志,我父親也被調(diào)到《紅旗》雜志工作。他本人是搞理論的,所以給我看了很多理論方面的書(shū)。當(dāng)時(shí)有干部必讀的書(shū),這當(dāng)然是給成年干部看的,但是他也給我讀。坦白地講,從初中開(kāi)始我就看馬列主義的書(shū),《共產(chǎn)黨宣言》等都是我在初中的時(shí)候就讀過(guò)的。記得《毛澤東選集》出版后,父親馬上給我買(mǎi)了一套。小時(shí)候我或許還不能真正領(lǐng)會(huì)這些書(shū)中的內(nèi)涵,但卻讀得津津有味,并且反復(fù)重讀、溫故知新。
高三我就不學(xué)大提琴了,而是跟著黃老師學(xué)習(xí)音樂(lè)理論。高三上半年,他讓我寫(xiě)了一篇關(guān)于德國(guó)作曲家舒伯特的論文,集中談他的兩部聲樂(lè)套曲:《美麗的磨坊女》和《冬之旅》。到了下半年,他又給我出了個(gè)題目,讓我寫(xiě)聶耳。當(dāng)時(shí)關(guān)于聶耳的資料很少,本來(lái)中央音樂(lè)學(xué)院有一個(gè)民族音樂(lè)研究所,那里保存著部分聶耳的日記、書(shū)信、筆記、手稿等,后來(lái)這個(gè)研究所獨(dú)立出去,所址遷到了北京。當(dāng)時(shí)我們?cè)谔旖颍屈S老師給我開(kāi)的介紹信,讓我到研究所找他的幾位朋友。研究所給了我很多照顧。那時(shí)候我年紀(jì)比較小,黃老師的朋友拿飯票請(qǐng)我吃飯,我在民族音樂(lè)研究所看資料,有些很長(zhǎng)的資料經(jīng)所里特批允許我?guī)Щ丶页?yīng)該說(shuō),高中最后半年,我都是在研究聶耳。或許也說(shuō)不上研究,那時(shí)我還是個(gè)中學(xué)生,但是我把能找到的關(guān)于聶耳的東西都找到了,同時(shí),我還看了不少有關(guān)近現(xiàn)代音樂(lè)史的資料。
黃老師過(guò)去是地下黨員,對(duì)革命事業(yè)和革命音樂(lè)非常忠誠(chéng)。他對(duì)我說(shuō),寫(xiě)救亡抗日歌曲,并非始于聶耳等左翼音樂(lè)家,黃自在他們之前就寫(xiě)了《抗敵歌》和《旗正飄飄》,但真正在音樂(lè)中寫(xiě)出群眾的心聲,深入到廣大老百姓中去,以至掀起救亡歌詠運(yùn)動(dòng),是從聶耳開(kāi)始的。與黃老師一起,在他的指導(dǎo)下研究聶耳,對(duì)我的世界觀、文藝觀產(chǎn)生了巨大影響。
黃老師曾和我說(shuō),你學(xué)這個(gè)專(zhuān)業(yè),不僅要看音樂(lè)方面的書(shū),關(guān)于文學(xué)、歷史、哲學(xué)等的古今中外的書(shū)都要看,面要打?qū)挕N业呐d趣比較廣泛,基本上按照老師的思路去做,在中學(xué)期間為理論研究打下了一點(diǎn)基礎(chǔ)。后來(lái),我順利考上了中央音樂(lè)學(xué)院音樂(lè)學(xué)系,并成為1957年該系成立時(shí)招收的第一屆學(xué)生。
附中畢業(yè)進(jìn)入大學(xué),全國(guó)轟轟烈烈的反右斗爭(zhēng)也開(kāi)始了。那時(shí)幾乎每天都開(kāi)會(huì)批判右派,課也上了一些,但上得不算很正規(guī)。那一年趙沨來(lái)了,接替呂驥當(dāng)中央音樂(lè)學(xué)院院長(zhǎng)。趙沨很重視業(yè)務(wù),邀請(qǐng)?zhí)K聯(lián)專(zhuān)家來(lái)講學(xué),外地很多人都慕名來(lái)聽(tīng)課。蘇聯(lián)專(zhuān)家也不是只講社會(huì)主義的東西,他們從西方古典音樂(lè)講起,從巴赫、莫扎特、貝多芬一直講到浪漫樂(lè)派、民族樂(lè)派和現(xiàn)代音樂(lè),蘇聯(lián)音樂(lè)也講一些。
我們學(xué)校還是主要擅長(zhǎng)于西方音樂(lè),但我自己對(duì)民族音樂(lè)比較感興趣。大學(xué)第二年,中央民族事務(wù)委員會(huì)和文化部組織全國(guó)第一次少數(shù)民族普查。我被派往湖南苗族、瑤族、侗族、土家族地區(qū)進(jìn)行普查,為期一年,我覺(jué)得收獲很大。我不僅收集音樂(lè),也收集民間故事等。那時(shí)候縣城一般通汽車(chē),縣城以下就不一定通汽車(chē)了。我要到縣城以下去調(diào)查,就得一頭挑著行李,一頭挑著碩大的鋼絲錄音機(jī),有時(shí)候一天要走幾十里路,那一年我不知道跑壞了多少雙鞋。我跑了十來(lái)個(gè)縣,還去了一趟湖北。湖北也有土家族,就在恩施一帶。當(dāng)時(shí)湖南調(diào)查組要和湖北調(diào)查組交換信息,就派我前往恩施同他們交換材料,同時(shí)也在那邊做了些實(shí)地考察。
許:這次實(shí)地考察您有何經(jīng)驗(yàn)與收獲?您最早是學(xué)習(xí)大提琴的,后來(lái)又參加了很多民族音樂(lè)的考察。對(duì)于西樂(lè)與民樂(lè),您當(dāng)時(shí)的態(tài)度是怎樣的,是否存在某種轉(zhuǎn)變?
鄭:我收獲很大。不僅了解了一些音樂(lè),也了解了一些老百姓的生活。那時(shí)候農(nóng)村沒(méi)有招待所,下鄉(xiāng)就把我們派到多家貧下中農(nóng)那里住,自己帶著鋪蓋卷,吃“派飯”。老百姓很尊重我們,看我們是北京來(lái)的,會(huì)給我們改善一下伙食。那時(shí)候人們生活水平比較低,老百姓給我們弄點(diǎn)豆腐、豆芽菜,有時(shí)候還會(huì)有少量肉。同吃同住,我們和老百姓的距離更近了。收集民歌,不是擺譜擺得越大,說(shuō)我是北京來(lái)的,我有什么來(lái)頭,人家就會(huì)給你表演,而是你必須跟他交朋友,他才能放得開(kāi),能夠自然地唱給你聽(tīng)。我們有時(shí)先唱一兩句當(dāng)?shù)厣贁?shù)民族的歌,他們覺(jué)得很稀奇、很親切,你也能唱他的東西,感受到了我們對(duì)他的理解、尊重,他也就開(kāi)口唱了。
對(duì)于西樂(lè)和民樂(lè)的態(tài)度,其實(shí)不存在什么轉(zhuǎn)變。小時(shí)候我就喜歡看唱本,我對(duì)福州評(píng)話、閩劇都感興趣。我拉二胡,曾給閩劇伴奏過(guò)。對(duì)西洋音樂(lè)我也很喜歡,比如我對(duì)貝多芬、柴科夫斯基近乎崇拜。我也崇拜咱們中國(guó)的聶耳、冼星海。但是我不喜歡那種不顧群眾需要、覺(jué)得群眾欣賞水平太低、擺出一副高人一等姿態(tài)的音樂(lè)家。
新時(shí)期以來(lái),我們引進(jìn)了不少西方現(xiàn)當(dāng)代文化新成果。有些人很關(guān)注現(xiàn)代派文藝。其實(shí)在西方,受眾最多的是他們的“大眾文藝”,如街舞、流行音樂(lè)等等。西方“大眾文藝”和我們講的“大眾化”并不是一碼事,它是速成的、類(lèi)型化的、時(shí)尚的、適應(yīng)大眾趣味的。我們的一些作者吸收它的積極成果,創(chuàng)造了一些為群眾所喜愛(ài)的東西。至于說(shuō)追崇現(xiàn)代派音樂(lè),在西方也是很少數(shù)人。比如有一首西方現(xiàn)代派音樂(lè)叫《4分33秒》,全程沒(méi)有聲音。還有西方后來(lái)的一些現(xiàn)代派器樂(lè),基本沒(méi)有樂(lè)音、沒(méi)有諧和音、沒(méi)有旋律,群眾聽(tīng)得很吃力。公元前6世紀(jì),古希臘的畢達(dá)哥拉斯學(xué)派就提出“美是和諧”。我認(rèn)為美不等于和諧,但美還是同和諧有很大關(guān)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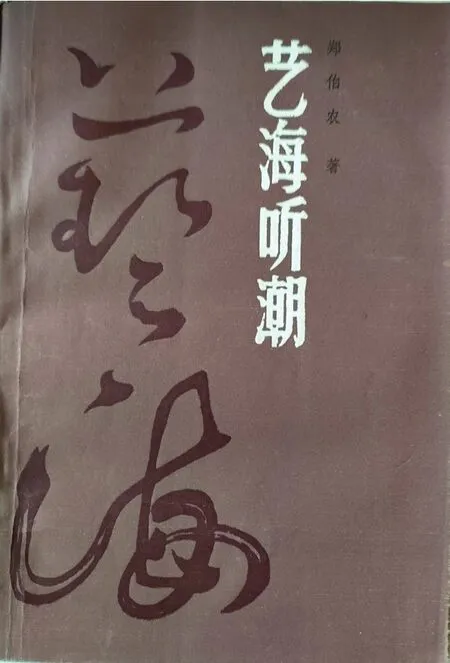
圖2 理論評(píng)論集《藝海聽(tīng)潮》 鄭伯農(nóng) 著
許:在《鄭伯農(nóng)文選》文論卷中,第一篇收錄的就是您在1962年10月發(fā)表的《淺論歌劇中的戲劇與音樂(lè)關(guān)系》。能否和我們談?wù)勀谝魳?lè)理論評(píng)論方面初登文壇的故事?
鄭:我在下面跑了一整年,回來(lái)之后我繼續(xù)上學(xué)寫(xiě)了不少東西。大學(xué)畢業(yè)以前,我的文章就比較引起社會(huì)注意了,當(dāng)時(shí)的我應(yīng)該算是音樂(lè)評(píng)論界的一個(gè)新人了。

圖3 《鄭伯農(nóng)文選》四卷 鄭伯農(nóng) 著
但是“反右”以后,大批判比較厲害,我也跟著這股思潮寫(xiě)了一些“左”的文章,比如說(shuō)當(dāng)時(shí)我批判過(guò)李凌,寫(xiě)過(guò)兩篇批判文章,一篇講“雙百”方針問(wèn)題,另一篇講輕音樂(lè)問(wèn)題。李凌是國(guó)統(tǒng)區(qū)新音樂(lè)運(yùn)動(dòng)的代表人物,曾任《新音樂(lè)》雜志的主編。解放前《新音樂(lè)》雜志的發(fā)行量達(dá)到一兩萬(wàn)份,影響和貢獻(xiàn)都很大。李凌后來(lái)成為中央樂(lè)團(tuán)團(tuán)長(zhǎng)。我覺(jué)得這兩篇文章傷害了這位老前輩。在1979年召開(kāi)的音代會(huì)上,呂驥同志在工作報(bào)告中講到當(dāng)年的這場(chǎng)批判,他為此承擔(dān)責(zé)任,做了自我批評(píng)。事實(shí)上文章并不是呂驥組織的,我們這些寫(xiě)文章的人理應(yīng)承擔(dān)責(zé)任。粉碎“四人幫”之后,1980年初在廣州召開(kāi)的一個(gè)音樂(lè)討論會(huì)上,我就批判李凌問(wèn)題做了自我批評(píng)。
那時(shí)我寫(xiě)音樂(lè)理論評(píng)論文章也不是一無(wú)是處。比如1962年大批判已經(jīng)很厲害了,小提琴協(xié)奏曲《梁祝》未能幸免,這部作品是1958年上海音樂(lè)學(xué)院的何占豪和陳鋼兩人創(chuàng)作的。當(dāng)年批判《梁祝》,說(shuō)這部作品寫(xiě)的是帝王將相、才子佳人。我覺(jué)得就算是寫(xiě)才子佳人它也是在反封建、反對(duì)包辦婚姻。《梁祝》受批判后,《人民音樂(lè)》頭條刊發(fā)了我的《為〈梁祝〉辯》,當(dāng)時(shí)這篇文章在音樂(lè)界產(chǎn)生了一定的影響。如今,《梁祝》在當(dāng)代音樂(lè)史上的地位已毋需多言,我也就沒(méi)有將這篇文章收到文選中去。
還有一篇文章值得一提,但是也沒(méi)有收到我的文選中。20世紀(jì)60年代,國(guó)內(nèi)音樂(lè)界有不少人對(duì)蘇聯(lián)的克林姆遼夫很崇拜。但在我看來(lái),他是形而上學(xué)、經(jīng)常將問(wèn)題簡(jiǎn)單化的理論家。他主張音樂(lè)就是反映現(xiàn)實(shí)生活中的聲音,認(rèn)為音樂(lè)家要多聽(tīng)生活中的聲音,還說(shuō)俄羅斯格林卡在家里養(yǎng)了一只鳥(niǎo),聽(tīng)著鳥(niǎo)叫的聲音進(jìn)行音樂(lè)創(chuàng)作。我認(rèn)為音樂(lè)不是簡(jiǎn)單地寫(xiě)生活中的聲音。寫(xiě)月亮的音樂(lè)作品有很多,比如貝多芬的《月光曲》、華彥鈞的《二泉映月》、德彪西的《月光》,還有根據(jù)琵琶曲《潯陽(yáng)月夜》改編的《春江花月夜》……月亮有什么聲音呢?你們誰(shuí)聽(tīng)過(guò)啊?在我們那個(gè)年代,誰(shuí)也沒(méi)聽(tīng)過(guò)月亮的聲音,為什么有那么多音樂(lè)寫(xiě)月亮呢?我認(rèn)為,音樂(lè)是用來(lái)表達(dá)人的感情的,但人的感情未必都是有聲音的。當(dāng)然,克林姆遼夫也有他的一套理論。1964年,我寫(xiě)了一篇談音樂(lè)特征的長(zhǎng)文,批評(píng)了蘇聯(lián)克林姆遼夫?qū)ξㄎ锓从痴摰挠顾谆_@篇文章有一定的建設(shè)性見(jiàn)解,也有突出的缺陷。它不承認(rèn)音樂(lè)有“不確定性”,這個(gè)論斷太極端化。同一個(gè)曲調(diào)、曲牌,因演唱演奏的不同,因旋律有變化,可以表現(xiàn)不同的感情。對(duì)于這一常見(jiàn)現(xiàn)象,應(yīng)當(dāng)進(jìn)行深入探討。
至于“文革”前書(shū)寫(xiě)的唯一被收錄進(jìn)文選的這篇《淺論歌劇中的戲劇與音樂(lè)關(guān)系》,比較認(rèn)真地探討了歌劇創(chuàng)作中的核心問(wèn)題。新歌劇這個(gè)稱(chēng)呼,是時(shí)任文化部副部長(zhǎng)劉芝明在1956年第一屆全國(guó)音樂(lè)周閉幕詞中確定的。它既不是外國(guó)歌劇的簡(jiǎn)單移植,也不是中國(guó)戲曲的新劇種,而是一種既繼承民族傳統(tǒng)又借鑒外國(guó)寶貴經(jīng)驗(yàn)的藝術(shù)樣式。20世紀(jì)20年代黎錦暉的《麻雀與小孩》《小小畫(huà)家》等作品開(kāi)了新歌劇的先聲,1945年《白毛女》的誕生標(biāo)志著中國(guó)新歌劇從幼年走向成熟。有一些人主張學(xué)習(xí)外國(guó)歌劇從頭到尾都是唱。事實(shí)上,外國(guó)大歌劇從頭唱到尾,但外國(guó)輕歌劇、喜歌劇并非如此,它們也有說(shuō)話。西方歌劇始終沒(méi)有解決好唱和白的關(guān)系。外國(guó)正歌劇里有詠嘆調(diào)和宣敘調(diào),詠嘆調(diào)音樂(lè)性很強(qiáng),宣敘調(diào)把對(duì)話用音樂(lè)表達(dá)出來(lái),它不求旋律的動(dòng)人,只求音樂(lè)風(fēng)格的統(tǒng)一。我們也曾嘗試用宣敘調(diào)來(lái)展現(xiàn)對(duì)話,如“請(qǐng)坐下”“請(qǐng)喝茶”等等,但是演員一唱,臺(tái)下都跟著笑起來(lái)。
在我看來(lái),中國(guó)的戲曲是世界上最完美的一種綜合藝術(shù),它把各種藝術(shù)元素完美地交織在一起。它的包容度很大,戲劇、文學(xué)、音樂(lè)、舞蹈、雜技(如噴火、變臉),還有雕塑(如京劇凝固的亮相美)等元素都被容納其中,而且中國(guó)戲曲中不存在說(shuō)和唱不協(xié)調(diào)的問(wèn)題。京劇有韻白、有京白,《西廂記》里紅娘說(shuō)的是京白,崔鶯鶯說(shuō)的是韻白。中國(guó)戲曲在唱和白之間有種種過(guò)渡的東西,比如上場(chǎng)引子、定場(chǎng)詩(shī),介于唱和說(shuō)之間的吟誦。新歌劇當(dāng)然不一定要直接模仿戲曲的韻白,但是戲曲豐富的說(shuō)白傳統(tǒng)以及處理從說(shuō)到唱之間的種種藝術(shù)手法,對(duì)新歌劇創(chuàng)作是具有借鑒意義的。
“文革”前寫(xiě)的文章里,有個(gè)別幾篇還是能留下來(lái)的。那個(gè)時(shí)期我主要還是當(dāng)學(xué)徒,實(shí)習(xí)怎么去寫(xiě)音樂(lè)評(píng)論,還不能算是真正的音樂(lè)評(píng)論家。
二、把人民作為文藝審美的鑒賞家和評(píng)判者
許:2019年《文藝報(bào)》創(chuàng)刊70周年您和夫人李燕平老師親臨現(xiàn)場(chǎng),據(jù)我所知燕平老師比您到報(bào)社還要早。請(qǐng)談?wù)勀汀段乃噲?bào)》的往事吧。
鄭:1977年初,我被借調(diào)到文化部政策研究室。彼時(shí),研究室的總負(fù)責(zé)人是馮牧,復(fù)刊時(shí)的《文藝報(bào)》主編是馮牧、孔羅蓀。兩個(gè)單位的領(lǐng)導(dǎo)都是馮牧,相當(dāng)于“一主二仆”。辦公地點(diǎn)也緊挨著,研究室在東四禮士胡同路南,《文藝報(bào)》在路北,門(mén)對(duì)著門(mén),大家信息互通、工作互補(bǔ),關(guān)系十分密切。我也為《文藝報(bào)》提供過(guò)不少稿件,得到過(guò)他們的許多幫助。

圖4 與作協(xié)領(lǐng)導(dǎo)及《文藝報(bào)》同仁參加“瞿秋白散文、雜文”征稿、頒獎(jiǎng)活動(dòng),前排左起:嚴(yán)昭柱、楊子敏、鄭伯農(nóng)、吳泰昌、李興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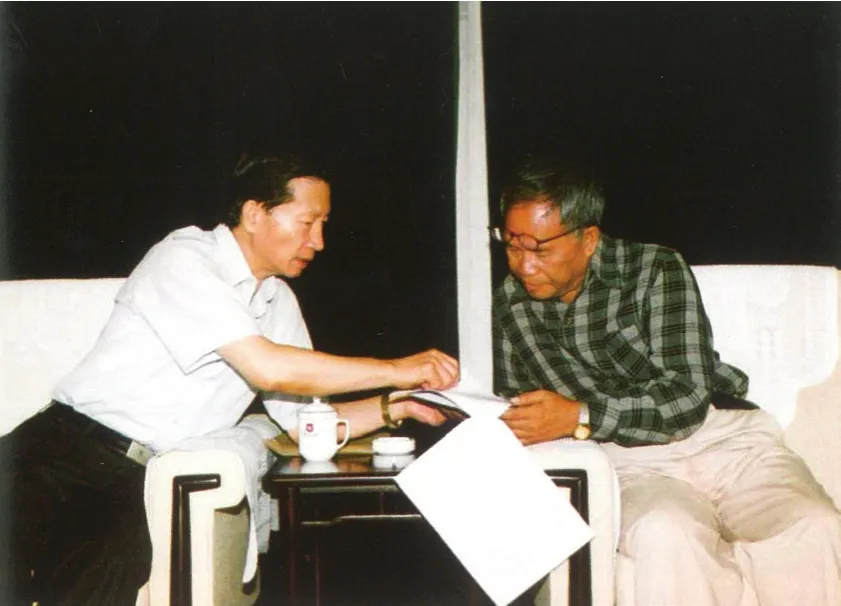
圖5 與金炳華在北戴河創(chuàng)作之家推敲文稿
我愛(ài)人剛辦完困退手續(xù)回京不久就生下我們唯一的女兒。一家三口,靠我一個(gè)人的工資過(guò)日子。我是借調(diào)干部,編制在中央音樂(lè)學(xué)院,沒(méi)有為音樂(lè)學(xué)院干任何活,人家沒(méi)理由給我發(fā)補(bǔ)助款、調(diào)工資。1978年6月,考慮到我的家庭困難,也考慮到我愛(ài)人的實(shí)際能力,丁寧、馮牧、謝永旺等領(lǐng)導(dǎo)同志商量,把她安排到將要復(fù)刊的《文藝報(bào)》去擔(dān)任編務(wù)工作。她在《文藝報(bào)》編務(wù)組、總編室先后干了十余年,我于1989年末到《文藝報(bào)》任職,由于夫妻倆不能在同一個(gè)單位,她被調(diào)到了作家出版社總編辦公室。
《文藝報(bào)》創(chuàng)刊于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成立前夕,原是中國(guó)文聯(lián)委托中國(guó)作協(xié)主辦的文藝界機(jī)關(guān)刊物。1978年文聯(lián)召開(kāi)全委會(huì),決定恢復(fù)《文藝報(bào)》,它面向整個(gè)文藝界。1985年,《文藝報(bào)》從刊物改成報(bào)紙。從1989年末到1998年上半年,我在《文藝報(bào)》當(dāng)了近九年的總編輯,曾提議請(qǐng)?jiān)袊?guó)文聯(lián)研究室的李興葉到《文藝報(bào)》工作,經(jīng)中宣部同意,任副總編輯,此外,我沒(méi)有帶去任何一個(gè)干部。報(bào)社原有新聞部、理論部、文學(xué)評(píng)論部、藝術(shù)部、副刊部,版面格局一律不變,各部負(fù)責(zé)人也沒(méi)有變動(dòng)。根據(jù)中宣部的安排,原副總編輯中留下吳泰昌、鐘藝兵二人。后來(lái),從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院文學(xué)所調(diào)來(lái)文藝?yán)碚摷覈?yán)昭柱,增加一名副總編輯。我主持《文藝報(bào)》期間,在兩屆作協(xié)黨組的領(lǐng)導(dǎo)下,和《文藝報(bào)》同仁對(duì)新時(shí)期各種文藝思潮進(jìn)行梳理,就若干重大問(wèn)題展開(kāi)討論:如文藝和政治的關(guān)系問(wèn)題、現(xiàn)實(shí)主義問(wèn)題、人性人道主義問(wèn)題、現(xiàn)代主義和后現(xiàn)代主義問(wèn)題、“文學(xué)的主體性”問(wèn)題、“重寫(xiě)文學(xué)史”問(wèn)題、“文學(xué)尋根”問(wèn)題、“啟蒙與救亡的二重變奏”問(wèn)題、美學(xué)中的“崇高”問(wèn)題等。我們大力支持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diǎn)分析評(píng)論這些問(wèn)題,同時(shí)也刊登了多種不同觀點(diǎn)的文章。我們繼承了《文藝報(bào)》推薦、扶植優(yōu)秀新人新作的優(yōu)良傳統(tǒng),特別強(qiáng)調(diào)留意和支持那些反映時(shí)代精神的優(yōu)秀新作,同時(shí)注意主旋律和多樣化的結(jié)合。1998年,我超過(guò)60歲了,這一年秋天,作協(xié)決定免去我《文藝報(bào)》總編輯的職務(wù)。離開(kāi)報(bào)社,我仍留在黨組,主要抓作協(xié)理論批評(píng)委員會(huì)的工作。2000年,金炳華同志到作協(xié)任黨組書(shū)記,超齡的黨組、書(shū)記處成員一律不再任職。
許:在您看來(lái)馬克思主義文藝觀的科學(xué)性和先進(jìn)性何在?如何看待文藝思想領(lǐng)域出現(xiàn)的種種分歧?
鄭: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中說(shuō),馬克思一生有兩大發(fā)現(xiàn),一是唯物史觀,一是剩余價(jià)值學(xué)說(shuō)。他說(shuō),正像達(dá)爾文發(fā)現(xiàn)有機(jī)界的發(fā)展規(guī)律一樣,馬克思發(fā)現(xiàn)了人類(lèi)歷史的發(fā)展規(guī)律。我至今仍舊堅(jiān)定地信仰馬克思主義,可以說(shuō),我一輩子信仰馬克思主義。為什么?首先是因?yàn)轳R克思主義所指導(dǎo)的“無(wú)產(chǎn)階級(jí)的運(yùn)動(dòng)是絕大多數(shù)人的,為絕大多數(shù)人謀利益的獨(dú)立的運(yùn)動(dòng)”[1][德]卡·馬克思、[德]弗·恩格斯:《共產(chǎn)黨宣言》,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11頁(yè)。。其次就是歷史唯物主義。過(guò)去人們認(rèn)為,歷史的發(fā)展是人的主觀愿望決定的,比如皇帝等大人物決定了歷史的發(fā)展走向,而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歷史發(fā)展的終極原因是物質(zhì)生產(chǎn)。生產(chǎn)力決定生產(chǎn)關(guān)系,經(jīng)濟(jì)基礎(chǔ)決定上層建筑和意識(shí)形態(tài),后者又反過(guò)來(lái)影響前者。思想意識(shí)的發(fā)展變化,不能僅從精神領(lǐng)域找原因,還要從物質(zhì)生活中找原因。文藝的發(fā)展也是這樣的。在我看來(lái),只有用歷史唯物主義作指導(dǎo),才能科學(xué)地解釋文藝的歷史發(fā)展和各種復(fù)雜的文藝現(xiàn)象。當(dāng)然,中外歷代文藝?yán)碚摷覍?duì)文學(xué)藝術(shù)的“秘密”進(jìn)行了多方面認(rèn)真的探討,其成果不容抹殺,我們要認(rèn)真加以繼承和借鑒。但只有用唯物史觀來(lái)觀照文藝,才能從根本上弄清文藝發(fā)展的真正動(dòng)因。
文藝是怎么產(chǎn)生的?正如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huì)上的講話》(以下簡(jiǎn)稱(chēng)《講話》)提出的,人類(lèi)的社會(huì)生活“是一切文學(xué)藝術(shù)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他還進(jìn)一步強(qiáng)調(diào),“這是唯一的源泉,因?yàn)橹荒苡羞@樣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個(gè)源泉”。[2]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huì)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60頁(yè)。有人說(shuō)《講話》只是講文藝的“外部規(guī)律”。生活當(dāng)然不等于文藝,但文藝是把生活加以藝術(shù)概括,加以典型化。作家必須深入社會(huì)實(shí)踐,了解人民的生活,對(duì)生活有獨(dú)特的感悟,才能寫(xiě)出有價(jià)值的文學(xué)作品。從生活到文藝,再?gòu)奈乃嚪醋饔糜谏睿瑥淖匀幻馈⑸鐣?huì)美到藝術(shù)美,然后藝術(shù)美又反過(guò)來(lái)提高人的審美水平和美感,文藝?yán)碚摼褪且芯窟@些東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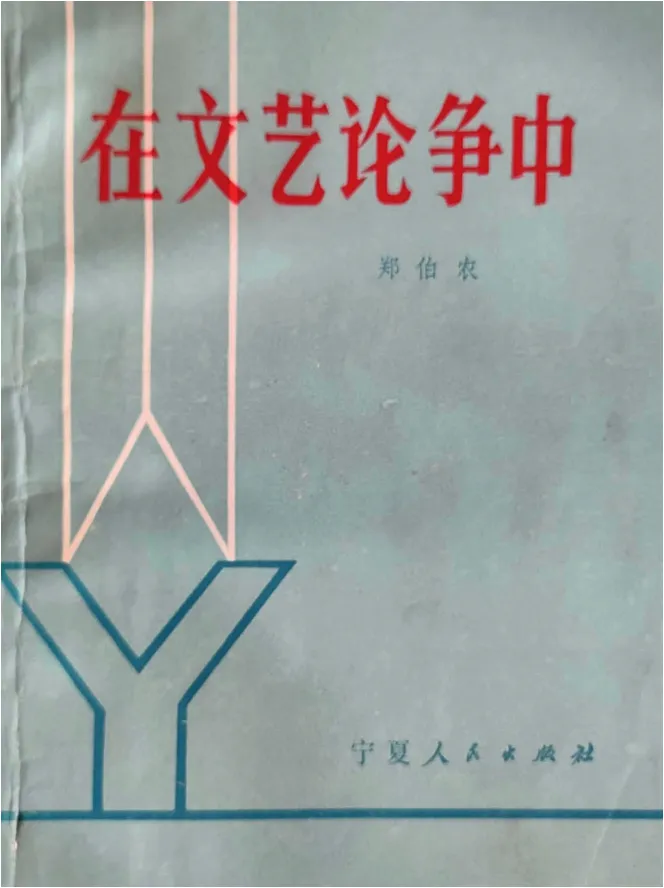
圖6 理論評(píng)論集《在文藝論爭(zhēng)中》 鄭伯農(nóng) 著
你問(wèn)到如何看待文藝思想領(lǐng)域出現(xiàn)的種種分歧,我以為有些是共同目標(biāo)下對(duì)具體問(wèn)題看法的分歧,也有原則性的分歧。粉碎“四人幫”之后,我們進(jìn)行了思想理論上的撥亂反正。在清理“四人幫”所制造的思想混亂以及總結(jié)歷史經(jīng)驗(yàn)的基礎(chǔ)上,黨中央作出了《關(guān)于建國(guó)以來(lái)黨的若干歷史問(wèn)題的決議》(以下簡(jiǎn)稱(chēng)《決議》),對(duì)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成立后的得失、對(duì)毛澤東同志和毛澤東思想,包括文藝思想,都作出了科學(xué)的評(píng)價(jià)。如何對(duì)待《決議》?這是分歧的始發(fā)點(diǎn)。許多同志擁護(hù)這個(gè)《決議》。有人對(duì)《決議》的精神不完全接受,但他們遵守紀(jì)律,有意見(jiàn)在內(nèi)部講,沒(méi)有公開(kāi)提出不同意見(jiàn)。也有人公開(kāi)叫板,把批判的矛頭指向毛澤東文藝思想和黨的文藝方針政策。譬如某公開(kāi)出版的著作居然說(shuō),“工具論、從屬論、服務(wù)論”,是“禁錮文藝生命的錯(cuò)誤文藝路線和極端化思想”。鄧小平同志《在中國(guó)文學(xué)藝術(shù)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huì)上的祝詞》中明確指出:“我們要繼續(xù)堅(jiān)持毛澤東同志提出的文藝為最廣大的人民群眾、首先為工農(nóng)兵服務(wù)的方向”[1]鄧小平:《在中國(guó)文學(xué)藝術(shù)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huì)上的祝詞》,《鄧小平文選》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10頁(yè)。。黨中央調(diào)整文藝政策,提出“文藝為人民服務(wù)、為社會(huì)主義服務(wù)”,以之作為新時(shí)期文藝工作的總口號(hào)。怎么能把“服務(wù)論”等打成“禁錮文藝”的“錯(cuò)誤文藝路線”?又譬如說(shuō),在評(píng)價(jià)新文學(xué)史的時(shí)候,有的著作貶低丁玲、柳青等革命作家,吹捧周作人等漢奸文人。在討論中學(xué)語(yǔ)文教材時(shí),有人認(rèn)為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成立以來(lái)的教材貫穿著“極左思潮”,應(yīng)當(dāng)“把從前所學(xué)的,全部扔掉”。還認(rèn)為魏巍的名作《誰(shuí)是最可愛(ài)的人》應(yīng)當(dāng)被剔出教材,因?yàn)槊绹?guó)發(fā)動(dòng)侵略戰(zhàn)爭(zhēng)是正義的,歌頌抗美援朝是“鼓吹民族間仇恨”“把歷史真相攪混”。習(xí)近平同志指出,要反對(duì)“歷史虛無(wú)主義”,這是很有針對(duì)性的。文藝領(lǐng)域確有大是大非之爭(zhēng),應(yīng)當(dāng)通過(guò)旗幟鮮明和鞭辟入里的講道理,繼續(xù)分清是非曲直。
許:您特別重視文藝創(chuàng)作、文藝批評(píng)與人民之間的關(guān)系。比如1988年您在《文學(xué):失去了什么》一文中就說(shuō)到了“不通電”現(xiàn)象,即群眾歡迎的作品很難得到評(píng)論界的熱情支持,群眾不感興趣的作品,往往成為評(píng)論界議論的熱門(mén)和重點(diǎn)扶持的對(duì)象……請(qǐng)您談?wù)勀鷮?duì)文藝工作的人民性導(dǎo)向的認(rèn)識(shí)。
鄭:過(guò)去孫犁說(shuō)過(guò)一句話,就是說(shuō)作家要少聚,要到老百姓里頭去。趙樹(shù)理就是走一條讓老百姓都接受他的道路,他曾告誡青年作者:“不是為了寫(xiě)作才去體驗(yàn)生活;惟其是自己的生活,所以他才有許多話要說(shuō),說(shuō)得那么好。認(rèn)真生活的人不會(huì)異想天開(kāi)地在筆下出現(xiàn)不真實(shí)的情況。”[2]轉(zhuǎn)引自趙勇:《趙樹(shù)理:與群眾“共事” 寫(xiě)作才能“得勁”》,《太原日?qǐng)?bào)》2021年9月27日,第7版。我們現(xiàn)在有些作品就是在知識(shí)界、文學(xué)界內(nèi)部看、內(nèi)部議,文藝家、評(píng)論家之間相互評(píng)一評(píng)。我以為文藝作品主要不是寫(xiě)給文藝家、專(zhuān)家看的。專(zhuān)家自然有他的長(zhǎng)處,但也有一些局限性,比如過(guò)于看重技巧,有時(shí)候還看重人緣。文藝作品有這樣一個(gè)特質(zhì),就是美的東西一下就能觸動(dòng)人,它是訴諸于人的感官的,比如音樂(lè)好聽(tīng)不好聽(tīng),第一耳朵就能感受到,喜歡的話聽(tīng)?zhēng)妆榫湍芨叱恕_^(guò)去孟子講,獨(dú)樂(lè)樂(lè)不如眾樂(lè)樂(lè)。我們?cè)趺茨苓B兩千多年前的孟老夫子都不如呢?我們是社會(huì)主義國(guó)家,文藝就是為最廣大的人民群眾服務(wù)的。過(guò)去周揚(yáng)寫(xiě)過(guò)一篇講“左聯(lián)”的文章,題目就叫《文藝也是一種服務(wù)型行業(yè)》。我以為服務(wù)型行業(yè)沒(méi)什么不好,我們就是干服務(wù)型行業(yè)的,這是我們的光榮使命與職責(zé)。文藝工作者總是在老朋友、小沙龍里打轉(zhuǎn)轉(zhuǎn),容易滋生互相吹捧、自我膨脹的壞毛病,我們要多聽(tīng)一聽(tīng)群眾的聲音。正如習(xí)近平總書(shū)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huì)上的講話中所談到的:“以人民為中心,就是要把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為文藝和文藝工作的出發(fā)點(diǎn)和落腳點(diǎn),把人民作為文藝表現(xiàn)的主體,把人民作為文藝審美的鑒賞家和評(píng)判者”[1]習(xí)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huì)上的講話》,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3-14頁(yè)。。
許:您認(rèn)為當(dāng)前文藝?yán)碚摗⑽乃囋u(píng)論存在哪些問(wèn)題?您對(duì)此有何建言與對(duì)策?

圖7 與老作家魏巍
鄭:搞文藝評(píng)論,要了解文藝界的行情。創(chuàng)作上有什么好的東西,有什么不好的東西,兩頭都要看,中間也要看。評(píng)論工作者要主動(dòng)把握當(dāng)前文藝思潮,弄明白群眾究竟在關(guān)心什么,文藝界在關(guān)注什么。有時(shí)候看似是一篇短文章,但你要了解很多情況才能完成好。文藝評(píng)論要研究實(shí)際問(wèn)題,要敢于發(fā)表自己的見(jiàn)解。講大話、套話、刮什么風(fēng)說(shuō)什么話,只栽花不栽刺、只討好不批評(píng)——這既不是共產(chǎn)黨人應(yīng)有的風(fēng)格,也不是文藝評(píng)論家應(yīng)有的品質(zhì)。一個(gè)搞評(píng)論的人要有自己獨(dú)立的思想,這并不是說(shuō)在馬克思主義之外、在黨之外另立門(mén)戶(hù),而是要針對(duì)某一具體問(wèn)題“深挖一口井”,從而產(chǎn)生獨(dú)特的見(jiàn)解與看法。我現(xiàn)在老了,看東西很慢,視力也大大減退,不可能大量閱讀、了解文藝界的全面情況。所以,進(jìn)入老年之后,我很少就目前的文藝?yán)碚撆u(píng)工作發(fā)表意見(jiàn)。沒(méi)有調(diào)查研究就沒(méi)有發(fā)言權(quán)。
三、詩(shī)詞錘字煉句的背后考驗(yàn)的是詩(shī)人情懷與氣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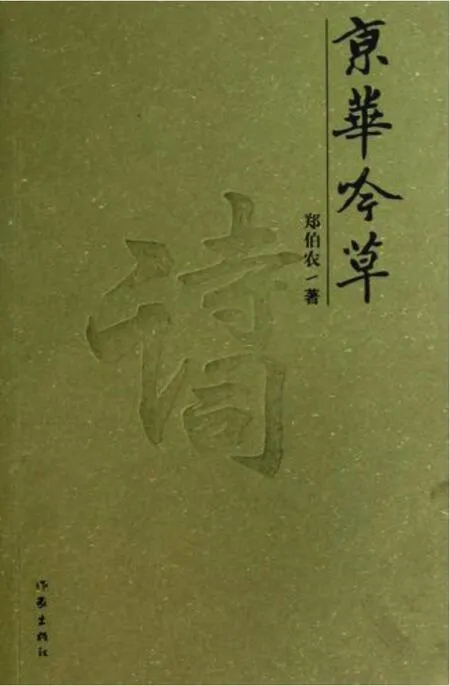
圖8 詩(shī)詞集《京華吟草》 鄭伯農(nóng) 著
許:雖然過(guò)去您也經(jīng)常利用業(yè)余時(shí)間寫(xiě)詩(shī),但要追溯起來(lái)真正從事詩(shī)詞創(chuàng)作、詩(shī)論詩(shī)評(píng)卻是臨近退休才開(kāi)始的。請(qǐng)您談一談您與詩(shī)詞結(jié)緣的過(guò)往,您如何看待新舊體詩(shī)的關(guān)系?
鄭:小時(shí)候我讀過(guò)《唐詩(shī)三百首》,背不全,《千家詩(shī)》也讀過(guò)一些,但是詩(shī)詞不是我的第一愛(ài)好。到了音樂(lè)學(xué)院以后,由于古代音樂(lè)大多沒(méi)有樂(lè)譜留下來(lái),要考證古代音樂(lè)需要閱讀大量文字資料,詩(shī)詞就是極為重要的憑證之一。專(zhuān)業(yè)迫使我與詩(shī)詞有了較多的接觸。“文革”時(shí)期我被批為“牛鬼蛇神”,逢年過(guò)節(jié)的時(shí)候,我還得在牛棚里反思自己的“罪行”。我有時(shí)一個(gè)人覺(jué)得委屈,也為國(guó)家的命運(yùn)而擔(dān)憂,就寫(xiě)了一些詩(shī)。那時(shí)候?qū)懺?shī)只能自己背下來(lái),不能寫(xiě)到紙上。
1993年,我曾帶領(lǐng)中國(guó)作家代表團(tuán)到越南訪問(wèn),當(dāng)時(shí)中越兩國(guó)剛恢復(fù)正常邦交,回來(lái)以后報(bào)紙要我寫(xiě)點(diǎn)訪越的文章,我覺(jué)得寫(xiě)詩(shī)比較簡(jiǎn)短,容易交差。發(fā)表后,未曾想臧克家老人寄了封信說(shuō):你這個(gè)材料還是可堪造就的,你將來(lái)要一邊寫(xiě)詩(shī)一邊寫(xiě)評(píng)論文章。而且他還要我寫(xiě)完了給他看,我備受鼓舞。1997年2月新春之際,我專(zhuān)門(mén)寫(xiě)了一首《丁丑春節(jié)呈臧老》,以表達(dá)知遇之恩:“又逢舉國(guó)慶新春,病榻何期久臥身。一代文章傳浩氣,百年風(fēng)雨鑄詩(shī)魂。藥當(dāng)茶水驅(qū)寒意,心騖云天懷故人。待到冰銷(xiāo)雪化日,再隨臧老覓花神。”
我退休以后,中華詩(shī)詞學(xué)會(huì)找我,要我參加一點(diǎn)學(xué)會(huì)的活動(dòng)。起先是偶爾參加,后來(lái)經(jīng)常參加,再后來(lái)就被“拉”進(jìn)學(xué)會(huì),在那里任職。我之所以下決心投入到詩(shī)詞事業(yè)中去,首先是從理性上覺(jué)得,中華詩(shī)詞長(zhǎng)期受壓制,應(yīng)當(dāng)為它出一把力。“五四”批判舊文學(xué),有擴(kuò)大打擊面的傾向,詩(shī)詞受害最烈。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成立后,音樂(lè)家協(xié)會(huì)是西洋音樂(lè)和民族音樂(lè)并重,美術(shù)家協(xié)會(huì)是油畫(huà)和國(guó)畫(huà)并重,戲劇家協(xié)會(huì)是話劇和戲曲并重,到了文學(xué)界,詩(shī)歌就是新詩(shī)一家獨(dú)大。我覺(jué)得應(yīng)該恢復(fù)中華詩(shī)詞的歷史地位。其次是出于個(gè)人感情,當(dāng)時(shí)的會(huì)長(zhǎng)孫軼青具有強(qiáng)大的人格魅力。孫老是抗日戰(zhàn)爭(zhēng)時(shí)入黨的老干部,曾任地下黨縣委書(shū)記。粉碎“四人幫”時(shí),中央派他和遲浩田同志一起接管《人民日?qǐng)?bào)》,離休后,他到中華詩(shī)詞學(xué)會(huì)任職。孫老年事已高,確實(shí)需要比他年輕一點(diǎn)的人當(dāng)助手,他親自到我家邀我到學(xué)會(huì)和他共事,我不能讓老人家失望,便欣然投入他的麾下。
當(dāng)前,詩(shī)詞處于復(fù)興階段。每年在公開(kāi)或內(nèi)部刊物上發(fā)表的詩(shī)詞作品有大幾十萬(wàn)首,有人說(shuō)是上百萬(wàn)首,大大超過(guò)全唐詩(shī)的數(shù)量。作者、作品的數(shù)量都是空前的,可以說(shuō)詩(shī)詞達(dá)到了空前的普及。目前,就詩(shī)詞界內(nèi)部來(lái)講,重要的問(wèn)題在于提高。就整個(gè)文學(xué)局面來(lái)講,還是要繼續(xù)恢復(fù)詩(shī)詞在文學(xué)事業(yè)中的重要地位。2002年6月,我在《人民日?qǐng)?bào)》發(fā)表《格律詩(shī)的現(xiàn)狀及發(fā)展》一文,提出詩(shī)詞要“三入”,即入史、入校、入獎(jiǎng):文學(xué)史不僅要講古代詩(shī)詞,現(xiàn)當(dāng)代詩(shī)詞也要進(jìn)入史書(shū);中學(xué)大學(xué)文科教育不但要講古典詩(shī)詞,也要開(kāi)設(shè)現(xiàn)當(dāng)代詩(shī)詞的課,還要講詩(shī)詞格律;全國(guó)性文藝評(píng)獎(jiǎng)不但要評(píng)新詩(shī),也要有反映新時(shí)代的詩(shī)詞新作。至于舊體詩(shī)和新詩(shī)的關(guān)系,我擁護(hù)孫軼青同志的意見(jiàn),二者并不對(duì)立,應(yīng)當(dāng)互相學(xué)習(xí),互相補(bǔ)充,攜手并進(jìn),同榮并茂。自由體、格律體都是人民所需要的。詩(shī)的品種,應(yīng)當(dāng)百花齊放。
許:當(dāng)下詩(shī)詞創(chuàng)作數(shù)量繁多,但有代表性的精品力作、被人們廣為吟誦的并不多。您認(rèn)為原因何在?此外,在您看來(lái),詩(shī)詞繁榮的標(biāo)志是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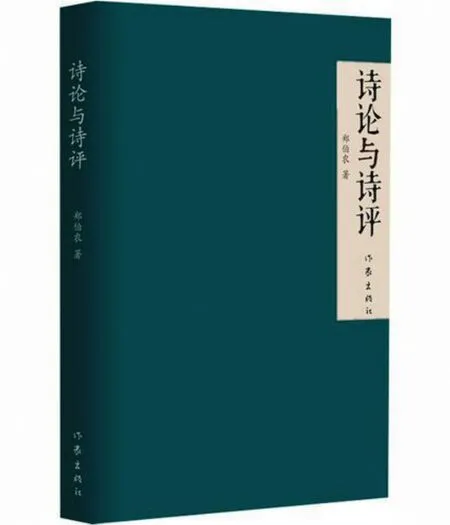
圖9 詩(shī)詞集《詩(shī)論與詩(shī)評(píng)》 鄭伯農(nóng) 著
鄭:當(dāng)下寫(xiě)詩(shī)詞的人很多,嫻熟掌握詩(shī)詞寫(xiě)作方法的人不在少數(shù),也出現(xiàn)了一些優(yōu)秀作品。但鮮有代表性的精品力作,原因在于:一是評(píng)選、評(píng)論工作跟不上,好作品未必引起社會(huì)的廣泛注意;二是優(yōu)秀作品數(shù)量有限,質(zhì)量也有待于進(jìn)一步提高。我們還沒(méi)有出現(xiàn)毛澤東詩(shī)詞、魯迅詩(shī)歌那樣的大作品。提高創(chuàng)作水平,需提高藝術(shù)素養(yǎng)、錘煉藝術(shù)技巧,但更根本的是詩(shī)人的胸襟和眼力。清人張際亮把詩(shī)分為三種:才人之詩(shī)、學(xué)人之詩(shī)、志士之詩(shī)。我們需要深入反映新時(shí)代的“志士之詩(shī)”,也需要各種風(fēng)格題材的好詩(shī)。有一個(gè)很有趣的現(xiàn)象:古代豪放派的代表人物,大多是貶官。屈原遭到流放,劉禹錫是“二十三年棄置身”,蘇東坡幾乎一生受貶。我不是說(shuō)人只有遭受大不幸,然后才能寫(xiě)詩(shī)。但人生太順了,沒(méi)有經(jīng)歷磨難,不了解老百姓的疾苦和訴求,是很難在文學(xué)上有大作為的。詩(shī)人要有豐富的人生閱歷、敏銳的歷史眼光和藝術(shù)眼光,有大胸襟、大視野。只盯住技巧、只會(huì)“雕蟲(chóng)小技”,不可能有大出息。
此外,我認(rèn)為做人要老實(shí),作詩(shī)不能太老實(shí),要講求馳騁心靈、放飛想象力。詩(shī)乃心聲。奇思異想也是詩(shī)人精神境界的體現(xiàn),詩(shī)只不過(guò)是一種折射。小說(shuō)講究細(xì)節(jié)逼真,但詩(shī)歌很難。杜甫在《登岳陽(yáng)樓》中寫(xiě)道,“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乾坤是天地,天地怎么能在湖中日夜浮動(dòng)呢?杜甫只有用大膽的想象方能寫(xiě)出這樣動(dòng)人的詩(shī)句。在我看來(lái),詩(shī)歌不好用現(xiàn)實(shí)主義全部囊括。恩格斯講,現(xiàn)實(shí)主義除了細(xì)節(jié)真實(shí)以外,還要塑造典型環(huán)境中的典型人物。這是針對(duì)小說(shuō)創(chuàng)作講的。我覺(jué)得蘇聯(lián)把社會(huì)主義現(xiàn)實(shí)主義當(dāng)成文藝的綱領(lǐng)是有積極意義的,但是毛澤東同志比斯大林高明,他沒(méi)有把創(chuàng)作方法當(dāng)作文藝綱領(lǐng),文藝綱領(lǐng)是為人民服務(wù)、為社會(huì)主義服務(wù),而方法可以是多樣的。現(xiàn)實(shí)主義是一種重要的敘事藝術(shù)手法,但不是一切藝術(shù)都要有細(xì)節(jié)真實(shí)。
臧克家和賀敬之常說(shuō):“與時(shí)代同步、與人民同心。”我認(rèn)為這兩句話不但適合于新詩(shī),也適合于舊體詩(shī)。詩(shī)人要有鮮明的個(gè)性,但個(gè)性要和人民性、民族風(fēng)格要和時(shí)代精神結(jié)合起來(lái)。有了正確的創(chuàng)作道路,有了嫻熟的創(chuàng)作技巧,有了嚴(yán)肅的創(chuàng)作態(tài)度,可以保證詩(shī)詞沿著正確方向發(fā)展,但不等于篤定能寫(xiě)出驚世之作。文藝創(chuàng)作有很大的偶然性,周恩來(lái)說(shuō),好作品往往是“長(zhǎng)期積累,偶然得之”[1]轉(zhuǎn)引自何春喜:《由周總理“一”字點(diǎn)評(píng)話文風(fēng)》,2020年3月16日,http://zhouenlai.people.cn/n1/2020/0316/c409117-31633980.html。。我在前面說(shuō)到,現(xiàn)在是詩(shī)詞的復(fù)興期,還不是高潮期。高潮的標(biāo)志是什么?作品的數(shù)量、參與者的數(shù)量都不是主要標(biāo)志。有了相當(dāng)數(shù)量的反映新時(shí)代的高精尖作品,涌現(xiàn)了大量尖端級(jí)人才,這才算達(dá)到高潮。我們要盡力推進(jìn)創(chuàng)作高潮的到來(lái)。至于什么時(shí)候到來(lái),我只能說(shuō)四個(gè)字:翹首以盼。
訪后跋語(yǔ):
6月的一個(gè)中午,受《中國(guó)文藝評(píng)論》所托,我如約來(lái)到北京潘家園附近的華威北里48號(hào)樓,對(duì)鄭伯農(nóng)老師進(jìn)行采訪。作為中國(guó)作協(xié)的老宿舍樓,這里匯聚著眾多當(dāng)代文壇響當(dāng)當(dāng)?shù)那拜叴蠹摇N胰グ菰L鄭老師那天,作協(xié)老宿舍樓外墻剛剛粉刷不久,橙黃相間、熱情似火,在一眾老舊小區(qū)的掩映中顯得格外不同。我想,革命人永遠(yuǎn)是年輕。
這種感受,自然也蘊(yùn)藏在此次與鄭伯農(nóng)老師近五個(gè)小時(shí)的采訪對(duì)話過(guò)程和逾四萬(wàn)字的整理素材中。年過(guò)八旬的鄭老經(jīng)歷了三次癌癥手術(shù),如今左眼視力只有0.5,右眼得了黃斑裂孔,視力僅0.02,但其記憶之精準(zhǔn)、邏輯之清晰、精神之矍鑠,實(shí)足讓人感佩。這么說(shuō)不是沒(méi)有依據(jù)的,鄭伯農(nóng)老師在對(duì)某一觀點(diǎn)、某一歷史進(jìn)行表述與回顧時(shí),會(huì)將各方主張以及自身態(tài)度悉數(shù)拋出,并通過(guò)有據(jù)可靠的文字記載輔以佐證。鄭老師對(duì)我說(shuō):“‘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春秋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韓非子以此公然與孔子和墨子持對(duì)立態(tài)度,盡管韓非子的觀點(diǎn)不全對(duì),但是當(dāng)年各種思想流派的碰撞交鋒卻促成了百家爭(zhēng)鳴的盛況,中國(guó)文化的深厚底蘊(yùn)也由此奠定。我不太喜歡含含糊糊的東西,講清楚有什么了不起的呢?”特別需要說(shuō)明的是,他不僅僅是用這把“刻度清晰的尺子”來(lái)量別人,同樣也用來(lái)量自己,對(duì)于過(guò)去自己在認(rèn)識(shí)上尚存局限的地方,他毫不避諱并坦陳不足。鄭伯農(nóng)老師所談及的所是所非,都指向觀點(diǎn),并不涉及任何個(gè)人關(guān)系,這一點(diǎn),是被明眼人看到心里的。在很多報(bào)社老人的眼里,他是放著公車(chē)不坐、邁著兩條腿上下班的老領(lǐng)導(dǎo),也是報(bào)社編前會(huì)常就文藝思潮問(wèn)題與編輯吵得“面紅耳赤”的較真人。憑著這份坦率、真誠(chéng)、正直,與對(duì)黨和國(guó)家的絕對(duì)忠誠(chéng),他收獲了一眾真心誠(chéng)意的同道摯友。
這里不得不單獨(dú)感謝一下李燕平老師。由于鄭老的身體原因,最后定稿確認(rèn)文字多有賴(lài)于燕平老師從中溝通協(xié)助,她作為鄭老的妻子、也是作協(xié)令人尊敬的前輩,曾幫報(bào)社追回一輛被盜公車(chē)白色桑塔納,協(xié)助公安機(jī)關(guān)抓住慣偷,還被評(píng)為“中央國(guó)家機(jī)關(guān)文化系統(tǒng)保衛(wèi)工作先進(jìn)個(gè)人”。去鄭老家拜訪,燕平老師親切地迎我入門(mén),不停往我手里遞剛洗好的小白杏,待我準(zhǔn)備就緒,她怕打擾便悄悄躲進(jìn)了臥室,“來(lái)來(lái),你和伯農(nóng)說(shuō)!”采訪結(jié)束后,她又問(wèn)了問(wèn)我報(bào)社曾經(jīng)共事同事的近況,只是在她眼里曾幾何時(shí)的小姑娘現(xiàn)在也到了退休的年紀(jì)。時(shí)間恍如隔世,如今因著這次訪談,我們又續(xù)上了一份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