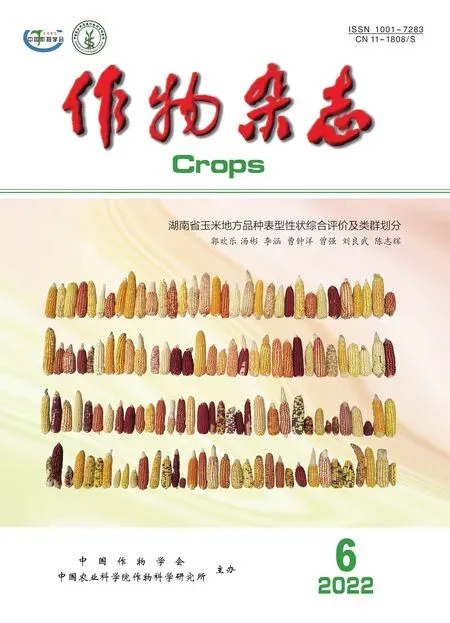根際溫度脅迫對小麥根系形態及生理影響的研究進展
沈文遠 陳昕鈺 余徐潤 吳云飛 陳 剛 熊 飛
(揚州大學生物科學與技術學院,225009,江蘇揚州)
根系是小麥(Triticum aestivum)重要的營養器官之一,其主要作用是吸收水分和營養,根系的生長發育狀況直接影響地上部的生長發育,進而影響小麥的產量和品質。根系的生長發育對環境因子變化較為敏感,小麥在生長期間常會經歷各種惡劣的環境條件(低溫、高溫、干旱、洪澇和鹽漬等)。近年來,溫度脅迫已成為制約小麥生產的主要限制性因素[1-2]。根際環境是指與植物根系發生緊密相互作用的土壤微域環境[3],而根際溫度指與植物根系發生緊密相互作用的土壤溫度[4],本文中根際溫度脅迫均指植株地上適溫情況下僅根系部分的極端根際溫度,環境溫度脅迫指小麥完整植株處于溫度脅迫。陳繼康等[5]研究發現,大氣溫度會對土壤溫度產生影響,淺層土溫會因氣溫的變化而變化,呈正相關性。目前,由于全球氣候變暖等因素影響,我國各地太陽輻射不斷增強,最終導致小麥產區大氣溫度與根際溫度升高,對作物產量造成影響[6]。可見,了解根際溫度脅迫對小麥根系生長的影響具有重要意義。但已有的研究更強調氣溫對小麥生產的影響,極少有人重視小麥地下部分所受脅迫的影響,因此針對根際溫度的理論研究還相當有限。
小麥根系形態及生理對根際溫度脅迫的響應復雜,根系的表觀形態及生理生化特性均會產生抗逆性變化[7]。深入了解小麥根系形態及生理對根際溫度脅迫的響應,有助于揭示小麥對根際溫度脅迫的適應性,為根系育種研究工作的開展提供理論基礎[8]。小麥根系的理論研究相對滯后,但近年來有越來越多的國內外學者開始對植物地下部分進行研究,關注小麥根系定量性狀的準確表型數據和生理生化指標,為更精確的QTL定位和小麥根系育種提供了可能[9-10]。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本文梳理和總結了小麥根系生長對根際溫度脅迫的響應,并對未來小麥根系抗逆研究方向進行總結與展望,以期為小麥根系育種和理想株型的培育提供參考。
1 小麥根系形態及生理對根際高溫脅迫的響應
1.1 根際高溫脅迫對小麥根系生長及根細胞形態的影響
研究[11-13]表明,如“干熱風”等極端高溫天氣頻發,植物根際溫度會顯著升高,并直接影響小麥根系的生長發育、功能和活力水平。根際高溫脅迫下,根系在植株的抗逆過程中起著關鍵作用,這與根系對溫度的高敏感和其基本功能有關[4]。根際高溫處理后,春、冬小麥幼苗的根重、最大根長、總根長及根冠比均顯著降低,小麥幼苗整體表現出細弱的特點[12,14]。春、冬小麥的初生根和總側根的延生生長在高溫時遠低于中溫的情況,但春、冬小麥的分生組織體積變化卻沒有明顯差異[15]。除了影響根系表觀形態外,根際高溫會造成根系總吸收面積和活性吸收面積的降低,導致根系活力顯著降低,當根際高溫脅迫發生時小麥根系吸收作用受阻[14]。
有研究[16]認為,根系活力的變化與根際高溫下根系的木質化和木栓化衰老程度加快有關。還有研究[17]認為,根際高溫會通過影響小麥根系對養分及生長調節劑的運輸,最終達到根系衰老的結果。正常小麥的根在開花后與地上部分器官一樣逐漸衰老,老化根的橫切結構特點主要表現為皮層細胞萎縮脫落,中柱鞘細胞壁及中柱原屬薄壁組織細胞壁出現明顯的增厚栓化現象[18]。根際高溫脅迫發生時小麥根系細胞衰老進程會產生相應變化,根際高溫對小麥多級初生根系和次生根系衰老進程的影響是否相同等問題仍然具有研究潛力,且檢測初生根系與次生根系的生理性狀及其對根際高溫脅迫響應有關的QTL位點有助于選育耐熱小麥品種。
當前,關于根際高溫脅迫對小麥幼苗根系生長及根細胞形態影響方面已有部分研究,但對于小麥成株根系的研究還嚴重缺乏,大田生產情況下小麥常在灌漿期經受根際高溫脅迫,而目前關于成株小麥根系生長及根細胞形態對根際高溫脅迫響應的認知還相當匱乏,加強這方面的理論研究有助于小麥根系育種和理想株型的培育。
1.2 根際高溫脅迫對小麥根系活性氧平衡及質膜的影響
研究[14,19]發現,根際高溫處理時小麥幼苗根系中丙二醛(malondialdehyde,MDA)含量大幅增加,根系質膜受害程度較大;小麥根系超氧化物歧化酶(superoxide dismutase,SOD)和過氧化氫酶(catalase,CAT)活性隨著脅迫時間的延長均呈先升后降的規律;SOD活性顯著下降時過氧化物酶(peroxidase,POD)仍保持較高活性。POD被認為是木質素和木栓素生物合成中催化最后一步反應的酶[20],其活性高低會影響根系木質化與木栓化的進程,這也說明,根際高溫脅迫下根系中POD活性長期處于較高水平,與根系衰老進程加快相關。SOD、POD和CAT作為細胞膜保護酶發揮作用,小麥通過提前調控相關基因的表達以有效消除活性氧(reactive oxygen species,ROS),Cu/Zn-SOD、Mn-SOD、POD和CAT基因均參與小麥幼苗高溫脅迫應答反應[21]。進一步研究小麥根系抗氧化酶調控相關基因的表達調控,包括小麥相關基因啟動子結構上與脅迫響應相關的轉錄因子結合位點等,對小麥抗逆性作用機制研究有重要意義,有助于了解信號傳遞途徑和相關基因表達調控模式。
郭天財等[22]研究了根際高溫脅迫對小麥根系質膜相對透性的影響,發現根系在長時間脅迫下透性顯著升高。高溫時,生物膜功能鍵斷裂,導致膜蛋白變性,膜脂分子液化,膜結構破壞,生理功能異常,最終導致細胞死亡[23]。維持植物細胞完整性與植物對高溫抗性有關,耐熱型小麥生物膜中飽和脂肪酸相對含量升高,不飽和脂肪酸相對含量降低,結合基因表達情況發現,其是通過改變不飽和脂肪酸相對含量來實現質膜對高溫的適應性[24]。不同植物或同一植物的不同組織部位在合成不飽和脂肪酸及其衍生物的種類與數量上存在差異,不同外來脅迫下植物不飽和脂肪酸及其衍生物的合成調控也存在差異,近年來學者關注去飽和酶基因的表達,驗證了玉米中FAD7和FAD8去飽和酶基因的表達受溫度脅迫的調節[25]。因此,進一步研究小麥根系中去飽和酶基因的表達,通過轉基因或基因編輯技術進行定向分子育種,可改變小麥相關基因的表達特性,從而實現小麥抗性的改良。
1.3 根際高溫脅迫對小麥根系滲透調節的影響
逆境下細胞積累無機離子以調節滲透勢,無機離子吸收和積累與三磷酸腺苷(ATP)酶的活性有關,H+-ATP酶是一種重要的跨膜蛋白,目前發現僅存在于植物與真菌的質膜和內膜系統中[26]。質膜H+-ATP酶長期以來一直被認為是植物生長的動力來源,為物質跨膜轉運提供能量[27]。郭啟芳等[28]發現,溫度敏感型小麥在環境高溫處理下細胞膜H+-ATP酶與Ca2+-ATP酶活性顯著下降,耐熱品種小麥細胞膜H+-ATP酶與Ca2+-ATP酶活性維持較高水平。小麥根系質膜Ca2+-ATP酶最適活性溫度低于葉質膜Ca2+-ATP酶,且根系質膜Ca2+-ATP酶活性遠比葉質膜Ca2+-ATP酶高[29]。脫落酸(abscisic acid,ABA)誘導小麥根系質膜H+-ATP酶基因表達增強,使小麥抗逆性增強[30]。植物在遭受環境高溫脅迫時,質膜H+-ATP酶活性在轉錄和翻譯水平的調控過程中還需要植物激素、氧化酶、磷酸酶和蛋白激酶等胞內信號分子的介導。未來關于小麥的研究可重點分析根系質膜H+-ATP酶在響應環境脅迫因子時,植物細胞內的信號分子在質膜H+-ATP酶活性的轉錄及翻譯后修飾調控過程中的作用及其介導途徑,這既可豐富逆境植物的致傷機理,又可為小麥逆境耐受能力的提高提供新的視角和新的方法。
前人總結發現,脯氨酸(proline,Pro)是重要的有機滲透調節物質,幾乎所有逆境,包括高溫脅迫都會造成植物體內Pro的積累[31],高溫條件下植物體內的Pro含量明顯提升,并且發現抗熱品種比不抗熱品種可積累更多的Pro[32]。耐熱抗旱品種小麥葉片與根系內Pro含量能夠保持一定水平[33]。小麥幼苗整體在環境高溫脅迫下Pro含量升高[34],但關于根系與葉片之間Pro含量調節的認知還相對匱乏,且確切的作用機制尚不清楚。對Pro轉運相關基因的研究中,ProT基因家族和AAP基因家族中部分成員與Pro轉運與吸收有關,其中AtProT1被認為在Pro長距離轉運中起作用[35],ProTs被證實對脅迫條件下維持Pro的內穩態具有重要意義[36],AtAAP1在根際吸收Pro方面起作用[37],PtAAP11對Pro的高親和力表明,其可能在木質部細胞分化時運輸Pro[38]。對Pro運輸和代謝的研究可了解逆境條件下植物積累Pro的規律及其作用機制,Pro代謝與轉運相關基因的發掘與其在植物中的抗逆機制還需要深入探求。
可溶性糖是另一類滲透調節物質,包括蔗糖、葡萄糖、果糖和半乳糖等。在高溫條件下,小麥幼苗根系可溶性糖含量隨脅迫時間延長而下降[39],幼苗整體總糖減少[40]。可能是由于高溫脅迫下隨著細胞膜透性變化,小麥根系細胞代謝紊亂、呼吸加強的結果[17,41]。郭洪雪等[42]發現,高溫脅迫下小麥幼苗整體可溶性糖含量升高,這可能是由于根際高溫脅迫下小麥會調節根系與地上部中可溶性糖含量。可溶性糖除具有滲透調節作用外,還對植物不定根的發生起誘導作用[43]。目前,對可溶性糖的代謝及調控已有一定認識,而根際高溫脅迫下小麥組織器官中可溶性糖分配的詳細機制尚未見報道。
1.4 根際高溫脅迫對小麥根系植物激素的影響
植物根系能感應根區環境變化,合成并輸出信號物質并作用于地上部[44]。環境高溫處理下,小麥幼苗根部ABA和吲哚乙酸(3-indoleacetic acid,IAA)的積累及其在葉與根中游離和結合形式的動態變化均表明植物激素在小麥發育與抗逆中的作用[45]。ABA是一種脅迫激素,根尖是合成ABA的主要場所,它沿著木質部運輸到小麥地上器官,能作為傳遞根源逆境信號的物質,在調節植物對逆境的適應中極為重要[46]。ABA信號轉導負向調控生長素的合成以調節植物根部分生組織活性,影響細胞周期進程;ABA與乙烯是協同與拮抗并存的相互作用,ABA通過介導乙烯途徑作用于乙烯上游,從而調控根系生長;生長素在乙烯響應途徑的下游起作用,介導根細胞的擴增[47]。此外,ABA對植物耐熱性的影響還與其調節熱激轉錄因子(heat shock transcription factor,HSF)和熱激蛋白(heat shock protein,HSP)有關[48]。
小麥根系中植物激素ABA、乙烯和IAA含量及其在植物體內的動態變化極具研究潛力。ABA調控細胞周期進程的研究已取得一定進展,但與根系生長直接相關的研究還十分有限,且ABA是否與其他植物激素互作進而精細調控小麥根系發育等問題也尚待探索,對其詳細生理機制的研究有助于小麥根系相關育種。
1.5 根際高溫脅迫下小麥熱激蛋白的研究
植物體內的熱激蛋白在非生物脅迫中可以延緩植物衰老,并增強抗逆性[49]。高溫環境脅迫下不同野生型小麥根系合成的HSP種類與總數存在顯著差異,并且其根系獲得的耐熱性也存在差異[50]。小麥Hsf家族基因之間特性和功能差異明顯,響應表達模式也不同[51]。熱沖擊下,HSF會促進HSP基因轉錄的起始,而在小麥根中HSF表達處于更高水平,其中TaHsfA2-10通過促進調節HSP基因的表達來對植物進行熱耐受性調節[52]。TaHsfC2a在小麥灌漿期表達較高,基因過表達可上調大量旱、熱和ABA相關基因的表達[53]。在環境高溫脅迫下,小麥TaHsfA2f在不同組織器官中均有表達,但在成熟根中高表達,其表達能上調一系列熱相關蛋白基因的表達,從而提高植株耐熱性[54]。小麥中包含多個A2亞族基因且功能復雜多樣,多個亞族基因如何相互協同調控下游不同響應基因的表達,如何賦予植株不同的耐熱性,還需要對小麥Hsf家族基因進行深入研究和探討。
以上文獻顯示,小麥根系對根際高溫脅迫響應的研究已取得一定進展,但也存在許多空白有待進一步研究,如圖1所示。

圖1 根際高溫影響小麥根系發育的生理機制模式Fig.1 The physiological mechanism of rhizosphere high temperature affecting wheat root development
2 小麥根系生長對根際低溫脅迫的響應
2.1 根際低溫脅迫對小麥根系生長及根細胞形態的影響
氣候變化帶來了極端低溫天氣的頻發,我國“倒春寒”尤為嚴重[55]。極端氣溫伴隨極端根際溫度,嚴重影響了小麥的品質和產量[56]。根際低溫處理下小麥根系生長緩慢,總根長、根系干重、最大根長及根系體積都顯著降低,根冠比顯著提高[14,57]。根際低溫脅迫時,小麥根系活力與活躍吸收面積提高,但由于根系生長受阻,總吸收面積和總根系活力降低[14]。
為適應根際低溫,小麥根系細胞壁會發生結構和物理特征的變化,包括特定多糖的合成與代謝[58]。環境低溫脅迫下小麥根尖細胞結構發生明顯變化,薄壁細胞形狀不規則,表皮細胞較小,皮層細胞較大,維管束結構不明顯,木質部排列無序[59]。目前主要從根系細胞顯微結構角度研究根際低溫根部輸導功能的變化與其對地上部分的影響,若能進一步從超微結構角度研究根際低溫脅迫對小麥根系的影響,包括根尖細胞的內質網、微體和高爾基體等在根際低溫脅迫下的結構及功能的變化,將有助于從細胞學角度理解小麥抗逆性變化。此外,小麥不定根系中多級初生根與次生根在形態及生理性狀方面存在差異,而二者在逆境下不同生育階段的發育和功能均會受到調控[60],對其進一步細化研究,檢測多級根性狀及其根際低溫脅迫響應有關的QTL位點,將有助于研究初生根與次生根的協調發展和小麥抗寒品種的選育。
當前關于根際低溫脅迫對小麥幼苗根系生長及根細胞形態的影響方面有了部分研究,但對小麥成株根系的研究還嚴重缺乏,大田生產中小麥常在返青拔節期經受根際低溫脅迫,而目前關于成株小麥根系生長及根細胞形態對根際低溫脅迫響應的認知還相當匱乏,其理論研究有助于小麥根系育種和理想株型的培育。
2.2 根際低溫脅迫對小麥根系活性氧平衡及質膜的影響
逆境脅迫下,ROS在植物體內大量積累,細胞穩態遭到破壞使細胞質膜受到過氧化傷害,且隨著脅迫時間的延長,MDA在植物體內不斷積累[61-63]。研究[14,64]發現,低溫環境脅迫對小麥根系SOD活性影響顯著,短期脅迫酶活性顯著增加,長期脅迫酶活性顯著降低;低溫環境脅迫下小麥根系POD活性提高并保持較高水平;低溫環境脅迫使越冬期小麥根系CAT活性顯著增加。小麥幼苗在低溫脅迫下,葉綠體Cu/Zn-SOD和線粒體Mn-SOD基因的轉錄受到誘導,在轉錄水平上引發編碼Cu/Zn-SOD和Mn-SOD基因過量表達,從而有效消除ROS,以應對低溫脅迫[65]。已知POD參與IAA的氧化分解[66],而IAA在調節植物細胞伸長、細胞分化、生根和休眠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因此POD與調控小麥越冬休眠有關,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根際低溫下小麥根系細胞壁結構的變化。編碼CAT的基因表達表現出器官特異性[67],CAT1主要在葉片表達,CAT3主要在上胚軸表達,目前鮮有關于根系中CAT相關基因表達調控的研究,找到其在越冬期小麥根系中的顯著變化與相關根系性狀的聯系是必要的。
小麥根系隨著低溫脅迫時間的延長其外滲液電導率明顯增大,細胞透性逐漸增大,這是由于膜體緊縮不均而出現斷裂,因而會造成膜的破損滲漏[39]。膜脂肪酸不飽和指數(index of unsatu-rated fatty acid,IUFA),即不飽和脂肪酸在總脂肪酸中的相對比值可作為衡量植物抗冷性的重要生理指標,低溫處理后小麥中不飽和脂肪酸含量上升,IUFA也上升,膜相變溫度降低,小麥抗冷性提高[68]。已知脂肪酸代謝在植物的耐寒機制中起重要作用[69],下一步工作就是發掘調控脂肪酸代謝的相關基因。植物中FAD2基因參與去飽和反應,其表達強弱對植物抗寒能力的影響非常顯著,并且該基因在不同組織器官中的表達量存在顯著差異[25]。目前,小麥根系組織中脂質代謝以及相關基因表達調控的研究十分有限,未來應將根系中不飽和脂肪酸代謝途徑分解,深入研究其中的特定路徑產物的定位、調控和功能,以及它們與其他信號通路間的關系。
2.3 根際低溫脅迫對小麥根系滲透調節的影響
植物根系無機離子的吸收和積累與ATP酶活性有關,H+-ATP酶、Ca2+-ATP酶和Mg2+-ATP酶的活性均決定了品種的抗逆能力[70]。劉煒等[71]研究發現,低溫環境脅迫下耐冷小麥品種質膜Ca2+-ATP酶活性呈先增后減的規律,且始終維持在較高水平。低溫脅迫下小麥幼苗根系質膜中H+-ATP酶活性下降,根液泡膜中H+-ATP酶活性增加[68]。王榮富等[72]研究認為,小麥質膜ATP酶活性的改變與膜脂相變無關,其原因可能是ATP酶本身結構的改變引起活化能的變化。目前,植物質膜ATP酶活性的調控機理是植物生理生態學領域的研究熱點,但植物響應根際低溫逆境因子的抗性機制中根系細胞內信號分子的作用及其傳導途徑在質膜ATP酶活性調控方面的研究還處于起步階段,進一步完善相關研究可為小麥逆境耐受能力的提高提供新的視角。
Pro作為重要的滲透調節物質,在植物抗逆中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于晶[59]對小麥各器官不同時期低溫脅迫下Pro含量進行了研究,發現脅迫初期葉與根中Pro含量大幅提高,但隨著脅迫時間的延長,Pro含量逐漸降低。游離Pro含量的增加與小麥抗寒能力有關[73]。吡咯啉-5-羧酸合成酶(P5CS)與脯氨酸脫氫酶(ProDH)是植物中Pro合成與降解的關鍵酶,P5CS和ProDH基因的調節作用是控制Pro水平的關鍵機制[74]。目前國內外學者主要聚焦于鹽堿與干旱脅迫下Pro積累機制的研究,已證明Ca2+、H2O2和ABA等信號分子參與了相關基因的調控[74-75],但關于根際低溫脅迫的研究還相對薄弱,具體哪些信號分子參與了轉導過程的研究尚不清楚,信號分子間的相互作用方式尚不明確,因此根際低溫脅迫下植物Pro代謝具體過程有待研究。
低溫逆境下植物體內常常積累大量的可溶性糖[76]。于晶[59]發現,在低溫脅迫下越冬前小麥中可溶性糖含量不斷增加,且根中的可溶性糖含量較高,而葉片中含量較少,這可能由于低溫信號刺激,葉片中可溶性糖轉移到地下器官中,為植物越冬積累必要物質。根系中可溶性糖含量差異決定了不同品種對根際低溫的耐受性[77]。因此,低溫脅迫下植物根系可溶性糖的積累與抗寒能力有關,進一步研究可溶性糖在小麥根系中的代謝與積累以及其在葉與根中的運輸調控機制,對理解小麥根系低溫耐受能力是很重要的。
2.4 根際低溫脅迫對小麥根系植物激素的影響
ABA和赤霉素(gibberellins,GA)是植物體內重要的生長類激素,這2類激素被認為與植物抗寒性相關[78],其中ABA對于植物抗寒能力的提升最為顯著[79]。低溫環境脅迫下,小麥根系中ABA含量相對較高且呈現先升高后降低的趨勢;GA在小麥根系中含量相對較低,隨著脅迫時間的延長,GA含量變動幅度不大[59]。
已在許多模式植物及小麥中證明了ABA處理能通過上調小麥中TaSPS和TaSS等基因的表達提高可溶性糖在組織器官中的積累,以助于增強小麥的低溫抗性[80-81]。當小麥經受環境低溫脅迫時,ABA提高了根系維管組織的分化[82],同時影響分生組織微管蛋白和肌動蛋白的含量[83]。目前關于ABA及其類似物AMF在小麥根系低溫響應調控中的表現仍未知,依賴ABA的信號調控通路在誘導產生低溫抗性過程中,ABA與其他信號物質之間的交互方式也尚不清楚,特別是對小麥低溫抗性及生長發育緊密相關的碳代謝系統的影響機制缺乏研究。
GA是植物根系伸長生長所必需的,其對根伸長生長的促進作用體現在促進細胞的伸長和增殖,其對根伸長生長的調控需要DELLA蛋白的參與。GA在根系生長發育過程中可能通過影響IAA的合成與運輸來調控根系的伸長與生長[84]。GA相關基因參與了植物耐低溫的調控過程,GA合成代謝和信號傳導過程緊密參與其中。目前關于GA在小麥根系低溫響應調控中的表現仍未知,逆境脅迫下GA與ABA等其他信號物質之間存在互作,但具體方式尚不能精確詮釋[85]。
研究小麥根系內源激素在根際低溫脅迫下的變化為研究小麥根系抗冷基因提供了生理生化基礎,進一步研究調控內源激素相關基因、揭示不同激素在調整根際低溫脅迫下根系生長的交互機制是未來重點研究方向。
2.5 根際低溫脅迫對小麥根系低溫誘導蛋白的影響
研究[86]表明,可將低溫誘導蛋白分為8種類型,當前研究抗凍能力集中于抗凍蛋白(antifreeze protein,AFP)和脫水蛋白(dehydrin,DHN)。
在很多植物中均有對AFP的研究,AFP多定位于細胞的質外體中,多數發現于植物的葉片、根和芽中[87]。目前認為,AFP在植物根系等組織器官抗寒中的作用主要包括降低原生質溶液的冰點、抑制重結晶、降低冰晶的生長速度、保護細胞膜系統和組織細胞內冰晶的形成等[88]。AFP的表達包含鈣信號的調控,鈣與激素可通過調節相關基因表達使AFP積累[86]。目前關于AFP基因的應用是一大熱點,如何提取出相關基因并在小麥等糧食作物中異源表達進而獲得抗寒性強的轉基因植株將是今后糧食作物基因工程研究的主要內容之一。
DHN家族成員通過多種轉運方式定位于植物細胞,主要在植物營養器官中受誘導表達[89],在冬小麥中2種脫水蛋白相似蛋白在線粒體中積累以響應環境低溫脅迫,其積累與植物耐寒能力呈正相關[90]。DHN在低溫刺激后有使蛋白維持正確折疊或防止聚集的作用,其高親水性可幫助植物維持細胞形態避免過度失水[91]。小麥的脫水蛋白WCS120、WCS200、Wcor410和COR39在低溫下可被誘導積累,細胞抗凍脫水能力提高,植物耐寒性增強[92-93]。從“鄭引1號”小麥中克隆得到脫水蛋白DHN14基因,其可響應低溫脅迫并對乳酸脫氫酶具有一定的保護作用[94]。DHN的表達有依賴ABA和轉錄激活因子(C-repeat binding factor,CBF)2種途徑[95]。隨著對DHN在逆境條件下對植物保護功能的廣泛研究,越來越多的DHN被發現。目前,小麥中關于DHN在干旱脅迫應答過程的作用機制研究較多,期待能進一步加深DHN抗低溫作用機制、表達調控以及相關信號轉導過程的研究,進而為利用DHN進行小麥抗低溫分子育種研究奠定基礎。
以上文獻顯示,小麥根系對根際低溫脅迫響應的研究已取得一定進展,但仍存在許多空白需要進一步研究,現總結如圖2所示。

圖2 根際低溫影響小麥根系生長的生理機制模式Fig.2 The physiological mechanism of rhizosphere low temperature affecting wheat root development
3 展望
近年來,國內外科研工作者已將目光從研究植物地上器官轉移至研究地下根系,針對小麥根際溫度脅迫響應生理機制及相關逆境蛋白和激素的調控效應等方面已取得一定進展,但關于小麥不同時期多級根如何響應根際溫度脅迫、相關信號分子間如何互作等問題尚缺深入研究,阻礙了小麥根系遺傳育種的發展。綜合已有研究成果,認為以下5個方面仍具有極大的研究潛力。
(1)根際溫度脅迫阻礙小麥根系生長,猜測根際高溫加快器官木質化和木栓化進程,進而導致根系衰老加速,根際低溫引起根系細胞結構無序,進而阻礙正常生理功能。當前小麥逆境抗性的理論研究多選擇幼苗作為試驗材料,但對于小麥成株的研究相對匱乏,其理論研究有助于小麥根系育種和理想株型的培育。此外,小麥初生根與次生根的生長進程存在差異,其在小麥不同時期的生理功能也存在差異,將根系結構細化并深入研究抗逆生理極有可能成為新的研究方向。
(2)植物地上部分與根系之間信號網絡錯綜復雜,并且會發生不同激素信號途徑的交互作用。目前已有大量研究者投入到植物激素信號通路重要元件的研究中。揭示不同激素在根系抗逆生長過程中的交互機制是未來小麥抗逆研究領域的重要課題,對小麥根系植物激素作用在合適發育階段的控制也將是抗性改良工程極具潛力的研究方向。
(3)目前,植物質膜ATP酶活性的調控機理是植物生理生態學領域的研究熱點,但植物響應根際溫度逆境因子的抗性機制中根系細胞內信號分子的作用及其傳導途徑在質膜ATP酶活性調控方面的研究還處于起步階段,進一步完善相關研究可為小麥逆境耐受能力的提高提供新的視角。Ca2+和ABA等信號分子參與調控Pro與可溶性糖代謝和轉運的相關基因,但關于根際溫度脅迫的研究還相對較弱,進一步完善響應機制有助于闡明植物的抗逆性機理,如何應用Pro和可溶性糖代謝與轉運相關基因改善植物的抗逆能力還需要深入探求。
(4)關于植物衰老響應及調控熱激蛋白信號通路的研究對了解植物適應性機制、提高抗逆性、培育抗逆作物及降低環境因素對植物的傷害等方面意義重大。小麥中Hsf家族基因是當前研究熱點,其功能復雜多樣性賦予其極大的研究潛力,研究結果將為今后小麥根系響應溫度脅迫的分子機制研究和抗逆品種的培育提供理論基礎。
(5)AFP和DHN可防止低溫脅迫對生物體細胞造成損傷和致死,從而提高生物體對低溫的適應能力,具備廣闊的應用前景。如何從植物中分離出活性更高的AFP和DHN,并通過遺傳轉化獲得抗凍性強的轉基因植株將是今后植物抗凍基因工程研究的主要內容之一。此外,在一些植物中還存在著一些具有調控AFP和DHN積累的物質,如ABA和乙烯等,進一步研究小麥根際溫度脅迫下根系調控低溫誘導蛋白積累的分子機制有助于理解小麥抗逆性的獲取并為抗逆品種的培育提供理論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