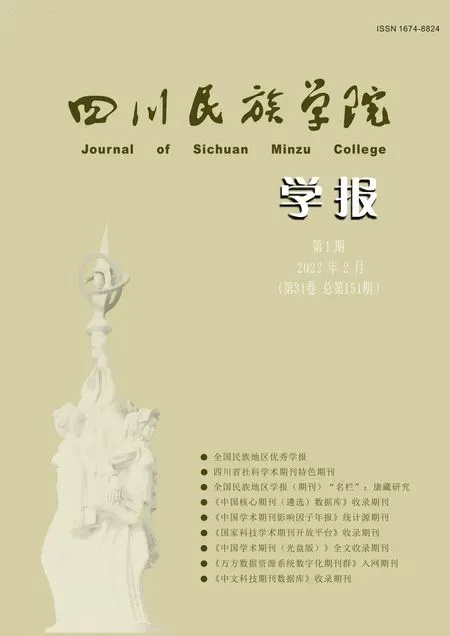二十世紀上半葉康藏研究譯著述評
袁 利
(四川民族學院,四川 康定 626001)
中國現代藏學萌芽晚于西方,康藏研究是中國現代藏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學者姚樂野,石碩曾指出“康區研究很大程度上成為我國現代藏學興起的一個重要發端”[1]。特殊的地理位置、文化要塞與歷史背景決定了康藏研究發展的必然性和重要性。1911以前有關西藏方面的外國著作已達百余部、論文100余篇,而同期國內有關涉藏地區研究的文章和著述寥寥無幾。康藏由于地勢孤懸,交通阻隔,民族文化多元,國內研究者甚少,而抗日戰爭使大批高校和科研機構西遷或南遷,為康藏研究興起與發展開辟了道路。近代,隨著英、日、德、法、俄等國家的科學家、傳教士、領事官員等主要從境外的印度和境內的青海、四川、云南等地進入西藏,國外對該地區的研究大量涌現,其窺探、覬覦西藏地區,在我國邊疆妄圖進行軍事擴張與干預的目的昭然若揭。國內相關研究論文和著述隨著藏事緊急的政治環境而迅速增加,其研究不得不借鑒和學習西方藏學研究成果以形成追趕之勢。二十世紀上半葉有關藏事研究的代表刊物《康藏前鋒》《康藏研究月刊》《康導月刊》系列,《蒙藏旬刊》《蒙藏月刊》等蒙藏系列《邊政》《邊政公論》系列和《禹貢》的《康藏專號》(1)二十世紀上半葉康藏或邊疆問題研究學術刊物眾多,康藏系列被整理為《〈康藏前鋒〉〈康藏研究月刊〉〈康導月刊〉》校勘影印全本》(下文簡稱《全本》), 主要研究康藏問題;蒙藏系列包括《蒙藏旬刊》《蒙藏月刊》等11種刊物, 主要研究蒙藏問題;邊政系列包括《邊政》《邊政公論》等7種刊物, 主要研究邊疆問題,其中《邊政》主要研究康藏問題;《禹貢》主要研究古地理和邊疆問題,曾在1937年第6卷第12期出了《康藏專號》。等刊物大量刊載了有關康藏或邊疆時政、人文地理、經濟教育等近萬篇論述和近百篇譯述。根據《康藏書錄題解》(2)參見《康藏月刊》1942年第3卷第12期第23-31頁,第4卷第1期第12-28頁,第2/3期第1-20頁;1943年第5卷第2/3期第62-70頁,第4期第46-55頁,第7/8期第47-57頁。所述,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康藏研究開始獨樹一幟并延續至今,這一時期催生了大量的專門論著和譯述,康藏系列期刊作為特色內容刊載了大量知名學者的譯述,“中國發表的關于藏區人文地理的文章中有相當一部分是翻譯作品”[2],相對其他漢語論著,這些譯作似乎微不足道,但其作用不可小覷,它是進一步了解康藏、治理康藏的基礎,為后世康藏研究者提供新的視野和必要的文獻、史料參考,也促進了藏學整體研究。
然而,過去的康藏研究中,這些譯文只是在歷史、文化、地理研究中作為重要史料被提及,諸如后文提及的學者趙艾東、王川、向玉成、霍仁龍、姚勇、王啟龍、鄧小詠等都曾參考《川滇之藏邊》《西藏東部旅行記》等譯文內容從各自研究領域對西方人在康藏地區的情報收集、傳教、外事、游歷考察等活動及其外文史料價值方面進行探討,雖然這些譯文史料價值影響深遠但至今沒有學者從翻譯的角度對其深入探討。筆者對上述康藏系列期刊近20年的譯文刊載情況及內容進行梳理和對比,結合二十世紀上半葉重要史實文獻對這一時期譯作進行深入探討,因《全本》中《康藏前鋒》《康藏研究月刊》所刊譯文的數量,影響力以及價值,故將其作為重點研究對象,這些譯作雖不可與同時代其他經典文學譯作比肩,但其藏學研究價值不可忽視。分析其獨特譯風,純粹的體裁以及以譯述為主的翻譯方式,旨在從歷史語境下原文、譯者、譯文三元共融關系中探討譯者主體性對譯作語言、翻譯策略的影響。
一、二十世紀上半葉康藏研究翻譯概述
關于康藏研究,國外早有關注,一些學者在其著述中早有提及并整理,《關于研究康藏問政中外參考書目舉要》(3)參見何璟《舉要》,載于《康藏前鋒》第2卷第10/11期第23-49頁、第3卷第3期第17-32頁。(下文簡稱《舉要》)全面而詳細地整理了關于康藏研究的中、英、日等文獻目錄。《青康藏新西人考察史略》《民國邊政史料匯編》(4)參見徐爾灝的《青康藏新西人考察史略》, 1945年編,內部發行資料;馬大正編《民國邊政史料匯編》,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9年出版,收錄了民國時期邊政方面的史料,即蒙藏院及蒙藏委員會相關史料;吳傳鈞《近百年外人考察我國邊陲述要》(上、下),載于《邊政公論》1944年第3卷第5期第54-60頁、第6期第52-58頁。等書籍中對90多個西方人在中國西部或西南邊疆地區游歷、考察、測量等文獻目錄進行整理,同時收錄了部分西方人所撰寫的康藏研究文獻。近年來,王啟龍、鄧小詠從地理研究角度對二十世紀上半葉外文論文和書籍譯述進行詳細梳理,語種涉及英、法、日語,其史料參考性較強,但有些文獻內容及出處仍有一些疏漏,需要完善。《舉要》輯選了1800年至1927年約130年間與康藏研究有關的英文著作160多部,論文近70篇,日語著述高達269篇(部)但主要研究內容為大藏經、藏傳佛教和梵教等,譯著少且主要涉及西藏概觀(5)參見太田保一郎著《西藏》,1907年四川西藏調查會譯刊;山縣君著《西藏通覽》,1913年陸軍部譯;青木文教著《西藏游記》,1931年唐開斌譯。。英語、法語類著述較多,但譯著大部分是以衛藏研究為主,正如《西康之神秘水道記》(6)參見Francis Kingdon Ward著,楊慶鵬譯,The Mystery River of Tibet《西康之神秘水道記》,1931年蒙藏委員會出版。譯者序言所言“吾國關于康藏兩地記載特少,又皆詳于藏而略于康”,足見研究者的選擇。《舉要》中大部分著述除了某些章節涉及康藏問題研究外,專門以康藏問題研究為主的譯述不過40篇(部),相對幾百篇(部)的涉藏地區外文文獻翻譯這并不多。譯作包括外文書籍和科研論文翻譯,主要涉及實地考察、探險和旅游,如研究者所熟知的《西藏東部旅行記》(7)參見Eric Teichman, Travels of consular officer in Eastern Tibet,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22。此書民國時期多次被節譯,詳見吳墨生譯《西藏東部游記》,載于《邊政公論》1931年第8期第69-83頁,1932年第9期第142-158頁;朱章譯《西藏東部旅行記》,載于《蒙藏委員會蒙藏政治訓練班季刊》1933 年第81-106頁,后以筆名‘之通’續譯并刊載于《蒙藏月報》1935年第4卷第2期第38-43頁、第3期第36-41頁、第4期第48-59頁;高上佑譯《西藏東部旅行記》,載于《康藏前鋒》1934年第2卷第1期第29-37頁、第3期第24-29頁、第8期第59-68頁、第9期第39-47頁、第10/11期第23-28頁、第12期第33-38頁,1935年第2卷第7期第33-39頁、第8期第41-47頁、第12期第33-38頁、第3卷第2期第31-36頁、第3期第41-46頁、第4期第23-26頁,1936年第3卷第8/9期第22-29頁;余生譯《西康游記》,載于《再生》1941年第63期第10-12頁、第64期第11-12頁、第68期第12頁。《川滇之藏邊》(8)參見古純仁著,李思純譯《川滇之藏邊》,載于《康藏研究月刊》1947年第15期第5-13頁,1948年第16期第2-11頁、第17期第18-26頁、第18期第21-28頁、第19期第26-31頁、第20期第20-29頁、第21期第18-24頁、第22期第10-16頁,1949年第23期第22-28頁、第26期第22-32頁、第27期第28-32頁。原文詳見Francis Goré, Notes Surles Marches Ttibétaines du Sseu-Tch’ouan etdu Yun-Nan, Bulletin de l’cole.Fran aised’Extrême, Orient, 1923.《西康之神秘水道記》《旅居藏邊三十年》(9)參見楊華明,張鎮國譯《旅居藏邊三十年》,載于《康導月刊》1943 年第5卷第6期第36-41頁、第9期第32-35頁,1944 年第5卷第11/12期第40-44頁、第6卷第1期第41-45頁;全文共三編:西藏鳥瞰、西藏天主教、漢藏邊境。《藏人論藏》(10)李安宅譯《藏人論藏》,載于《邊政公論》1942 年第1卷第7/8期第98-105頁、第9/10期第70-80頁。原文詳見G.A. Combe,A Tibetan on Tibet,London: Adelphi Terrace, 1926.《康藏故事集》(11)原文詳見A·L· Shelton,Tibetan Folk's Tales,New York: George H. Doran Company, 1925; 作者常見中文譯名為“史德文”,著作為胡仲持首譯,此后出現多個譯本,胡仲持譯《西藏故事集》,1930年上海開明書局出版;程萬孚譯《西藏的故事》,1931年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甘棠譯《西藏民間故事》,1933年商務印書館出版;李敬祥譯《西藏故事集》,1937年上海開明書局;李敬祥譯《七個王子》,1941年上海啟明書局。等,主要涉及康藏地區的地理、氣候、植物、民族 、宗教、民俗等。其中針對康藏問題的全譯本很少,80%譯作屬于著作節譯。一些涉及康藏問題的科普論述、游記以及研究論文,諸如源泉所譯的《西康人文地理述略》,陳告佳所譯《西康東部高原游記》以及洛克(Joseph F. Rock)所撰的游記譯作(12)參見源泉譯《西康人文地理述略》,載于《清華周刊》1933年第40卷第7/8期第155-163頁。陳告佳譯《西康東部高原游記》,載于《旅行雜志》1940年第14卷第11期第3-14頁。約瑟夫·洛克多篇游記被翻譯刊載,例如吳墨生譯《經過亞細亞的奇偉河峽》,載于《邊政》1931年第5期第190-215頁;李伯諧譯《雄偉壯麗之明雅貢噶山》,載于《邊政》1931年第8期第159-183頁;金飛譯《木里游記》,載于《邊政》1932年第9期第159-174頁。等,這些譯文多載于康藏《全本》和《邊政公論》,而《邊政》、蒙藏系列以及《清華周刊》等期刊偶有拾遺。
與《邊政公論》等期刊相比,《全本》刊載康藏研究的譯作數量最多,針對性也更強,獨具特色,其史學和學術價值受到學者和專家的普遍認可。“對國外學者關于康藏地區考察報告的翻譯與刊載,更反映了當時學者廣闊而獨到的學術視野和視角。”[3]其中《康藏研究月刊》刊載量最為突出,該期刊所共刊載65篇學術文章,譯述13篇,約占總篇目的13.8%,屬三種康藏期刊之最。這些節譯主要包括李思純所譯法國天主教士古純仁(Francis Goré)的《川滇之藏邊》之主要篇目,譯文總計約七萬字,這些譯文對后世研究影響較大,因為它們“反映外國人在康區考察活動的文章中,最具價值,所反映的康區內容最為詳細和豐富”[4]。雖然楊明華、張鎮國后來也選譯了古純仁所著的另一部短篇游記《旅居藏邊三十年》連載5篇刊載于《康導月刊》,但內容主要涉及西藏宗教和外交事件。故“《川滇之藏邊》在同時期外國人所著有關康區的論著中頗有代表性和獨特價值”,其譯文具有較高的史學價值。高上佑所譯英國人臺克滿(Eric Teichman)的著作《西藏東部旅行記》刊載于《康藏前鋒》。該著作早期被吳墨生翻譯過兩章,之后有其他譯者選譯過,但高譯篇目最多,居所有期刊之最,連載14篇,包括4篇藏史序言之藏邊各方之關系史略與10篇康藏旅行記事,以史料的形式詳細呈現康藏地區人文、社會、經濟、政治生活等狀況,對當時康藏研究提供寶貴的歷史素材和佐證。值得一提的是《康藏前鋒》等刊物的譯述改變了康藏研究模式——以譯促研,在康藏研究的拓荒者和奠基人中,大部分學者都從事過外譯。外文著述“具有相對較為完善的學術撰寫規范,其體系和理論都更加科學,從而為中國人提供了某種科學論著的范式。”[5]對國內相關研究從學科體系、行文特色、語言組織上都有一些影響。通過翻譯,讓國人了解到外國人對這一地區的認識和研究遠比我們深入,從而激發國人從更廣闊的視野去了解康藏研究的焦點、進度以及存在的問題,對比其研究思路和方法認識自身研究特色與優勢。
二、康藏問題著述翻譯的特點
二十世紀上半葉,國內有關康藏地區的典籍文獻甚少翻譯作品中探險、游記方面的內容比重大。早期國內學者為了進行深入研究康藏不得不參考這些國外文獻,因而所選譯文具有一定主題性和針對性,如上文所提及的《西藏東部旅行記》《川滇之藏邊》等著作以及一些國外地理雜志的科考、游記譯文,主要涉及當時康藏地區歷史、人文地理、自然環境、社會經濟狀況。因此這一時期譯文、譯風上具有如下特點,一方面,翻譯體裁以科研考察、實地探險和游記居多,翻譯風格以寫實、科普為主,語言形式多以半文半白。另一方面,翻譯策略多采用譯述,譯注常被用以作文化或語言注解或詮釋。
(一)文風樸實,多為游記
文風樸實符合科考、探險等文獻的要求。二十世紀初邊藏研究譯作延續清末“學西人”,“廣民智”[6]的思想。科研論文,考察報告,游記探險文獻的翻譯是康藏譯作突出特點。這個時期西方人在康藏地區科考、探險、旅行活動主要通過游記形式記錄并流傳[7],內容與康藏地區社會的基本情況有關,如《川滇之藏邊》的作者古純仁,一位法國天主教士,通英語,會漢、藏文,長時間滯留考察,其著作較為全面翔實地記錄了作者游歷考察康區各地之情形;該書分社會和地理兩部分,著名學者李思純選擇了該書的11篇內容節譯并刊發于《康藏研究月刊》包括《川滇之藏邊》《川邊之打箭爐地區》《川邊霍爾地區與瞻對》《理塘與巴塘》《維西》《旅行金沙江盆地(1922年)》和《察哇龍之巡行》《康藏民族雜寫》,內容涉及人文地理、社會,民俗等;譯文樸實,可讀性強,多次被學者引用。一般而言,寫作目的決定了內容,同樣翻譯目的決定了翻譯風格。從鴉片戰爭到民國時期,大部分西方人進入西南邊疆進行考察、探險和游歷達到高潮,固然一方面是因為東方文明的吸引,但大部分人根本的目的還是覬覦我國西藏,有所圖謀。這一時期,大量西方政客、傳教士、探險家和科學家通過合法或非法途徑入境,對藏邊進行考察、調研、游歷和資料收集。他們是早期康藏的研究者,也是西方世界了解中國西藏的探路人和情報收集者,例如,英國皇家地理學會主席古柏(T.T. Cooper),博物學家普拉特(A. E. Pratt),外交官川邊領事臺克滿和美國外交官兼漢學家柔克義(W.W. Rockhill)等(13)這一時期,西方人進入中國邊藏地區從事游歷、考察等活動可從其著述中窺知一二。古柏,第一個在川西和滇西北一帶探路的英國人, 撰寫考察文章和《身穿漢裝的商業先驅之旅》《藏東游記》等著作,為英國在中國西南邊疆擴張提供情報;普拉特,英國博物學家,收集動植物標本記錄于《西藏踏雪記》及《兩訪打箭爐游記》等著述中;柔克義,曾到打箭爐做人類學和民族學考察并采集標本,著有 《1891—1892年蒙藏旅行日記》等著作;古伯察是最早進入康藏地區的西方人之一,以傳教和考察之名進入西藏,著有《韃靼西藏旅行記》;史德文曾在回憶錄中記錄了康區情形和其在康區的活動。。其中一部分游歷者是西方基督教會的傳教士,他們到康區除了“傳福音”外,還在該地區進行地理考察、植物采集、文化交流等活動。例如,法國傳教士古伯察(Régis-Evariste Huc),美國傳教士史德文(A. Shelton)等。在這樣歷史背景下,而游記考察成為他們掩人耳目的一種方式。許多學者曾通過翻譯深入研究過這些科學家、傳教士在藏邊考察和游歷背后的宗教、政治、經濟、科學探索等目的。[8]翻譯這些游記可知康藏研究之概貌,窺西方學者之意圖,例如《西藏東部旅行記》作者臺克滿,曾任英國駐華公使館秘書,熟悉中國,特別留意研究西藏,1918年奉英國政府之命赴藏調節西藏糾紛,事后著書。其游記則分兩部分,一部分是關于中英在西藏問題的立場和外交關系,其政治立場鮮明,另一部分才是赴藏日記,同為游記,古純仁的《川滇之藏邊》立場更為客觀。另外,從1888年到1929年刊載于《皇家地理學會月刊》等專業學術期刊上40多篇有關康藏地區科考或游記文章,如普拉特就刊發過《兩游藏東邊境之打箭爐》,古柏四篇考察記錄則發表在《英國皇家地理學會文集》。部分論文在當時被國內學者翻譯,如上文提到的《西康人文地理述略》《西康東部高原游記》等。游記表達方式多樣,記敘、描述、論述作者所見、所聞、所感,其內容主要涉人文地理,社會面貌等。也包括很多專業科學知識如地理測量、動植物,水利等,因此譯文的體裁也如其科普文章一樣簡潔樸實而流暢,例如《貢噶各寺院探奇記》:“五月二十八日,自木里出發,四周森林,盡屬松橡,林際外矚,遙見里塘河,峽谷在其南,風景甚美…… 翌晨極早出古德村,冒霧行,過廣漠森林中,豐恬不颶,萬籟俱寂,僅杜鵑啼鳴,稍解清晨之沉寂而已。”[9]58
雖然這些考察游記有些觀點帶有主觀性,但其著述在一定程度上也客觀記錄了其考察游歷時期康藏社會發展情況,有一定翻譯價值。另外,民國時期,國內囿于研究條件的局限,而西方人使用了現代科學的考察方法和測量技術在西南邊疆進行游歷和考察,故翻譯這些圖情資料是一種深入學習和研究的方式。即使近幾年,學者要研究康藏邊境的歷史也要參考這些史料,而對西南邊疆游記資料的利用近年來又達到了一個“新的高潮期”[10]。
(二)譯為主體,述為補充
從翻譯角度看,“譯述”是二十世紀上半葉康藏譯作另一大特點,此術語常見于民初的翻譯或版權頁中,該語詞在明朝開始使用,傳教士高一志曾自謙稱其譯作為“譯述”。譯界熟悉的《天演論》就是一部譯述,“如果說譯述形成于嚴復,那么林紓則把這種方法發揚光大”[11];因此嚴復、林紓等實際掀起了譯述史上的一次高潮。何為譯述?學界并沒有統一定義,但意思大抵相似,譯述中“譯”是基礎,“述”是補充,“一般指譯者僅僅表達出原文的主要內容或大意,而不是那么完全忠實于原文。”[12]然而,這一時期的譯述呈現方式并不一樣,常通過以下幾種方式實現:其一,譯者根據原作,并不按照原文的順序和語言逐一譯出,只是譯出其主要意思,如《猴島交涉記》(14)詳見黃明信譯《猴島交涉記》,載于《邊政公論》1941年第1卷第3/4期第145-160頁。,譯者在序言已說明“原書版本不佳,而且錯字極多,好在前后行文連貫尚無大礙,就略去未譯”。其二,依托原文進行翻譯,翻譯過程中常有增刪,其目的是讓讀者更好地理解,譯者通常在篇首或篇尾以“譯者按”的形式進行補充說明,例如,《藏人論藏》(見上文注釋)在開篇洋洋灑灑幾百字補充了一大段原作者和翻譯背景與內容等相關信息,“譯者案:此文譯自英國駐打箭爐領事孔貝之藏人論藏一書……首末兩章為孔貝自傳,一論佛教,一述打箭爐之跳神,其余各章均藏民智慧保羅旅行與觀察所及…”。而楊明華、張鎮國所譯《旅居藏邊三十年》,譯者不僅在篇首對翻譯內容、目的及風格進行簡要概述,在篇末還補充對翻譯背景和譯事作了必要的介紹,“結語,本篇脫稿后,發生二件大事,影響西藏之前途必巨……誰能逆料此次戰爭如何結局乎,雖然,西藏絕無不受影響之理。”
另外,這一時期的譯述中的“述”有時也發生在翻譯過程中,譯者對句子或段落進行翻譯介紹、補充、說明和評述,看起來與“譯注”類似。“加注”是翻譯過程中必不可少的環節,二十世紀上初,譯注不像如今翻譯那么規范。任何語言都有其特殊性,譯者把一種語言轉換成另一種語言時,總會有言而未盡或言過其甚,加注是“譯者在翻譯過程中為了完整地傳達原文的語義和風格的一種補償方法,是為了盡可能達到翻譯等值而采用的輔助性手段”[13]。李思純在其《川滇之藏邊》中大量地使用“文中述”,譯者常采取兩種形式進行,一是翻譯內容后加括號補充注釋信息,二是以“譯者按”提示后增加解釋內容,這兩者略有區別,前者通常對時間、人名地名等進行解釋與說明,后者常對康區宗教、社會習俗、史事、事件等進行必要的闡釋與補充。
三、譯者視角下的康藏研究著述翻譯
中西方翻譯理論發展至今,各種理論和流派層出不窮。從翻譯語言學派到文化派的發展,從以“原文中心”翻譯觀到文化轉向后翻譯研究的多種思潮,其研究主體越來越指向譯者方向。霍姆斯(James S. Holmes)1972年提出了翻譯研究的整體框架中雖沒有在純粹的翻譯研究中考慮對譯者的研究,但在翻譯應用研究中通過translator training明確了譯者的重要性。[14]翻譯的外延不斷擴大,但翻譯的本質依然是“換易言語使相解”;直譯、意譯和忠實、通達等問題始終是評價翻譯實踐繞不開的問題,但其研究的切入點和范式早已不同。除了對原文與譯文討論外,學者也從譯者角度對翻譯進行研究。早期有如施萊爾馬赫(F. Schleiermacher)盡量讓讀者安居不動,使作者靠近讀者的歸化翻譯策略就已經開始討論譯者的狀況與活動。列文(S. J. Levine)認為“翻譯應該是一種批評行為……產生疑問,提出問題,對原文的意識形態重新語境化”[15]表明了譯者在翻譯中立場與作用。韋努蒂(L.Venuti)對文學譯者的“隱身與顯形”研究,提莫志克(M. Tymoczko)的“譯者文化與意識形態”以及霍米觝巴巴(Homi Bhabha)的“第三空間”等表明了譯者的立場和定位在翻譯研究中的日益重要性。[16]
相對民國時期籠統地稱為“譯述”,現代翻譯中對這類翻譯方式描述更為具體,“轉譯、譯寫、創譯、變譯”等常被學者們使用。譯述是什么樣的翻譯?國內學者常用“translating and reviewing,reviewing,transwriting”等英語術語,反映了學者對其不同的理解。印度翻譯家拉爾(Purushot Lal)曾定義譯創為“具有可讀性、不嚴格忠實的翻譯”。[17]大部分學者認為“譯創”應該在一定的翻譯基礎上改編,增刪甚至再度創作,從這個意義上講,譯創亦可稱創譯,這和譯述有相似之處;不管采用“先譯后述”還是“夾譯夾述”的方式,譯是主體,這里的“述”既有綜述又有評述之意。如上文提到朱章所譯的《西藏東部旅行記》,在其卷首“譯者附識”,相當于譯者序,簡要概述該書的主要內容的同時,對其內容進行簡短評述:“民念一年下(即1932年),余讀該書一過,覺其議論見解,雖不無偏頗之處,然大體尚能持之穩健,堪供參考,日記部分,更多珍貴材料,爰即從事移譯…”。有些學者認為譯述之“述”更多體現為“撰寫”,或“創作”。譯述和譯創主體都是譯,但呈現方式上,前者有綜述、評論之形,而后者有撰寫、創作之意。相對而言,上文提到的譯文,其體裁和翻譯目的決定了“述”原比“創”更實際,更符合讀者的需求。近年來,“譯述”隨著翻譯外延的拓寬其定義也有些改變,國內學者黃忠廉把這種翻譯方式又稱之為“變譯”,他認為“述,即轉述,是在譯文中轉述原作相關內容,與‘述’相應的變譯方法是譯述,即譯者用譯語轉述原作主要內容或部分內容的變譯活動”[18]。因此譯述更強調譯者的作用,譯者不但要吃透原作內容,領悟其要旨所在,用目的語準確再現,還要對原作內容進行概括和提煉,對其主要觀點進行評述,如譯者在《貢噶各寺院探奇記》“按”中述評道: “余以一九二八年三月二十日,自云南省城出發,挈隨從多年之納書(藏書)人偕行,由大理抵麗江,作探奇之籌備,添雇隨從,部署行裝,一切既妥”乃復北發,行十日而抵木里土司境,(15)木里土司譯作木里,在四川西康云南三省交界處,系雍正八年歸附,授安授司印,所管皆番僧,清時隸屬會監營。當地人民,稱土司為大王,故西籍常譯作kingdom,實不過一族之酋長而已,(16)筆者注:原文無此句,屬于譯者評。擬晴土司護送往貢噶,鄉城,即定鄉縣。”[9]58
“譯述”中譯者除了將原文主旨內容盡量譯出,還會以譯者身份對其加以介紹和評論,韋努蒂根據自己翻譯意大利實驗派詩歌和小說經驗提出譯者將譯文譯成流暢、地道、可讀的語言,創造出一種“透明的幻覺”可以使其“隱身”,譯文看上去不是譯文,而是“原創文本”,受到更多的青睞[19]。如上面的譯者評述的一句,文中并無明顯提示和譯文融為一體。為此“譯者要先對原文了然于胸,下筆時不要太拘泥于一字一句 ,主要在把意思表達出來 ,可以增 ,可以減 ,可以夾譯夾述。”[20]即譯者要把作者的真實意思表達出來可以對原文的信息進行適度的創造或加工,譯述能給予譯者一定的求真務實的空間與適度的自由[21]。然而,在民國時期康藏研究的語境中,這種強調內容順暢通達,述評具有點睛之筆的譯述,讓譯者不能完全“隱身”,在譯文中,譯者通過不同的“述”得以“顯形”,當然這里“顯形”不同于韋努蒂針對文學翻譯者的“行動號召”方式,因為它并非原文本身的翻譯。根據費爾斯蒂納(J. Felstiner)對譯者“隱身”的理解,他認為“新詩歌一旦定稿,翻譯時投入的工作就‘隱身’了,其中包括譯者背景、研究,翻譯構思等”[22],而這里的譯述,除了對翻譯的補充、說明和評述外,還包括學者的研究成果。例如上文提及《川滇之藏邊》,文中大量的“譯者按”就是作為研究者學者譯者的一些研究成果體現。
“譯述”立足于“原文——譯者——譯文”三元關系,譯者研究是翻譯研究“一個嶄新的切入點”[23];譯者是紐帶和媒介,“譯”到“述”的過程復雜多變,在其對原文深入理解后并結合讀者情況對原文進行注解和述評,從原文到譯文,再從譯者到讀者,以譯者為出發點建構“譯者——譯文——讀者”新三元關系。譯述內涵決定了其所指可以是上面提及的“轉譯、譯寫、創譯、變譯”任何一種,這由翻譯行為的主體——譯者來決定。忠實暢達,直譯意譯等二元對立關系有時無法更好地解釋諸多的翻譯現象,諸如康藏譯著翻譯中譯者身份、社會因素、讀者因素等對翻譯內容、語言,翻譯方法的制約。近年來,國內對譯者及其行為進行了廣泛地研究,如胡庚申從“譯本、譯者、譯境”[24]三者相互關系討論作為翻譯主體的譯者。周領順從譯者行為批評視角討論,認為譯者行為批評研究是既不同于以二元對立式判斷的譯文與原文忠實度靜態研究范式,也不同于社會背景下對文本和譯者理性批評的研究范式,它強調譯者行為與譯文品質的相互作用,充分考慮了譯者的意志性、翻譯的社會性、譯文生存空間的復雜性。[25]民國時期康藏譯著中“譯述”的名與實比較復雜,誠如李奭學談及明清之際天主教的翻譯文學史時指出的那樣“這期間耶穌會士的翻譯,很少列出原作者和原書名,也不會在書中告訴我們有多少成分是‘譯’多少是‘撰’”[26]。這表明譯述中,譯者主體性在“譯者——譯文——讀者”三元關系中貫穿整個翻譯過程,譯者在材料選擇、翻譯策略,語言使用等都具有一定抉擇權。從譯者身份來說,上文提及的學者李思純是民國時期四川大學教授,現代藏學開拓者之一,而高上佑是康藏前鋒社社員,后來的西康省代議長,政府官員,其選擇的材料亦有所不同,《川滇之藏邊》出自學者、教士古純仁,而《西藏東部旅行記》則出自具有強烈政治色彩的川邊領事臺克滿;所譯內容,前者翻譯與康藏地區人文地理、社會歷史,經濟狀況,民風民俗等內容,后者翻譯與外交軍事、邊疆沖突等;從翻譯策略和語言使用上,李思純在《川滇之藏邊》翻譯策略采取“注”多于“述”皆因目的語讀者鮮有法語習得者,故注釋較多,這也成為該譯文一大特色,據統計其每一篇譯作至少四五十個注釋,而高上佑則反之,李思純作為學者的嚴謹性體現無疑。在語言使用上高在《西藏東部旅行記》譯文中保留了康藏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異域特色給讀者以新鮮感,由于其涉及三種語言的轉換,文中大量轉譯的英語和藏文化新詞匯,如惡魔舞(devil dances),黑帽舞(dance of the black),西藏藍皮書皮紙(The Tibet blue book),皮紙(pichils),銀卓卡(trangka)莊酒(chang),西藏雍(dzong)(17)藏語文化詞“黑帽舞”是指惡魔舞,西藏戲劇的表演形式;“皮紙”是指既硬又粗的西藏紙;“銀卓卡”指西藏貨幣;“莊酒”指清淡之啤酒,大麥所釀成;“雍”指堡及官吏之住地;另外,Pichils,trangka,chang,dzong均為音譯詞。等直接采用英語或藏文加注,不作更多解釋,突出了文化差異,作為年輕編輯的高上佑用詞尚算大膽新穎。
另外,同一譯本不同譯者,語言使用上的差異也顯示了其不同的立場。《西藏東部旅行記》中關于第一部分藏史序言之藏邊各方之關系史略的翻譯,有三位譯者都翻譯過這部分,除高上佑外其他兩個背景不詳,但從其翻譯可以審視其立場。值得一提的是此書對英帝國的野心可謂見微知著(18)英國人在康定的活動顯示其覬覦西藏的野心。1868年英國人首次進入打箭爐(1908年后稱康定),出于英國對西藏的侵略陰謀1913年英帝國在康定設領事館分館,1922年撤館。前兩任領事Louis King(金路易),Oliver Coales(郭立實),臺克滿(漢名趙錫孟)為第三任,插手并干預1917年“康藏糾紛”,《西藏東部旅行記》記述了臺克曼擔任領事期間考察并插手康藏軍事糾紛的經歷。。在翻譯時,一方面,譯者吳墨生、朱章(后用“之通”之名)都翻譯了原文第一章序,交代了中國對西藏的主權的歷史,在與事實不相符的敘述上做了改譯,而譯者高上佑卻直接將原文第一章序言刪掉。另一方面,具體翻譯上也能體現,例如對該書第一章的標題翻譯來看,原文“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ibet Up to the Time of the British Expedition to Lhasa in 1904”三位譯者分別翻譯為“1904年英軍到拉薩以前中藏之關系”(吳墨生譯),“1904年英國遠征拉薩前之中藏關系”(朱章譯),“1904年之中藏關系”(高上佑譯),對臺克滿使用的“China and Tibet”并未作說明,這和當時譯者所處的歷史背景有莫大聯系,這里暫不作討論。單說翻譯,標題中作者把軍事干預和侵略說成Expedition,從英語釋義上看該詞條中大都和“journey”有聯系,具有“考察、探險,遠足”之意,而“遠征”相對來說比較符合該詞的意義和英國真實意圖。審視各譯者的翻譯,只有朱章翻譯到位,其他兩譯者要么沒有翻譯出來,要么直接刪掉不譯,其立場和態度躍然紙上難免讓人猜度,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
以譯者為切入點的譯者行為研究并不等于不研究文本和其社會性,上文中譯者對文本中語言的處理實則具有一定社會性。譯者作為翻譯主體,具有語言和社會雙重性,因此有譯者主張翻譯內外結合來研究。二十世紀上半葉,一個特定的歷史時期,內憂外患,社會動蕩,戰事不斷。這時期外語原著選擇少,局限性大,懂外語且對康藏研究感興趣的不多,且翻譯的專業性不強,對康藏研究不深,這種譯內環境和譯外環境不僅影響了譯述的數量和質量,還影響了譯者對文本的體裁,內容,語言與風格的選擇。例如上述譯述源語言多為英語,偶有法語,譯者正確解讀原作的風格與語言定位,這是由文本的所處時代決定,前面已經提及不再贅述。故譯文體現了原文的風格,語言簡單明了,用詞準確,專業術語使用恰當,雖是半文半白,但可讀性強,即使現在讀起來也不覺晦澀。《西藏東部旅行記》多種譯本,雖大都文白相伴,細讀不難發現其語言略有不同,例如同一句譯文,朱譯“十八世紀初葉,準格爾蒙古人侵略西藏,滿清皇帝派兩路軍隊援助藏人。”吳譯“十八世紀之初,準格爾犯藏,清帝派救兵兩路援藏。”此兩句簡潔順暢,正如巴斯內特和勒費弗爾(S. Bassnet & A. Lefevere)談及譯入語文本所實現的功能時所說“有些文本主要用于傳遞信息,那么這類文本的翻譯應該力圖傳遞該信息才合理。”[27]而高譯“方十八世紀之始也,準格爾蒙古人(19)三位譯者的譯文在現在來看有些用詞并不恰當、不嚴謹,這也同時說明了特定的譯外環境對當時翻譯的影響。(Dzimgarian Mongols)侵入西藏,清帝發兵二路助藏攻之。”較之前兩者譯文更偏文,且使用原英文注釋,在其選譯文本中此現象比比皆是,對一些專有名詞的翻譯,要么意譯加注,要么音譯加注,要么直接用英文,保留了一些異域特色,正如其編者開篇介紹其譯文時這樣評價道“其內容詳確而精美,詞句新穎而暢達”。三譯文所用語言對于現代人來說閱讀不是非常順暢,但不至于佶屈聱牙,就譯者當時的社會性和語言性而言,該譯文確實通俗易懂,表達流暢,符合當時新文化運動后文白參半的社會需求。另外,就讀者群來說,譯作受眾大多是康藏研究的學者或政界要員,受教育程度較高,對譯入語基本要求就是語言雅致暢達,但如果對普通讀者,“語欲簡雅,意欲明易”的譯文,其可讀性會增強。
四、結語
中西方對翻譯的討論是以文本為主體,對直譯與意譯,忠實與通達這些二元對立命題討論一直呈螺旋式推進。縱觀二十世紀上半葉與康藏有關的譯述,總的來說,其主題明確,針對性強,語言暢達,意思清楚,譯評結合,風格突出。在人們關注這一時期有關康藏研究的翻譯時,注重其譯文內容多于其呈現形式與翻譯策略,也許有人認為,從現實的角度探討這一時期的譯作對當下翻譯似乎沒有很好的參照,但在筆者看來,從譯者的視域下從翻譯外問題到翻譯內問題重新探討這一時期著述翻譯,既有史料研究意義,也能對當下部分缺乏譯者深度理解的譯作有一定反思。譯者是聯系原文與譯文、作者與譯文讀者的重要紐帶,其翻譯行為受時代、政治、歷史、文化、意識形態、讀者群等客觀性因素的影響。通過對這一時期外國有關康藏問題研究著述翻譯問題的討論,客觀地分析和認識譯作內容和其所產生的時代背景,對其譯文內容進行批判性認識和接受可以更好地把握其史料價值。另外,這一時期的譯者多采用譯述,他們或評,或撰,或改再現了原作內容和意義以達到譯者追求譯文的“真”,其背后體現了譯者在具體語境中對譯文的語言性和社會性的“務實”,最終達到吸引讀者并使其獲取通達的史料信息。這種“譯述”的方式對研究新的語境下的變譯、創譯等翻譯形式仍有一定借鑒,對進一步研究這一時期的譯者群有一定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