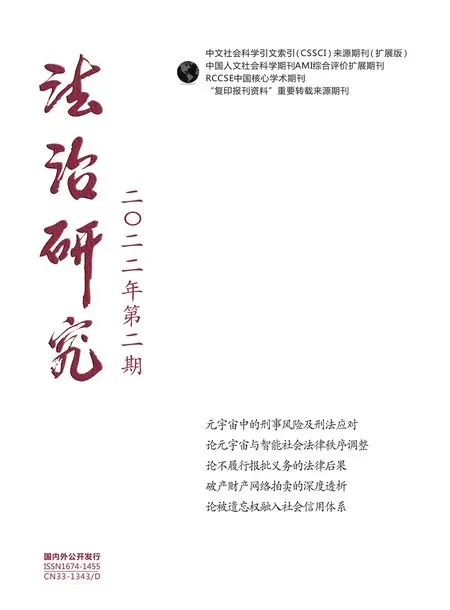論禁止重復評價的判斷標準及其適用爭議問題*
孫萬懷 劉環宇
禁止重復評價是刑事法域下評價具體犯罪的準則。然而,刑法尚未將其與罪刑法定、罪刑均衡等一同視為基本原則,禁止重復評價只不過是學界和司法實務一廂情愿的稱謂。由于禁止重復評價“嫡系身份”的缺位,加之學界研究興致的寡淡,其無法像刑法的基本原則一樣形成獨具特色的評判標準。目前學界對于其研究停留于點的感性認識層面,尚未達致面的理性認識高度,同時司法實務僅就事論事未能提煉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判斷標準。鑒于此,本文著眼于禁止重復評價的正當性、判斷標準及其適用爭議問題三個方面試圖對其形成系統化、體系性認識,希冀填補理論空白,解決現實困境。
一、禁止重復評價的正當性依據
雖然禁止重復評價不屬于刑法的基本原則,但客觀上是評價具體犯罪的準則,并已獲得學界和實務的廣泛認同。誠如,“存在即合理”,任何事物的存在必然蘊藏著道理。正當性可以解釋為合理性,禁止重復評價的正當性可理解為禁止重復評價的存在基礎,應從禁止重復評價之于傳統法律理念的傳承、自身功效、刑法基本理念的守護三個維度加以論證。
(一)禁止重復評價是對“一事不再理”的傳承
禁止重復評價發軔于羅馬法的“一事不再理”。“一事不再理是指對于判決、裁定已發生法律效力的案件或者自訴人撤訴的案件,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得再行起訴或受理。”①陳興良:《禁止重復評價研究》,載《現代法學》1994 年第1 期。由于古羅馬是實體與程序合一的時代,“一事不再理”兼具實體與程序雙重屬性。古羅馬的案件審理包含法律審理與事實審理,法律審理是原告向法官主張訴求,被告可以進行申述,法官在充分聽取雙方意見的基礎上決定是否受理案件,而事實審理是案件受理后法官根據案件事實作出判決,法律審理終結的標志是“證訴”,事實審理結束的標志是判決。②參見賴宇、董琳:《論一事不再理原則》,載《法制與社會發展》2003 年第5 期。在法律審理階段,法官發現原告基于同一事實再次起訴有權基于“一案不二訴”駁回起訴;在事實審理階段,法官所做的判決是對案件事實的法律評價,法律審理側重于程序,事實審理著眼于實體。法官基于“一案不二訴”駁回原告訴訟請求,通過維護判決的權威性限制被告敗訴后再次起訴,約束原被告重復起訴旨在避免“一案二訴”,節約司法資源,維護判決權威。
禁止重復評價是“一事不再理”在刑事實體法的展現。“一事不再理”在刑事法域發衍為刑事實體法的禁止重復評價和程序法的一事不再理原則。雖然我國刑訴法沒有明確一事不再理原則,但兩審終審制是對該原則的彰顯,其目的是限制司法機關重復處理已經生效的案件。值得注意的是,再審制度是兩審終審制的例外,在符合一定條件下司法機關有權對已生效案件再次處理。禁止重復評價原則是“一事不再理”在刑事實體法上的表述。如前所述“一事不再理”在實體法上的效果是抑制被告敗訴后重新起訴以維護判決的權威性。對于刑事案件而言,法律評價與判決的權威性之間存在客觀、必然的聯系,依照正常邏輯,案件事實得到全面、充分的法律評價,刑罰與罪行相匹配,行為人會息訴服判,判決的權威性亦得以維護。換言之,如果對同一事實進行重復或遺漏評價直接影響到判決的公正性,引起行為人的憤恨之心,不能息訴服判,則有損判決權威。在評價具體犯罪時,應遵循禁止重復評價,不得對同一事實作出不利于行為人的重復評價,實現罪行與刑罰相匹配。因此,禁止重復評價是“一事不再理”在刑事實體法上的表達。
(二)禁止重復評價是評判具體犯罪的法律方法
法律方法作為一種方法論,是解決法律問題的路徑。“法律方法就是那種運用規則、尊重法治、維護一般正義但又不放棄個別正義、智慧靈活地處理案件的思維方法。”③陳金釗:《法律方法的概念及其意義》,載《求是學刊》2008 年第5 期。法律方法內含三個層次:一是文本分析方法,著重研究針對法律文本所進行的技術性理解,或按解釋學的語言,是對法律意義上的“前理解”內容。主要包括類型及類型化思維、法律注釋方法、法律原則的意義及適用、不確定法律概念及其判斷等內容;二是事實發現方法,主要是研究在法律適用中與法律處于同等地位的事實的認定與發現問題,表現為事實的采證方法、解釋方法和判斷方法等;三是法律適用方法,在對文本進行正確理解及科學發現事實的基礎上,將具體的法律條文適用于個案之上的規則和路徑,包括法律解釋、法律推理、利益衡量、漏洞填補等方法。④參見胡玉鴻:《法律方法及其在實現司法公正中的意義》,載《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 年第5 期。應當看到,法律方法內部自成體系,內含“三個階層”,針對不同的法律問題做類型化處理,并提出應對之道。
禁止重復評價是刑法在評價具體犯罪時所應遵循的準則,本質上是法律方法。準確地說,禁止重復評價是評價具體犯罪的法律適用方法。刑法在評價具體犯罪時應遵循一定章法,首先要理清所要評價的案件事實,即完整的羅列評價對象,然后運用正確的方法保證評價對象得到全面、充分的評價,最后對犯罪作出綜合評判,對行為人適用與罪行相匹配的刑罰。值得注意的是,全面、充分評價的對立面是重復或遺漏評價,重復、遺漏評價是具體評價時存在的謬誤,重復評價的發生概率高于遺漏評價,這也導致重復評價在學界和司法實務具有較強的存在感。禁止重復評價之所以被頻繁適用在于重復評價確實是評價犯罪過程中面臨的突出問題,如果不將其納入原則或準則會導致問題愈演愈烈,重復評價可能淪為一種常態,甚至被允許。反之,將其視為評價犯罪的準則有益于避免重蹈覆轍,同時引導刑法堅持正確的評價方法對案件事實作出全面、充分的評價。在此意義上,禁止重復評價作為一種評價方法,不僅具有懸崖勒馬避免重復評價的作用,還起到指示引領全面、充分評價案件事實的效果。
(三)禁止重復評價是對刑法基本理念的守護
禁止重復評價沒有被奉為刑法的基本原則,但卻是對刑法基本理念的守護,是確保理念得以貫徹遵行的保障。禁止重復評價的“保障性”突出體現在對刑法明確性和罪刑均衡的堅守。
1.禁止重復評價維護了刑法的明確性
“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法無明文規定不處罰”是對罪刑法定原則的經典表述,明確性是罪刑法定的當然要義。明確性是指刑法對行為是否構成犯罪、構成何罪以及判處何種刑罰予以明確。“這表明規則的意義是確定的,即任何一個正常理性人都能理解規則的含義,以此規則為標尺,在國民預測可能性范圍內規范自身行為。”⑤李潔:《論罪刑法定的實現》,清華大學出版社2006 年版,第78 頁。預測可能性原理是對明確性的引申,公民依照刑法或參照“先例”判斷行為性質規范自身言行。刑法是對犯罪的否定評價,禁止重復評價作為評判具體犯罪的準則與明確性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系,體現在立法與司法兩個層面。
在立法層面,刑法不得對同一事實做兩次以上的否定性評價。例如,《刑法》第233條過失致人死亡罪、第133 條交通肇事罪均對致人死亡行為作出表述,在交通肇事的場合,行為人違章駕駛致一人死亡,且負事故全部或主要責任的,既符合過失致人死亡罪的犯罪構成,又符合交通肇事罪的犯罪構成。過失致人死亡罪罪狀表述為“本法另有規定的,依照規定”,由此判斷《刑法》第133 條是特別法條,第233 條是普通法條,上述情形,應以交通肇事罪追究刑事責任。誠如,刑法是對公民設定“負擔”的規范。刑法對同一事實進行多次評價意味著對行為人多次設定相同的“負擔”,而“負擔”累積的后果是行為人本不應承受的。因此,刑法通過條文明確禁止對同一事實進行重復評價,以彰顯明確性和保障行為人權利。
在司法層面,司法機關不得對同一事實做兩次以上的否定評價。定罪與量刑是司法的兩大核心環節,定罪量刑的過程也是評價具體犯罪的過程。堅持明確性同樣是司法面臨的任務,確保對于具體犯罪的定罪量刑具有可參照性,公民可以參照“先例”評判行為性質及其法律后果。為了實現評判結果的明確、公正,應堅持正確的評價原則,禁止重復評價無疑是評價犯罪的準則,堅持全面、充分地評價案件事實,避免重復評價同一事實。試想,如多次評價同一事實,必會導致裁判結果與應然結果之間存在偏差,存在畸輕畸重的弊端,無法對“后例”起到示范效果。
2.禁止重復評價是對罪刑均衡原則的貫徹
罪刑均衡原則是刑法的基本原則,該原則強調所判刑罰應與所犯罪行和其他影響刑事責任大小的因素所產生的刑事責任相適應。簡言之,反映社會危害性與人身危險性大小的因素決定了刑事責任的輕重。禁止重復評價原則作為刑法的評價原則肩負著準確評判上述因素的重擔。立法上已經將犯罪劃分為三六九等,重罪對應重罰,輕罪對應輕罰。“既然存在著作為私人利益相互斗爭的必然產物的契約,人們就能找到一個由一系列越軌行為構成的階梯,它的最高一級就是那些直接毀滅社會的行為,最低一級就是對于作為社會成員的個人所可能犯下的、最輕微的非正義行為。在這兩極之間,包括了所有侵害公共利益的、我們稱之為犯罪的行為,這些行為都沿著這無形的階梯,從高到低順序排列。”⑥[意]貝卡里亞:《論犯罪與刑罰》,黃風譯,中國法制出版社2005 年版,第80 頁。由高到低的犯罪階梯對應著由重到輕的刑罰梯度。既然立法已經作出指示,司法理應貫徹執行,具體表現在評價犯罪時應全面、充分地評價犯罪事實,堅持禁止重復評價,不得對同一事實進行重復評價以避免對行為人帶來不利影響,實現罰當其罪。
禁止重復評價強調不得對同一事實做不利于行為人的重復評價。定罪量刑的過程實際上是評價犯罪事實的過程,此處論及的犯罪事實不僅包括影響犯罪構成的事實,還包括罪后發生的影響量刑的事實,如自首、坦白、立功、被害人諒解等。犯罪事實中滿足犯罪成立條件的事實與其他反映罪責程度的事實,而罪后發生的事實反映了人身危險性大小,其中反映社會危害性的事實影響到定罪與量刑,反映人身危險性的事實影響到量刑。厘清影響定罪量刑的事實只不過是評價犯罪的前提,至關重要的是,準確評價犯罪事實,正確定罪量刑,達致罪刑均衡。全面、充分地評價犯罪事實,避免對同一事實做不利于行為人的重復評價是實現罪刑均衡的保障。倘若某一符合基本犯罪構成的事實已被評價為定罪情節,該事實不得再次評價為量刑情節;某一事實不得同時評價為不同的量刑情節,除非評價為不同的量刑情節是對行為人有利。
二、禁止重復評價的實質內涵
在厘清禁止重復評價的判斷標準之前,應當澄清其實質內涵,這是亟待解決的“元問題”。所謂的“元問題”可拆解為如下命題:一是如何看待刑法評價;二是何謂評價對象;三是如何理解重復評價。
(一)刑法語境下的評價是對具體行為的價值判斷
日常話語中的評價是對人之善惡、事之曲直的一種價值判斷,其在刑法語境下理解為對具體行為的價值判斷,是對犯罪行為的否定評價。“所謂評價,在一個犯罪事件審理的過程中,指的是對行為人之行為,宣告其構成犯罪而應接受處罰。換句話說,就是犯罪以及國家刑罰權的宣告。”⑦黃榮堅:《刑法問題與利益思考》,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 年版,第204 頁。行為人作為犯罪的“始作俑者”,理應承受否定評價帶來的法律后果。由于不利后果的承受者是行為人,在此意義上是對行為人的否定和貶損,展現刑法愛憎分明、嫉惡如仇的一面。
刑罰權的宣告昭示出國家對具體犯罪的否定。經過審理的刑事案件存在四種處理意見:一是宣告無罪;二是單純宣告有罪;三是宣告有罪,并適用非刑罰處罰措施;四是宣告有罪,并判處刑罰。應當看到,第一種意見表明行為人沒有觸犯刑罰法規,不應被宣告有罪,其余三種意見屬于刑事責任的承擔方式,是對具體犯罪的否定評價。值得注意的是,三種刑事責任的承擔方式直接亮明了刑法對具體犯罪的價值取向和評判立場,同時不容否認宣告無罪也表明刑法的態度,只不過該意見與通常意見不一致而已,無論是宣告有罪還是無罪都是經過深思熟慮、審慎論證得出的意見,都是對行為的一種價值判斷。鑒于此,本文認為,刑法的評價不僅限于宣告行為人承擔刑事責任的否定性評價,還包括宣告無罪的“肯定性”評價,其展現了對具體犯罪的全面、充分的評判過程,評價側重于過程,而非最終的認定結果。
(二)罪前、罪中與罪后事實是評價對象
綜觀刑法,考察實務,刑法的評價對象除了包含構成要件要素之外,還覆蓋到行為人的罪前和罪后表現。
首先,罪前事實是對行為人在犯本罪前行為表現的反映。雖然罪前事實與本罪無直接關聯,不影響對本罪的認定,但是影響量刑。例如,犯罪前科是相較于本罪而言的概念,犯罪前科表明行為人在犯本罪前存有“黑歷史”,并且刑法已經對其作出過否定性評價。在具有犯罪前科的情況下,行為人屢教不改、重操舊業表明刑法對其再犯可能性抑制的失利,刑法在評價本罪時通過將犯罪前科視為酌定從重量刑情節的方式以實現對其再次犯罪的報應,達致預防犯罪之目的。應當看到,犯罪前科作為量刑情節儼然已成為慣常做法,是充當本罪的罪前事實被獨立評價的典型適例。
其次,罪中事實是對行為人罪責大小的呈現。誠如,“犯罪構成是認定犯罪的法律標準。任何行為,凡是符合某種犯罪構成的,就成立犯罪;凡是不符合犯罪構成的,就不成立犯罪。就認定犯罪的法律標準而言,除了犯罪構成之外沒有別的標準,也不能在犯罪構成之外附加其他任何條件,所以,犯罪構成是認定犯罪的唯一法律標準。”⑧張明楷:《刑法學》(第五版),法律出版社2016 年版,第99 頁。易言之,犯罪構成是對犯罪的類型化表達,構成要件要素是刑法的評價對象,屬于罪中事實,如犯罪主體、行為、對象、結果等。同時,刑法分則以單一犯罪的既遂形態為藍本屬于基本的犯罪構成,而修正的犯罪構成是在基本的犯罪構成之上考量犯罪形態和共同犯罪而做出變通所形成的犯罪構成,修正的構成要件要素也屬于罪中事實。由此觀之,罪中事實所指向的是構成要件要素,其反映了行為人的罪責程度。
最后,罪后事實是對行為人認罪悔罪態度的展現。考慮到犯罪行為已經完成,并且犯罪構成是評判行為性質的唯一標準,行為人的罪后表現是對認罪悔罪態度的反映,無法對完成之罪的定性帶來影響,但會牽涉到量刑,屬于量刑情節,如自首、坦白、立功、被害人諒解、退贓退賠等。罪后事實是對罪中事實的發展和延續,反映行為人的人身危險性和再犯可能性。
(三)重復評價是對同一評價對象給予兩次以上的價值判斷
在知曉評價內涵,明確評價對象的基礎上,重復評價的含義便易于把握。重復評價,是指刑法將同一評價對象進行多次評判,導致行為人所承受的法律后果與其本應承擔的刑事責任存在偏差。重復評價作為一種客觀存在,體現在刑事立法與司法兩個層面。
立法上的重復評價是指同一犯罪同時匹配于數個罪名,符合數個犯罪構成,這是立法技術的產物,為了有效應對此問題,法條競合犯、想象競合犯應運而生。可以說,法條競合犯、想象競合犯的處斷意見是對立法疏漏的彌補,更是對重復評價導致不利后果的有效規避。同時,司法上的重復評價是司法機關在定罪量刑時對同一評價對象進行反復適用,導致罪刑失衡。立法上的重復評價易被覺察,但司法上的重復評價似乎更為隱蔽,也更普遍,一方面,每個案件獨具特色,全面、準確地梳理評價案件事實本身就是一項重任,能夠避免重復評價亦是難上加難;另一方面,司法機關面對罪與非罪、重罪與輕罪、重罰與輕罰的抉擇存在選擇前者的內心傾向,在重復評價同一對象可能產生有罪、重罪或重罰的結果時,司法機關極可能為了實現這一目標而不懈努力,這在一定程度上證實司法上的重復評價更為普遍。
三、禁止重復評價的判斷標準
禁止重復評價作為刑法評價具體犯罪的方法,理應同罪刑法定、罪刑均衡等原則自成體系脈絡,對評價具體犯罪發揮指引效用。如前所述,罪前、罪中與罪后事實作為評價對象,是評價具體犯罪的著眼點、突破口,犯罪構成是評價犯罪的唯一標準,評價對象與犯罪構成相勾連。同時,定罪與量刑是評價具體犯罪的兩大核心環節,定罪是基于定罪情節,量刑是憑借量刑情節,定罪和量刑情節隸屬于評價對象。由此觀之,落實案件中評價對象的歸屬是實現全面、準確評價的關鍵,有必要從評價對象入手,明晰評價具體犯罪應把握的要點,以樹立禁止重復評價的判斷標準。
(一)堅持每一個評價對象擁有唯一歸屬原則
所謂唯一歸屬,是指每一個評價對象都有自己的固定身份,要么是定罪情節,要么是量刑情節,不存在兩者兼備的情形。無論是罪前事實,還是罪中事實,抑或是罪后事實都僅具有唯一身份。
1.罪前事實是量刑情節
罪前事實是對行為人一貫表現的反映,品格證據等正向表現不納入罪前事實,而負向表現是罪前事實,如犯罪前科。犯罪前科僅充當量刑情節,無法認定為定罪情節。根據前罪與本罪的關聯度,犯罪前科包括與本罪無關的犯罪前科和與本罪有關聯的累犯兩種類型。普通的犯罪前科是酌定的從重處罰情節,⑨《刑法》第356 條:“因走私、販賣、運輸、制造、非法持有毒品罪被判過刑,又犯本節規定之罪的,從重處罰。”毒品犯罪的再犯包括普通的毒品再犯與毒品犯罪累犯,兩者是法定的從重處罰情節。而累犯是法定的從重處罰情節,兩者都是從重量刑情節。出于特殊預防目的,普通的犯罪前科和累犯作為量刑情節是既成事實,無可厚非。但是,將犯罪前科作為入罪門檻或降低入罪門檻的條件而被認定為定罪情節有待商榷。事實上,該情節是對已經被刑法否定的行為再次,是重復評價,且對行為人不利,應當禁止。
值得注意的是,行政處罰亦是對行為人平時表現的反映,但并非任何違法行為都可以評價為定罪或量刑情節,應著重考察其與本罪的關系,作出準確判斷。關于行政違法的角色定位,應關注如下問題:一是與本罪無關的違法行為被行政處罰后不得評價為本罪的定罪或量刑情節。與本罪無關的違法行為,是指行為人所實施的行為僅由行政法規制,無需動用刑法的情形。受過行政處理的違法行為表明行為人已經得到應有的懲罰,再次將受過行政處理作為入罪或降低入罪門檻的條件而評價為定罪情節是一種重復評價。二是與本罪有關的違法行為被行政處罰后能夠評價為本罪的定罪情節。與本罪有關的違法行為發生于法定犯的場合,行為人所實施的行為因具有雙重違法性而應受到行政與刑事雙重處罰。雖然行為人僅實施一行為,但該行為同時違背不同性質的法律,應受到雙重法律評價。即使行為受過行政處罰,也不妨礙將其視為定罪情節接受刑法的否定性評價。
2.罪中事實中符合犯罪成立條件的事實是定罪情節,其余事實是量刑情節
罪中事實對應的是構成要件要素,其包括齊備犯罪成立條件的事實和其他反映罪責程度的事實。對于滿足犯罪成立條件的事實,通常而言故意犯罪中表明犯罪主體、行為⑩行為不僅包括行為本身,也包括行為的狀況,如《刑法》第292 條聚眾斗毆罪中的“聚眾”就是對行為狀況的描述。、故意心態的事實;過失犯罪中展現犯罪主體、行為、結果、過失心態的事實,是定罪情節。對于構成要件要素中其他反映罪責大小的事實,與罪狀中關于情節嚴重程度、數額大小等表述相契合的事實是量刑情節。同時,共同犯罪、故意犯罪停止形態是修正的構成要件要素,屬于量刑情節。由此觀之,犯罪成立條件是對罪在“質”上的標準,而其他反映罪責大小的要素是對罪在“量”上的把控,“質”對應的是定罪,“量”對應的是量刑。
符合犯罪成立條件的事實是定罪情節,不得再次評價為量刑情節,其他反映罪責大小的事實是量刑情節,不得作為定罪情節。簡言之,構成要件要素對應的每一個事實只有一個身份,定罪情節與量刑情節不可兼而有之。舉例而言,國家工作人員的主體身份符合犯罪主體條件的情況下,無法再將其視為對行為人從重處罰的情節。鑒于此,評價時應注意如下內容:一是犯罪成立條件對應的事實是定罪情節,不得再次評價為量刑情節;二是犯罪成立條件以外的構成要件要素和共同犯罪、犯罪形態反映罪責大小的事實是量刑情節,不得重復評價為定罪情節;三是量刑情節內部不得重復評價。某一構成要件要素被評價為A 量刑情節后不得再次認定為B 量刑情節。例如,綁架罪包含“情節較輕”這一減輕的犯罪構成,在行為人主動釋放人質的場合,該事實屬于犯罪未遂,不得再將其解釋為“情節較輕”,否則,該事實被評價為兩個獨立的量刑情節,客觀上是重復評價。
3.罪后事實是量刑情節
罪后事實是反映行為人認罪悔罪態度的事實,表明行為人的罪后態度和立場。雖然罪后事實映射出行為人的罪責大小,但是其與罪中事實不同,不屬于構成要件要素無法影響定罪,卻影響到量刑,是量刑情節。通常而言,同一罪后事實不得同時評價為不同的量刑情節,即禁止將同一事實評價為A 量刑情節和B 量刑情節予以同時適用。
(二)允許有利于被告人的重復評價
有利于被告是刑事法治的基本理念,其在刑事程序法展現為存疑時有利于被告人原則,在刑事實體法體現為允許有利于被告人的類推解釋、從舊兼從輕的刑法溯及力原則和允許有利于被告人的重復評價。縱觀刑事立法,我國對類推解釋的態度歷經允許類推解釋——禁止一切類推解釋——允許有利于被告人的類推解釋三次轉變,該演變歷程表明刑法對類推解釋持有限度的容忍立場,以充分保障被告人權利。應當看到,準自首制度是允許有利于被告人的類推解釋的典型適例。一般自首的成立條件是自動投案和如實供述罪行,而準自首的成立條件是被采取強制措施后如實供述司法機關尚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與一般自首相比,準自首沒有自動投案而不成立自首,但為節約司法資源,將其類推解釋為自首,以鼓勵行為人如實供述罪行。同時,從舊兼從輕原則的通俗理解是:適用對被告人有利的法律,排除適用不利的法律。
禁止重復評價作為刑法評價準則同樣遵從有利于被告理念,其主張不得對同一事實進行多次不利于被告人的重復評價,但允許有利于被告人的重復評價,而非禁止一切重復評價。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以下簡稱“認罪認罰”)與自首、坦白等量刑情節并存情形下的重復評價是允許有利于被告人的重復評價之典型適例,不違背禁止重復評價原則。
1.司法實務禁止對認罪認罰與自首、坦白等量刑情節做重復評價的意見有待商榷
認罪認罰作為司法改革的制度成果被載入刑訴法,其與自首、坦白、退贓退賠等常見量刑情節相勾連,均體現對被告人的“寬”。在認罪認罰與上述量刑情節并存的場合,應如何評價,能否重復評價,儼然已成為司法實務關注的話題。禁止對認罪認罰與自首、坦白等量刑情節的重復評價是司法實務的明確態度。該立場展現于相關司法解釋:一是2019 年“兩高三部”《關于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2019 年《指導意見》)就認罪認罰與自首、坦白等量刑情節并存時如何從寬作出專門解釋,即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有自首、坦白情節,同時認罪認罰的,應當在法定刑幅度內給予相對更大的從寬幅度。認罪認罰與自首、坦白不作重復評價。二是2021 年“兩高”《關于常見犯罪的量刑指導意見(試行)》(以下簡稱《量刑指導意見》)再次重申對認罪認罰與自首、坦白等量刑情節并存的處理意見,認罪認罰與自首、坦白、當庭自愿認罪、退贓退賠、賠償諒解、刑事和解、羈押期間表現好等量刑情節不作重復評價。三是最高檢《人民檢察院辦理認罪認罰案件開展量刑建議工作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2021 年《指導意見》)亦做類似表述。
雖然司法實務旗幟鮮明地亮出自身立場,但研讀司法解釋發現認罪認罰與自首、坦白等量刑情節并存的處理意見與生成結論的過程不匹配,換言之,司法解釋的論證過程無法當然地得出禁止對認罪認罰與自首、坦白等量刑情節作重復評價的結論。具體而言,兩份《指導意見》形式上主張不得對認罪認罰與自首、坦白等情節予以重復評價,卻又強調認罪認罰與自首、坦白等情節并存時給予更大幅度的從寬,“更大”當然是相比于認罪認罰、自首、坦白等情節獨立出現且不并存的場合,“更大的從寬幅度”表明了可以同時評價的立場,這與不得重復評價的立場相矛盾,存在左右逢源之嫌。令人遺憾的是,《指導意見》尚未達致預期目標,反而讓實務部門更加迷茫,學者也不知其用意何在。此外,《量刑指導意見》的處理意見與《指導意見》相契合,但未能給予明確解釋。
2.基于有利于被告理念,應允許對認罪認罰和自首、坦白等情節進行重復評價
將認罪認罰視為法定量刑情節是探討認罪認罰與自首、坦白等情節并存處理意見的邏輯起點,這是罪刑法定的題中之意。認罪認罰作為司法改革的制度成果,要讓被告人享受到司法改革成果,僅依靠程序法的改革是無法實現的。定罪量刑的情節必須法定化即法典化是罪刑法定原則的題中之意。因此,僅根據刑訴法上的“認罪認罰從寬”不能直接決定對被告人最終可以從寬到何種程度,而必須相應地修改刑事實體法。?參見周光權:《論刑法與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銜接》,載《清華法學》2019 年第3 期。認罪認罰的法定化不僅彰顯了罪刑法定原則,還有助于實現從寬幅度的可操作性,為司法適用提供指引。然而,《刑法修正案(十一)》對認罪認罰只字未提,似乎默許了司法實務將其視為量刑情節的做法。考慮到認罪認罰與自首、坦白等情節并存的適用是擺在面前且無法回避的現實問題,為回應實際問題,理應提出應對路徑。
在認罪認罰與自首、坦白等從寬量刑情節并存的場合,根據有利于被告理念,應當同時適用,不違背禁止重復評價。理由如下:
第一,認罪認罰的“認罪”與自首、坦白存在質的差別,“認罪”是對犯罪事實與行為性質的雙重認可,而自首、坦白是對犯罪事實的如實供述。根據2019 年《指導意見》規定,認罪,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對指控的犯罪事實沒有異議。“認罪”與自首、坦白在成立條件上的“共性”是如實供述罪行。根據司法解釋規定,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是指如實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實和對定罪量刑有重要影響的身份信息,如姓名、年齡、職業、前科等。其中,“主要犯罪事實是指已供述的內容與刑法中具體犯罪的構成要件要素相對應的事實,主要犯罪事實的認定牽涉到犯罪構成理論,如果被告人供述的事實達致構成要件齊備的標準,應認定被告人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實;被告人的身份情況一般會影響到定罪量刑,涉及身份犯、累犯的認定等問題。”?劉環宇:《被告人辯解對自首制度中“如實供述”的影響》,載《江西警察學院學報》2018 年第5 期。由此觀之,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不等于“認罪”。
對行為性質的辯解關涉到“認罪”與自首、坦白的認定。對行為性質的辯解影響“認罪”,但不影響自首、坦白的認定。行為人的辯解是對犯罪事實或法律適用發表的意見,包括正當辯解與不正當辯解,對行為性質的辯解屬于正當辯解,而對客觀事實的歪曲、狡辯,如翻供是不正當辯解。?參見劉環宇:《被告人辯解對自首制度中“如實供述”的影響》,載《江西警察學院學報》2018 年第5 期。對行為性質的辯解無非是將有罪辯解為無罪或將重罪辯解為輕罪,是行使辯護權的表現。自首、坦白的如實供述是對客觀事實的描述,而認罪包括如實供述罪行與承認行為定性兩層內容。2019 年《指導意見》指出,承認指控的主要犯罪事實,僅對個別事實情節提出異議,或者雖然對行為性質提出辯解但表示接受司法機關認定意見的,不影響“認罪”的認定。但是,對行為性質的辯解與接受司法機關的認定意見是一種對立、排斥關系。對行為性質辯解但表示接受司法機關認定意見在不同階段有不同的表現形式,如審查起訴階段是對行為性質辯解但接受檢察院指控的罪名,審判階段是對行為性質辯解但認可法院認定的罪名。然而,實踐中對行為性質辯解但表示接受司法機關認定意見的情形是比較難把握的,畢竟對行為性質的辯解與司法機關的認定意見是對立的,對行為性質的辯解意味著對司法機關認定意見的否定,其與自首、坦白的如實供述罪行不同,超越了如實供述犯罪事實的客觀描述性已經具有價值判斷的色彩。由此觀之,認罪是行為人對行為定性的認可,呈現出價值判斷的“主觀性”,而如實供述罪行具有“客觀性”,其與認罪存在明顯差別。
第二,認罪認罰的“認罰”涵括退贓退賠等反映行為人悔罪態度的事實。退贓退賠等酌定量刑情節是“認罰”的表現形式。根據2019 年《指導意見》規定,“認罰”,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誠悔罪,愿意接受處罰。“認罰”考察的重點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悔罪態度和悔罪表現,應當結合退贓退賠、賠償損失、賠禮道歉等因素來考量。應當看到,退贓退賠、賠償損失是酌定從寬處罰情節,反映行為人的悔罪態度,是認罰的具體表現。
第三,雖然認罪認罰與自首、坦白、退贓退賠等量刑情節存在“共性”,但認罪認罰兼具實體與程序從寬效果。“其中‘實體從寬’主要是指控辯合意中的量刑減讓和刑事判決中的量刑從寬,‘程序從寬’主要是指強制措施的減緩適用。”?陳衛東:《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理論問題再探討》,載《環球法律評論》2020 年第2 期。如前所述,認罪認罰與自首、坦白的交集是如實供述罪行,差別在于前者不僅包括如實供述罪行,還有對司法機關對行為定性的認可。同時,退贓退賠、賠償損失等酌定從寬情節是認罰的主要表現形式。
綜上,在認罪認罰與自首、坦白、退贓退賠等量刑情節并存的場合,應同時適用,但從寬幅度應介于僅有認罪認罰、自首或坦白等情節與自首、坦白等情節和認罪認罰疊加適用之間。一方面,雖然認罪認罰與自首、坦白等存在交叉,但前者包括對量刑建議的認可和庭審程序的選擇,具有訴訟分流,節約司法資源的價值意義;另一方面,分別評價適用,給予行為人更多獲得感,有助于實現特殊預防與一般預防效果。?參見苗生明、周穎:《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適用的基本問題——〈關于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指導意見〉的理解與適用》,載《中國刑事法雜志》2019 年第6 期。認罪認罰與自首、坦白等從寬情節的疊加限制適用凸顯有利于被告人理念,是對寬容理念的貫徹,不違背禁止重復評價原則。
(三)遵從比例原則
比例原則是公法領域的重要原則。“比例原則是指在立法、司法與執法過程中對國家公權力與公民的基本權利之間的邊界劃分上起著指導與制約作用,并依據其自身的適當性、必要性與均衡性來判斷公權力運行是否合法、合理的準則”?姜濤:《追尋理性的罪刑模式:把比例原則植入刑法理論》,載《法律科學》2013 年第1 期。比例原則通俗易懂的解釋是,運行公權力的手段與所欲達致的目的應符合比例,避免對私權利造成不必要的損害,不得用大炮打小鳥。比例原則作為公法原則,也是刑法的“外部原則”,其旨在監督刑法的“內部原則”,以保證其合法運行。在評價具體行為時,堅守底線思維,秉持比例原則。在犯罪前科、一般累犯與毒品再犯并存的場合,堅持禁止重復評價原則的同時,還應遵從比例原則,避免對行為人的過度懲治。
1.由于犯罪前科、一般累犯與毒品再犯是對行為人再犯新罪的否定性評價,三者在處罰方向上保持一致,應堅持禁止重復評價原則,避免同時適用
第一,再犯制度是對行為人再次犯罪的“報復”,已被法定化、制度化,但是在多種再犯制度并存的場合,理應恪守比例原則,避免同時適用,不得“重上加重”。一般累犯、犯罪前科與毒品再犯將被評價過的前罪再次作為對后罪從重處罰的理由以實現特殊預防目的而獲得禁止重復評價原則的“豁免”,如果再將其適用于行為人,將導致其承擔不可承受之重,突破禁止重復評價原則的最后防線。
第二,一般累犯、犯罪前科與毒品再犯具有同質性,屬于從重量刑情節。犯罪前科是相較于新犯之罪的概念。一般累犯、毒品再犯與犯罪前科在處罰方向上具有同向性,即對新罪從重處罰,以凸顯對再次犯罪的有力打擊。在三者并存的場合,如果同時適用三者或其中兩者,行為人承擔的不利后果將超越其本應承擔的范疇,這與追求手段與目的相匹配的比例原則相背離。
2.在一般累犯、犯罪前科與毒品再犯并存的場合,應當優先適用毒品再犯
一般累犯、毒品再犯與犯罪前科是對行為人再次犯罪的積極回應與從嚴懲治。誠然,再犯制度因彰顯對已然之罪的報應和對未然之罪的預防而具有正當性,將前罪作為對新罪從重處罰的依據,這似乎是毋庸置疑的“真理”。但是,在一般累犯、犯罪前科與毒品再犯并存的場合,應當秉承比例原則,適用毒品再犯,排除一般累犯與犯罪前科的適用。理由如下:
第一,從刑法總則與分則的關系角度分析,毒品再犯是特別規定,應當優先適用。一般累犯、犯罪前科屬于總則規定,而毒品再犯是分則規定。“總則規定犯罪與刑罰(以及其他法律后果)的一般原則、原理,分則規定具體的犯罪及其法定刑。所以,總的來說,總則規定與分則規定大體上是一般與特殊、抽象與具體的關系。”?張明楷:《刑法分則的解釋原理》(第二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 年版,第109 頁。“因為總則是共通規定,所以,它一方面指導分則,另一方面也補充分則。由于分則是具體或特別規定,所以,它完全可能在總則要求之外另設特別或例外規定。”?同上注,第109-110 頁。關于再犯的處罰,刑法總則設定了累犯制度,分則創設了毒品再犯,毒品再犯更具“針對性”,其作為特別規定應優先適用于一般累犯和犯罪前科。
第二,從罪刑關系角度入手,應適用毒品再犯。再犯與一般累犯、毒品再犯之間是屬種關系,再犯是上位概念,而一般累犯、毒品再犯是下位概念,一般累犯與毒品再犯是交叉關系。當一般累犯、犯罪前科與毒品再犯競合時,應當優先適用毒品再犯的專門性、針對性規定,不再適用一般累犯或犯罪前科之規定。值得注意的是,根據司法解釋規定,累犯的從重幅度是增加基準刑的10%至40%,毒品再犯的從重幅度是增加基準刑的10%至30%,由此面臨的問題是:毒品再犯的從重幅度小于累犯的從重幅度,行為人適用毒品再犯受到的刑罰可能輕于適用一般累犯的刑罰。建議提升毒品再犯的從重量刑幅度,調整為增加基準刑的10%-50%,具體適用時,結合前后的罪名、刑種、刑度、間隔時間等因素,確定增加的基準刑,以實現罪刑匹配。
四、禁止重復評價的適用爭議問題及其解決
刑法對犯罪的評價體現在定罪和量刑兩個層面,禁止重復評價作為刑法評價準則也在定罪和量刑上發揮效用。但是,禁止重復評價的貫徹遵循存在諸多障礙,在具體適用中面臨困境。
(一)禁止重復評價原與定罪
禁止重復評價在定罪層面上的適用爭議集中體現在將罪前事實評價定罪情節,將犯罪前科、行政處罰(處分)作為入罪條件或者降低入罪門檻的條件。
1.行政處罰作為犯罪成立條件的重復評價
行政處罰累計次數作為犯罪成立條件是在定罪上重復評價的典型適例。涉及的罪名有:一是走私普通貨物、物品罪。行為人1 年內歷經兩次行政處罰是判定其新的走私行為成立犯罪的充分條件,這表明過往的走私行為在已經受到行政法否定性評價的同時,再次被“舊事重提”作為認定走私犯罪的條件,行為人過往的走私行為被重復評價。二是尋釁滋事罪。根據司法解釋規定,行為人因婚戀、家庭、鄰里、債務等糾紛而實施辱罵、毆打或毀損財物等行為,一般不認定為“尋釁滋事”,但在有關部門予以批評制止或處罰后,仍然實施上述行為的,構成尋釁滋事罪。簡言之,因該類糾紛而實施的行為成立尋釁滋事罪應同時滿足兩項條件:一是行為人因婚姻、家庭等糾紛引發沖突受過批評制止或處罰;二是行為人以同樣事由再次實施擾亂社會秩序的行為。“第一次”是行政違法,“第二次”因“第一次”的行政違法衍變為刑事犯罪,“第一次”被重復評價。三是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根據2021 年修訂的《關于審理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 條規定,1 年內曾因掩飾、隱瞞犯罪所得及其產生的收益受過行政處罰,又實施掩飾、隱瞞犯罪所得及其產生的收益行為的,構成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換言之,行為人因具有掩飾、隱瞞行為受過行政處罰是該罪的入罪條件,但是該行為已經受到法律評價,再次將其評價為入罪條件屬于重復評價。四是非法行醫罪。非法行醫罪采取“定性”即“未取得醫生執業資格的人非法行醫”+“定量”即“情節嚴重”的定罪模式。根據司法解釋規定,行為人因非法行醫受過兩次以上行政處罰后再次非法行醫的,屬于情節嚴重。非法行醫行為被行政處罰后再次作為“情節嚴重”的認定標準,這是對非法行醫行為的重復評價。
2.犯罪前科、行政處罰(處分)作為降低入罪門檻條件的重復評價
將犯罪前科、行政處罰(處分)作為降低入罪門檻條件的情形體現在財產犯罪和貪污罪之中。財產犯罪的盜竊罪、搶奪罪、敲詐勒索罪等采取“定性+定量”的定罪模式,即行為人實施特定行為+數額較大。司法解釋不僅明確“數額較大”的“普通標準”,也規定了“數額較大”的“特殊標準”,“特殊標準”對“普通標準”的“數額較大”予以變通,即相關犯罪前科或行政處罰+犯罪數額為“數額較大”的50%=“數額較大”。該變通規定表明行為人過往的違法犯罪行為被重復評價,第一次是違法或者犯罪行為受到行政或者刑事處罰,第二次是處罰經歷成為新罪的入罪條件。同時,貪污罪入罪條件也存在重復評價的問題。司法解釋明確了“數額較大”“其他較重情節”的認定標準,“其他較重情節”對“數額較大”予以修正,其中貪污數額在1 萬元以上不滿3 萬元,并且曾因貪污、受賄、挪用公款受過黨紀、行政處分或者曾因故意犯罪受過刑事追究的,屬于“其他較重情節”。簡言之,其他較重情節=貪污數額1 萬元以上不滿3 萬元+犯罪前科/受到相關行政、黨紀處分。犯罪前科、行政或黨紀處分對貪污罪的認定起到“功不可沒”的效果,但該認定標準違背了禁止重復評價。
因此,司法解釋將犯罪前科、行政處罰(處分)作為犯罪成立條件或降低入罪門檻的條件是對已經受到否定評價的違法犯罪行為的重復評價。鑒于行為人已經為自己的錯誤埋單,再次將過錯評價為入罪條件則有失公允,與禁止重復評價原則背道而馳。
(二)禁止重復評價與量刑
禁止重復評價原則在量刑層面上的重復評價集中體現在將符合犯罪成立條件的事實評價為量刑情節。
1.齊備犯罪成立條件的事實被評價為加重法定刑依據的重復評價
禁止重復評價強調某一事實被評價為定罪情節后不得再次評價為量刑情節,因此,在某一事實已被評價為基本犯罪構成事實的情況下,其不得再次評價為量刑情節。例如,交通肇事罪的“逃逸”被評價為基本犯罪構成事實后,不得再次作為加重法定刑的依據,不得對行為人適用第二檔法定刑。具體而言,交通肇事罪包含三檔法定刑,基本法定刑、第二檔法定刑(逃逸或有其他特別惡劣情節)和第三檔法定刑(逃逸致人死亡)。交通肇事罪的基本犯罪構成包括三種情形:一是負事故全部或主要責任,致一人死亡、三人以上重傷或者無能賠償數額在30 萬元以上;二是負事故同等責任,致三人以上死亡;三是致一人以上重傷,負事故全部或主要責任,并符合司法解釋規定的特定情形。?司法解釋規定了六種情形:(一)酒后、吸食毒品后駕駛機動車輛的;(二)無駕駛資格駕駛機動車輛的;(三)明知是安全裝置不全或者安全機件失靈的機動車輛而駕駛的;(四)明知是無牌證或者已報廢的機動車輛而駕駛的;(五)嚴重超載駕駛的;(六)為逃避法律追究逃離事故現場的。“逃逸”是司法解釋列羅的特定情形。?本文的“逃逸”限定于為逃避法律追究逃離事故現場的行為,而不包括基于其他原因逃離事故現場的行為。應當看到,“逃逸”不僅關涉到交通肇事罪的認定,也事關法定刑的選擇,其有時充當定罪情節,有時作為量刑情節。何時評價為定罪情節,何時評價為量刑情節,是司法實務面臨的難點和痛點。
在交通肇事后致一人重傷,負事故全部或主要責任,逃逸致人死亡的場合,21因逃逸致人死亡包括兩種情形:一是被害人因行為人逃逸得不到救助而死亡;二是被害人被第三人碾壓致死。司法實務對于法定刑的選擇無法達成一致意見。研讀相關判例,適用第三檔法定刑(因逃逸致人死亡)作為司法實務的一種處理意見受到學界的質疑與批評。雖然學界對司法實務的處斷意見不予認可,但內部也無法達成共識。一種觀點主張,“具體就被害人因行為人逃逸而被第三人碾壓死亡的情形而言,滿足交通肇事罪基本定罪標準的結果只有一個,即被害人的死亡。按照對一個死亡結果只能作一次刑法評價的原則,在該死亡結果已作為基本犯罪成立結果予以刑法評價后,上述情形其實屬于交通肇事罪的情節加重犯,即在構成交通肇事罪的基本犯罪的基礎上,符合刑法第133 條第2 段‘交通運輸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惡劣情節的’情節加重構成。”22田宏杰:《認定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具體情形要素》,載《檢察日報》2019 年1 月11 日,第3 版。另一種觀點認為,無論是被害人因逃逸得不到及時救助死亡還是被第三人碾壓致死,逃逸行為與死亡結果之間存在直接的因果關系,逃逸行為與死亡結果是無法割裂的,因此,應當將逃逸行為與死亡結果予以整體評價,符合交通肇事罪的基本構成要件,同時考慮到死亡結果,在基本法定刑幅度內從重處罰。23參見姜濤:《“交通肇事后逃逸加重處罰”的合憲性思考》,載《比較研究》2019 年第2 期;李會彬:《“因逃逸致人死亡”情節的獨立性解讀》,載《政治與法律》2014 年第8 期。值得注意的是,學界關于加重法定刑的適用以成立交通肇事罪的基本犯為基礎能夠達成默契,但對于逃逸與死亡關系的認識存有差異。
在交通肇事致一人重傷,負事故全部或主要責任,逃逸致人死亡的情境下,符合交通肇事罪的基本犯,考慮到死亡結果,在基本法定刑內從重處罰。逃逸的“身份定性”是爭議焦點。司法實務的認定邏輯是:首先判斷行為人符合交通肇事罪的基本犯,然后再評價“逃逸”,適用第二檔法定刑。司法實務將逃逸行為與死亡結果予以割裂,分開解釋。然而,加重法定刑的適用理當以符合交通肇事罪的基本犯為前提。司法解釋是對此意見的極好佐證,2000 年《關于審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3 條:“‘交通運輸肇事后逃逸’,是指行為人具有本解釋第二條第一款規定和第二款第(一)至(五)項規定的情形之一,在發生交通事故后,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為。”該條是對交通肇事罪加重罪狀(交通運輸肇事后逃逸)的解釋,闡明了加重法定刑的適用以符合交通肇事罪的基本犯為前提。對于司法實務的處理意見,“逃逸”同時評價為定罪情節與量刑情節,是對同一事實的重復評價,違背禁止重復評價原則,導致行為人承擔更重的不利后果。對于學界的認定意見,雖然能夠對加重法定刑的適用以成立基本犯為前提達成共識,但對于逃逸與死亡的關系仍有待理清。無論是逃逸導致被害人得不到救助而死亡還是被第三人碾壓致死,逃逸與死亡結果之間都存在必然的因果關系,應將逃逸與死亡結果視為一個整體,不能人為地將其割裂開來,將死亡結果充實為基本構成要件,逃逸充當加重構成要件,適用第二檔法定刑。相反,應當將逃逸與死亡視為整體,符合基本犯罪構成,考慮到死亡結果,在基本法定刑內從重處罰,該處理意見既規避對“逃逸”的重復評價,又實現對犯罪事實的充分評價,體現了罰當其罪。
2.犯罪成立的伴隨條件被同時評價為加重法定刑依據的重復評價
既然符合犯罪成立條件的事實已被評價為定罪情節,那么犯罪成立條件的伴隨條件因具有“附隨性”“依附性”也不得被評價為加重法定刑依據。其中,轉化型搶劫罪的“入戶”“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是基本犯罪構成事實伴隨條件的典型適例,不得將其視為加重量刑情節。詳言之,根據《刑法》第269 條規定,轉化型搶劫罪包含前行為、后行為與目的要素三個要件,前行為是行為人實施盜竊、詐騙或搶奪行為;后行為是行為人當場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脅;目的要素是為了窩藏贓物、抗拒抓捕或毀滅罪證。轉化型搶劫罪同普通搶劫罪一樣,包含基本犯與加重犯。然而,司法解釋將入戶或在公共交通工具上盜竊、詐騙或搶奪后,為了窩藏贓物、抗拒抓捕或者毀滅罪證,在戶內或者公共交通工具上當場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的行為認定為搶劫罪的加重犯有待商榷。該意見將“入戶”“在公共交通工具上”被評價為定罪情節的同時,又被評價為量刑情節,違背禁止重復評價原則。實際上,“入戶”“在公共交通上”作為前行為的伴隨狀態,不應再被評價為加重的量刑情節。理由如下:
第一,從應然層面分析,窩藏贓物、抗拒抓捕或毀滅罪證是行為人犯罪后的本能反應,刑法將其視為構成要件有違常理。刑法對于護贓行為設定了專有罪名,即洗錢罪與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犯罪主體是本犯以外的人,而洗錢罪的犯罪主體隨著刑法修正案的修訂拓展至上游犯罪本犯,卻與不可罰的事后行為之理論基礎相背離。如前所述,護贓行為是行為人罪后的本能反應,刑法加以懲治是對人類本能的否認,有違常理。實際上,刑法規制護贓行為已經超出國民的可預測范疇。
第二,從實然層面分析,將“入戶”“在公共交通工具上”評價為轉化型搶劫罪的加重情節是一種重復評價,違背禁止重復評價原則。按照司法解釋的認定意見,“入戶”“在公共交通上”被評價兩次:一是“入戶”“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是定罪情節。前行為發生在戶內或在交通工具上,“入戶”“在交通公共上”是前行為的便隨狀態;二是“入戶”“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是量刑情節。行為人在戶內或交通工具上實施后行為認定為搶劫罪的加重情節。應當看到,“入戶”“在公共交通工具上”作為前行為的伴隨狀態已經被評價為定罪情節,雖然后行為也發生在戶內或交通工具上,但這是對伴隨狀態的延續,沒有必要再次評價為加重量刑情節。一方面,將“入戶”“在公共交通工具上”評價為定罪情節,不存在前行為的“入戶”“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和后行為“在戶內”“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沒有被評價的問題。另一方面,將其再次評價為量刑情節有違罪刑均衡原則。轉化型搶劫罪與普通搶劫罪相比,前者是先取財后實施暴力或暴力威脅,后者相反,前者的取財手段比后者平和。“入戶”“在公共交通工具上”轉化型搶劫與“入戶”“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搶劫相比,前者的社會危害性小于后者,因此,將前者與后者“同等對待”是有失公允,將“入戶”“在交通公共工具上”同時評價為定罪、量刑情節超越了罪刑均衡原則的容忍限度。
第三,轉化型搶劫罪是一種法律擬制,實質上是對行為人權利的限制和抑制。如果刑法沒有設定轉化型搶劫罪,行為人盜竊、詐騙或搶奪后,為窩藏贓物、抗拒抓捕或者毀滅罪證而當場使用暴力致輕傷以上后果的,構成盜竊、詐騙或搶奪罪與故意傷害罪,數罪并罰。然而,刑法將其認定為轉化型搶劫罪,這屬于法律擬制。誠如,法律是“由國家專門機關創制的,以權利義務為調整機制并通過國家強制力保證的調整行為關系的規范,它是意志與規律的結合,是階級統治和社會管理的手段,它是通過利益調整從而實現某種社會目標的工具”。24張文顯主編:《法理學》(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07 年版,第102 頁。轉化型搶劫罪的創設凸顯刑法從嚴懲治盜竊、詐騙或搶奪后為窩藏贓物、毀滅罪證或者抗拒抓捕實施暴力或暴力威脅的行為以充分維護被害人人身、財產安全之立法旨趣。
既然刑法設定轉化型搶劫罪已是對行為人的不利影響,那么在具體適用中應恪守審慎態度,特別是對搶劫罪加重犯的認定更應慎之又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