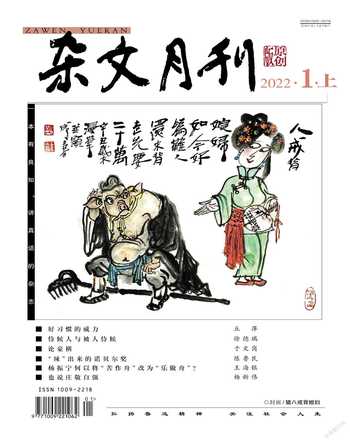大師亦怕“后生笑”
沈棲
自不待言,世人普遍敬重、仰慕大師,是因為他們在各自的領域高屋建瓴,別樹一幟,以思想前衛、見識超群、格局創新而被樹為一個時代的界碑彪炳于史冊。我認為還有一個理由就是大師的人格魅力,其為人謙恭,虛懷若谷,求真務實,不媚權勢,臣服真理,將畢生精力和智慧貢獻給自己心儀的事業,當是令人肅然起敬!
大師的斐然實績不止是影響他所在的年代,還將遺澤于后世。有鑒于此,大師生前往往很注重自己產下的“寧馨兒”,不使瑕疵誤人,不以訛謬禍世。北宋古文運動的代表歐陽修,名列“唐宋八大家”和“千古文章四大家”,其散文創作的卓然成就與其革新的古文理論相輔相成,從而開創了一代文風。據明代何良俊所撰《四友齋叢說》記載:歐陽修晚年竄定生平所有文章時,逐字逐句地改,且一改再改,改了又改,堪為“一絲不茍”。其間,他還常常是擱一擱,等一等,讓時間過濾一陣子,檢驗之后再拿出來重改,不厭其煩。其夫人勸止:“何自苦如此,尚畏先生嗔耶?”答曰:“不畏先生嗔,卻怕后生笑。”畏懼先生嗔怒,顧及的僅是一時的個人面子;而生怕后人恥笑,則是擔心誤人子弟、遺毒后世。高度的責任感和事業心驅使這位文學大師暮年依然精益求精,謹慎為文。
無論哪個知識領域,大師們都是矢志不渝地孜孜追求兩個字:真理,通過自己頑強的意志和不懈的心力日臻“必然王國進入自由王國”的完美境界。尤其是科學研究,其結果并不存在絕對的真理,糾錯則是科學界的常態;唯有糾錯才不會導致“后生笑”。裘錫圭研究了60多年的古文字學,是公認的當代考古領域的泰斗,但他生怕“后生笑”而坦然認錯、決然改錯。位于山西省臨汾市翼城縣的大河口西周墓地從2009年開始考古挖掘,發現墓葬615座、車馬坑22座,首次發現西周時期三足銅盂等珍稀古物,被列入“2010年中國十大考古新發現”。裘錫圭在2012年第三期《中國史研究》雜志上發表了論文《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出土鳥形盉銘文解釋》,對出土盉銘逐句加以解讀。其中有一個“笰”字,裘錫圭認為是“并”之異體字。時隔6年,《考古學報》公布了大河口西周墓地隨葬青銅器的全部資料。根據這些發表的照片和拓本細審,裘錫圭驚詫不已,原來那個字確實應該解釋為“笰”(古代車廂后面的遮蔽物),而非原先推斷的“并”字變體。僅僅是區區一個瑕疵,裘錫圭卻來了個“小題大做”:他在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官網刊出《大河口西周墓地2002號出土鳥形盉銘文解釋》,慎重宣布自己2012年發表的那篇論文“所論全誤”,“拙文可謂毫無是處,自應作廢,以后編文集也不收入”。在國內外享有崇高聲譽的裘錫圭忌憚“后生笑”而徹底推翻自己以往的斷論,委實難能可貴,彰顯出“高逸學者之風”。
倘若不被“后生笑”,任何科學結論或學術定論都亟待經受歷史的考問和實踐的檢驗。其邏輯前提是必須摒棄“唯我獨尊”的思維,除了以平等的姿態相互切磋外,還得營造質疑、討論、批評的氛圍。大師們亦然。誠如薩義德在《知識分子論》一書中所說:“批評必須把自己設想成為了提升生命。”這里不妨說說張中行。這位大師在20世紀末給《文匯報·筆會》撰文,認為生在亂世的知識分子,除了效忠一君,君敗亡則竭力致死和滅跡山林之外,可以走馮道的第三條路。黃裳旋即在“筆會”撰文批評,并以汪精衛和錢謙益在家國危亡之際的表現,說明走第三條路的危害性。面對如此言辭激勵的批評,張中行并沒有勃然大怒,予以反駁,而是在認真反思后,給“筆會”編輯致函:“拙作確有不妥處,年來老境頹唐,丟三落四,以致立論時只顧及原其不殉節,而說得偏激片面”,檢討自己“失誤很多而成就很少,人視為失誤,正是言必有中,心是不會不安然的”,并要求編輯公開發表此函。黃裳和張中行,乃是大師邂逅大師——一方是提升生命式的批評,一方是懷揣生命被提升的意識來接受批評。這無疑是對“批評”一詞的完美詮釋。
大師亦怕“后生笑”,那么后生呢,當以這些高風亮節的大師為楷模。
童玲/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