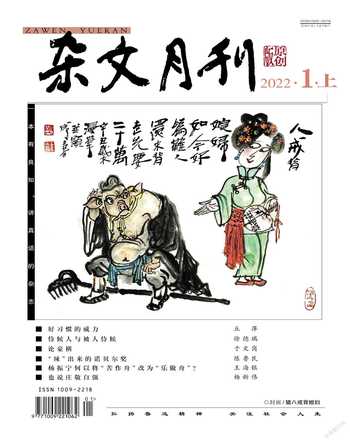打發無聊的三六九等
陳慶貴
世事皆分三六九等,打發無聊亦然。面對無聊,沒有能躲過之人,只有打發等次差異。
叔本華說:“人生永遠就在痛苦和無聊之間搖擺。”既然生活原點要么痛苦要么無聊,那么本初問題來了,無聊到底是個什么東西?朱生豪如是描述性狀:“是一種無事可做,即有事而不想做,一切都懶,然而又不能懶到忘懷一切,心里什么都不想,而總在想著些不知道什么的什么,那樣的感覺。”究竟該當如何打發無聊?全民手機時代,打發方式“趙錢孫李,各有所喜”。多數人選擇刷視頻、看公號、打網游、粉愛豆、蹭飯局……但也有人另辟蹊徑,或趙師秀式“有約不來過夜半,閑敲棋子落燈花”,或祝允明式“日斜睡起無聊甚,獨倚闌干看樹陰”,或朱自清式“一個人在這蒼茫的月下,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然而,人活著可以不追問意義,但不可以放任無聊如死水;人生本無無聊之事,只有無聊靈魂。確如托爾斯泰洞悉:“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無聊給人帶來“幸福”抑或“不幸”,完全取決于打發無聊方式的等次。
設若把創造視為幸福的話,無聊也能給人帶來幸福。美國有研究發現,無聊可以激發個體生產力和創造力。實驗表明,相較于最初完成有趣手藝活動的同齡人,經歷過無聊任務(將一碗豆子按顏色逐一進行分類)者,在之后創意任務上表現更佳,后者數量質量均超前者。問題在于,從打發無聊中收獲創造力福利,并非“天上掉餡餅”;無聊之福利,只垂青有準備的智者。
英國心理學家研究認為,無聊的本質是“尋找神經刺激未果”。無聊可讓大腦游蕩做白日夢,從而產生創造力和解決力。做白日夢可以“暫時舒緩一下”,讓人從繁瑣生活中暫時解脫出來,但前提是遠離屏幕、工作和其他壓力來源,直至感到無聊才會有益。別讓“太忙了”“沒時間”成為托詞,學會從冗務中按下“暫停鍵”,為大腦“格式化”,既堪稱打發無聊的上等能力,又可謂從無聊中收獲意外福利的充要條件。
無聊不等于刻意放松。像瑜伽或冥想類刻意保持平靜的活動,并不符合“尋找刺激未果”定義。體驗真正的無聊,需要選擇一種不需事先刻意規劃和全神貫注的活動。比如關閉手機和電子產品,走一條自己熟悉的路線,或去泳池游上幾圈或閉目養神,反正只需讓大腦游蕩,讓音樂或刺激走開。現實矛盾在于,這廂,當下眾生對手機欲罷不能,既破壞了感知和享用無聊的能力,又無法從被手機綁架中帶來歡娛;那廂,趨之若鶩甘愿被社會流俗裹挾,介入過度社交應酬泥沼不能自拔,覬覦以群體無聊排解打發個體無聊,結果殊途同歸在“拿無聊當放縱”中娛樂至死。殊不知,烏合之眾非但無從享用無聊帶來的衍生福利,反而會讓打發無聊者打發無聊后,陷入越發無聊的深淵和持續無聊的苦海。
下等無聊,莫過于把無聊的事干得一本正經。比如,有一類既無生計之虞又非職務行為的“大V”,動輒“語不驚人死不休”嘩眾取寵,或烹制“深度好文”販賣毒雞湯麻醉受眾,或炮制“震驚體”雜碎博人眼球,或打“跪求體”“哭暈體”“嚇尿體”雞血謀求“精神勝利”,或有熱點必蹭,施放“大棋論”“陰謀論”信息霧霾妖言惑眾……再比如,張天翼筆下那個華威先生,擔任著十來個空銜,此公從來不干正經事,卻整天忙于酒肉應酬拉攏關系,參加會議總是遲到早退,開會時借口還要去參加另外的會,隨時打斷主席報告站起來胡侃,空洞說教讓人不勝其煩。“無聊大V”與“官痞混混”均屬人格分裂病人,他們同病相憐內心痛苦卻又樂此不疲。不幸的是,他們不是沒有能力把自己從蠅營狗茍中解脫出來,做一回白日夢打發無聊“暫時舒緩一下”,而是喪失了感知真正無聊的能力和享用無聊福利的興趣。
周國平在《在無趣的時代活得有趣》中開示:“人不僅僅屬于時代。無論時代怎樣,沒有人必須為了利益而放棄自己的趣味。”王小波啟蒙:“我看到一個無趣的世界,但是有趣在混沌中存在,我要做的就是把它講出來。”無聊是一種心靈自由,打發無聊就是享用心靈自由;無聊也是一種人生大趣,享用無聊就是消費人生大趣;無聊更是一種靈感胚胎,打開無聊就是孕育生命意義。人生苦短,打發無聊這檔事兒,還真不該不當回事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