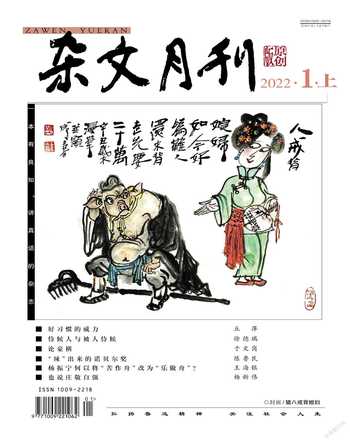君之趣好
嚴(yán)陽
公元前89年,漢武帝在石閭山祭祀地神并接見群臣時說:“朕自即位以來,干了很多狂妄悖謬之事,使天下人愁苦,朕后悔莫及。從今以后,凡是傷害百姓、浪費(fèi)天下財力的事,一律廢止!”田千秋說:“很多方士都在談?wù)撋裣芍拢瑓s都沒有什么明顯的功效,我請求皇上將他們一律罷斥遣散。”漢武帝說:“大鴻臚說得對。”于是將等候神仙降臨的方士們?nèi)壳采ⅰ#ㄋ抉R光《資治通鑒·漢紀(jì)·漢紀(jì)十四》)
在漢武帝當(dāng)著群臣的面所做的自我檢討里,提到的“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之事,當(dāng)然不是一件兩件,而是很多很多。這些事,都包括哪些?至少應(yīng)該包括窮兵黷武,向四夷頻繁用兵,在耗盡了國家財政的同時,給無數(shù)家庭帶來的悲劇;還包括他經(jīng)常巡幸,屢次到泰山封禪,以及對于尋求不死之藥的無限迷戀;等等。而從此之后,漢武帝不再派兵出征,并封田千秋為富民侯,任命他為丞相,以表示他要使百姓休息,希望能增加財富,養(yǎng)育百姓。他還任命趙過為搜粟都尉——趙過精通輪耕保持地力的代田之法,在土地耕耘技術(shù)和農(nóng)具制造方面都有改良。趙過傳授這些技巧給老百姓,使老百姓用力少而收獲多。
有感于漢武帝晚年這些的思維與具體做法上的變化,司馬光感嘆道:天下信(果真、果然)未嘗(未必)無士也!武帝好四夷之功,而勇銳輕死之士充滿朝廷,辟土廣地,無不如意。及后息民重農(nóng),而趙過之儔(等)教民耕耘,民亦被(享受)其利。此一君之身趣好殊別(迥然不同),而士輒應(yīng)之,誠使武帝兼三王(夏禹、商湯、周文王)之量(氣度)以興(復(fù)興)商、周之治(太平盛世),其(難道)無三代(夏、商、周)之臣乎!
我們都知道,司馬光可不僅是《資治通鑒》的主編,他還是歷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官至尚書左仆射兼門下侍郎(地位相當(dāng)于首相)的著名政治家。所以,他編《資治通鑒》的目的可絕不僅僅是為了記錄歷史,更加重要的目的則是以史為鑒,為后代帝王提供治國理政的參考。因此,對于漢武帝這位建樹甚多、在中國歷史上居有重要地位的人物,在他看來,功績固然多多,但可反思與批判的東西也不少。尤其是他個人的某些“趣好”,因?yàn)閷τ趪摇τ诎傩债a(chǎn)生了巨大的負(fù)面影響,讓他痛心疾首,所以,他有意不強(qiáng)調(diào),以使后來者引以為戒。
在這里,司馬光“一君之身趣好殊別,而士輒應(yīng)之”,給人留下的印象特別深刻:不正是因?yàn)闈h武帝早年特喜歡對四夷用兵,所以,他的身邊才集聚了如李廣、衛(wèi)青、霍去病這些軍事人才?不正是他因?yàn)槭置孕牛瑢τ谏裣伞⑴钊R、不死之藥無限向往,所以,李少君、齊少翁等方士方才趨之若鶩,緊緊圍繞在他身邊,并把他騙得團(tuán)團(tuán)轉(zhuǎn)?而當(dāng)晚年漢武帝忽然夢醒,意識到從前很多做法的荒唐與可笑,作出了改變,開始重視民生,那么,如田千秋、趙過等治國之才,則出現(xiàn)在他身邊。所有這些,是不是足以證明做國君的“趣好”,對于“士人”的巨大影響力?
上有所好,下必投之。作為一國之君,對于國家的前途和命運(yùn),對于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具有十分重大的影響,所以,國君的“趣好”絕不僅僅是國君個人的事兒,因此,必須慎之又慎。而我們能夠想象的是,假如漢武帝不是在他去世前兩年,方才大夢醒來,而是更早一些就能意識到對于一個國家、對于這個國家的老百姓來說,更重要的是什么,那么,漢武帝可能是一個更偉大的歷史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