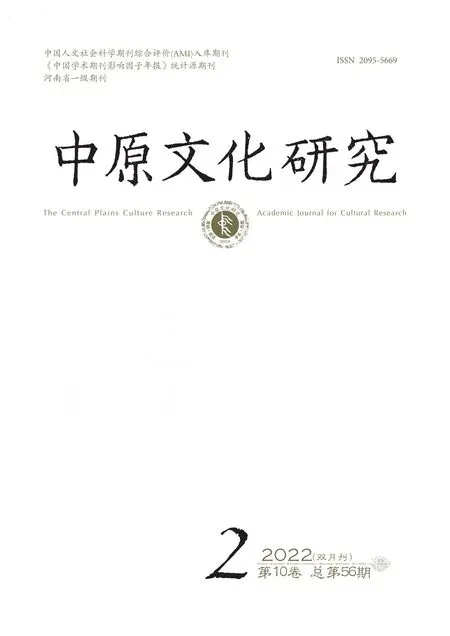漢代在文章樣式重大主題方面確立的范型
李炳海
漢代是中國(guó)古代歷史的輝煌期。漢承秦制,建立了以郡縣制為基礎(chǔ)的大一統(tǒng)封建帝國(guó)。這種體制在中國(guó)古代延續(xù)兩千余年,是一筆重要的歷史遺產(chǎn)。漢代文學(xué)在中國(guó)古代也具有垂范后世的作用,處于重要的歷史地位。對(duì)某段歷史進(jìn)行評(píng)價(jià),既要考察它做了哪些事情,更要考察它提供了哪些前代未曾有過(guò)的有價(jià)值的東西。漢代文學(xué)的歷史貢獻(xiàn)體現(xiàn)在多個(gè)方面,其中包括對(duì)一系列文學(xué)范型的確立。通過(guò)對(duì)漢代所確立的文學(xué)范型的考察,可以從一個(gè)側(cè)面透視漢代文學(xué)的歷史地位,即它在繼承先秦文學(xué)的基礎(chǔ)上又有哪些超越,這些超越又如何垂范后世。漢代對(duì)文學(xué)范型的確立是全方位的,可以劃分為多個(gè)系列,下面主要從文章樣式、重大主題兩個(gè)維度切入,探討漢代文學(xué)所確立的幾個(gè)范型。
一、文章形態(tài)的凝結(jié)固化
漢代文學(xué)確立范型有些體現(xiàn)在文章形態(tài)方面,許多文章的形態(tài)在漢代進(jìn)入穩(wěn)定階段,是文體的凝結(jié)固化時(shí)期。
漢代的主要文類是賦,章學(xué)誠(chéng)在追溯漢賦源頭時(shí)寫道:
古之賦家者流,原本詩(shī)騷,出入戰(zhàn)國(guó)諸子。假設(shè)問(wèn)對(duì),莊列寓言之遺也。恢廓聲勢(shì),蘇張縱橫之體也。排比諧隱,韓非《諸說(shuō)》之屬也。征材聚事,《呂覽》類輯之義也。[1]1064
章氏所持的賦類文章多源論的理念,其說(shuō)可取。需要進(jìn)一步探討的是戰(zhàn)國(guó)有些文類如何在漢代定型,中間經(jīng)歷了哪些轉(zhuǎn)換方式。
(一)設(shè)辭:從無(wú)韻無(wú)題的短章到有韻有題之鴻文
漢代確立的重要文體形態(tài)是設(shè)辭。這類文章采用的是主客問(wèn)答的方式,抑客而揚(yáng)主。東方朔的《答客難》、揚(yáng)雄的《解嘲》《解難》、班固的《答賓戲》、張衡的《應(yīng)間》、蔡邕的《釋誨》,均是屬于這個(gè)系列的文章,文體形態(tài)基本相同,已經(jīng)形成固定的模式。漢代設(shè)辭類文章的直接源頭,可以追溯到以宋玉為主角的兩篇對(duì)話文章,均收錄在劉向所編的《新序》一書中。第一篇文章是“楚威王問(wèn)于宋玉”[2]25,第二篇是“宋玉事楚襄王而不見(jiàn)察”[2]170-171。《文選》卷四十五收錄上述第一篇文章,標(biāo)題是《宋玉對(duì)楚王問(wèn)》,楚威王,作楚襄王,應(yīng)作襄王。如果把漢代設(shè)辭與《新序》所載以宋玉為主角的主客問(wèn)答體文章相對(duì)比,會(huì)發(fā)現(xiàn)三方面差異。第一,《新序》所收錄的與宋玉相關(guān)的兩篇文章,原來(lái)均無(wú)標(biāo)題,至于第一篇文章稱為《宋玉對(duì)楚王問(wèn)》,是《文選》編者所追加,或稱為《郢中對(duì)》,題目亦是后人所追加。漢代設(shè)辭則是各篇均有標(biāo)題,而且文題與文意相契,顯然是精心設(shè)計(jì)的結(jié)果。第二,《新序》所收錄的以宋玉為主角的問(wèn)答體文章是兩則故事,篇幅短小,而漢代的設(shè)辭則洋洋灑灑,長(zhǎng)篇大論,屬于巨制鴻文。第三,以宋玉為主角的兩篇文章是無(wú)韻之文,而漢代設(shè)辭則追求聲韻的和諧,往往句尾用韻,還有運(yùn)用五言韻語(yǔ)的段落。由此可見(jiàn),漢代文人是在以宋玉為主角的問(wèn)答體文章為基礎(chǔ),作了三方面的增益,從而形成設(shè)辭體系列,并且最終定型。《駢體文鈔》卷二十八收錄的漢代以后設(shè)辭體文章,有晉束皙的《玄居釋》、皇甫謐的《釋勸論》、夏侯湛的《抵疑》,采用的均是漢代設(shè)辭的體式[3]559-567。
(二)九體:從章無(wú)標(biāo)題到章末綴目
漢代騷體賦有九體,傳世文獻(xiàn)能夠見(jiàn)到的最早的九體文章是王褒的《九懷》。全文共九段,每段末尾都綴以標(biāo)題,依次是匡機(jī)、通路、危俊、昭世、尊嘉、蓄英、思忠、陶壅、株昭。繼《九懷》之后,劉向有《九嘆》、王逸有《九思》,所采用的體式與《九懷》相同。九體作為騷體賦的一種樣式,它的形態(tài)范型在漢代已經(jīng)確立。
提到九體,人們自然首先聯(lián)想到篇名冠以九字的戰(zhàn)國(guó)楚辭類文章,通常都從那里追尋九體的源頭。屈原所作的《九歌》系組詩(shī),共十一篇作品,詩(shī)篇的數(shù)量與組詩(shī)的名稱不相一致。屈原的《九章》也是組詩(shī),雖然詩(shī)篇的數(shù)量與組詩(shī)名稱相符,但是,各首詩(shī)獨(dú)立成篇,無(wú)法組合成一篇文章。宋玉的《九辯》在體式上與漢代的九體最為接近,朱熹把它劃分為九段[4]119-131,其說(shuō)可取。然而,《九辯》各個(gè)段落均無(wú)標(biāo)題,如果加上標(biāo)題,就與漢代九體的樣式不存在差異了。漢代九體樣式的直接源頭確實(shí)是《九辯》,它是在《九辯》的基礎(chǔ)上各段綴以標(biāo)題,從而確定了九體樣態(tài)的范型。
(三)七體:從變量到常數(shù)
枚乘所作《七發(fā)》是漢代散體賦的奠基之作,李兆洛稱它:“楚人之遺則,源亦從《招魂》,《大招》出耳。”[3]569這是把《七發(fā)》的源頭追溯到戰(zhàn)國(guó)楚辭的《招魂》《大招》。魯迅先生亦稱:“然乘于文林,業(yè)績(jī)之偉,乃在略依《楚辭》、《七諫》之法,并取《招魂》、《大招》之意,自造《七發(fā)》。”[5]53把《七發(fā)》的源頭追溯到《招魂》《大招》,確實(shí)有其道理,因?yàn)檫@三篇文章都是列舉多種美好事物進(jìn)行誘導(dǎo)。《招魂》《大招》是誘導(dǎo)游魂返回故土,而《七發(fā)》則是吳客對(duì)楚太子進(jìn)行誘導(dǎo)。不過(guò),如果對(duì)三篇文章用以進(jìn)行誘導(dǎo)的美好事物按照種類進(jìn)行量化統(tǒng)計(jì),會(huì)發(fā)現(xiàn)它們之間存在的差異。《招魂》用以誘導(dǎo)游魂歸來(lái)的美好事物共有三大類,即居處之樂(lè)、美食之樂(lè)、女樂(lè)游戲之樂(lè)。在鋪陳居處之樂(lè)的前邊一個(gè)段落,敘述的是進(jìn)行招魂的方式,與后邊三個(gè)板塊出現(xiàn)的欲望對(duì)象的美好事物不屬于同類,因此,《招魂》用于誘導(dǎo)游魂歸來(lái)的美好事物是三大類。《大招》列舉美好事物呼喚游魂歸來(lái),首個(gè)段落如下:“魂魄歸來(lái)!閑以靜只。自恣荊楚,安以定只。逞志究欲,心意安只。窮身永樂(lè),年壽延只。魂乎歸來(lái)!樂(lè)不可言只。”王逸注:“言居于楚國(guó),窮身長(zhǎng)樂(lè),保延年壽,終無(wú)憂患也。”[6]219這個(gè)段落是敘述楚國(guó)安定的環(huán)境,對(duì)游魂進(jìn)行呼喚,意謂返回楚國(guó)可以意定神安,能夠終生歡樂(lè),延年益壽。這是誘導(dǎo)游魂歸來(lái)的第一種美好事物。《大招》在這個(gè)段落之后所列舉的美好事物,依次是飲食之美、女樂(lè)之樂(lè)、居處之樂(lè)、政治昌明之美。這樣看來(lái),《大招》從正面誘導(dǎo)游魂來(lái)的文字共五個(gè)段落,列舉五類美好事物,與《招魂》的以三類美好事物相誘導(dǎo)在類別數(shù)量上明顯不同。
《招魂》《大招》所出現(xiàn)的用以進(jìn)行誘導(dǎo)的美好事物或是三類,或是五類,數(shù)量上不固定,屬于變數(shù)。再看《七發(fā)》及漢代七體文章。關(guān)于《七發(fā)》,《文選》李善注:“《七發(fā)》者,說(shuō)七事以起發(fā)太子也。”[7]478枚乘《七發(fā)》列舉七類美好事物用以啟發(fā)楚太子,這種寫法確實(shí)可以溯源到《招魂》《大招》。然而,《七發(fā)》并沒(méi)有完全沿襲《招魂》《大招》的文章格局,而是作了調(diào)整:一是所列舉的美好事物的總體數(shù)量增多,由三種、五種增加到七種;二是所列舉對(duì)象的類別有較大變化,其中的廣陵觀濤,要言妙道等,都是《招魂》《大招》所未曾出現(xiàn)的。
從《招魂》到《大招》,對(duì)美好事物所作的鋪陳,在類別數(shù)目上呈現(xiàn)的是變量,即數(shù)量不確定。而漢代自《七發(fā)》問(wèn)世之后,七體文章的樣態(tài)遵循相同的結(jié)構(gòu)模式。傅玄《七謨序》有如下論述:
昔枚乘作《七發(fā)》,而屬文之士若傅毅、劉廣世、崔骃、李尤、桓麟、崔琦、劉梁之徒,承其流而作之者紛焉,《七激》、《七興》、《七依》、《七疑》、《七說(shuō)》、《七蠲》、《七舉》之篇。通儒大才馬季長(zhǎng)、張平子亦引其源而廣之,馬作《七厲》,張?jiān)臁镀咿q》。[8]1020
漢代文壇出現(xiàn)的這種狀況,表明七體作為一種文章樣式,它的基本形態(tài)在漢代已經(jīng)牢固地確立,不再有大的變化。漢代所確立的七體文章樣式,在后代一直沿用。《藝文類聚》卷五十七在收錄漢代七體文章之后,又對(duì)從曹植《七啟》到蕭子范《七誘》等八篇文章予以著錄[8]1027-1035,采用的均是七段成文的結(jié)構(gòu)模式。直到清代,由漢代確立的七體范型仍在沿用,李炁伯的《七居》即是其例證[9]907-909。
(四)連珠、先文后詩(shī):從渾然一體到剝離成文
最先把連珠作為文章名稱的是揚(yáng)雄,而真正使連珠體得以確立的是班固。班固有《擬連珠》五首傳世,其中四首只存片斷,只有一首完整地保存下來(lái):
臣聞聽(tīng)決價(jià)而資玉者,無(wú)楚和之名;近習(xí)而取士者,無(wú)伯王之功。故玙璠之為寶,非駔儈之術(shù);伊尹之為佐,非左右之為舊。[10]111
這篇《擬連珠》屬于袖珍型文體,篇幅短小,運(yùn)用偶句,以比興發(fā)端,多格言警句,累累如貫珠。關(guān)于這種文體的起源,通常把它追溯到《韓非子·內(nèi)外儲(chǔ)說(shuō)》。李兆洛稱:“此體昉于《韓非》之《內(nèi)外儲(chǔ)說(shuō)》,《淮南》之《說(shuō)山》。”[3]591近人林傳甲亦稱:“《內(nèi)外儲(chǔ)說(shuō)》實(shí)連珠體之所昉,《淮南·說(shuō)山》即出于此。漢班固以后,遂遞相模仿矣。”[11]294把連珠體的源頭追溯到《韓非子》,確實(shí)有一定道理,因?yàn)樵摃秲?nèi)外儲(chǔ)說(shuō)》的各篇開(kāi)頭段落,所采用的表述方式確實(shí)與后來(lái)的連珠體相似。除此之外,《莊子》《文子》《禮記·中庸》等先秦文獻(xiàn)中也可以找到類似段落。如《文子·符言》:
其文好者皮必剝,其角美者身必殺。甘井必竭,直木必伐。物有美而見(jiàn)害,人希名而召禍。華榮之言后為愆,先騁華辭,后招身禍。[12]177
把這個(gè)段落與前邊所錄班固的《擬連珠》相對(duì)比,兩者相似之處頗多。連珠體的多種基本屬性,在《文子》的這個(gè)段落中均已具備。在西漢文獻(xiàn)中,《淮南子》的《說(shuō)山訓(xùn)》《說(shuō)林訓(xùn)》《說(shuō)苑·談叢》,也可以見(jiàn)到類似段落。不過(guò),在揚(yáng)雄正式以《連珠》為文章標(biāo)題之前,這類段落是以散金碎玉的方式分布在文章中,是整篇文章的組成部分,還沒(méi)有獨(dú)立成篇。揚(yáng)雄使連珠體具有獨(dú)立性,班固則進(jìn)一步從文章形態(tài)方面加以規(guī)范,從而形成固定的文章樣式,為后世確立了文體范型。《藝文類聚》卷五十七在收錄揚(yáng)雄、班固的連珠體文章之后,又依次收錄了從東漢潘勖到南梁劉孝儀的一系列這類文章[8]1036-1039,體式基本相同。到了魏晉南北朝時(shí)期,連珠體已由附庸變?yōu)榇髧?guó),文章數(shù)量頗多,蔚為壯觀,所遵循的均是班固確立的文體范型。
漢代所確立的文章樣式的范型,還有先文后詩(shī)的結(jié)構(gòu)模式,這個(gè)范型最初是由劉向確立的。他所編纂的《列女傳》每篇文章分前后兩個(gè)板塊:第一個(gè)板塊對(duì)傳主的情況進(jìn)行敘述,援引《詩(shī)經(jīng)》的句子作總結(jié);第二個(gè)板塊是劉向所作的“頌”,通常是八句四言詩(shī),如卷一《有虞二妃》作為文章結(jié)尾的頌是如下詩(shī)句:
元始二妃,帝堯之女。嬪列有虞,承舜于下。以尊事卑,終能勞苦。瞽叟和寧,卒享福祜。[13]2
這八句詩(shī)主要是復(fù)述前邊敘事已經(jīng)講過(guò)的內(nèi)容,表達(dá)自己對(duì)傳主的評(píng)價(jià)。這篇傳說(shuō)前邊是散文,后邊是詩(shī),明顯分成兩個(gè)板塊,兩者形成相互對(duì)應(yīng)的關(guān)系。《列仙傳》也是出自劉向之手,這部仙話集各篇文章采用的仍然是先文后詩(shī)的結(jié)構(gòu)模式。前邊敘述傳主的成仙故事,后邊用八句四言詩(shī)加以復(fù)述。
先文后詩(shī)的文章格局在先秦典籍中可以找到它的雛形。《楚辭·漁父》前一部分?jǐn)⑹銮蜐O父的對(duì)話,后一部分是漁父唱著《滄浪之歌》而離去,基本是一篇先文后詩(shī)的文章。不過(guò),這篇文章在敘述漁父所唱的《滄浪之歌》的后邊還有如下交待:“遂去,不復(fù)與言。”[6]181真正作為文章結(jié)尾的不是詩(shī),而是文章作者的敘述性語(yǔ)言。《戰(zhàn)國(guó)策·楚策四》收錄了荀子寫給春申君的一封書信,前邊是援引歷史典故進(jìn)行議論,然后是荀子所作的賦,其實(shí)是一首詩(shī),《荀子·賦篇》所載的《佹詩(shī)》把這首詩(shī)收錄[14]567-572,字句稍有不同。從總體上看,《楚策四》收錄荀子的書信,呈現(xiàn)的是先文后詩(shī)的格局。然而,這封書信并不是以荀子所作的詩(shī)結(jié)尾,而是后邊還有如下句子:“《詩(shī)》曰:‘上天甚神,無(wú)自瘵也。’”[15]567這是援引當(dāng)時(shí)流傳的《詩(shī)經(jīng)》句子進(jìn)行議論,整篇書信從是否自作的角度考察,不是嚴(yán)格意義的先文后詩(shī)格局。
先秦文獻(xiàn)中已經(jīng)存在先文后詩(shī)的文章雛形,但是,其中的文和詩(shī)無(wú)法分割開(kāi)來(lái),置于后部的詩(shī)是前邊散文敘事或議論的延伸,如果把詩(shī)剝離出來(lái),文章就變得殘缺不全。另外,這類文章最終結(jié)尾的句子往往不是作者所寫的詩(shī),而是其他類型的句子。劉向所確立的先文后詩(shī)的結(jié)構(gòu)模式,則是文章的文和詩(shī)作為兩個(gè)板塊,都有相對(duì)獨(dú)立性,已經(jīng)把置于后邊的詩(shī)與前邊的文作了剝離,兩者不再是渾然一體,而是二元并立,相互對(duì)應(yīng)。作為這類文章結(jié)尾的文字純是作者的詩(shī)句,剔除了后綴。
先文后詩(shī)的文章結(jié)構(gòu)模式在東漢得到廣泛的運(yùn)用。班固的《兩都賦》結(jié)尾是五首四言詩(shī),《封燕然山銘》結(jié)尾是五句騷體詩(shī),張衡《思玄賦》結(jié)尾是十二句七言詩(shī),馬融《長(zhǎng)笛賦》結(jié)尾是十句七言詩(shī),王延壽《夢(mèng)賦》結(jié)尾是六句七言詩(shī),趙壹《刺世疾邪賦》結(jié)尾是兩首五言詩(shī)。賦尾附詩(shī)是東漢文壇的一種風(fēng)尚,這種先文后詩(shī)的文章結(jié)構(gòu)模式對(duì)五言、七言詩(shī)具有孕育作用,“一旦這兩種詩(shī)體成熟,就開(kāi)始逐漸脫離辭賦母體,以獨(dú)立的文學(xué)樣式出現(xiàn),詩(shī)賦之間的界限也由模糊變得清晰”[16]498。
班固所撰寫的先文后詩(shī)格局的文章,還見(jiàn)于《漢書·敘傳》。這篇文章前一個(gè)板塊敘述家族譜系及自身經(jīng)歷,以散文為主,也收錄了班固所作的《答賓戲》。后一個(gè)板塊是對(duì)《漢書》各篇內(nèi)容、主旨所作的總結(jié)概括,則是采用詩(shī)的形式,末尾一則是三言詩(shī),其余基本都是四言。歷史著作的書寫采用先文后詩(shī)的結(jié)構(gòu)模式,還見(jiàn)于《晉書》和《南齊書》。《晉書》的人物傳記除《宣帝紀(jì)》《景帝紀(jì)》兩篇之外,其余各篇傳記結(jié)尾的贊都是四言詩(shī),《南齊書》則是所有人物傳記結(jié)尾的贊全都是四言詩(shī)。不過(guò),這種先文后詩(shī)的文章結(jié)構(gòu)模式,在后來(lái)的正史系統(tǒng)中沒(méi)有延續(xù)下去。
在整個(gè)中國(guó)古代,采用先文后詩(shī)的結(jié)構(gòu)模式,并且世代相承的文類是碑文。蔡邕撰寫了一系列碑文,全部采用先文后詩(shī)的結(jié)構(gòu)模式。前一個(gè)板塊用散體敘述碑主的生平經(jīng)歷及譜系,第二個(gè)板塊的銘則是用詩(shī)體,主要是四言詩(shī)。傳世的東漢其他碑文,采用的也是這種結(jié)構(gòu)模式。這種先文后詩(shī)的碑文樣式,成為后代效仿的范型。韓愈的《平淮西碑》是古代碑文的名篇,盡管它是碑文的變體,所采用的仍然是先文后詩(shī)的模式,只是詩(shī)的板塊篇幅加大,與前邊文的板塊平分秋色而已[17]284-286。先文后詩(shī)的文章結(jié)構(gòu)模式是劉向在《列女傳》《列仙傳》中確立的,這兩書系傳記類文章的結(jié)集。這種結(jié)構(gòu)模式開(kāi)始是在傳記類文章中得到確立,后來(lái)又在作為傳記類別的碑文中世代延續(xù),有其歷史必然性。
二、文章重大主題的確立
中國(guó)古代文學(xué)許多重大的主題是在漢代確立的,這些重大主題有的是先秦時(shí)期就已經(jīng)形成,但是處于萌芽、潛在形態(tài),到了漢代才變得明朗,得以真正確立。還有的主題先秦時(shí)期根本沒(méi)有涉及或很少提到,到漢代才真正形成并且得以確立。漢代文學(xué)對(duì)這些重大主題的確立,在具體文章中采用的方式多種多樣,重大主題的確立經(jīng)由多個(gè)渠道。
(一)悲士不遇與圣主得賢臣頌
悲士不遇作為文章主題在先秦時(shí)期就已經(jīng)形成,屈原的《離騷》《九章》多數(shù)篇目,宋玉的《九辯》,是這方面的代表作。不過(guò),明確把悲士不遇作為文章主題,這個(gè)進(jìn)程是從漢代正式啟動(dòng)的。漢代文學(xué)悲士不遇主題的確立,是以對(duì)屈原的悼念發(fā)端。賈誼作《吊屈原賦》,僅從文章題目就可看出這是哀悼屈原的懷才不遇。文中稱屈原“遭世無(wú)極”“逢時(shí)不祥”[18]410,也就是生不逢時(shí),因此造成“乃隕厥身”的人生悲劇。
董仲舒作《士不遇賦》,所用的標(biāo)題使得悲士不遇主題進(jìn)一步明朗化。賈誼是通過(guò)哀悼屈原表達(dá)悲士不遇主題,董仲舒則是直接抒發(fā)自身的感受:“生不丁三代之盛隆兮,而丁三季之末俗。”[19]146他感慨自己生不逢時(shí),陷入進(jìn)退維谷的困境。司馬遷是董仲舒的弟子,他的《悲士不遇賦》用篇題把這個(gè)主題進(jìn)一步明朗化。文章慨嘆“士生之不辰”,“雖有行而不彰,徒有能而不陳”[19]189。司馬遷把自己懷才不遇,壯志難伸的抑郁之情抒發(fā)得淋漓盡致。至此,悲士不遇作文章的重要主題正式確立,在中國(guó)古代文學(xué)史上具有標(biāo)志性意義。
漢代涌現(xiàn)出一大批以悲士不遇為主題的文章,設(shè)辭、九體都屬于這個(gè)系列。還有一些九體之外抒發(fā)個(gè)人情志的騷體賦,也以悲士不遇為主題。把悲士不遇作為文章主旨,并且通過(guò)文章題目加以昭示,這種做法在后代仍然可以見(jiàn)到。陶淵明有《感士不遇賦》[20]145-148,明代伍瑞隆有《惜士不遇賦》[21]卷三,顯然是把董仲舒、司馬遷的上述兩篇文章作為范型,以悲士不遇為主題而以篇名道其志。
古代士人有懷才不遇之感,還有圣主賢臣相遇的企盼,兩者往往交織在一起,屈原的《離騷》《天問(wèn)》就是如此。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其他文章也有這方面的內(nèi)容。至于明確地把歌頌圣主賢臣相遇作為文章主旨,并且用篇題加以標(biāo)示,這是在漢代開(kāi)始的。王褒從蜀地被朝廷征招到長(zhǎng)安,“既至,詔褒為圣主得賢臣頌其意”[22]2822。圣主得賢臣頌這個(gè)題目是漢宣帝所定,文章是王褒所寫,屬于命題作文。文中寫道:“故世必有圣知之君,而后有賢明之臣。”“故圣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yè),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22]2826-2827這幾句話把圣主與賢臣之間互依、互動(dòng)的關(guān)系論述得非常透徹,成為格言警句。韓愈《雜說(shuō)四》稱:“世有伯樂(lè)然后有千里馬。”[17]128這與《圣主得賢臣頌》給出的結(jié)論同出一轍。王褒這篇文章是頌揚(yáng)君主得賢臣重大主題正式確立的標(biāo)志,是后代同類主題文章的范型。
(二)盛世頌歌與刺世疾邪
歌頌與批判是中國(guó)古代文學(xué)具有互補(bǔ)性的兩類重大主題,先秦時(shí)期已經(jīng)出現(xiàn)大量這方面的文章。然而,通過(guò)文章題目明確標(biāo)示對(duì)現(xiàn)實(shí)的頌揚(yáng)和批判,這個(gè)進(jìn)程還是從漢代真正開(kāi)始。
司馬相如的《封禪文》是事先為漢武帝到泰山封禪而作。所謂的封禪是天下大治、太平盛世的標(biāo)志,因此,司馬相如這篇文章的題目,標(biāo)示出為太平盛世歌功頌德的主旨。文中寫道:“大漢之德,逢涌原泉,沕潏曼羨;旁魄四塞,云布霧散;上暢九垓,下泝八埏。”[22]2601對(duì)西漢盛世進(jìn)行歌功頌德,達(dá)到無(wú)以復(fù)加的程度。后來(lái)?yè)P(yáng)雄的《劇秦美新》、班固的《典引》,沿襲的是司馬相如的路數(shù)。對(duì)現(xiàn)實(shí)社會(huì)歌功頌德而用文章題目明確地加以昭示,這種模式在東漢傅毅、崔骃那里凝固為對(duì)天子的贊美。《后漢書·文苑列傳下》記載:“毅追美孝明皇帝功德最盛,而廟頌未立,乃依《清廟》作《顯宗頌》十篇奏之。”[23]2613《清廟》是《詩(shī)經(jīng)·周頌》首篇,是周族用于宗廟祭祀的歌詩(shī)。傅毅為祭祀東漢明帝所作的廟頌借鑒《清廟》一詩(shī),篇名定為《顯宗頌》,明顯是為明帝歌功頌德。崔骃作《四巡頌》,即《東巡頌》《南巡頌》《西巡頌》《北巡頌》[24]99-108。所謂的巡,這里專指天子巡狩。這四篇文章都作于漢章帝時(shí)期,把漢章帝寫成圣明天子,把當(dāng)時(shí)的社會(huì)渲染為太平盛世。繼崔骃之后,馬融、劉珍都有《東巡頌》[24]108-111,是對(duì)漢安帝進(jìn)行歌功頌德的篇章。把對(duì)現(xiàn)實(shí)社會(huì)的贊美聚焦在天子身上,這種做法始于司馬相如的《封禪文》,到東漢傅毅、崔骃等人的頌類文章而最終確立,成為歌功頌德的一種模式。北魏高允的《南巡頌》[24]112-114,明顯是沿襲東漢的天子巡狩頌。這類為天子歌功頌德的文章在后代頗為常見(jiàn),可以從上述漢代諸篇頌類文章那里找到源頭。
從先秦到兩漢,各個(gè)歷史階段都不乏憤世嫉俗之士,并且出現(xiàn)數(shù)量眾多的針砭時(shí)弊的文章。這類文章絕大多數(shù)選擇一個(gè)或幾個(gè)側(cè)面對(duì)現(xiàn)實(shí)社會(huì)進(jìn)行批判,至于從整體上對(duì)社會(huì)作全盤否定,進(jìn)行徹底批判,并且把這種主旨明確地用篇名加以標(biāo)示,則是始于東漢的趙壹。《后漢書·文苑列傳下》記載:趙壹恃才倨傲,為鄉(xiāng)黨所排斥,乃作《解擯》。后來(lái)幾次入獄,險(xiǎn)些喪命,被友人搭救,作《窮鳥(niǎo)賦》,感謝友人。“又作《刺世疾邪賦》,以舒其怨憤。”[23]2630趙壹這篇賦是在他屢經(jīng)坎坷之后胸中憤怒的集中噴射,同時(shí)也是以批判現(xiàn)實(shí)為主題的意義指向的凝結(jié)強(qiáng)化,并且通過(guò)文章題目明確地顯示出來(lái)。這篇文章的標(biāo)題既是對(duì)以往批判現(xiàn)實(shí)文章主題所作的高度概括,也為后代這類文章確立了主題范型。
(三)立言不朽與激賞使者邊功
《左傳·襄公二十四年》記載魯國(guó)叔孫豹如下話語(yǔ):“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25]1088叔孫豹提出的“三不朽”價(jià)值觀,在先秦時(shí)期就已經(jīng)得到普遍的認(rèn)可,但是把立言不朽和激賞使者的邊功作為文學(xué)的重大主題,卻是在漢代才開(kāi)始真正確立的。
先秦時(shí)期有一大批追求立言不朽之士,確實(shí)有許多人實(shí)現(xiàn)了立言不朽。然而,先秦時(shí)期有立言不朽之人,卻基本見(jiàn)不到以立言不朽為主題的文章。《史記·孔子世家》把孔子修《春秋》的動(dòng)機(jī)歸結(jié)為“君子病沒(méi)世而名不稱焉”[26]1943。這是司馬遷所作的推測(cè),孔子本人并沒(méi)有明確地把修《春秋》與立言不朽聯(lián)系在一起。《史記·呂不韋列傳》稱,《呂氏春秋》成書之后,呂不韋令人在咸陽(yáng)市場(chǎng)懸賞,能增損一字者賞千金[26]2510,暗示呂不韋有立言不朽之意。可是,《呂氏春秋·十二紀(jì)》自序,根本沒(méi)有明確提到立言不朽,只是說(shuō)這部書是“上揆之天,下驗(yàn)之地,中審之人”[27]122。大量事實(shí)表明,先秦時(shí)期的文章還沒(méi)有把立言不朽作為重大主題。
進(jìn)入漢代以后,陸續(xù)涌現(xiàn)出一大批以立言不朽為主題的文章,這些文章有一個(gè)共同的特點(diǎn),則是在文章或著作的結(jié)尾處點(diǎn)明主題,是篇末點(diǎn)題,卒章通其志,而不像以悲士不遇、圣主得賢臣等作為主題的文章那樣以篇名道其志。
《太史公自序》是《史記》的敘傳,放置在全書最后。這篇文章結(jié)尾稱他對(duì)《史記》這部書有如下期待:“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后世圣人君子。”[26]3320顯然,這是希望立言不朽,揚(yáng)名后世。
《漢書·敘傳》是該書最后一篇,是班固自述家世及撰寫《漢書》的始末。文中稱:“故雖堯舜之盛,必有典謨之篇,然后揚(yáng)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22]4235這幾句還是暗示立言可以使人生不朽,名揚(yáng)后世,他撰寫《漢書》的目的也在于此。《論衡·自紀(jì)》是該書的末篇,王充在文中稱:“身與草木俱朽,聲與日月并彰;行與孔子比窮,文與揚(yáng)雄為雙,吾榮之。”[28]287在王充看來(lái),立德立言是人生的根本,立德是以孔子為楷模,立言要與揚(yáng)雄比肩而立,以此實(shí)現(xiàn)人生不朽。王符在《潛論·敘錄》也提到立德、立功、立言,他選擇立言:“芻蕘雖微陋,先圣亦咨詢。”[29]193他相信自己的著作會(huì)有讀者,產(chǎn)生反響,把立言作為人生寄托。
設(shè)辭是漢代確立的文章樣式之一,這類文章往往在結(jié)尾表達(dá)立言不朽的理念。揚(yáng)雄《解嘲》結(jié)尾稱:“默然獨(dú)守吾《太玄》。”[22]3573揚(yáng)雄為什么獨(dú)守《太玄》,班固稱揚(yáng)雄:“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以為經(jīng)莫大于《易》,故作《太玄》。”[22]3583揚(yáng)雄是通過(guò)撰寫《太玄》等一系列著作,用以揚(yáng)名于后世。班固的《答賓戲》結(jié)尾把自己的人生選擇鎖定在“故密爾自?shī)视谒刮摹保亷煿抛ⅲ骸懊埽o也,安也。”[22]4233班固是把料理文章作為人生的寄托。他在《幽通賦》稱:“要沒(méi)世而不朽兮,乃先民之所程。”[22]4222班固追求人生不朽,又把寫文章作為人生的選擇,顯然,《答賓戲》結(jié)尾表達(dá)的正是立言不朽的理念。張衡作《應(yīng)間》一文,設(shè)主客問(wèn)答以表達(dá)自己的心志。文章結(jié)尾段落寫道:“愍《三墳》之既頹,惜《八索》之不理。庶前訓(xùn)之可鉆,聊朝隱于柱史。”[23]1908這里所說(shuō)的《三墳》《五典》用的是《國(guó)語(yǔ)·楚語(yǔ)》的典故,文中泛指古代文獻(xiàn)。“柱史”指老子,老子曾在東周朝廷任柱下史,負(fù)責(zé)管理圖書。張衡把自己的人生寄托在與文章打交道方面,其實(shí)還是強(qiáng)調(diào)立言不朽。
綜上所述,漢代文學(xué)把立言不朽確立為文章的重大主題,這個(gè)進(jìn)程發(fā)軔于武帝時(shí)期的司馬遷,經(jīng)由揚(yáng)雄,到班固而最終完成。其后王充、王符、張衡等陸續(xù)有這類文章問(wèn)世。以立言不朽為主題的文章,無(wú)論在歷史散文中,還是設(shè)辭類作品,主題的昭示均置于文章或著作末尾,幾乎已成定制。立言不朽的意義指向是未來(lái),把主旨的昭示置于文章末尾,與它的意義指向相契合,可謂順理成章。“文章千古事”是古代文人的普遍理念,漢代文學(xué)確立的這一重大主題,在后代文學(xué)中不時(shí)地發(fā)出回響。
頌揚(yáng)外交使者在邊塞絕域建功立業(yè),是漢代文學(xué)確立的又一個(gè)重大主題。清人趙翼稱:“自武帝擊匈奴,通西域,徼外諸國(guó)無(wú)不懾漢威……而其時(shí)奉使者亦皆有膽決策略,往往以單車使者,斬名王定屬國(guó)于萬(wàn)里之外。”[30]57這種氣象在先秦時(shí)期是見(jiàn)不到的,那個(gè)歷史階段外交使者的活動(dòng)范圍局限在中土之內(nèi),西域與中土基本上屬于隔絕狀態(tài),當(dāng)然也不會(huì)出現(xiàn)在西域建功立業(yè)的使者,更無(wú)法出現(xiàn)這方面題材、主旨的文章。《史記》《漢書》對(duì)于這些充滿冒險(xiǎn)精神的外交使者,予以充分的肯定,由此確立激賞使者邊功的文章主題。
張騫是首位通西域的西漢使者,《史記·大宛列傳》詳細(xì)記載張騫出使西域的始末,并且用贊揚(yáng)的筆調(diào)敘述張騫的歷史功績(jī)。司馬遷稱:“張騫鑿空。”裴骃集解引蘇林語(yǔ):“鑿,開(kāi)。空,通也。騫開(kāi)通西域道。”司馬貞索隱:“案,謂西域險(xiǎn)阨,本無(wú)道路,今鑿空而通之也。”[26]3170所作的解釋大意得之,但是不夠確切,所謂鑿空,指鑿出窟窿,通道。空,通孔,窟窿。《史記·五帝本紀(jì)》稱“舜穿井為匿空旁出”,張守節(jié)正義:“言舜潛匿穿孔旁,從他井而出也。”[26]35所作的解釋是正確的。這里出現(xiàn)的“空”字,指的是孔,《史記》本身提供了內(nèi)證。司馬遷在《大宛列傳》中把張騫通西域的歷史功績(jī)從多方面予以敘述,展示出絲綢之路開(kāi)通之初中土與西域交往出現(xiàn)的嶄新局面。《大宛列傳》初步確立了激賞外交使者邊塞絕域建功的文章主題。
《漢書》卷六十一設(shè)張騫傳,基本沿襲《史記·大宛列傳》的相關(guān)記載。《漢書·敘傳》稱:“博望杖節(jié),收功大夏。”[22]4256亦對(duì)張騫通西域予以高度贊揚(yáng)。《漢書》卷七十是傅介子、常惠、鄭吉、甘延壽、陳湯、段會(huì)宗六人的傳,他們都是經(jīng)營(yíng)西域的著名外交使者。該傳記結(jié)尾稱:“自元狩之際,張騫始通西域,至于地節(jié),鄭吉建都護(hù)之號(hào),訖王莽世,凡十八人,皆以勇略選,然其有功跡者具此。”[22]3032這是對(duì)西漢開(kāi)啟陸上絲綢之路階段的外交使者群體作出總的評(píng)價(jià),指出他們勇敢而又有謀略,是智勇雙全的人物。該卷的主旨是贊揚(yáng)六位外交使臣所建立的功勛,是把激賞使者邊功作為文章主題牢固確立的標(biāo)志。
東漢經(jīng)營(yíng)西域的著名使者是班超,《后漢書》卷四十七設(shè)《班超列傳》,對(duì)于班超經(jīng)營(yíng)西域所作的敘述極其詳細(xì),時(shí)間跨度長(zhǎng)達(dá)30 余年。篇末贊語(yǔ)稱:“定遠(yuǎn)慷慨,專功西遐。坦步蔥雪,咫尺龍沙。”李賢注:“蔥嶺、雪山,白龍堆沙漠也。八寸曰咫。坦步言不以為艱,咫尺言不以為遠(yuǎn)也。”[23]1549這幾句贊詞昭示了《后漢書》班超傳記的主題,就是高度贊揚(yáng),充分肯定班超在西域建立的功勛,贊揚(yáng)他的冒險(xiǎn)精神和家國(guó)情懷,繼承的是《史記》《漢書》同類傳記確立的主題范型。
兩漢是陸上絲綢之路開(kāi)啟階段,涌現(xiàn)出一批在邊塞絕域建功立業(yè)的外交使者,并且使得以激賞使者邊功為主題的文章陸續(xù)出現(xiàn),可以說(shuō)是時(shí)勢(shì)造英雄,也是時(shí)勢(shì)造文章。兩漢之后,往來(lái)于陸上絲綢之路的主要人物不再是朝廷的外交使者,而是商人和僧侶。由此而來(lái),漢代確立的激賞使者邊功的文章主題,在后代出現(xiàn)的頻率很低。從嚴(yán)格意義看,它真正作為范型而被沿用,到《后漢書·班超傳》就已經(jīng)基本結(jié)束。不過(guò),張騫、班超這兩位在陸上絲綢之路開(kāi)啟時(shí)期作出巨大貢獻(xiàn)的外交使者,作為歷史典故仍然經(jīng)常出現(xiàn)在后代的各類文章中。
(四)災(zāi)異示禍與符瑞顯德
古人秉持的是天人相通、天人感應(yīng)觀念,認(rèn)為人間萬(wàn)象與自然界的災(zāi)異禎祥存在對(duì)應(yīng)關(guān)系,這種觀念在先秦時(shí)期就已經(jīng)形成,并且有明確的表述。《國(guó)語(yǔ)·周語(yǔ)上》記載東周王朝的大夫內(nèi)史過(guò)有如下話語(yǔ):
昔夏之興也,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祿信于聆隧。商之興也,禱杌次于柸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鳴于岐山;其亡也,杜伯射王于鄗。[31]29-30
這是列舉有關(guān)夏、商、周三代的歷史傳說(shuō),把禎祥和災(zāi)異與國(guó)家興亡聯(lián)系在一起,認(rèn)為彼此之間存在對(duì)應(yīng)關(guān)系。《禮記·中庸》亦稱:“國(guó)家將興,必有禎祥;國(guó)家將亡,必有妖孽。”朱熹注:“禎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禍之萌。”[32]33《中庸》出自孔子之孫子思之手,屬于儒學(xué)正宗,也是孔子家學(xué)的嫡傳。先秦文獻(xiàn)雖然對(duì)于災(zāi)異禎祥多有記載,但是不夠系統(tǒng)、集中,而是零散地分布在各種典籍中,還沒(méi)有成為文章的重要主題,當(dāng)時(shí)人們對(duì)災(zāi)異禎祥所作的解說(shuō)也比較簡(jiǎn)略,很少有長(zhǎng)篇大論而構(gòu)成獨(dú)立的文章者。
進(jìn)入漢代以后,情況發(fā)生了很大變化,出現(xiàn)了一大批言說(shuō)災(zāi)異的學(xué)人。對(duì)此,《漢書》卷七十五結(jié)尾寫道:
漢興推陰陽(yáng)言災(zāi)異者,孝武時(shí)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則眭孟、夏侯勝,元、成則京房、翼奉、劉向,谷永,哀、平則李尋、田終術(shù)。此其納說(shuō)時(shí)君著明者也。[22]3194-3195
班固提到的上述諸人都是西漢時(shí)期的經(jīng)師,研論“五經(jīng)”,各有所長(zhǎng),學(xué)問(wèn)上也有高低之分。班固在谷永傳記中指出:“永于經(jīng)書,泛為疏達(dá),與杜欽、杜鄴略等,不能洽浹如劉向父子及揚(yáng)雄也。”[22]3472西漢推言災(zāi)異的經(jīng)師有的學(xué)問(wèn)淵博,推言災(zāi)異頗有學(xué)理性,所寫的是學(xué)者之文。而學(xué)術(shù)粗疏者則近乎術(shù)士,推言災(zāi)異則牽強(qiáng)附會(huì)頗多。
在古人觀念中,災(zāi)異和禎祥是相互對(duì)立的,因此,漢代的經(jīng)學(xué)著作往往是兼顧兩者。董仲舒《春秋繁露·同類相動(dòng)》同時(shí)提到災(zāi)異和禎祥[33]45,班固編纂的《白虎通德論》則分別設(shè)立《災(zāi)變》和《封禪》兩個(gè)欄目,后者主要論符瑞。推言災(zāi)異禎祥是漢代經(jīng)學(xué)的重要組成部分,災(zāi)異示禍和符瑞顯德理念是在經(jīng)學(xué)框架內(nèi)體系化、嚴(yán)密化,并且成為文章的重要主題。
禎祥和災(zāi)異在先秦時(shí)期就與國(guó)家的興亡建立起對(duì)應(yīng)關(guān)系,漢代以符瑞顯德、災(zāi)異示禍為主題的文章寫作背景,也與世道的興衰大體構(gòu)成橫向?qū)?yīng)關(guān)系。西漢最早把符瑞集中寫入文章的是司馬相如的《封禪文》,是為武帝到泰山封禪預(yù)先而作。這篇文章不但在正文板塊中提到多種符瑞,而且在所附的五首詩(shī)中有四首展示符瑞,這篇文章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shuō)是符瑞的萃集。班固的《典引》是受《封禪文》的啟發(fā)而作,其中出現(xiàn)的符瑞數(shù)量較之《封禪文》有過(guò)之而無(wú)不及。崔骃和班固是同時(shí)代人,他所寫的《東巡頌》《北巡頌》,也提到一系列符瑞。另外,班固《東都賦》后邊所附的《靈臺(tái)詩(shī)》《寶鼎詩(shī)》《白雉詩(shī)》,符瑞在三首詩(shī)中都是主要展示對(duì)象。漢代文學(xué)對(duì)符瑞集中加以表現(xiàn)的作品,一是出自西漢武帝時(shí)期的司馬相如之手,二是東漢明帝、章帝時(shí)期班固、崔骃所作。這兩個(gè)歷史時(shí)期是漢代的盛世,也是以符瑞顯德為主題文章的繁榮時(shí)期。以符瑞顯德為主題,這類文章在漢代由司馬相如首創(chuàng),初步確立傳統(tǒng)。到了東漢明、章之世,則由班固、崔骃等把這類文章的范型穩(wěn)固地確立下來(lái),基本已成定制,并且一直被后代所沿襲。
如前所述,班固曾對(duì)漢代推言陰陽(yáng)災(zāi)異的主要人物進(jìn)行羅列,總共十位,其中元帝、成帝以后的六位,在三個(gè)歷史階段中人數(shù)最多。西漢從元帝開(kāi)始就走向衰落,成帝時(shí)期已經(jīng)進(jìn)入亂世階段。與此相應(yīng),這個(gè)時(shí)期以陰陽(yáng)推言災(zāi)異的風(fēng)氣也最盛,并且已經(jīng)形成體系,代表人物是劉向和京房。班固稱劉向:“劉氏《洪范論》發(fā)明《大傳》,著天人之應(yīng)。”[22]1972《漢書·藝文志》著錄劉向的《五行傳記》十一卷,他是用陰陽(yáng)五行學(xué)說(shuō)解釋災(zāi)異,形成完整的體系。至于京房,“其于天官、《京氏易》最密,故善言災(zāi)異”[22]3472-3473。京房擅長(zhǎng)以天象解說(shuō)災(zāi)異,也是自成體系。漢代推言災(zāi)異的文章始于董仲舒,及至劉向、京房所處的西漢后期,這類文章已經(jīng)確立固定的范型,是衰世亂世而使這類文章定型。東漢以災(zāi)異示禍為主題的文章集中出現(xiàn)在桓帝、靈帝兩朝,也是亂世的產(chǎn)物。蔡邕傳世的文章有《日蝕上書》《答詔問(wèn)災(zāi)異》《答特詔問(wèn)災(zāi)異》,都是以災(zāi)異示禍為主題。其中《答詔問(wèn)災(zāi)異》序言稱,光和元年(179年)七月十日,朝廷召集蔡邕、楊賜、張華、馬日、單飏等朝廷大臣,傳達(dá)天子指令:“朝廷以災(zāi)異憂懼,特旨密問(wèn)政事所變改施行,務(wù)令分明。”[34]239蔡邕的《答詔問(wèn)災(zāi)異》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寫的,篇幅甚長(zhǎng)、其他人當(dāng)然也要遵旨撰寫,是以災(zāi)異示禍為主題文章的集中推出。這個(gè)事件發(fā)生在靈帝光和元年,當(dāng)時(shí)正值亂世。《后漢書·方術(shù)列傳》首列八位與災(zāi)異星占有關(guān)的方士,除排在前邊的房檀、公沙穆之外,其余六位均是桓、靈之世的人。這也可證明東漢后期的亂世言說(shuō)災(zāi)異之風(fēng)頗盛,因此,以災(zāi)異示禍為主題的文章在這個(gè)階段成批地出現(xiàn)。
災(zāi)異示禍、符瑞顯德為主題的文章,分別初步定型于董仲舒、司馬相如,而穩(wěn)固定型于劉向、班固。司馬遷生活在這兩類文章的初步定型到穩(wěn)固定型的中間階段,災(zāi)異示禍和符瑞顯德也成為《史記》的重大主題之一。《秦始皇本紀(jì)》列舉許多災(zāi)異,暗示這是上天向秦始皇提出的警告。《高祖本紀(jì)》著眼表現(xiàn)劉邦對(duì)各種符瑞的心領(lǐng)神會(huì),對(duì)上天啟示所作的巧妙回應(yīng)[26]369-370。這是災(zāi)異示禍與昏君亡國(guó)相對(duì)應(yīng),而把符瑞顯德與明君興國(guó)創(chuàng)統(tǒng)相貫通,這在后來(lái)的史書中成為一種模式。
漢代文人推言災(zāi)異致禍,多數(shù)把災(zāi)異與人間禍患之間的關(guān)系說(shuō)得很清楚,所用的話語(yǔ)容易被人理解。也有的文章帶有神秘色彩,用語(yǔ)艱澀,含義隱晦,不易理解,甚至產(chǎn)生誤解。
谷永是西漢成帝時(shí)著名的推言陰陽(yáng)災(zāi)異的代表人物之一,與京房齊名,他所寫的奏書中有如下幾句:
陛下承八世之功業(yè),當(dāng)陽(yáng)數(shù)之標(biāo)季,涉三七之節(jié)紀(jì),遭《無(wú)妄》之卦運(yùn),直百六之災(zāi)厄[22]3468
這幾句話的特點(diǎn)是用了一系列數(shù)字,破譯這些數(shù)字的含義是解讀的關(guān)鍵。“當(dāng)陽(yáng)數(shù)之標(biāo)季”,顏師古注引孟康語(yǔ):“陽(yáng)九之末季也。”[22]3468成帝是西漢第九代天子,即前邊所說(shuō)的“承八世之功業(yè)”。九是陽(yáng)數(shù),孟康所言在這方面可取。至于把標(biāo)季釋為末季,則在情理上捍格難通。如果把標(biāo)季釋為末季,“當(dāng)陽(yáng)數(shù)之標(biāo)季”就等于是說(shuō)成帝處于第九代天子的末期,這無(wú)疑是對(duì)他的詛咒,谷永不會(huì)說(shuō)出這樣的蠢話。標(biāo),應(yīng)釋為標(biāo)志。季,謂朝代,代。“當(dāng)陽(yáng)數(shù)之標(biāo)季”,意謂處在第九代天子的位置,標(biāo)示的是西漢的第九代天子。“涉三七之節(jié)紀(jì)”,顏師古注引孟康語(yǔ):“至平帝乃三七二百一十歲之厄,今已涉向其節(jié)紀(jì)。”[22]3468谷永的這篇奏書寫于元延元年(公元前12年),上距西漢王朝建立已經(jīng)190 余年,谷永在此前奏書中也提到“漢興九世,百九十余載”。如果按照孟康所作的闡釋去理解“涉三七之節(jié)紀(jì)”,就等于說(shuō)西漢王朝只有210年的壽命,你已經(jīng)步入王朝的滅亡期。這無(wú)疑是詛咒西漢王朝迅速滅亡,谷永如果真是這樣陳述,難免招來(lái)殺頭滅族之災(zāi),他絕對(duì)不可能如此喪失理性。其實(shí),這里所說(shuō)的“涉三七之節(jié)紀(jì)”,三和七分別指十二地支的寅和午,它們?cè)谑刂е蟹謩e排在第三、第七。古人對(duì)十二地支分別賦予象征意義。《史記·律書》:“寅言萬(wàn)物始生螾然也,故曰寅。”[26]1245寅是物之始生之義,具體指怎樣一種狀態(tài)呢?《說(shuō)文解字·寅部》:“寅,髕也。正月陽(yáng)氣動(dòng),去黃泉欲上出。陰尚強(qiáng)也,象宀不達(dá),髕寅于下也。”[35]745照此說(shuō)法,寅字是物之始生而受到阻礙之義。髕,通“擯”。王筠稱:“小徐說(shuō)髕為擯斥之意(大徐本脫擯字,便難解),蓋得其旨。”[36]258寅字指的出生受到阻礙,與寅對(duì)應(yīng)的數(shù)字是三,所謂的“三七之紀(jì)”,三應(yīng)指出生遇到障礙。
十二地支排在第七位的是午,《史記·律書》:“午者,陰陽(yáng)交,故曰午。”[26]1247午指陰陽(yáng)交,于人事指男女媾和。“涉三七之節(jié)紀(jì)”,意謂步入男女交媾而出生受到阻礙的時(shí)期,具體指成帝沒(méi)有子嗣之事。此前谷永的奏書就建議成帝廣納宜子?jì)D人,寧肯“得繼嗣于微賤之間”[22]3453。由此看來(lái),谷永的“涉三七之節(jié)紀(jì)”是專門針對(duì)成帝無(wú)繼嗣而發(fā),絕不像孟康所解釋的那樣是預(yù)測(cè)西漢王朝即將滅亡。后代基本是沿襲孟康之說(shuō),三七之厄被視為讖言。
三、范型之間的邏輯關(guān)聯(lián)
漢代在文章樣式、主題方面確立了一系列范型,各種范型并不是孤立存在,而是彼此之間存在邏輯的關(guān)聯(lián)。這種關(guān)聯(lián)既體現(xiàn)在同一系列范型之間,又反映在不同系列范型之間。文章樣式系列的范型之間,主題系列的范型之間存在內(nèi)部關(guān)聯(lián),文章樣式系列和主題系列的范型還存在外部關(guān)聯(lián)。它們之間的關(guān)聯(lián)按邏輯劃分主要有三種類型,即因果關(guān)系、依存關(guān)系、兩極互補(bǔ)關(guān)系。
首先看因果關(guān)系。漢代文學(xué)確立的主題范型包括悲士不遇和立言不朽,是因?yàn)榱⒐o(wú)門而產(chǎn)生悲士不遇情懷,又因?yàn)楸坎挥龆盐恼聦懽饕暈槿松募耐校虼税蚜⒀圆恍嘧鳛槲恼碌闹黝}。立言不朽與激賞使者邊功兩個(gè)主題之間也存在因果關(guān)聯(lián)。《后漢書·班梁列傳》結(jié)尾有如下評(píng)論:
時(shí)政平則文德用,而武略之士無(wú)所奮其力能,故漢世有發(fā)憤張膽,爭(zhēng)膏身于夷狄以要功名,多矣。祭肜、耿秉啟匈奴之權(quán),班超、梁謹(jǐn)奮西域之略,卒能成功立名,享受爵位,薦功祖廟,勒勛于后,亦一時(shí)之志士也。[23]1594
太平之世多出現(xiàn)一系列追求立言不朽之士,文章寫作得到朝廷的重視。與此相應(yīng),那些有膽略和冒險(xiǎn)精神的人就要另尋出路,到邊塞絕域去建功立業(yè)。班超年輕時(shí)就投筆而嘆:“大丈夫無(wú)它志略,猶當(dāng)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間乎?”[23]1571班超不肯久事筆硯間而投筆從戎,成為以激賞使者邊功為主題文章的取材對(duì)象,這與班固的“密爾自?shī)视谒刮摹毙纬甚r明的對(duì)比。立言不朽和激賞使者邊功兩個(gè)主題的生成,彼此呈現(xiàn)的是互為因果的關(guān)系。
再看依存關(guān)系。設(shè)辭、九體是漢代確立的兩種文體范型。綜觀這兩個(gè)系列的文章,基本都是抒發(fā)悲士不遇的情懷,只是設(shè)辭類文章是作者直抒胸臆,而九體文章則往往以屈原為依存。這樣看來(lái),作為文體范型的設(shè)辭、九體,成為重大主題范型悲士不遇的載體,悲士不遇主題依存于設(shè)辭、九體。漢代確立的重大主題范型有立言不朽,這類文章也往往依存于設(shè)辭。漢代確立的文學(xué)重大主題有盛世頌歌和刺世疾邪、災(zāi)異示禍和符瑞顯德,這兩組文學(xué)主題之間也具有依存關(guān)系。盛世頌歌則鋪排符瑞,刺世疾邪則推言災(zāi)異,盛世頌歌是以符瑞顯德為依存,刺世疾邪則是以災(zāi)異示禍為依存。
最后看兩極互補(bǔ)關(guān)系,這種關(guān)聯(lián)主要體現(xiàn)在重大主題范型內(nèi)部。漢代文學(xué)確立的重大主題范型主要有八種,可劃分為四組。悲士不遇和圣主得賢臣頌,反映的是現(xiàn)實(shí)與理想的關(guān)聯(lián)。悲士不遇是許多文人的現(xiàn)實(shí)處境,而圣主得賢臣頌表達(dá)的則是文人的普遍理想。士不遇經(jīng)常可見(jiàn),圣主得賢臣則是千載難逢,兩者均成兩極對(duì)立而又互補(bǔ)的關(guān)系。災(zāi)異示禍和符瑞顯德這組重大主題也是兩極互補(bǔ)。人有趨利避害的本能,又有逢兇化吉的愿望,這兩個(gè)文章主題范型,體現(xiàn)的就是利與害、吉與兇之間的相反相成,對(duì)立互補(bǔ)。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同類相動(dòng)》寫道:“帝王之將興也,其美祥亦先見(jiàn);其將亡也,妖孽亦先見(jiàn)。”[32]445董仲舒秉持的是先秦時(shí)期就已經(jīng)形成的理念,把禎祥、妖孽的出現(xiàn)與帝王的興亡聯(lián)系在一起,認(rèn)為有其必然性。清人趙翼有如下論述:
漢興,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yáng),為儒者宗。宣、元之后,劉向治《穀梁》,數(shù)其禍福,傳以《洪范》(《五行志·序》),而后天與人又漸覺(jué)親切。[30]39
所謂的“天與人又漸覺(jué)親切”,指的是天人相通、天人感應(yīng)理念。災(zāi)異示禍和符瑞顯德主題,是以相反的方式表現(xiàn)天人感應(yīng)理念,構(gòu)成的是兩極對(duì)立而又互補(bǔ)的關(guān)系。立言不朽與激賞使者邊功,這兩個(gè)主題從生成層面考察,構(gòu)成的是互為因果的關(guān)系,而從意義層面考察,呈現(xiàn)的又是立言與立功的兩極互補(bǔ),兩者并不構(gòu)成對(duì)立,而是同屬于人生不朽系列。盛世頌歌和刺世疾邪,亦屬兩極互補(bǔ)。漢代文學(xué)所確立的重大主題范型每?jī)蓚€(gè)為一組,彼此之間存在兩極互補(bǔ)的關(guān)系,有內(nèi)在的邏輯層次,因此呈現(xiàn)為孿生形態(tài)。
漢代在文章樣式和重大主題方面確立了一系列范型,而諸多范型之間又存在邏輯關(guān)聯(lián),構(gòu)成比較完整的體系。就此而論,可以說(shuō)漢代文學(xué)之所以在歷史上處于重要地位,很大程度上是因?yàn)樗_立了一系列范型。劉熙載稱:“西漢文無(wú)體不備,言大道則董仲舒,該百家則《淮南子》,敘事則司馬遷,論事則賈誼,辭章則司馬相如。”[37]10劉氏對(duì)西漢文章給以高度評(píng)價(jià),充分肯定它的歷史地位。然而,并非“西漢文無(wú)體不備”,中國(guó)古代還有許多文體是在西漢以后生成的。漢代確立了一系列文學(xué)范型,但是,中國(guó)古代文學(xué)范型的確立并沒(méi)有到此結(jié)束,而是還在繼續(xù)進(jìn)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