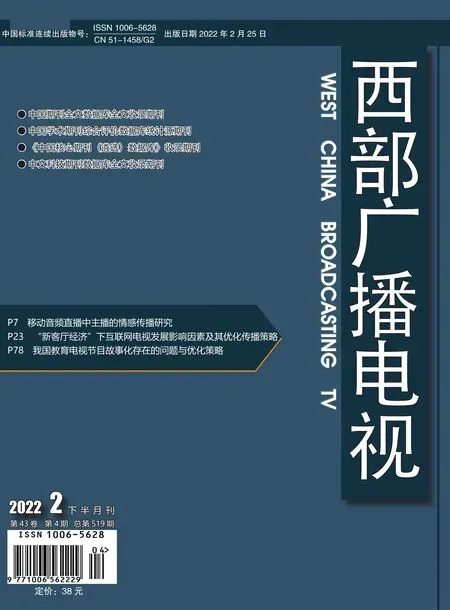兩極反饋:媒介融合背景下青少年媒介使用影響探究
楊靖毅
(作者單位:河海大學公共管理學院)
Web 3.0時代,在信息交互技術高度成熟的基礎上,5G、人工智能、大數據、區塊鏈等技術不僅改變了傳播生態,也改變了媒介使用環境,大眾的媒介接觸與使用狀況呈現出交互性強、涉及面廣、更新速度快的特點。如今的青少年作為“數字原住民”,是新興媒介的新一批使用者。在此背景下,關注青少年的媒介使用影響和反饋可以更好地了解“數字原住民”的媒介使用行為,從而更好地幫助其培養健康向上的媒介素養。目前,學界對于青少年媒介使用的研究僅僅停留在影響探究層面,不夠全面,因此本文首先分析與總結青少年的媒介使用情況與影響,在此基礎上提出假設并通過實踐證明,總結較為完整的反饋行為,為后續相關人員的研究提供幫助。
1 研究綜述
1.1 媒介融合背景
1983年,美國傳播學者浦爾首次提出“媒介融合”的概念,指各種媒介呈現出多功能一體化的發展趨勢。從技術層面看,21世紀以后,互聯網以極快的速度發展,隨著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技術革命的深化,媒介融合的大勢更是對傳播格局的重構起著深刻且巨大的作用[1]。在傳播格局融合重構的過程中,依托于5G、物聯網等技術,智能手機、平板電腦、智能手表等新一代媒介產品呈現出較強的交互性、便捷性,實現了媒介在時空維度的轉向,從而實現用戶在虛擬空間的互動。
1.2 青少年使用媒介現狀
青少年作為一個特殊群體,其特殊的根本便在于成長環境。如今12~18歲的青少年自出生以來便沉浸于數字化的環境中。相關數據表明,城鎮未成年人互聯網普及率達到93.9%,農村未成年人達到90.3%[2],也就是說,如今的青少年與數字互聯網已息息相關,媒介使用率較高。在日常生活中青少年媒介接觸行為和以往不同,以線下教育為例,學生除了使用傳統的書籍進行學習,教育類動畫片、短視頻及各種搜題軟件也為青少年攝取知識助力。以媒體使用類型為例,學生對于網媒的使用也遠大于紙媒、電視等傳統媒體。換言之,以“05后”為主體的這一代青少年是隨著媒介融合的趨勢成長起來的,研究其與媒介的雙向關系頗有意義。已有研究表明,“網絡新生代”的兒童對新媒體的適應性、依賴性較強;一個由新媒介組成的全新的環境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未成年人的生活和思維方式。
1.3 反饋行為
根據傳播學的定義,威爾伯·L·施拉姆與梅爾文·德弗勒等人所提出的傳播模式中都涉及受眾的反饋,指受眾也可以是傳輸者,以達到信源-受眾雙向互動的目的。根據控制論的定義,反饋就是控制系統把信息輸送出去,又把其作用結果返送回來,并對信息的再輸出產生影響,起到控制作用[3]。
而本研究中涉及的反饋行為則為控制學理論的遷移,青少年媒介使用是信息流輸送的過程,其產生的影響即控制論中所說的“作用結果”對青少年的媒介再使用產生的影響,起到正反饋(增加媒介使用行為)或負反饋(減少媒介使用行為)的控制作用。
2 研究設計
2.1 研究方法
為探究青少年媒介使用行為的影響和后續反饋作用,本研究先對相關文獻進行梳理與分析,然后對青少年媒介使用的影響進行綜述,并基于已有綜述提出假設:在媒介使用中存在反饋作用。同時,使用問卷調查的方式對反饋作用進行評價,驗證假設是否成立。首先,設計問卷,在筆者周邊的青少年群體中進行小規模抽樣調查,以0.7為量化標準,篩除可信度較低的問卷題目,多次篩除直至獲得一份成熟的問卷。而后以非概率抽樣的方式搜集南京市建鄴區、廈門市思明區、上饒市信州區三個地區部分青少年(12~18歲)的相關數據,并對數據展開描述性分析,用M表示題項得分的算數平均值,評價數據的總體水平;SD表示題項得分的標準差,評價數據的離散程度,這兩項指標可以幫助筆者更好地評價青少年媒介使用的反饋作用。
2.2 問卷設計
2.2.1 控制變量
人口統計變量。人口統計因素主要包括被訪者的性別、年齡、目前學歷、家庭年收入。
2.2.2 反饋作用評價
作為本問卷的核心調查指標,本研究采用李克特五級量表對受訪青少年的反饋行為進行分析,用以評價他們的媒介再使用行為。例如:“你會因為搜題軟件的便捷性、高效性而在往后的答疑中都采用同類搜題軟件嗎?”“你會因為某些軟件(或電視節目、廣播頻道、雜志等)造成了不良影響(浪費時間、提供不良信息等)而放棄使用嗎?”“你會因為視頻軟件提供了自己想觀看的視頻而在往后的使用中都采用同類視頻軟件嗎?”等7個問題,這7個題項的均值構成了反饋作用的指標(M=3.49,SD=1.08)。
3 問卷數據
3.1 樣本組成情況
本研究的正式調查采用非概率抽樣的方法,于2021年7月14日至7月30日期間通過紙質問卷、問卷星在線問卷等形式在線下、QQ、微博等同時發布。被訪者自愿無償填寫,筆者共收集有效問卷109份,刪除年齡不在12~18歲的和答卷時間低于1分鐘的問卷,最終有效樣本量為108份,其中男性青少年47人,女性青少年61人。
3.2 描述性分析
在對青少年的反饋使用行為展開分析時,7個題項的均值達到了3.49(值域[1,5],SD=1.08),分值最高的題項為“你會根據媒介對自己的作用來改變使用時間與頻率嗎”(M=3.93,SD=0.72),分值最低的題項為“你每過一段時間會思考哪些手機軟件(或電視節目、廣播頻道、雜志等)沒有用并放棄使用”(M=3.04,SD=1.21),這表明受訪青少年在媒介使用中是存在反饋行為的,假設成立。
4 多重影響:媒介融合造就新形勢
本研究首先采用文獻搜集法等方式對青少年媒介使用的影響展開綜述,為后續反饋作用的實證調查奠定一定基礎。
4.1 積極影響
在媒介融合的大趨勢下,新興媒介對于傳統媒介傳播話語權的沖擊客觀上促成了泛眾化傳播時代的到來,也為當代青少年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媒介體驗環境與數不勝數的媒介接觸機會,讓青少年能夠更好地行使自己的參與權,更快地融入媒介圈子。
4.1.1 時空延伸:平等參與與高效交流
傳統認知上,包括青少年在內的社會大眾要想參與社會或者家庭事務,就必須親自在場。大多數時間里,青少年的參與權被極大地弱化或直接被成年人所接管,但在新興技術愈發進步的今天,一方面,青少年可以通過智能手機、平板電腦、智能手表等智能終端,利用互聯網技術打破時空上的限制,實現技術上的“在場”,在絕大多數地方都可以行使參與權;另一方面,如今青少年在媒介使用過程中會主動尋求信息、被動接收信息,許多以往只有成年人能接觸到的信息也可以同步地輸入青少年的認知中,青少年的參與能力會在潛移默化中得到提高,平等參與的可能性也極大增加。
同時,在當下的培養體系中,青少年的時間大多用來提高自我素質,青少年通過新興媒介可以將碎片化時間用以參與社會事務或其他事務。以微博為例,作為新時代的產物,該產品定位便是“隨時隨地分享新鮮事”,對于青少年來說,他們不僅可以隨時在微博、微信、QQ上發表心情或文章,還可以隨時在網絡媒體平臺上與屏幕前的另一個人進行交流,提高了交流的效率。
4.1.2 平臺打造:聚合興趣與獲得認可
圈子是以情感、利益、興趣等維系的具有特定關系模式的人群聚合[4]。以興趣圈子為例,人會以自我為中心尋找與自己有相同興趣愛好的人,并形成特殊的關系結構。在以往電視、廣播等主流媒介占據媒介市場時,青少年想要尋找情感寄托、興趣伙伴,就只能通過親友關系或經由特殊的活動、儀式集聚來實現,而新媒介的涌現打造了一批強關系社交平臺,幫助青少年達到了這個目的。以微博平臺的“超話”為例,每一個“超話”其實都可以視作是展現自我、交流同質情感的虛擬朋友圈。也就是說,未成年個體在圈子的尋找、構建及融入上獲得了更多自主性與便捷性。這其中的積極意義不僅僅在于擴大社交范圍,在心理學上這是一個尋求認可的過程,而融入圈子則是獲得認可的途徑。媒介融合的背景下,新媒體極大地加速了此進程。換言之,青少年在媒介使用中的獲得感、認同感、滿足感會大大高于從前。
4.2 消極影響
4.2.1 童年消逝:成人化的問題
尼爾·波茲曼在《童年的消逝》中,對童年消逝現象作出了經典論述,認為電子媒介不分觀眾,通過暴露成人的性、暴力以及成人世界的無能、競爭和擔憂,瓦解其對于兒童的神秘性,從而導致兒童羞恥心的喪失、童年的消逝[5]。
媒介融合背景下,新媒體借助5G、大數據、人工智能、物聯網等新興技術在傳播信息上打破了固有的物理區隔,可以傳輸海量信息,為青少年提供多領域、多層次、全球化的信息,這其中也包含著暴力、犯罪、色情等青少年原本接觸不到的有害信息。這些信息一定程度上擠占了青少年理應接受的友善、法制、自律等正面信息的空間,這是媒介融合背景下信息世界入侵青少年文化邊界產生的結果。首先,青少年正處于心智發育、價值觀養成的關鍵時期,其心理和心智的變化是與周圍環境互動協調的過程,因文化邊界消逝,他們或多或少地將接受成人世界的價值理念,如“金錢至上”“弱肉強食”“唯結果論”等,這有可能會催生浮躁、冷漠、功利的價值觀,讓他們失去原本該有的共情能力,導致他們價值觀念的成人化。其次,成人話語體系對未成年話語世界的入侵已成為學界共識,以往被視作成人專屬的話語——“臟話”如今在青少年的世界里也不再是秘密和禁忌,孩子們從繁雜的信息世界里接觸了許多跨越年齡的話語。青少年基于自己超強的學習能力對這些語言進行模仿,而后在社會實踐中進行呈現,這在一定程度上將導致青少年的言語暴力、粗鄙等,造成“行為-話語”體系的成人化。
4.2.2 隱私泄露:透明化的信息
麥克盧漢指出,“媒介是人的延伸”,這意味著手機等智能設備也具有私密性的特征,獲得的過程則以使用者的個人隱私作為代價。同理,青少年在使用網絡的過程中,其個人信息也會被高流動性、高互通性的互聯網所裹挾,大數據分析技術通過對用戶的立體化、全方位識別,使得青少年的個人信息透明化[6]。
從社交平臺的視角來看,目前各類網絡社交平臺并未對用戶年齡作出限制,社交平臺用戶低齡化早已成為全社會公認的事實,滿足自身社交需求是青少年網絡接觸行為的主要目的之一,青少年在網絡上的社交行為還在不斷延伸。而如今的網絡社交平臺融合態勢使得平臺間原本明晰的界限逐步被消解,青少年的信息將會在各平臺的后臺被窺視,也就是說,其信息泄露的風險也隨之增加。同時,隱私的泄露不僅會增加青少年遭受侵害的風險,也會增加其監護人的監護成本。
5 兩極反饋:基于資源保存理論
問卷結果顯示,青少年使用媒介后對于自身的影響會對具體的某項媒介使用產生反饋作用。青少年在使用媒介過程中,可以豐富自己的社交、學習、娛樂等資源,從中達到上一代青少年受技術局限而無法實現的網絡社會交往、線上獲取知識、多媒介娛樂行為等目的,對其自身產生了增強參與感、更快融入圈子等正面影響。基于資源保存理論,個體具有努力獲取、保持、培育和保護其所珍視的資源的傾向,為了持續獲得利己的資源,青少年將重復、增加媒介使用行為。以評價“搜題行為的反饋”題項為例(M=3.40,SD=1.06),青少年會因為某搜題軟件的便捷、高效而在往后的學習中多采用該途徑,人們無法保證搜題行為對于青少年真正的學習是否有益,但可以肯定的是,青少年的行為選擇中是存在正向反饋的。
資源保存理論指出,資源受損對于個體的影響遠大于獲得資源,也就是說,個體會傾向于及時止損。題項“發現隱私泄露后(收到陌生短信、電話等)你會減少或停止在互聯網上公布個人信息嗎?”(M=3.84,SD=0.82)的結果顯示,即使青少年社會閱歷不足,但在如今媒介融合大背景下,成年人的世界與青少年的世界邊界已經模糊,對于隱私泄露這一大眾化問題,青少年也有著自己的理解——避而遠之,即負向反饋。
6 結語
媒介融合是大勢所趨,邊界消融已無法阻擋。在新的生活場域中,媒介使用無可厚非地將帶來兩面性的影響,青少年一方面享受著媒介融合帶來的紅利,實現平等參與、高效交流,另一方面不得不面對成人化、隱私泄露等問題。在此基礎上,青少年后續媒介使用存在反饋效應,這為后續的研究奠定了一定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