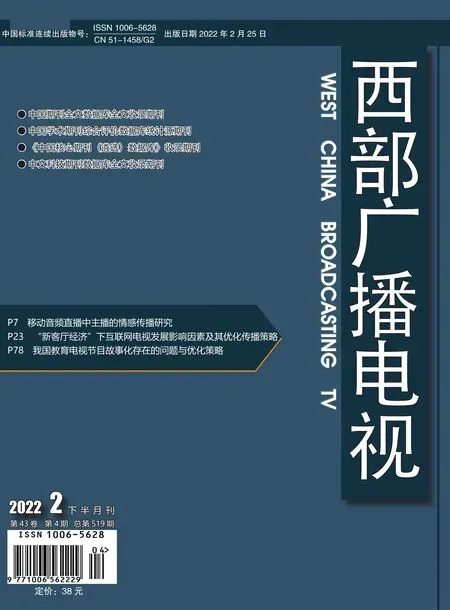紀錄電影《一直游到海水變藍》的藝術(shù)文化價值
楊若槿
(作者單位:中國海洋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
作為中國第六代導演群體的重要代表,賈樟柯執(zhí)導的電影始終關(guān)注并展現(xiàn)著中國現(xiàn)代化進程中的社會變遷和普通個體的生存狀態(tài),踐行著為當代社會存像的創(chuàng)作追求和反思現(xiàn)實的文化使命。2021年9月19日,賈樟柯導演執(zhí)導的紀錄電影《一直游到海水變藍》在國內(nèi)正式公映。在此之前,該片已經(jīng)在柏林電影節(jié)等多個電影節(jié)上進行展映,并在北美等地區(qū)發(fā)行。影片以中國當代著名作家馬烽、賈平凹、余華和梁鴻等的自述為線索,通過松散有序的結(jié)構(gòu)和影像美學的藝術(shù)化運用,回溯作家們成長的文化語境和創(chuàng)作的心路歷程,展現(xiàn)鄉(xiāng)土中國畫卷以及蘊藏其中的當代中國人精神還鄉(xiāng)的旨歸。
1 章回體結(jié)構(gòu):松散有序的口述史
對于賈樟柯導演而言,《一直游到海水變藍》是他繼《海上傳奇》之后,時隔10年再度回歸紀錄片創(chuàng)作的最新表達。該片源于其本人近年來返回故鄉(xiāng)賈家莊暫居的生活感悟,體現(xiàn)著導演對于中國鄉(xiāng)土文化的觀察和反思。影片從當下的社會現(xiàn)實場景出發(fā),根據(jù)2019年在山西省汾陽舉辦的主題為農(nóng)村或鄉(xiāng)鎮(zhèn)生活經(jīng)歷敘述,提煉出關(guān)乎日常生活的18個章節(jié),通過一種松散有序的敘事,以“從鄉(xiāng)村出發(fā)寫作”的呂梁文學季系列文化活動為契機,挖掘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創(chuàng)作與鄉(xiāng)土經(jīng)歷的內(nèi)在聯(lián)系。在此基礎(chǔ)上,賈樟柯導演選擇賈平凹、余華等四位不同年齡段的作家,借由他們對于自身的生活經(jīng)歷的敘述,連綴起一幅橫跨70年的鄉(xiāng)土中國的文化畫卷。
首先,從主體內(nèi)容來看,《一直游到海水變藍》采用“口述史”的紀實采訪形式,從山西出發(fā),輾轉(zhuǎn)陜西、河南和浙江多地,帶領(lǐng)觀眾走進四位作家的個人經(jīng)歷和創(chuàng)作之路。正如作家梁鴻所寫道:“所謂村莊的整體面貌,就是一個個生動的、相互糾結(jié)的家庭故事,是一個個鮮活的生命。”[1]在這個過程中,作家身為歷史的見證者,以文學為名重返歷史現(xiàn)場,體會日常生活的瑣碎與變遷。作為影片中的第一位主人公,賈樟柯選擇了曾在賈家莊下鄉(xiāng)的“山藥蛋派”代表作家馬烽,通過其女兒和同鄉(xiāng)老人的回憶,講述了馬烽帶領(lǐng)村民治理鹽堿地、創(chuàng)造糧食豐收,并最終離開北京,扎根三晉大地進行小說創(chuàng)作的故事;作為“尋根文學”的標志性人物,生長在陜西省商洛的賈平凹則圍繞著自己與父親的關(guān)系,將貧困年代的大家族生活、父親被勞改對于自身成長的影響娓娓道來,展現(xiàn)出時代變革對于個人命運的深刻影響;對于作家余華來說,在故鄉(xiāng)的醫(yī)院成長和工作的經(jīng)歷為他觀察世界提供了一種別樣的視角,對文化館工作的想象挖掘了他的文學天賦,并最終使其走上了創(chuàng)作之路;作為影片中唯一一位女性作家代表,出生于20世紀70年代的梁鴻深情地回憶了自己的家庭往事,包括久病沉默的母親、父親的再婚風波及大姐對于家庭的辛勤付出,描繪出無數(shù)中國家庭遇到的困境與溫暖。作家們對于過去生活經(jīng)歷和個人鄉(xiāng)土經(jīng)驗的紀實性口述,從多個側(cè)面聚合成一種歷史敘事的文化脈絡,實現(xiàn)了對于中國現(xiàn)代化進程的深描和反思。
其次,從形式結(jié)構(gòu)來看,影片呈現(xiàn)為一種松散有序的章回體敘事架構(gòu)。賈樟柯導演將作家們的個人故事和口述信息重新建構(gòu),進一步提煉為吃飯、戀愛、生病、遠行、父親、姐姐、兒子等18個關(guān)鍵詞,并以標題化的字幕呈現(xiàn)。每一章節(jié)的長短各異,引領(lǐng)觀眾由關(guān)注作家的個人敘事進一步深入對日常生活和生命本身的觀照,從而試圖建構(gòu)起一部描繪中國人在時代變遷下的心靈史。在此過程中,賈樟柯導演還展現(xiàn)了大量的現(xiàn)實場景片段,如養(yǎng)老院中老人們排隊打飯、送餐的外賣員在街道中穿梭、西安火車站前旅客們聚集往來、農(nóng)民在麥田中收割勞作的場景……這些現(xiàn)實場景穿插在作家們的個人自述之中,使得時間上的過去與現(xiàn)在、空間上的此地與遠方在屏幕前交錯匯聚,有效地增強了影片敘事的歷史感和真實性。此外,圍繞著作家這一核心敘事要素,影片還設(shè)計了多段普通人朗誦文學片段的鏡頭,將不同作家對于故鄉(xiāng)的闡釋予以呈現(xiàn),形成了對于不同篇章主題的呼應,使影片敘事節(jié)奏更加靈活豐富。至此,作家口述、現(xiàn)實場景、詩歌朗誦這三部分作為影片的主要架構(gòu),形成了賈樟柯導演對于鄉(xiāng)土文化的探索與追尋。
2 藝術(shù)化策略:交疊凝視的美學時刻
法國著名電影理論家馬塞爾·馬爾丹曾說:“在紀錄片的創(chuàng)作中,不是將思想處理成畫面,而是通過畫面去思考。”[2]對于電影《一直游到海水變藍》而言,如何用影像這一視聽綜合藝術(shù)將個人經(jīng)驗與時代變革、文學表達與生活呈現(xiàn)有效地結(jié)合起來,是這部紀錄電影要解決的關(guān)鍵問題。一方面,賈樟柯導演通過“文學與故鄉(xiāng)”這一敘事母題,為影片中四位作家口述史的展開奠定了基礎(chǔ);另一方面,則是通過對于影像美學的藝術(shù)化運用,充分展現(xiàn)并深化影片的思想內(nèi)涵。
首先,從影片的視聽呈現(xiàn)來看,其依舊延續(xù)了賈樟柯導演標志性的紀實美學風格,充分踐行著巴贊“影像本體論”的理論本質(zhì),即“攝影的美學特性在于揭示真實”[3]。電影使用了大量的固定機位和長鏡頭,通過對于一定段落時間的完整記錄,使影像具有“自己說話”的藝術(shù)魔力。無論是《三峽好人》中對于船艙乘客的描摹,還是《江湖兒女》中關(guān)于棋牌室的刻畫,回顧賈樟柯導演的電影創(chuàng)作,可以發(fā)現(xiàn)他對于群像面孔的特寫式塑造具有一種強烈的偏好,這種造型取向在這部紀錄電影中被表現(xiàn)得更加淋漓盡致。養(yǎng)老院中,老人們清晰可見的皺紋,是歲月給予人的寧靜與安詳;火車站前,旅客們行色匆匆的神態(tài),是日常生活的奔波與勞碌;學校食堂中,年輕人刷手機的笑容,是當下社會最常見的交往情境。賈樟柯導演用最忠實的影像刻畫著鮮活的生命個體和轉(zhuǎn)瞬即逝的現(xiàn)實存在,這些被鏡頭捕捉到的普通人群像,展現(xiàn)出的是蕓蕓大眾被忽略的、最真實的生存狀態(tài)。在鏡頭的凝視下,一張張帶有生命印跡的“自然臉”在鏡頭的特寫下化身為一個個動人的肖像,讓觀者在相對靜止的畫框中感受到一種情緒留存和張揚,他們與被鏡頭聚焦的作家們并置,作為時代變遷中社會影像檔案的一部分,生成了一種樸實而動人的美學意味。
其次,除了對于群像面孔的獨特描摹,賈樟柯導演還刻畫了普通人作為“朗讀者”的形象,將文學還原至生活的現(xiàn)場,進而探究文學與人、文學與現(xiàn)實的關(guān)系。正如契訶夫說:“現(xiàn)實主義按照生活的本來面目描寫生活,而最優(yōu)秀的作家都是現(xiàn)實主義的。”[4]無論是賈平凹的《雞窩洼的人家》、余華的《活著》還是梁鴻的《中國在梁莊》,幾位優(yōu)秀的現(xiàn)實主義作家身上所具有的鄉(xiāng)土文化特性為影片敘事的展開奠定了基調(diào)。但賈樟柯導演并沒有選擇讓作家本人充當文學的闡釋者,而是將解讀文學的權(quán)力交給了普通人。于是,影片中出現(xiàn)了這樣的片段:在田間勞作的農(nóng)婦自信、高昂地朗誦著于堅的詩歌“高舉著鋤頭,猶如高舉著勞動的旗幟”;年輕的女子在橋頭深情地朗誦著沈從文的名篇“橋的那頭是青絲,橋的這頭是白發(fā)”;鄉(xiāng)村青年在樹林旁朗誦著賈平凹的散文“你生在那里其實你的一半就死在那里,所以故鄉(xiāng)也叫血地”。在這樣的場景下,文學作為一種表意符號被提煉出來,但又被戲劇性地置于生活之中,建立起人與世界之間隱秘而流動的聯(lián)系。在詩歌和散文的指引下,這些普通民眾從現(xiàn)實生活的日常動作中停下來,短暫地進入文學的世界,通過語言、姿態(tài)和情感傳達著自己對于文學的感知和理解,呈現(xiàn)出一種脫離世俗庸常的詩意氣質(zhì)。在這樣的時刻,文學不再是觸不可及的高雅存在,而是每個人所面對的生活本身,其賦予了普通個體擁有同等文化記憶的權(quán)力,彰顯出生命本身的尊嚴和光輝。
再次,這部電影對于聽覺符號的巧妙運用,也為影像敘事的審美表達提供了重要支持。對于賈樟柯導演而言,方言的使用是其電影創(chuàng)作的一個顯著標識,代表著一種重要的地域指向和文化身份。作家們帶著各自獨有的鄉(xiāng)音出場,賈平凹樸實厚重的陜西商洛口音與余華風趣明快的浙江海鹽腔調(diào)形成了鮮明對比,有效地塑造了豐富的人物形象,并與作家們的方言寫作形成了一種呼應。除此之外,賈樟柯導演在紀錄片中還將戲曲納入標志性的方言表意系統(tǒng)中,更加凸顯出不同地域的傳統(tǒng)文化特征。對應著不同作家的段落,賈樟柯導演將晉劇、秦腔、越劇與豫劇適時地穿插其中,有效地推動著影片的敘事進程。在這個過程中,作家們時而化作講故事的人,時而成為戲曲舞臺的欣賞者。戲曲作為傳統(tǒng)文化的重要形式,與文學一起承擔著傳承歷史經(jīng)驗和民族記憶的重要功能。與此相對的是,賈樟柯導演還在影片中大量使用了包括鋼琴和大提琴在內(nèi)的西方古典樂器,這在其之前的創(chuàng)作中是極少出現(xiàn)的。古典音樂所具有的結(jié)構(gòu)性和韻律感,可以成為不同章節(jié)之間的紐帶,配合著作家們的個人講述,營造出一種相對平和莊重的氛圍。作為一種聽覺媒介元素,西方古典音樂與方言戲曲代表的地方文化形成了強烈的對比,有效地增強了影片的敘事張力和審美表現(xiàn)力。
3 人文性旨歸:精神還鄉(xiāng)的歷史意識
影片《一直游到海水變藍》最初構(gòu)思的名字是《一個村莊的文學》,但最終呈現(xiàn)的內(nèi)容并沒有局限在“文學還鄉(xiāng)”的主題設(shè)定上,而是轉(zhuǎn)向了對于當代中國人的“精神還鄉(xiāng)”這一更大命題的探究和呈現(xiàn)上。在這個敘事過程中,賈樟柯導演帶著自己對于鄉(xiāng)土文化的觀察出發(fā),選擇四位不同年代的作家以“口述史”的方式記述各自不同的鄉(xiāng)土經(jīng)驗和生活往事,串聯(lián)起中華人民共和國七十余年的社會變遷。賈樟柯導演認為電影是“一個記憶的方法”[5],其不僅是個人情感的寄托和表達,還可以從電影中找尋某個歷史階段中國人的日常生活狀態(tài)。
對于賈樟柯導演而言,在山西汾陽小鎮(zhèn)的成長經(jīng)歷使他將攝影機堅定地投向了默默無聞的小城和鮮活各異的普通人,關(guān)注并記錄著時代變遷中的個體命運。在這樣的拍攝理念的指引下,影片并沒有過度聚焦在作家與作品本身,而是在保留文學性的基礎(chǔ)上,盡可能地將作家還原為普羅大眾,使他們跟隨著時代變革的步伐,將私人化的鄉(xiāng)土記憶和歷史經(jīng)驗娓娓道來。對于賈平凹來說,回憶起身處窮困年代的少年生活,他講述了大家族一同吃飯藏勺子的趣事,當談到因父親被下放而自己前途未卜時,凝重的語調(diào)背后是那一代人無法回避的傷痛;對于余華而言,政治動亂的陰霾已經(jīng)逐漸遠去,留在記憶中的是在太平間午睡的涼爽體驗,以及第一次前往北京改稿并且盡興游玩的美好時光,折射出20世紀80年代的社會變革與精神風貌;而在梁鴻看來,有關(guān)故鄉(xiāng)的記憶更多是關(guān)于家庭的傷痛,因病臥床的母親像是一道陰影,父親的再婚風波和長姐的無私奉獻仍是她難以忘卻的心結(jié)。在影片中,作家們重返文學創(chuàng)作的生養(yǎng)之地,身處在街邊的小飯館、常見的裁縫店、古樸的戲臺等這些充滿生活氣息的空間,面對攝影機袒露著自己的心緒過往。這些關(guān)乎人倫親情、生老病死的生命命題,正是每一個普通人都要面對和思考的,這種由個體記憶和生活經(jīng)驗建構(gòu)起來的歷史細節(jié),其表征著某種時代普遍性。正如賈樟柯導演在采訪中所談到的:“我希望能夠通過四代作家的接力表達,來談一談幾代中國人的心事。”[6]
就像影片《一直游到海水變藍》所隱喻的,一代代人都是他們所處時代的弄潮兒,每個人都迎著潮水而上,向著理想的海域進發(fā),而那些試圖掙脫卻無法回避的東西,就是每個人所面對的鄉(xiāng)土記憶和時代烙印。回不去的遙遠故鄉(xiāng)與不可磨滅的成長記憶,成為每一代人懷舊的主題。同賈樟柯導演一樣,作家們從家鄉(xiāng)走到大城市,被裹挾進現(xiàn)代社會的快速變革中,但他們的創(chuàng)作根基始終在故鄉(xiāng)。他們有意識地從城市返回農(nóng)村或小鎮(zhèn),在各自的生養(yǎng)之地徘徊守望,尋找、確認并傳承各自的鄉(xiāng)土記憶,以故鄉(xiāng)為根據(jù)地,探尋萬千變化的世界。如同跟隨著母親梁鴻返鄉(xiāng)的兒子一樣,這些生長在城市的當代青年們,正試圖尋找祖輩生活的印跡,重新學習熟悉又陌生的鄉(xiāng)音。對于快速發(fā)展的中國社會而言,鄉(xiāng)土文化對于當代中國人的情感結(jié)構(gòu)和精神文化的塑造有著深刻的影響,為人們觸摸歷史、理解現(xiàn)實提供了重要的落腳點和歷史維度。
回望賈樟柯導演的創(chuàng)作歷程,他始終用一種略顯“粗糙”的紀實影像風格和緩慢沉穩(wěn)的敘事節(jié)奏,注視著中國艱難的現(xiàn)代化進程中社會底層人物,甚至是邊緣人物的離合悲歡,展現(xiàn)出個人命運與時代發(fā)展的映射與沖突,使觀眾在他的影像世界中尋找到回憶和人生經(jīng)驗。從《二十四城記》《海上傳奇》這兩部紀錄片開始,賈樟柯導演關(guān)注普通個體的文化記憶成為其電影中反復咀嚼的主題。通過紀實口述等方式,呈現(xiàn)中國人內(nèi)在的精神特質(zhì)和情感結(jié)構(gòu),展現(xiàn)時代變遷對于社會及個人的深刻影響,建構(gòu)起一種理解當代社會現(xiàn)實的文化路徑,以觀照人們當下生存的危機與焦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