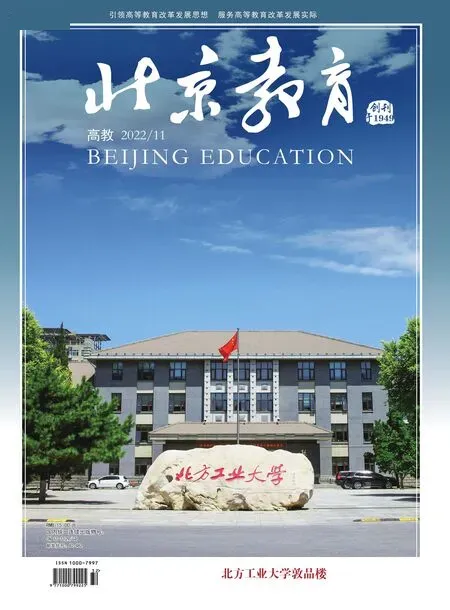學科融合視角下科研團隊組織模式變遷及權變分析
——以北京大學和東京大學為例
□ 文/姬 懿 李芳敏
交叉學科團隊建設是交叉學科發展的重要根基。隨著知識的創新、發展與進步,單一科研人員已經很難緊跟多門學科知識的更新與進步[1]。而現實社會對科技發展與進步的需求又刻不容緩,這使得科研的發展不得不從個體的、自發的科研向集體的、團隊的科研工作轉換[2]。那么,高校交叉學科研究團隊組織模式究竟經歷了何種變遷?受哪些因素的影響?本文擬通過比較北京大學和東京大學的交叉學科團隊組織模式,擬重點采用權變理論①進行詮釋和解答。
北京大學和東京大學交叉學科團隊組織模式的比較
1.北京大學交叉學科團隊組織模式變遷與現狀
北京大學交叉學科經歷了一個從自發到有組織、從虛到實、從散到合的發展過程:20世紀90年代,北京大學的交叉學科研究開始出現了以人才培養為核心的跨學科組織模式,如課程、研討班、講座等,交叉學科團隊建設仍無固定的、特殊的形式,以自發的組織為主。21世紀初,北京大學出現了一批以跨學科為目的的研究機構。例如:2000年10月,北京大學成立了生物醫學跨學科研究中心(Biomed—X Center of Peking University),雖然學校并未給該中心配備額外資源,參與者的人事關系和管理體制均保留在原院系不變,在跨學科中心參與的事項僅可作為社會服務考核中的內容體現,但這已經成為跨學科研究團隊具體依托的機構雛形。
從21世紀初至今,北京大學已經發展成立了多個跨學科中心,初期以理工科領域為主,如分子醫學研究所、定量生物學中心等,后期還出現了西方古典學中心、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院等人文社科領域的跨學科研究中心。2006年,北京大學成立了前沿交叉學科研究院,將生物醫學跨學科研究中心等11家研究機構的學生管理、招聘引進、學術交流等多項事務納入統一管理。至此,北京大學的跨學科團隊組織模式開始逐漸地正規化、規范化,團隊組織模式逐漸形成三種發展模式:一是自發組織的“民間”團體,基于個人興趣匯集在一起;二是依托于虛體研究機構,這類機構對團隊的管理多起到聚合作用,學校并不投入實際的資源,更多的是爭取外部支持;三是依托于實體研究機構的團隊組織形式。實體機構又分為掛靠類實體研究機構,這類機構的管理更多依靠于院系,院系原有的研究團隊和機構的研究團隊結合得更為緊密,希冀其相互碰撞獲得學術創新。而另一類則是獨立實體研究機構,他們的團隊組織則更加自主,從人才引進、人才評估考核到后期的各項人事業務均由其自行管理。實體研究機構已成為學科交叉的重要力量,截至目前,北京大學共成立了49個學術實體研究機構,其中跨學科類33個。實體研究機構的蓬勃發展為跨學科團隊的發展提供了土壤。
2.東京大學交叉學科團隊組織模式變遷與現狀
20世紀70年代,東京大學開始實行“大講座制”,是較為初期的交叉學科團隊組織模式。“大講座制”中的每個講座由1個或多個研究方向構成,每個研究方向由1位教授、1位~2位準教授或講師和若干位助教組成,并會相應配有1間研究室。
2005年—2008年,東京大學牽頭組建了多個跨學科研究機構,這些機構成為全校知識創新平臺。例如:系統疾病生命科學先進醫療技術開發據點(Translational Systems Biology and Medicine Initiative,以下簡稱為TSBMI)[3],該組織形成了與多個研究機構之間的聯合狀態,研究人員具有極強的流動性。這種開放性為具有不同學科背景的人員之間的學術目標、學術興趣甚至合作方式的契合提供了良好的機制。
目前,東京大學交叉學科組織已經發展出多種形態,有的交叉學科組織是實體型的,具有正式的組織建制、專職的研究人員、獨立的場地和實驗設施;有的交叉學科組織是虛實結合型的,即在容納多學科的綜合性學院中設立的各種交叉學科實驗室、研究中心、研究所,這些機構雖然有組織構架并經常舉辦各種前沿講座和會議,但其研究人員和學生的身份都歸屬在各個院系。
團隊組織模式變化的權變因素分析
1.外部環境:高等教育的變革
1999年,中央和教育部先后提出,要進一步轉變高校治理模式,加強了高校辦學自主權。高校辦學自主權的增大,使學校在人事管理方面的權利相對獨立,編制、崗位嚴控的局面已更多轉變為總量控制。學校能夠更自主地調配其內部資源,這為一部分交叉學科機構誕生提供了制度土壤。
日本也基本于同期開展了法人化改革。2003年7月,《國立大學法人法法案》和另外五個與國立大學法人化相關法案的頒布,標志著國立大學獨立行政法人化改革正式開始。改革后,日本的國立大學都相應獲得了獨立的財政權,可自由支配取得經費。約在一年后,東京大學便大力發展了多個跨學科中心,積極布局交叉學科,這些跨學科中心慢慢擁有了獨立的科研團隊和經費。
2.戰略:學校目標的轉變
2007年,《北京大學章程》制定工作啟動,該項工作于2014年完成。章程的發布明確了學校的使命、愿景和責任。例如:章程“第二章職能”的第一條,即學校動員和組織資源,優化資源配置,主要發展自然科學、人文學科、社會科學、醫藥科學、工程與技術科學,開展人才培養、科學研究、文化傳承創新、社會服務,開展深入、廣泛的國際交流與合作。可見,學科建設是大學的首要職能之一,且學科被分為了不同類別,為了讓學科做大做強,大學必須發展出與之相匹配的組織模式予以支撐。
2005年,《東京大學2005-2008行動綱領》對大學的發展重點進行了闡述,它提到大學戰略實施的兩個重點是“自律分散協調系統”和“知識的構造化”[4]。知識的構造化實際上就是要構建起有利于現代知識創新實踐的學科發展的組織網絡體系。這些變革也導致了東京大學交叉學科科研團隊組織模式的變化。隨著學校戰略目標的轉化,東京大學的跨學科建設已經逐漸上升到了戰略高度,跨學科團隊的組織也越來越規范,由原先的游散于各個院系到后期的專職再到最后的大學院制集合性組織。
3.規模:教師數量激增
從20世紀末至今,東京大學和北京大學的規模和人才引進方式都發生了較大變化。1997年,日本頒布了《關于大學教師等的任期制的法律案》后,日本公立、私立大學廣泛采用聘任制,東京大學也不例外。北京大學改革稍晚,2014年,全面推行“預聘制—長聘制”(Tenure Track-Tenured)。這些變革都讓人才引進、評估、晉升成為學校的常規業務固化下來。目前,在北京大學已形成每季度召開人才引進、晉升會議的工作慣例,這些都直接導致跨學科團隊的管理方式必須依托于某一院系或獨立實體機構的學術委員會。
4.內部環境:成員素質
無論是北京大學還是東京大學,教師的素質和結構也都發生了較大的變化,隨著海歸群體的增多,教師對跨學科研究的重要性和關鍵性都有了更深的認識。從跨學科團隊的構建看,北京大學和東京大學后期跨學科機構引進的人員層次都比較高,有些是在世界范圍內有較高聲譽的學者。這些學者大多帶來了自己的支撐團隊,并將這種跨學科交流的文化和氛圍進一步根植高校。
結論與展望
北京大學和東京大學交叉學科團隊組織模式都經歷了一個從自發性組織到實體性組織的過程,并根據外部環境和團隊科研項目特點建立符合團隊本身的發展模式,最終建立適應環境發展需求、契合團隊內部發展規律的發展路徑。不同之處在于,東京大學跨學科研究團隊的組織對實體研究機構的依賴相對較小,方式更加多樣,對學校資源的需求也相對更低。基于權變理論的分析框架,本文認為,交叉學科團隊組織模式是基于其根植的外部環境調整形成的,為了更好地促進交叉學科團隊建設,我國高校在交叉學科團隊的環境建設方面應予以加強。
第一,要建立真正促進學科交叉的制度環境。現有高校人事管理必須有實體依托,如北京大學的人才引進、評估必須由院系或獨立實體中心組織同行評審、學術委員會審議等,還需要出具院系評估、推薦意見和師德師風審核,因此由院系(所、中心)統籌的管理方式必然會長期存在。但在此基礎上,我國高校可多推廣交叉學科項目、多搭平臺、多配資源,以項目制吸引和聯合教師。例如:東京大學在交叉學科發展中特別注重利用校外資源,如與相關企業集團、科研院所、醫療機構都建立了合作伙伴關系,開展交叉學科交流活動,這種做法大大降低了交叉學科對實體中心的需求與依賴。
第二,要特別注意對部分團隊的精準支持,充分挖掘、激活現有團隊活力。目前,很多高校在長期發展過程中培育了一些團隊,其中不乏成熟群體,如北京大學人工智能團隊已與校內工學、計算機科學、醫學、藝術等團隊均建立交叉與聯系。發展交叉學科并不一定非要做增量,高校可在現有成熟團隊基礎上,適時地引入整合其他學科資源,并加以重點培養和扶持,特別是要注重對團隊首席科學家的重點扶持和資源傾斜,使現有團隊以最小的資源消耗迅速成長起來。
第三,要建立促進交叉學科發展的人事評價體系。例如:北京大學的人才評估小組特別注重理科、工科交叉,人文和社科交叉,注重人員構成中的學科平衡。同時,北京大學建立了相對完善的聯合聘用制度,在考核評價時充分考慮教學科研人員在交叉學科平臺方面的工作量,使在交叉學科平臺供職的教學科研人員有了制度和政策的保障。
注釋:
①權變理論,是系統設計思路的一個重要分支,其核心思想是強調設計決策取決于環境條件,是對環境權衡的結果,即將組織看作一個開放的動態系統,側重點在于組織結構必須根據所處環境的變化而不斷地進行調整。權變觀點的最終目的在于提出適宜具體情況的組織設計和管理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