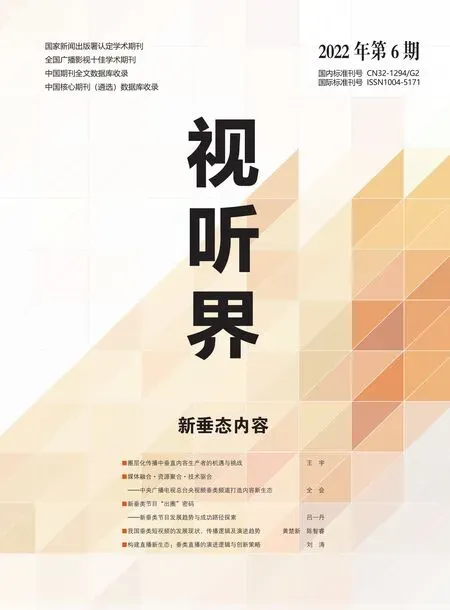記憶再塑與個體敘事:新媒體語境下人文紀錄片的社會記憶構建
駱靜瀟
近些年,一批高質量的國產人文紀錄片在電視與網絡空間中相繼熱播。這些紀錄片不僅收獲了國內多個年齡圈層受眾的好評,有些還“出口”海外,成為他國人民了解中華文化和中國社會風貌的窗口。不難看出,人文紀錄片呈現出強大的文化感召力,或可作為構建社會記憶的材料,成為聯結代際差異與文化區隔中斷裂縫隙的媒介。
但在媒介技術的視角下,社會的記憶只有通過特定的媒介才得以被傳播、固定下來。那么在當今的媒介生態下,社會需要怎樣的記憶?人文紀錄片又通過何種方式書寫社會記憶?本文從媒介與記憶的雙重視角出發,通過對人文紀錄片的研究管窺再塑社會記憶的方法。
一、新媒體環境下社會記憶的傳播特征
自20世紀80年代起,學界逐步將記憶研究的對象由個體擴大至群體,其研究的理論框架也從精神分析、心理學走入更廣闊的人文社科領域。個體的記憶生發于人腦的思維之中,那么由無數個體組成的社會是如何擁有記憶的?社會的記憶又是如何產生與儲存的?這是彼時學者著重關心的問題。雖說學界還未能將“社會記憶”予以一個準確的定義,但社會記憶的存儲與傳遞離不開特定的媒介。如傳統節日只有將其內涵熔鑄于身體的儀式化實踐與典籍的書寫實踐之中,可作為一種文化力量喚醒社會集體的共時性認識,進而完成歷時性的社會記憶構建。因而,無論是在口耳相傳的原始社會,還是文字、印刷盛行的工業時代,媒介始終是社會記憶傳播的主要工具。
同樣,媒介自身的邏輯也對社會記憶的構建方式產生影響。在“萬物皆媒”的網絡大眾傳播時代,媒介的運行邏輯日益滲透到大眾生活的諸多方面,社會的媒介化進程愈發迅猛。[1]因而媒介作為一種技術力量,成為形塑社會記憶形態的關鍵因素。在新媒介技術的影響下,媒介表達權利的不斷下移充分釋放了個體意識,進而促使海量且龐雜的內容涌現于互聯網空間。這使得社會記憶的話語內容和構建主體從單一走向多元,不斷沖擊著主流話語對于社會記憶的構建能力。
海量的媒介內容重塑了用戶的媒介使用習慣和表達方式。現如今,表達音量被不斷提高的個體成為參與記憶建構中的關鍵意見領袖,以快節奏為主要特征、個性化算法為推薦機制的短視頻構成了儲藏社會記憶的一種形態。由此不難推斷,當下媒介技術與記憶生產的綁定日益牢固,受互聯網傳播語態的影響,原型記憶被碎片化的視覺影像所肢解。而在蕪雜的媒介內容中,真實與虛假常相伴而行,短時長與片段式的表達是吸引用戶的手段,強烈的感官刺激體驗成為提升內容產品觀看數據的重要方法,用戶困在平臺所編織的信息繭房中,往往斷絕了與更多元社會碰撞的機會。個性化的釋放與集體性的消弭,昭示著一個充滿后現代性與斷裂性的時代來臨。弗雷德里克·杰姆遜在論述后現代主義特征時說:“那種從過去通向未來的連續性的感覺已經崩潰了,新時間體驗只集中在現時上,除了現時以外,什么也沒有。”[2]除卻社會原型記憶的崩塌,在向現代社會轉型的歷史契機下,原有的社會關系也一一瓦解,并代之以一個個零散的利益族群和“文化部落”[3],社會本身也呈現出“碎片化”的特征。因而在新媒體時代形成一個橫亙于社會之上的集體記憶,顯得尤為困難。
二、人文紀錄片再塑社會記憶的價值
(一)社會記憶的價值
法國年鑒學派的代表人物莫里斯·哈布瓦赫在《論集體記憶》一書中將記憶的研究納入社會的框架之中,因而其能闡明群體記憶的生成機制。他認為,群體性的記憶“是一個社會建構的過程”[4]。這種構建性不僅體現在自身形態的組成方式中,更體現于其能影響社會中的個體記憶。在個體記憶的構成中,人的主觀經驗雖能占據一席之地,但社會性因素也同樣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成長于不同民族背景下的個人對同一歷史事件常有著相異的記憶,對于個體而言,社會記憶作為一種能確證自我存在的媒介,構成了其行動的依據和自我身份認同的來源。而社會集體記憶的構建,則關涉到社會中個體與集體、個體與個體間關系的狀態,是維系社會團結穩定的結構性要素。正因如此,社會記憶的構建方式成為被爭奪的意識形態“高地”,成為喚起個體的情感認同,凝聚廣泛社會共識的重要方法。
(二)人文紀錄片在構建社會記憶中的優勢
多元化、淺層化與碎片化的表達特征引發社會集體記憶的缺失。在新媒介環境下,人文紀錄片可作為一種特殊的記憶刻寫實踐,成為整飭、再塑社會記憶的媒介,原因體現在語言學概念、拍攝內容與表現形式這三個方面。在認知語言學的視角下,當約翰·格里爾遜將紀錄片命名為documentary一詞時,詞干document(作為名詞,翻譯為“文獻、文檔”)便構成了其基本層次范疇的概念。[5]繼而不難推斷,自誕生之初,以真實性為敘事準繩的紀錄片便蘊藏著承載社會記憶的文獻價值,而弗拉哈迪早期的影像實踐也恰好證實了這一點。就人文紀錄片的內容而言,鮮活的文化生活和多情的風土是其攝像機對準的拍攝主體。人文紀錄片將遠方的風景與遙遠的歷史藝術化地呈現在觀眾眼前,有機地為觀眾構建起對社會與民族的認知框架,因而成為構建社會記憶的絕佳素材。就接收端而言,人文紀錄片所提供的兼具真實性與具象化的視聽影像文本,能給予觀眾更為沉浸的審美體驗。而在視覺影像當道的數字化時代,人文紀錄片更彰顯出綜合調用視聽元素的潛力,如在《但是還有書籍》《早餐中國》《守護解放西》等網絡人文紀錄片中,創作者便有意在紀實性畫面之上添加手繪動畫、圖表、特效花字等視覺元素,這樣的內容構建方式不僅符合觀眾的媒介審美取向,也向觀眾提供了一個更多元、可感的內容空間。由是觀之,人文紀錄片成為新媒體語境下負載社會記憶的重要媒介。
三、以個體敘事為特征的社會記憶書寫方式
人文精神“是對‘人’的‘存在’的思考;是對‘人’的價值,‘人’的生存意義的關注”[6]。而以彰顯人文精神為創作旨歸的人文紀錄片,在敘事上便格外關注對個體生存狀態的描摹。如在反映藏地風情的紀錄片《第三極》中,藏區壯美的山川湖泊只是作為該片的陪襯,而一個個生長于高原上的人則成為影片著重刻畫的對象。創作者正是通過對藏地居民日常生活的忠實記錄,使其得以呈現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獨特藏地風貌。進入新媒體時代,宏大敘事日漸消隱,以個體經驗為切口的敘事方式也更契合觀眾的審美期待。以《我在故宮修文物》為代表的人文紀錄片在網絡空間的“走紅”,便足以證明個體敘事的藝術魅力。而個體的經驗在社會記憶的書寫中同樣占據著重要地位。如果說社會記憶是一條涌動著的大江,那么個體的記憶便是散落在江邊的一條條支流。只有當鮮活的個體記憶不斷地向“干流”涌入,社會記憶的江河才能更加豐盈充沛,而個體記憶的支流也在干流的補給下愈發生生不息。因而不難發現,個體既是社會記憶傳播的落腳點,又是構成社會記憶的重要元素。正緣于社會記憶與個體記憶間的耦合性關系,人文紀錄片常以個體敘事方式實現對當代社會記憶的構建,并具體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一)題材選取:差異性文本的提煉
紀錄片的核心并非是簡單地復制現實,而是要“揭示隱藏在生活表象之后的真理”[7]。敏銳捕捉具有差異性的特征個性化經驗是人文紀錄片能深入展露社會風貌的原因。從藝術傳播的角度,差異化的題材是吸引觀眾觀看的有效方式,而對個體經驗的挖掘則是創作者所力圖展現的宏觀性社會記憶的顯影。如央視出品的歷史微紀錄片《如果國寶會說話》,在選題上與以往的歷史類人文紀錄片呈現出明顯的差異。《如果國寶會說話》并未選擇大眾所熟知的文物,而以更寬闊的視野將眼光從中原投射到邊陲,從上古延伸到近代,以差異化的視角勾勒出中華文明蜿蜒的脈絡。差異性同樣體現于文本的敘事方式中,該片放棄長篇累牘的宏觀敘述,而將古代文物作為凝聚民族文化精神的記憶刻寫符號,以每集五分鐘的敘事體量講述蘊藏于國寶之外的中國精神。
差異化的文本需經創作者的重新編排與提煉,方能使觀眾對陌生的事物產生情感認同。在《三星堆青銅人像》一集中,片中解說詞在描述性話語與抒情性話語間靈活地切換,使本集主題得以深化。在片尾解說詞的寫作中,創作者卻一改陳述性的敘述方式,娓娓道來:“與他們對視,那些超越語言的心動,也許就是我們心中的謎底,我們是人,我們站在這里,站在地球上。”在片尾解說詞的尋喚下,觀眾與同樣生長于中華大地的遠方文明產生了奇妙的聯結,并與影像文本產生有機的情感共振。由此,差異性的文本便在創作者的提煉與轉譯中,悄然實現了對社會記憶的書寫。
(二)敘事角度:多元的“微”視角展演
蘇聯電影理論學家吉加·維爾托夫所創造的“電影眼睛”理論,對世界紀錄影像的創作有著很深的影響。他認為攝像機遠比人眼更能捕捉到客觀的現實,因而在“探索充塞空間的那些混沌的視覺現象”[8]時,攝像機有著更大的優勢。誠然,在記錄過程中,作為機械的攝影機有著無可置疑的客觀性。但在紀錄片的實際拍攝過程中,創作者可通過把握敘事視角的選擇權,來傳遞自身的價值判斷和創作追求。而不同的敘事角度則為影片打造出獨特的藝術風格和內容構建方式。在新媒體語境下,人文紀錄片多從小切口的個體經驗出發,通過對個體行動的記錄來展現社會的文化面貌。而在其社會記憶的構建之中,單一的個體經驗只有被編織在具有一定意義的敘事框架中,個體記憶才獲得參與社會記憶構建的“準入證”,否則個體記憶便只是缺乏時間與空間連貫性的碎片化畫面。[9]因而在微觀化的敘事視角中,人文紀錄片的創作者常以整合大量零散的個體行動為基礎進行敘事框架的搭建,以便將眾多獨立的個體經驗推向社會集體記憶的構建之中。
從橫向來看,吸納多元視角意味著更多個體記憶的涌入,體現出記憶總量的積累。如在央視網出品的紀錄片《人生第一次》中,編導仿照單元劇的制作模式,選取人生中具有儀式化意義的12個節點,如出生、長大、上學等,勾勒出中國人一生的成長軌跡。影片以充滿溫暖詩意的敘事話語,塑造了一個個處于人生重要時期的國人形象。群像化的敘事結構將片中人物積極、堅強、從容、樂觀的生活態度注入當代中國人的“成長相冊”之中。在季與季間,《人生第一次》敘事視角也得到進一步延展。在《人生第一次》熱播后,央視網推出“人生三部曲”的第二部——《人生第二次》。與前作相似,《人生第二次》依舊將當代社會中的普通人作為刻畫的對象。但相較于著力展現人生中美好一瞥的前作,《人生第二次》則聚焦于那些暫困于人生失意瞬間的個體。兩季的影像從不同敘事的視角出發,立體地展現出當今社會中多元主體的生存面貌,為構筑當代的社會記憶提供了寶貴的“原料”。
縱向觀之,在單一文本的內部引入多元的敘事視角,有助于打破個人記憶的局限,使客觀事件得以完整全面地展現,并表現出對個體記憶厚度的挖掘。在紀錄片《人生第二次》中,編導記錄了一個被拐賣多年的男孩終與父母相認的故事。在該集中,導演大膽使用非線性的敘事手段,并于文本中引入了多重的敘事視角,如男孩的視角、男孩親生父母的視角、男孩養父母的視角、偵破該案件警官的視角。多元的視角構成了多條的故事線,使這一事件的親歷者依次呈現在屏幕之上,全面地展現了不同個體對某一事件的不同看法。多元視角的展演不僅表現出生活的復雜性,更彰顯了拐賣這一社會惡性事件的危害性。借由男孩個人遭遇在媒介空間的傳播,對人口拐賣這一違法行為的激烈討論再次進入公共的話語空間,不失為一種銘刻社會記憶的方式。
(三)文本主題:與流動中社會的互文
福柯曾有個極富趣味的表述,即“重要的是講述神話的年代,而不是神話所講述的年代”[10]。 人文紀錄片選擇分享怎樣的個體記憶,講述何種歷史年代下的個體記憶,其考量的依據無疑是創作者所置身的社會現實。個人記憶能否被建構為社會公共話語,需審視其是否能與彼時社會的共同期待、經歷和價值緊密相連。如在2015年前后,中國的制造業高速發展,不僅產業規模躍居全球第一,產業質量也穩步提升。在“中國制造”轉向“中國智造”的社會背景下,以《大國工匠》《了不起的匠人》《我在故宮修文物》為代表的人文紀錄片相繼播出。這些作品通過對中國“工匠”們的故事進行多畛域、深層次的整理與挖掘,講述了中國制造中蘊藏的匠心與傳承。也正是時代精神的注入,觀眾才對影片中所傳遞的工匠精神有了更深的體悟,這些體悟也增強了觀眾對于時代精神的認同。
現代社會是經由歷史的洗禮一步步演進而來,歷史作為社會個體間所共享的集體記憶,是民族國家的意識形態認同常需征用的文化資源。[11]而這種用歷史事件講述當下故事的方法,是歷史類人文紀錄片的常用創作手段。如在中國共產黨建黨一百周年的偉大歷史節點下,市場中涌現出一批以黨史為敘事主線的優秀紀錄片,像《百煉成鋼:中國共產黨的100年》《山河歲月》《無聲的功勛》等。這些紀錄片通過重現黨史中的重要人物與重大事件,生動地描繪出中國共產黨的百年奮斗圖景。在特殊的歷史節點下,人文紀錄片通過對黨史的深入挖掘,有助于讓當代人了解到歷史的真實發展進程,使觀眾形成對歷史事件的共識性追憶。在共同的歷史記憶之上,觀眾更容易與黨史中的先進人物形成情感共鳴,并將之轉化為行動的力量,彰顯出黨史紀錄片的當代價值。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影片主題與時代熱潮的遙相呼應下,人文紀錄片也悄然加深了公眾對社會的某種文化想象,有效地將縈繞在觀眾間的整體情感氛圍結構成社會的集體記憶,進而形成一個更富內聚力的文化共同體。
四、結語
人文紀錄片在抽取與提煉個體經驗的過程中,實現了對被新媒介所肢解的社會記憶的再塑造。而近些年人文紀錄片跨越年齡圈層的熱播現象,也再次確證了其構建社會記憶的可能。就具體創作而言,人文紀錄片通過對社會文化生活的再度編碼,形成了在小切口的敘事下運用差異化的選題、以多元的敘事視角積淀個體記憶的重量、提煉與時代精神相吻合的敘事主題等獨特的社會記憶書寫策略。在人文紀錄片的未來發展中,編導除需考慮其在記憶構建中所具備的潛力外,還要主動打破思維的局限,積極地與新媒體時代的受眾審美相呼應,不斷嘗試新的影像表達方式。
注釋:
[1]孟建,趙元珂.媒介融合:粘聚并造就新型的媒介化社會[J].國際新聞界,2006(7):24-27.
[2][美]弗雷德里克·杰姆遜.后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M].唐小兵,譯.西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杜,1987:207.
[3]喻國明.解讀當前中國傳媒發展關鍵詞[J].新聞與寫作,2006(9):3-6.
[4][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論集體記憶[M].畢然,郭金華,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24.
[5]聶欣如.“紀錄片”概念:一種源自認知語言學的闡釋[J].上海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4):62-69.
[6]高瑞泉,袁進,張汝倫,李天綱.人文精神尋蹤[J].讀書,1994(4):73-81.
[7]張同道.真實:支點還是陷阱?——紀錄片的真實觀念[J].電影藝術,2004(1):111-114.
[8]李恒基,楊遠嬰,主編.外國電影理論文選(增訂本)上冊[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216.
[9][德]阿萊達·阿斯曼,王蜜.重塑記憶:在個體與集體之間建構過去[J].廣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2):6-14.
[10]戴錦華.電影批評[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193.
[11]邵雯艷.歷史紀錄片的當代性[J].中國電視,2016(10):3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