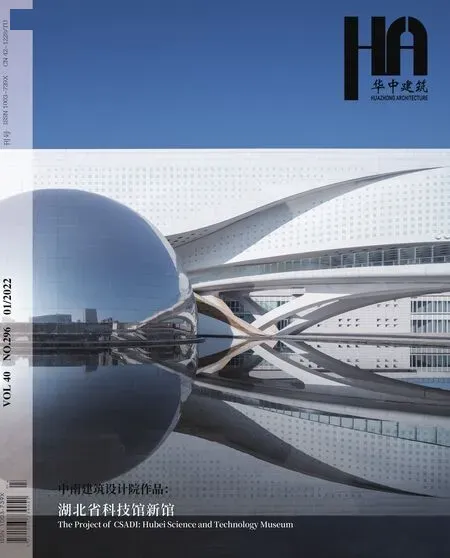新疆錫伯族聚落形態探析
馮甜甜 | Feng Tiantian
塞爾江·哈力克 | Saierjiang Halike
張 巧 | Zhang Qiao
公元1764年,乾隆為加強伊犁地區防務,調四千多錫伯族兵民到伊犁屯墾戍邊,形成八牛錄軍事駐防格局。“牛錄”是八旗軍政單位的名稱[1],現意為鄉鎮。錫伯族聚落是新疆基層屯墾戍邊的歷史產物,同時是研究清朝邊疆旗屯城堡聚落的典型實例。本文根據影響因素和聚落肌理兩方面出發,通過歷史和現狀的結合,探析聚落的的形態和演變特征。
1 錫伯聚落概況
1.1 錫伯族聚落現狀
錫伯族遷移至新疆察布查爾錫伯自治縣,至今已有250多年。錫伯族初駐扎于綽霍爾渠沿岸(圖1),成大分散、小聚居的聚落形態。道光二年后,因環境因素和軍事需要,遷移于察布查爾渠沿岸,形成南北寬約10km,東西長約44km的狹長區域,為現八牛錄布局形式(圖2)。現聚落第六牛錄發展成為察布查爾縣的縣城,位于整個錫伯族聚落中心位置,其他各牛錄均發展為鄉鎮,各鄉鎮之間相距2~4k m,并通過察愛公路和察坎公路道路串聯。聚落之間穿插一些其他小村落和農田,形成一個錫伯族聚落群(表1)。

表1 錫伯族聚落概況

圖1 清乾隆年間錫伯營城堡布局示意圖

圖2 錫伯族聚落現狀分布圖
1.2 聚落肌理特征
(1)街巷格局
每個聚落以十字大街為中心,向四周輻射擴張,聚落原城區范圍為中心向外展開。聚落內建筑布置較為密集,道路構架以棋盤式,布局規整,主次分明。道路等級為三級:一級道路寬約12m;二級道路寬約6m;三級道路寬約1.5~2.5m。一、二級道路可通行車輛,兩側均布置水渠和樹木;三級道路僅能通行人和牲畜,布置有道路、水渠或樹木,是居民出行、相互往來和鄰里和睦的通道。聚落內的水渠成網格式布局,布設于街道兩側,并與道路平行,形成“家家門外有樹木,戶戶門前有流水”的街巷特征。聚落中院墻與道路平行,形成規整的街道界面,使街道的規整性和美感增加。院落入口處設有約1.5~3m寬的入戶小橋,圍墻與街道之間栽種花草,布設座椅。其中一些聚落南側分布泉水和墓地。原城區外圍區域,道路曲折,局部道路兩側無水渠和樹木(圖3)。

圖3 聚落肌理圖
(2)公共空間
①泉水公共空間:按分布特點分為村內交叉口型、村內街邊型和村邊型。泉水出露位置與街道、交叉口相結合,形成聚落公共空間。該公共空間既是居民的飲用水源又是居民們休閑娛樂的活動場所。
②三角形公共空間:按使用特點分為服務空間型、休閑娛樂型和入口空間型。休閑娛樂型是居民閑暇時間的活動場所,多栽種樹木和布設座椅;服務空間型多擺放路標、垃圾箱和居民堆放草垛等服務設施;入口空間型是居民利用道路拐角空間作為院落入口,增加其入口空間的面積(圖4)。

圖4 公共空間節點圖
1.3 聚落建筑特征
(1)民居建筑特征
院落為南北長的矩形,面積約2~4畝[2],多建有水渠,用以灌溉院落內農作物,院墻為高約1.5m的夯土墻,院落布局特點如下:
①前后兩區:以民居分界,各設一門,均通向街巷,人車從前門進入,牲畜從后門進入,潔污分區明確,兩門之間設有一條道路,連接院落前后街道,方便通行。前院為潔區,一般設有花池,種有果樹、葡萄架和各種花卉等,并搭設高架棚和輔助用房,為夏季乘涼和存放物品等用處。后院為污區,主要為耕種和畜牧所用,因常年盛行東風,居民大多將畜牧的圈房設在院落北側,與街道平行建造,舍與住房之間耕種農作物與蔬菜,有效地避免了氣味對居所的干擾。院落東側多與街道垂直栽種楊樹,網格形種植布局與道路布局相呼應,有效改善氣味對鄰里的干擾和減小風力對居住環境的影響,并改善聚落整體環境。
②前中后三區:以民居和現代居住建筑為分界,前后院為潔區,供人居住生活,布設輔助用房,栽種花草樹木;中院為耕種畜牧使用,按其功能又分為東西兩區,分別為耕種和圈房;院落布設前后門,前門供人行走,后門成為人畜通用入口。
聚落形態通過以上兩種院落形式變得更加豐富多樣(圖5)。

圖5 院落布置示意圖
民居作為錫伯族聚落的象征,是錫伯族生活方式的體現,根據錫伯族現存民居調研,其中多為“一”字型、“L”型和仿劈夏以旺三種,“一”字型是延續了原錫伯族民居形式,遷移新疆后,民居在適應環境和借鑒當地民居特點情況下,形成“L”型或仿劈夏以旺形制的民居類型。因相同的居住環境和文化特點,民居均為坐北朝南偏東的單層生土建筑,并與街道近似平行。建筑為抬梁式結構,平面布局以“一明兩暗”的三開間為主,屋頂大多為人字形屋頂,一般為7根和5根大梁,20多根椽子,建造材料均使用生土、木材和蘆葦等。民居顏色以白色和淺藍色為主,使聚落給人以清晰自然感,奠定聚落主色調。相同建造材料和方式,使民居建筑形態趨于一致,聚落肌理清晰(圖6)。

圖6 民居建筑平面類型圖
(2)公共建筑特征
錫伯族聚落內建有娘娘廟和關帝廟[3],寺廟是居民祀奉祖先和舉辦大型活動的重要空間,是明清錫伯族精神文化信仰在空間上的反映,是聚落內重要的公共空間,聚落內的大型活動在此舉行。寺廟均分布于聚落北側,因聚落初建時,居民多居住城南,城北較為荒涼,所以居民將寺廟修建于城北,象征鎮壓城北邪氣(圖7)。寺廟分為街間型和沿街型:沿街型占地面積較小,入口僅向道路一側開設,一般為一個出入口,寺廟內公共空間較少。街間型占地面積較大,一般與2~3條街道相連,分設2~3個出入口。寺廟的建造材料和屋頂形式與民居建筑類似,相似的建筑類型使得聚落內建筑肌理統一。寺廟建筑風格獨特,屋頂為人字式和勾連搭式,其下設有臺基,高度在750~1000m m之間。臺基的存在使得寺廟建筑整體高于民居建筑,這種建筑風格在聚落內有絕對的識別性和標志性(圖7)。為現今修繕圖。

圖7 公共建筑分析圖
2 錫伯聚落形態影響因素辨析
2.1 自然環境因素
錫伯族聚落形態的主要自然環境因素為河流、泉水、地形地勢和風向。
①河流與聚落形態有密切聯系,乾隆三十一年,村落坐落于綽霍爾河兩岸,道光年后各牛錄陸續向察布查爾大渠以北遷移,一、三牛錄毀城建房時期,以原城堡為中心,大部分建筑向河流一側延伸。牛錄中建筑的布局呈現出北疏南密的特點[4]。
②歷史上泉水是聚落生產和生活的重要資源[5]。現今,泉水在聚落依舊起著積極的作用。察布查爾縣受南高北低的地勢條件影響,斜坡平原分布大量出露泉水,部分聚落坐落于泉水密集分布地區,以八牛錄為例,根據原城堡城墻殘留遺址可看出,聚落內大部分泉水分布在城南,是居民重要的飲用水資源。以一牛錄、三牛錄和四牛錄可看出,聚落后期發展以泉水為點,形成局部團狀分布。
③聚落位于斜坡平原,部分聚落缺少防御性地形優勢,以屯墾戍邊為目的錫伯族,需要通過修筑城堡來抵御外敵,因此八城堡聚落群形成。在城堡規劃中,較為平坦的地形為城堡內平整布局和矩形城墻建設提供有利條件。
④聚落內盛行東風,年平均風速2.5m/s,最大風向為西風,風速28m/s[1]。為減小風力對居住環境的影響,聚落周邊和內部栽種大量樹木,形成聚落內小氣候,有效改善聚落環境。
2.2 軍事防御因素
古代新疆人煙稀少,土地遼闊,大量的綠洲未被開墾,錫伯聚落屯墾戍疆,以旗屯的方式存在。“旗屯”始源伊犁地區,內屯民為八旗兵民[6]。錫伯族抵達伊犁后,因選址駐營考慮軍事駐防需求。從《西域水道記》“渠北地隘,慮在無田;渠南阻崖,患在無水”[7]。可知錫伯營初駐軍時,在沒城堡保護的情況下,利用地形環境形成軍事防線,各牛錄分別利用南側險峻的阻崖和綽豁爾河,形成易守難攻的防御屏障。聚落遷移至斜坡平原后,修建旗屯城堡。古意中“堡”,是指居住或屯駐地區,用土或石圍合成的軍事防御小城[8]。
①城墻和城壕的修筑,使聚落空間形態緊湊,極具向心性,縮短外圍邊界線,加強聚落防御性。②城堡內布設防御性構筑物,巷道式民居、“牛錄”檔房等辦事機構、糧庫和牢房等[9],有利于軍事防御。③棋盤式路網布局,敵人進入城堡后因規整統一和寬敞的道路失去方向感并且無處藏身。胡同和環途道路的設置,主要功能為便于傳遞情報、疏散人群以及快速組織軍民。④城堡內居民的防御性意識較強,約1.5m高的院落圍墻保護了居民的個人安全,前后門的設置,有效連接院落前后街道,為戰爭時期快速傳遞消息、集結軍隊提供了有利條件。
2.3 生產方式因素
錫伯族先民以“畜牧遷徙、射獵為業”,因此錫伯族到達伊犁前,安排其游牧屯田,以游牧為主業[10]。抵達伊犁后,因伊犁將軍發現錫伯族善農耕,而非游獵。《伊江匯覽》載:“如錫伯之力農也,男耕女織,終歲勤儉。”[11]原本計劃以游牧為主業的駐軍方式更改為以農耕為主的駐軍方式,筑城戍邊,將各城堡建于伊犁河南岸,形成城內居住,城外耕種、輔以捕魚、狩獵、養殖業的聚落空間形態特點,聚落依河流而建,城內布置密集水網,院內還設有水井,以供居民使用。畜牧的耕種方式使每家每戶均設圈舍飼養牲畜,錫伯族通過耕種和畜牧,居民日漸富足,城堡內建筑密度增加,聚落空間形態不斷改變。
3 錫伯聚落的形態演變
錫伯族聚落發展分為兩個重要時期,分別為城堡發展時期和自然村落發展時期。
3.1 城堡聚落發展階段
錫伯族城堡規劃是一個不斷完善的過程,從未遷址的一、三牛錄可知,城堡初建時是根據地形地勢而建,其規劃并不完善,城墻為不規則圓形,道路并未垂直相交,道路等級僅為簡單的二級,城門設置若干。而其他各牛錄均有遷移,在多次先筑城后遷移的過程中,城堡規劃不斷完善,軍事防御特點更加明確,形成一套獨具錫伯族特色的城堡聚落形態。錫伯族城堡不僅有軍事防御特點,并兼顧錫伯族人民生產生活。城堡布局特征如下。
八個牛錄城堡均具有軍事、政治及經濟職能,修建在地勢較為平坦的斜坡平原上,平面呈長方形或方形,個別表現為圓形(一、三牛錄),周長約2~4 km之間。城堡防御層次分為道路、城門、城墻和城壕。城墻約高5~6m,寬3~4m的夯土墻[12]。內設環涂,便于迅速調配兵力[13],外設城壕,可防御敵人。城墻上建有女兒墻、垛口、射擊口和車道,分設隱蔽堡和城門,城門數量一般3~4個。
城內道路與水網呈雙棋盤式布局,道路可分為十字大街,東西街道和胡同三級,道路交叉口為十字形和丁字形。南北主街兩側布設衙門、校場、檔房和糧倉;一般街道為居民入戶街道,主要為東西向街道,可通行車輛;胡同分布于東西街道之間,僅可步行和騎行,以供快速傳遞消息。寺廟位于主街的一側布設(圖8)。

圖8 城堡布局示意圖
3.2 自然聚落發展階段
(1)城外規劃發展
新中國成立后,由于聚落內防御性功能消失、人口增長和城墻內部使用空間不足等因素,居民毀城向城外發展。城外擴建初期,以老城區為中心,集中分布,擴張面積較小,地形地勢與城內相近,加之受城內文化及規劃理念影響,因此布局與城內相同。城外路網布局,以延伸和新增南北向道路,東西向垂直與南向道路建設。院落建造方式相同,但面積縮減,民居建筑建造形式和使用材料與城內民居相同,平行于道路建造,建筑肌理不變,局部形成沿道路兩側定居,建筑密度增加。因城墻的制約性和邊界性不復存在,殘留城墻成為院落分割線。休閑娛樂類公共空間出現,軍事防御類空間消失。以七牛錄和八牛錄為列,因聚落內地勢較為平坦,城外發展以城內規劃形制的延伸發展較為明顯,規劃特征突出(圖9)。

圖9 街道對比分析圖
(2)城外指狀發展
現各聚落邊界擴大,空間由團狀集約化布局向指狀延展[14]。①地形地勢制約:原有聚落規模和占地面積較小,地形地勢變化不大,均位于較為平坦的斜坡平原上,當聚落規模不斷擴張后,地勢高差使得聚落發展依托地形擴張,打破團狀規劃型布局,向四周延伸發展,根據自然地理條件和經濟交通線進行擇優選擇,盡可能選擇地勢平坦和交通便捷宜居住的用地。②大雜居:部分當地少數民族回屯定居和其他民族搬遷定居,各民族文化相互交融,規劃思想削弱,居民建房較為隨意,部分居民圈占道路土地,不受鄉鎮規劃束縛,使得規劃布局被打破。這兩個方面顯然變成聚落形態演變的重要因素,使聚落形態成指狀發展,聚落整體性和規劃性降低(圖9)。
聚落形態呈現自然聚落形態,路網布置曲折雜亂,水網布置局部消失。入戶道路平行與等高線布置,南北成爬坡形道路,道路彎曲起伏,局部為爬坡型建筑,以五牛依據地形發展較為明顯。以河流與道路成帶狀分布,局部居民以泉水為點,在周圍集中分布,以三牛錄和四牛錄較為凸顯(圖10)。

圖10 四牛錄聚落演變示意圖
結語
錫伯族聚落作為旗屯典型傳統聚落,其規劃布局、建筑形態、演變趨勢和影響因素都造就了錫伯族獨具特色的聚落形態,體現了錫伯族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無論是因軍事需要而修建的城堡,還是因適應環境而就地取材的建造方式,都是錫伯族人民的智慧結晶。錫伯族在不斷遷移發展中形成和完善了獨具錫伯族特色的城堡規劃理念,為上百年聚落的演變發展奠定了基礎,八個牛錄的聚落區位更是奠定了今天察布查爾錫伯自治縣的發展格局。本研究對國家鄉村振興戰略下西北地區聚落的傳承改造再發展有十分積極的意義。
資料來源:
圖1:改繪自察布查爾錫伯自治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察布查爾錫伯自治縣地名圖志》[M].新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清乾隆年間錫伯營八旗和伊犁城池分布圖;
圖8:參考陳振東編著,《新疆民居》[M].北京: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09:143.錫伯族民居,移民聚落之旗屯村鎮布局示意圖;文中其余圖片均為作者自攝自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