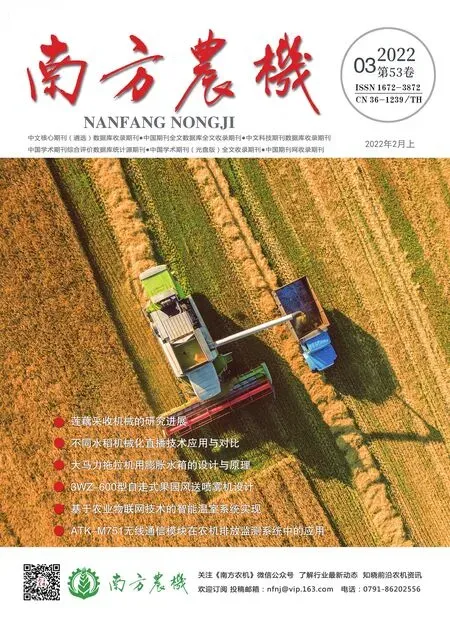生計脆弱性評價研究綜述
魯靜芳 , 盧天亮
(1.貴州財經大學大數據統計學院,貴州 貴陽 550025;2.貴州財經大學管理科學與工程學院,貴州 貴陽 550025)
生計脆弱性評價是研究農戶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工具,同時也是研究貧困農戶致貧因素的重要工具。在這個工具的使用上,不管是在可持續發展方面還是在貧困研究方面,單就評價過程上來說二者對其的使用是沒有多大差異的,都是對研究對象的生計脆弱性情況進行評價進而得到一個評價結果的過程,其差異主要還是在對生計脆弱性的評價結果的后續處理上。在研究可持續發展問題時,對研究對象的生計脆弱性情況進行評價后,一般不會直接應用這個評價結果,而是會通過這個評價結果來對研究對象的可持續發展能力進行二次評估,其研究的焦點主要是在可持續發展情況的評估上;但在研究貧困問題時,對農戶的生計脆弱性進行評價后,則會對這個評價結果直接進行分析,以評價指標的表現找到農戶的致貧原因,再從生計脆弱性情況來研究探討實現農戶脫貧的措施或方法,其研究的焦點主要就在生計脆弱性評價上。正是由于上述這種研究重點的差異,所以導致了對于生計脆弱性定義的差異,進而基于不同的生計脆弱性定義也就產生了多種不同的生計脆弱性分析框架及評價方法。而本文要說明的就是生計脆弱性評價從定義到分析框架、從指標設計到評價方法以及指數計算法的差異特征是什么,以求能方便其他研究者在使用生計脆弱性評價進行研究時對其有更清晰的理解。
1 生計脆弱性的定義
生計脆弱性是一個“生計”與“脆弱性”結合的綜合概念,了解生計脆弱性的概念,需要分別對“生計”與“脆弱性”的概念都有一定的理解。首先是生計,生計的研究始于20世紀80年代,最先是Amartya Sen[1]及其他一些國外學者對部分生計問題展開研究。Robert Chambers最早提出了關于生計的理念,后來又被他本人和 Conway等人發展與完善,他們把生計的概念定義為“一種謀生的方式,這種謀生方式是建立在能力、資產(包括儲備物、資源、要求權和享有權)和活動的基礎之上的”[2]。脆弱性的概念最早則是出現在地學領域的自然災害研究中,Timmerman首次提出了脆弱性概念,他認為脆弱性是系統在災害事件發生時對不利影響的反應以及對于災害事件的承受和從中恢復的能力[3]。脆弱性這一概念曾被多個學科所引用,后來研究生計的學者也把這一概念引入生計研究中,而由于脆弱性這一概念是一個引入詞,所以在生計脆弱性的定義中對于脆弱性的解釋也就一直都未得到統一。目前在眾多具有差異的定義中,對脆弱性的解釋起重要影響的則主要有三個,一個是英國國際發展署(DFID)在其提出的可持續生計分析框架(SLA)中對脆弱性做出的定義:脆弱性是家庭和個體的生計受外部沖擊、壓力、趨勢和季節性等因素影響,導致生計對環境變化極為敏感并呈現出不穩定的狀態[4];另一個則是世界銀行對脆弱性做出的定義:脆弱性是個人或家庭面臨某些風險的可能,并且由于遭遇風險而導致財富損失或生活質量下降到某一社會公認的水平之下的可能[5]。在這兩個定義中,脆弱性都表示既包含受到的風險威脅,也包含抵御沖擊的能力。還有一個則是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提出的定義:一個系統受不利因素影響的敏感度及無法應對這種影響的程度[6]。與前面兩種定義相比,IPCC的定義中提出了一個新的概念,那就是敏感性的概念,在研究中,敏感性可以理解為當農戶面臨同樣的生計風險的時候,不同農戶對這種風險的反應強弱程度。
國內對生計脆弱性的研究大都是在國外研究的基礎上加以展開,所以對于生計脆弱性的定義與國際上的定義都十分類似,如李小云等在研究生計脆弱性分析的本土化應用中,就把脆弱性定義為個人或農戶在現有的資產配置狀況下承受打擊的能力或者緩解及解除生計風險的狀況[7]。趙鋒等也在總結國外對于生計脆弱性的定義以后,認為生計脆弱性一般是指家庭和個體在生計活動過程中,因其生計結構變化或面臨外力沖擊時所具有的不穩定的易遭受損失的狀態[8]。他們兩人的定義就是基于DFID和世界銀行的定義展開的。
綜合來看,雖然國內外對生計脆弱性的定義目前仍然還沒有統一,但是通過對比各種定義的異同可以發現,對于生計脆弱性定義的本質都是圍繞著生計“遭受沖擊的風險”與“抵御風險沖擊的能力”或者加入一個“敏感性”展開的。
2 生計脆弱性分析框架
生計脆弱性評價研究最初主要是采用定性評價,但定性評價的不確定性和特殊性使得研究結果難以做到廣而適之,于是依托一種生計脆弱性分析框架,建立生計脆弱性評價指標體系,選用合適的分析方法得出定量結果的定量評價方法便應需而生,并且逐漸成為生計脆弱性評價研究的主流方法。
目前,使用在定量研究中的生計脆弱性分析框架主要有兩種,一種是納入DFID可持續生計分析框架中的以脆弱性環境、生計資本、適應能力為基礎建立評價指標體系對生計脆弱性進行分析評價的方法,另一種則是以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提出的“暴露-敏感性-適應能力”分析框架為基礎建立指標體系對生計脆弱性展開分析評價的方法。除了以上這兩種主要的分析框架以外,國內外學者也還提出了一些其他的分析框架,但這些框架與DFID和IPCC的框架都有很多重合之處,或者就是在這二者的基礎上再加以完善。國外如Dercon建立的“風險-生計脆弱性”分析框架,就是在傳統生計資本風險的基礎上增加了對收入風險和福利風險的分析,構建了集生計資本、收入和享受等社會服務于一體的系統分析框架[9]。國內的如左停等提出的構建農村相對貧困群體生計系統“風險-脆弱性”整合性分析框架,可以從不同維度和不同層次單元分析嵌入中國鄉村生計系統中的“風險-脆弱性”的各種表現[10],他的這個框架也是在前面兩者的基礎上,綜合考慮了預防打擊、保護、免受打擊、緩解壓力和遭遇打擊后的救助的整個過程情況,不把這些情況單獨提取分析,而是由整體分析的思路形成的,其本質核心仍然與前面二者一致。
在上面的分析框架中,基于可持續生計的生計脆弱性分析框架進行的生計脆弱性評價更多的是以被評價地區農戶客觀存在的風險與抵御風險的資本及措施來評價農戶的生計脆弱性,分析的是客觀存在的差異及差異所帶來的生計脆弱性變化,因其最終目標與發展中國家的農村發展和扶貧工作目標更為契合,也就常被一些國際發展組織用來對因客觀環境致貧明顯的發展較為落后的貧困地區進行生計脆弱性情況評估[11]。IPCC的“暴露-敏感性-適應能力”分析框架與可持續生計下的生計脆弱性分析框架比起來,在敏感性方面有了不一樣的地方。在“暴露-敏感性-適應能力”分析框架中,暴露其實就是指面臨的脆弱性環境,適應能力與可持續生計框架中生計資本內容基本一致,其主要差異表現是在敏感性部分,在可持續生計脆弱性分析框架,適應能力主要指客觀存在的對風險的抵御行為。而在“暴露-敏感性-適應能力”分析框架中,敏感性主要指的則是個體農戶對風險造成影響的程度判別,這個判別可以是客觀的,也可以是主觀的,而加入一些主觀判別后,其好處就是在研究農戶的生計脆弱性情況時,不僅考慮客觀環境對農戶生計脆弱性的影響,還能夠考慮到農戶個體主觀意識和行為差異對生計脆弱性產生的影響,所以這種框架常被用在農戶個體差異較為明顯地區的生計脆弱性評價中。
其他的分析框架基本都脫胎于前面兩者,只是介于分析目標的差異而有所區別,對于特定分析目標來說都各有所長,但也因為它們特異性的原因,所以普適性也就不高。通過對比以上兩種分析框架的研究目標差異與功能性差異,可以發現,在面對一些農戶個體差異不明顯的落后地區時,使用基于可持續生計的生計脆弱性分析框架能很全面地分析出研究對象的生計脆弱性情況,并且這種分析框架下評價指標設計更為簡單明了、易于操作;但在面對農戶個體差異更為明顯的地區時,IPCC的“暴露-敏感性-適應能力”分析框架則更能兼顧生計脆弱性評價的適用性與分析全面性,充分體現出農戶個體主觀因素對生計脆弱性的影響,但它的缺點就是對于指標設計的要求會比可持續生計分析框架更高。
3 生計脆弱性的評價指標體系
生計脆弱性評價指標體系的建立主要根據所選用的生計脆弱性分析框架來確定,在目前的研究中,主要分為可持續生計分析框架和“暴露-敏感性-適應能力”分析框架兩類。
在可持續生計分析框架中,生計脆弱性評價的指標建立一般以生計主體面臨的脆弱性環境和擁有的生計資本為基礎,然后再根據研究對象的差異建立對應的生計脆弱性評價指標體系,綜合來說,在指標體系的建立過程中,主要還是圍繞脆弱性環境、生計資本、適應能力三大部分來展開,進而構建二級、三級指標。在具體指標上,一般主要包括五大生計資本的風險狀況和占有情況,生計主體應對風險的措施和來自政府、社會的救助情況等。例如任威等[12]在研究喀斯特地區不同地貌下農戶的生計脆弱性影響因子時設計的生計脆弱性評價指標體系就是基于這種分析框架建立的,其中適應能力與生計資產就是抵御風險沖擊的能力,生計風險就是遭受沖擊的風險。
在“暴露-敏感性-適應能力”分析框架中,Hahn等提出了生計脆弱性指數(LVI),并以受災度、適應性和敏感度為基本框架建立了生計脆弱性指標體系,生計脆弱性評價的指標建立則主要圍繞暴露情況、敏感性情況、適應能力展開[13]。暴露一般指生計主體所受的風險影響,敏感性一般指生計主體對各種風險的敏感程度和對沖擊發生概率的感知情況,適應能力一般指生計主體抵御風險沖擊的能力,一般從生計主體的生計資產和受到的外部救助等進行測量。指標設計時,暴露主要就是圍繞自然風險、家庭
風險、社會風險展開,也可以根據研究問題的不同進行適當增減;敏感性主要圍繞自然災害、環境污染、疾病、子女教育、就業、財產安全等方面展開,同樣地,在研究過程中可以根據研究問題和生計主體的情況對指標做相應的增減;適應能力則主要圍繞對生計主體的五大生計資本的評價展開[14]。框架會考慮主觀因素對生計脆弱性的影響,所以在使用這種分析框架進行研究的過程中,研究者對研究目標的了解必須深刻,只有這樣才能完成合格的指標設計。國外的例如Endalew Haron Agegnehu等[15]、Laila Shahzad等[16],國內的例如劉偉等[17]、和月月等[18]都是采用這種方法構建生計脆弱性評價指標體系的。
4 生計脆弱性評價方法及指數計算方法
首先,是生計脆弱性評價方法的采用方面,童磊等對生計脆弱性評價方法做過一個細致的梳理,認為在生計脆弱性評價中主流的方法有綜合指數法、函數模型法和參與式農村評估法,還有BP人工神經網絡模擬法、模糊物元法和模糊認知映射法[19],并且對各種方法的原理和優缺點做過解釋。通過對照其他學者的研究,可以發現,函數模型法是以各因素的相互關系建立指標體系,更適用于“暴露-敏感性-適應能力”分析框架,只是由于對生計脆弱性構成要素的理解尚未統一,會導致模型的表現形式存在差異。綜合指數法則以生計脆弱性的特點和起因等建立指標體系,操作比較簡單,但這種方法的主觀性較強,故單獨使用綜合指數法進行生計脆弱性評價的研究并不多。綜合指數法和函數模型法的本質都是構建函數模型來對生計脆弱性進行評價分析,它們的界限并不是十分明顯,所以在研究過程中,研究者應該根據研究的具體需要選擇相應的評價方法,像前文提到的劉偉、和月月等人,另外像趙雪雁等[20]、韋惠蘭等[21]使用的都是“暴露-敏感性-適應能力”分析框架,但選擇的評價方法卻各有差異。
其次,在生計脆弱性指數計算方面,因為采用的分析框架不同,所以其指數計算方法也會存在差異。而主流的分析框架就是DFID的可持續生計分析框架和IPCC的“暴露-敏感性-適應能力”分析框架構兩種,所以就主要介紹這兩種評價方法下的指數計算法。
基于可持續生計分析框架的指數計算法,是通過計算生計風險值(R)、生計資產值(L)、適應能力值(A)或五大生計資本(H,M,N,F,S)的脆弱性來計算生計脆弱性值,計算公式如下:

在可持續生計分析框架中,計算生計脆弱性指數(LVI)時,式(1)、(2)中R、L、A關系都是一樣的,只是得出的指數一個是正值,一個是負值而已,前面的任威使用的就是第一種計算方法。LVI值并不是一個絕對的度量單位,而是一種相對的概念,反映的是一種趨勢。若LVI為正值,表明風險較大,其值越大表明農戶生計越脆弱;若 LVI 為負值,則相反。式(3)則是自然資本(N)、金融資本(F)、物質資本(M)、人力資本(H)和社會資本(S)的總和。
基于“暴露-敏感性-適應能力”分析框架的計算法,則是通過暴露度(R)、適應能力(A)、風險敏感度(S)之間的關系來計算生計脆弱性值,計算公式如下:

在“暴露-敏感性-適應能力”分析框架中,計算生計脆弱性指數(LVI)時,風險暴露度(R)、適應能力(A)、風險敏感度(S)之間的關系有式(4)、(5)、(6)三種。正常情況下,可以如式(4)把風險敏感度作為擾動項,也可以如式(5)把三方面都作為同量級來評價,兩種計算的效果差異不大,式(5)更簡單明了,但對風險敏感性的測量需要更加準確。如果研究對象的適應能力(A)差異不明顯,還可以用式(6)的比值形式計算評價。
5 總結
通過對生計脆弱性概念及其應用過程的梳理,可以發現:
1)目前的生計脆弱性研究主要應用在可持續發展和解決脫貧問題上,對生計脆弱性的研究也形成由定性研究為主轉向更加規范化的定量研究為主的趨勢,同時,生計脆弱性的定義并未統一,目前主流的定義以世界銀行、DFID、IPCC三家的三種為主。
2)在定量研究中,由于對生計脆弱性定義的差異,目前出現各個研究者在研究不同地區群體和問題時會選擇不同的分析框架和評價方法的現象。但總的來看,使用IPCC的“暴露-敏感性-適應能力”分析框架展開的研究最多,除了前文提到的幾位學者,楊婧等[22]、李會琴等[23]也都使用這種框架對貧困問題或可持續發展問題展開過研究,其次是使用DFID的可持續生計分析框架的,除了前文提到的任威,史俊宏[24]、崔曉明[25]也有使用這一框架展開研究。當然,使用其他的研究分析框架或評價方法也有,但相比前面兩種方法要少一些。
3)從評價方法來看,評價方法很多,但主要的就是函數模型法與綜合指數法。其他的方法也有,例如王建洪等[26]就使用了熵權TOPSIS方法對脫貧戶生計可持續性進行了評價,賈紅麗等[27]則使用了參與式農村評估法(PRA)研究探討影響農戶生計脆弱性的重要因素,其次還有劉進等[28]曾使用BP人工神經網絡模擬法對云貴高原的農戶生計脆弱性展開過研究,具體采用什么方法需要研究者根據研究目的自行考量。
4)從目前生計脆弱性的研究關注點來看,已有的研究更多是對脫貧與可持續發展的關注,但隨著國內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完成,在絕對貧困已經消除的社會背景下,未來對于生計脆弱性的研究,則需要打開更廣的研究領域,適時地從關注脫貧向關注返貧、關注發展的方向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