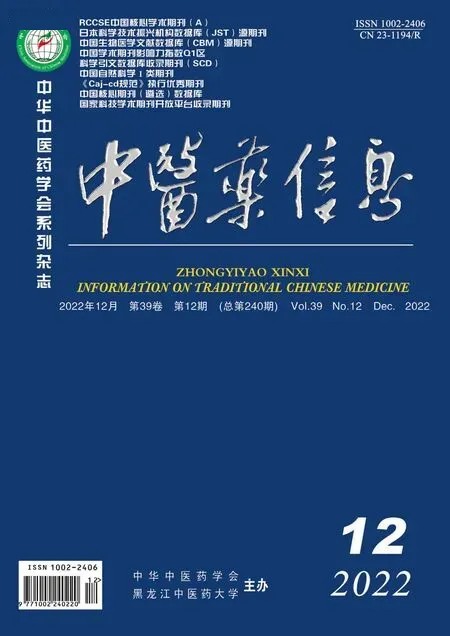關于實驗用大鼠腧穴定位的爭議
——以神闕穴為例
袁涌昊,趙若曦,夏慶昌,崔文哲,于曉華,曹雯,耿潤杰,陳錦澍,張晶
(山東中醫藥大學,山東 濟南 250355)
經過歷史上對針灸實踐經驗與經絡理論的研討,腧穴的定位已相對得以固定,準確定位腧穴是針刺操作有效性的重要前提。在進行實驗操作時,精準定位同樣也是實驗成功的關鍵保障。不過目前的取穴底本仍是華氏的42 穴平面圖譜,其繪制年代過于久遠,已不適用于如今實驗所需。盡管其后如徐東升等也設計出了立體骨架定位標志圖譜作為參考,但近年來的實驗動物腧穴定位仍缺乏統一標準,不同文獻的定位間均有誤差,影響了實驗結果的可靠程度。關于腧穴針刺操作深度的描述至今也仍然并不明確,故有必要對有關爭議及解決方案進行探討。
1 以大鼠神闕穴的定位為例
現在對實驗動物的腧穴定位,一般依賴比較解剖學模擬骨度,但實驗動物在組織結構特點上與人有些許差異。如大鼠生長迅速,為無臍動物,離乳前已沒有明顯的肚臍。定位在肚臍的神闕穴是任脈關鍵腧穴,也是其他腹部腧穴定位的重要標志之一,判斷其定位在操作相關腧穴的動物實驗結論可靠性上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還有待于出現更為客觀、標準、統一、準確的操作依據。在具體的定位操作上,早期動物腧穴定位將神闕穴的位置描述成模糊的腹中點,不利于具體應用。還有些文獻中按胸骨柄上緣至外生殖器上3/4 與下1/4 交界處取穴,但大鼠外生殖器部位有性別差異,雄性個體比雌性略高1~2 mm,這就導致這種定位方式其實存在不可避免的誤差[1]。由于在乳鼠發育過程中,可觀察到肚臍逐漸消失的狀態。紀峰等[2]據此,通過在乳鼠階段給肚臍注入墨汁染黑的方法,確定了成鼠相對應的位置。在數據處理時,剔除個別差異較大的個體后,發現若下肢自然松弛,大鼠第4對乳頭中點到肚臍(神闕穴)的距離,與第4、5 對乳頭中點間距比例為1/3;下肢完全拉伸時,肚臍(神闕穴)平行第4 對乳頭,約相當于在劍突至恥骨聯合上緣上2/3 與下1/3交界處[3],也可以此定位。
2 定位其他方式
2.1 現代技術
由于腧穴存在疾病態與常態、穩定態與激活態等的不同,甚至可能存在移動現象,這就導致取穴的定位在說法上常常存在爭議。在具體定位時,可以通過理化特性、組織結構差異及對比經穴與非經穴的療效、腧穴-臟腑相關效應等輔助。近年來,也出現了通過放射追蹤染色定位、紅外線、良導絡、高導聲、離子濃度對比等現代理論技術介入經絡循行線和腧穴位置定位的方案,比如經絡穴位處的皮膚溫度要比附近非經穴部位高出0.5~1.0 ℃的特性就可以用來指導取穴[4]。在肌骨超聲等現代醫學檢驗技術作用下,也可以確定腧穴的大致范圍。但這些不同的測量方式得到的結論之間,尚且存在偏差。在進一步驗證中發現,找到的點大多是現代醫學生物學上認為的具有高密度神經末梢易興奮的皮膚/肌肉-神經復合體,而不能很好地給予一個有中醫風格的腧穴命名[5]。這些性質也并不穩定,動物情緒、健康狀況、皮膚清潔狀態等等都會影響指標的可靠度,更適合由多種方法復合決定[6]。其中更宜以療效和腧穴-臟腑相關效應作為決定性。比如在判斷人迎穴的定位時,除了動脈血管、壓力感受器的位置外,更重要的依據是刺激該點時表現出來的降壓效率[7]。
2.2 傳統理論的現代解釋
尋找經絡的一大關鍵問題就是關于經絡實質目前還并不明確,但已經出現了諸多假說。如經絡“伏行分肉之間”,通過此前研究的對比顯示,與肌、筋膜、骨等結構間形成的孔隙密切相關,尤其與結締組織有著聯系,在接受刺激時,能產生較強的生物信號。張超等[8]通過HE、Masson 三色改良染色技術,對比穴區和非穴區結締組織情況,發現穴區膠原纖維更加豐富。且發現不同經脈按“十二經氣血多少”的規律,分布著不同量的膠原蛋白,可作為客觀化解釋。這可能有助于分離不同經絡的定位鑒別,可用于處理由于大鼠四肢較細導致的六經空間上距離較短,降低僅為毫米級的細微差距帶來的操作高難度。在刺激不同經時,會引起不同腦區活躍,也可以作為區分六經的一個方式[5,9]。
3 大鼠腧穴定位爭議
3.1 組織結構差異
大鼠的組織結構與人體還存在較大差異,如頸部活動度比人類大,肌肉的分布情況與人類存在不同,全身長度與頸部長度也比人類更大[10]。大鼠也沒有手指同身寸的比例,有文獻認為當取正對坐骨結節的一節尾椎長度折量一寸。大鼠與人體一樣有七節頸椎,但胸椎13 節,腰椎6 節,還有27~31 節不等的尾椎和沒有融合成骶骨的4 節薦椎,這導致大鼠的骨性標志與人體無法完全對等[6,11]。當大鼠前肢水平固定時,第二胸椎棘突最高,頸椎中第二頸椎棘突最高,腰椎棘突從上往下越來越長,第五、六腰椎最長。肩胛后角平第五胸椎,骶結節平第六腰椎,坐骨結節平第一尾椎。大鼠的脊柱生理性彎曲中,頸胸曲、胸腰曲明顯,頸胸曲最低平第二胸椎,薦尾曲不明顯。大鼠第九到十一胸椎連接緊密,但在體表容易觸及,也可用于定位[12?13],相應腧穴的位置確定仍有商榷余地。
3.2 中獸醫理論的差異
中獸醫學的基礎理論仍然是經絡腧穴,只是名稱、長度、走行方向及數目上與對人體的認知有所出入。根據中獸醫的經絡腧穴理論,也是判斷實驗動物腧穴定位的主要原則之一。但中獸醫在長期的實踐中發現的大多是動物特有的腧穴,這部分腧穴在人體上沒有相對應的定位,不能直接應用于最終目的旨在落實到人體、為臨床服務的實驗操作中去[14]。
4 討論
腧穴的準確定位是實驗可靠的前提條件,但目前仍缺乏對動物腧穴的認識,統一實驗動物腧穴定位是腧穴標準化進程中亟待解決的問題。由于中醫自身學術體系具有模糊性和不確定性等特點,在臨床上這樣的定位都只能做到相對精確。人體各部骨度分寸每寸均不一致,指寸定位法與骨度折量得到的一寸也有差異,故實際臨床定穴上,往往是先確定十四經體表解剖標志,相對定位后再尋找附近的敏感反應點。這樣的操作過程,往往摻雜著醫生個人經驗之間的分歧,隨意性過強[15]。盡管動物在解剖和組織結構、生理功能、生化反應和發病機制等方面都與人類似,是包括針灸在內的醫學學科理想的實驗對象[16],仍然還存在各文獻使用的定位標準不一致,差別較大的問題[17]。分析原因,可能與以下一些情況有關: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取穴標準本身的不實用性[18],文字標準難以形成圖形。在圖片標準里,又以平面為多,缺乏立體模型,不利于直觀感受,實際操作時容易出現操作者的主觀臆斷,陷入經驗至上的誤區[19]。
現在經穴的實質仍不明確,也可能是導致實驗動物腧穴定位欠精準的一個因素。不過目前已經出現了很多從解剖學角度分析腧穴內部深層次結構的血管神經網絡,也確實取得了一些可以用來輔助定位的結論[20]。臨床上可在相關理論的指導下,通過肌骨超聲等儀器判斷深層組織情況指導取穴,確定針刺深度[21],這樣的儀器也可用于實驗室確定動物腧穴定位。然而如今仍對穴區與非穴區的斷層解剖是否確實存在結構差異缺乏特異性結論,針對此種方案提出的爭議頗多,可能意味著完全依賴此種方案定位實驗動物腧穴還不太現實[5]。此外,還有些取穴方案通過生物物理特點定義,比如根據良導絡的理論基礎,運用伏安特性曲線判斷電阻差異,制定區分穴區與非穴區標準的方案[22],或從穴區與非穴區的溫度測量值差值出發[23]。但這些技術在普遍性、特異性等方面尚存爭議,有關儀器設備也存在過于繁重等問題,不便于實驗使用。
此外,動物四肢著地,前肢與人上肢功能不同,骨骼肌形態有一定區別,發育程度也明顯相異。僅依據比較解剖學投射,就會發現很多結構并不能直接對應[24]。實驗動物與人體各部分結構比例并不相同,目前對于實驗動物結構比例的研究尚缺乏有效統計。盡管有學者提出,大鼠以坐骨結節對應的一節尾骨寬為一寸[25]的“大鼠同身寸”,但似乎并無文獻使用此種方法進行實際取穴定位,這或許表明了其可操作性較差。而且我們無法明確實驗動物的主觀表達,難以用“按壓有酸脹感處是穴”的方案取穴定位[12]。現在主流的動物腧穴仍是以經典的針灸使用的人體穴位作為依據模擬定位,以比較解剖學為考量。在面對筆者上面提到的這些存在的問題時,處理方案主要是通過多坐標綜合衡量,以確定穴點的定位[26]。被選作坐標的常常是視相鄰兩穴間位置的相對關系而定,這就導致作為標志的穴位一旦定位模糊,其他穴位的定位就很難明確了[27]。比如上文提到的神闕,就由于大鼠臍窩不明顯,無法用于確定關元位置。諸如此類的情況,也體現了這種定位方式可能并不可靠。
當然,也有很多穴位是可以通過比較解剖學進行定位的。在動物身上一般認為與人類結構差別較小的大關節附近的腧穴,均可直接投射到動物身上[28],如委中、委陽、昆侖等;按比例取用的腧穴,也可等分肢體后取得,如上文介紹的神闕,不必拘泥于尋求“大鼠同身寸”;解剖結構明確的腧穴,都可以解剖結構為準,這類腧穴大多是一些組織間形成縫隙的開端或結束處,如承山[29];定位在赤白肉際處的腧穴,大多動物被毛在此生長方向不同,可以被毛分叉根部作為判定依據[30];末端井穴均可以直接取在動物肢體末端[31]。動物與人體結構有區別的,也可變通到以相近區域的近似結構為標志取用。進針角度按人體相同即可,深度可等比例縮小。筆者主要討論的實驗動物大鼠由于組織薄,體表面積小,需要更加精細定位。在實驗操作時,針刺用具的長度和深度都應相應減小,否則稍微偏差一點就可能扎到其他穴位或非經非穴上,影響實驗的順利進行。
除了經驗外,動物腧穴的認識也有一些理論指導下的方案,比如中獸醫對動物穴位的認識。雖然在獸醫實踐活動中確實積累了很多穴位,但在這套方案中,有些定位相同但命名有所異,有些命名相同但定位相去較遠,不能確定是否為同功穴,難以把實驗結果推廣到人體身上。同名異位的腧穴比如人的百會在頭頂,動物的一般在腰間;人天宗在崗下窩,動物在肩胛下角;曲池人在肘外側,動物在跗外側。同位異名的腧穴比如人的陽陵泉在動物叫后三里,人的天井在動物叫肘髎,人的陽白在動物叫垂睛,人的外膝眼在動物叫探草,人的髀關在動物叫大胯,人的頰車在動物叫抱腮等。筆者主要討論的實驗動物大鼠幾乎沒有傳統獸醫文獻記載,這就限制了理論聯系實際運用的可能。
目前對實驗動物腧穴定位方案,仍然是主要從比較解剖學的角度出發,根據人體穴位所處部位,按比例投影到動物身上,或采用絕對的距離長度進行定位,或依據骨度分寸折量。但由于實驗動物與人體組織結構不同,中獸醫理論上和中醫的認識也存在一定差異,還需要跟進腧穴實質研究進展,通過放射追蹤染色、腦科學定位、紅外線、良導絡和高導聲、離子濃度和膠原蛋白量的對比及熱力信號等現代理論技術分析腧穴效應機制,綜合進行經絡循行線和腧穴位置的定位判斷。取穴首先要明確所使用實驗動物的正常體位,但在實驗過程中,動物難以保持體位,固定方法也可能影響取用穴位。除尋求更明確的取穴方案外,筆者還將在后續的實驗中改進固定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