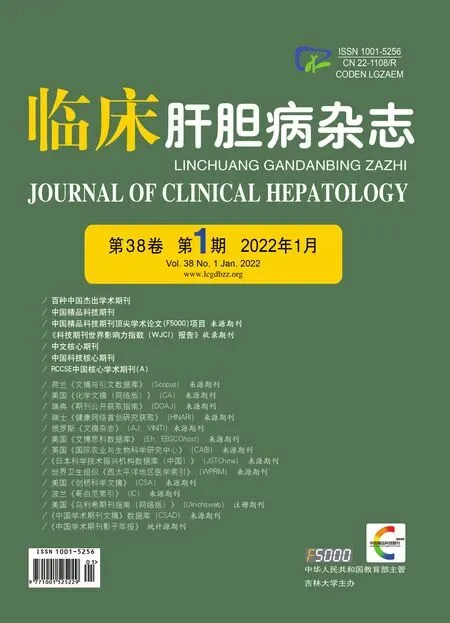自身免疫性肝炎診斷和治療指南(2021)
中華醫學會肝病學分會
1 概述
自身免疫性肝炎(autoimmune hepatitis,AIH)的臨床特點包括血清氨基轉移酶水平升高、高免疫球蛋白G(IgG)血癥、血清自身抗體陽性,肝組織學上存在中重度界面性肝炎等。早期診斷和恰當治療可顯著改善AIH患者的生存期和生活質量,減輕社會醫療負擔。
2015年由中華醫學會肝病學分會、中華醫學會消化病學分會和中華醫學會感染病學分會組織國內有關專家制訂了我國首部《自身免疫性肝炎診斷和治療共識(2015)》[1],在規范我國AIH的診斷和治療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在此基礎上,中華醫學會肝病分會組織有關專家結合國內外最新進展制定本部指南,旨在進一步提高我國AIH診治水平。指南中提及的證據和推薦意見按照GRADE系統(推薦分級的評估、制定和評價)進行分級(表1)。
2 流行病學
AIH可以在任何年齡和種族人群中發病。歐洲與亞洲人群中以女性患者居多,發病率和疾病狀態存在種族差異[2-3]。在歐洲國家,AIH的時點患病率為10/10萬人~25/10萬人。新西蘭一項前瞻性研究[4]顯示2008年至2010年AIH的發病率為1.37/10萬人,而在2014年至2016年增長到2.39/10萬人。同樣,日本的兩次流行病學調查發現2004年AIH的時點患病率為8.7/10萬人,2016年時點患病率已經增長至23.9/10萬人[5]。此外,AIH患者性別比例也發生了明顯變化。在日本,男女比例由1∶6.9(2004年)增長為1∶4.3(2016年)。

表1 推薦意見的證據等級和推薦強度等級
來自其他研究[6]中AIH患者的男女比例由1∶9~1∶10增長到1∶4~1∶7。最近,我國開展的一項包含1020例AIH患者的單中心回顧性觀察研究[7]顯示,AIH患者的峰值年齡為55(6~82)歲,在20歲有小的波峰,男女比例為1∶5。
3 診斷與鑒別診斷
AIH的診斷主要是基于臨床表現、實驗室檢查和肝組織學特征性表現,并排除其他肝病病因。
3.1 臨床表現 多數AIH患者無明顯癥狀或僅出現乏力等非特異性癥狀。大部分AIH患者隱匿起病,少部分患者為急性發作,其中部分為慢性AIH的急性加重,甚至發展為急性肝功能衰竭。約1/3的患者初診即為肝硬化表現。
3.2 實驗室檢查
血清氨基轉移酶水平升高、自身抗體陽性、IgG和/或γ-球蛋白水平升高是 AIH 的重要實驗室特征。
3.2.1 血清生物化學指標 AIH的典型血清生物化學指標異常主要表現為肝細胞損傷型改變,血清丙氨酸轉氨酶(ALT)和天冬氨酸轉氨酶(AST)水平升高,而血清堿性磷酸酶(ALP)和γ-谷氨酰轉移酶(GGT)水平基本正常或輕微升高。病情嚴重或急性發作時血清總膽紅素水平可顯著升高。
3.2.2 自身抗體與分型 大多數AIH患者血清中存在一種或多種高滴度的自身抗體,但這些自身抗體大多缺乏疾病特異性。AIH可根據自身抗體的不同分為兩型:抗核抗體(antinuclear antibodies,ANA)和/或抗平滑肌抗體(anti-smooth muscle antibodies,ASMA)陽性者為1型AIH,約占AIH病例的90%;抗肝腎微粒體抗體-1型(anti-liver kidney microsome-1,抗LKM-1)和/或抗肝細胞溶質抗原-1型(anti-liver cytosol-1,抗LC-1)陽性者為2型AIH。ASMA的主要靶抗原是微絲中的肌動蛋白,又可分為G-肌動蛋白和F-肌動蛋白。高滴度抗F-肌動蛋白診斷AIH的特異度較高。抗LKM-1的靶抗原為細胞色素P450 2D6。在成人AIH患者中,抗 LKM-1對AIH的敏感度較低(1%),而在兒童AIH患者中敏感度較高(13%~38%)。約10%的2型AIH患者中抗LC-1是唯一可檢測到的自身抗體,且抗LC-1與AIH的疾病活動度和進展有關。抗可溶性肝抗原抗體(anti-soluble liver antigen,抗SLA)診斷AIH時特異度較高,并具有一定預后預測價值,但我國AIH患者中僅2.5%呈SLA陽性。我國一項單中心臨床研究提示約10.2%的AIH患者起病時ANA、ASMA陰性,后續隨訪期間有患者出現ANA抗體陽性。抗體陰性的AIH患者相較于經典AIH患者,其血清IgG水平更低且起病時可能處在纖維化進展期,但兩組患者在起病時組織學炎癥程度及半年內生化應答緩解率方面均無統計學差異。及時明確診斷并啟動治療,有助于改善抗體陰性AIH患者的預后[8]。
3.2.3 血清免疫球蛋白 IgG和/或γ-球蛋白升高是AIH特征性的血清免疫學改變之一。血清IgG水平可反映肝內炎癥活動,經免疫抑制治療后可逐漸恢復正常。來自國內的大型隊列研究[7]結果表明AIH患者初診和治療3個月后較低的血清IgG 水平與生化和組織學緩解相關。
3.3 肝組織學檢查
肝組織學檢查對AIH診治的重要性表現為:(1)提供AIH患者確診依據,特別是在自身抗體陰性患者;(2)有助于與其他肝病(如藥物性肝損傷、Wilson病等)鑒別;(3)明確有無合并其他自身免疫性肝病,如原發性膽汁性膽管炎(primary biliary cholangitis,PBC)和原發性硬化性膽管炎(primary sclerosing cholangitis,PSC)重疊存在;(4)評估分級和分期;(5)治療后復查有助于判斷合適的停藥時機,如Ishak評分系統中肝炎活動度(hepatitis activity index,HAI)<4分時停藥相對安全[9]。因此,建議盡可能對所有擬診AIH且無肝活檢絕對禁忌證的患者行肝組織學檢查,可采用的方法包括:經皮肝活檢、經頸靜脈肝活檢以及腹腔鏡下肝活檢等。AIH組織學以肝細胞損傷為主,病理學特點如下。
3.3.1 門管區表現 (1)界面性肝炎:在組織學上,肝細胞和門管區/纖維間隔交界處稱為“界板”,炎癥細胞由該區域向小葉內延伸,導致相鄰肝細胞呈單個或小簇狀壞死、脫落,稱為界面性肝炎。界面性肝炎是AIH的組織學特征之一,中重度界面性肝炎支持AIH的診斷,但需排除其他慢性肝病如病毒性肝炎、藥物性肝損傷、Wilson病等。(2)淋巴-漿細胞浸潤:門管區及其周圍浸潤的炎性細胞主要為淋巴-漿細胞。漿細胞評分>3分(即漿細胞占炎癥細胞≥20%)或小葉內/門管區見漿細胞灶(≥5個漿細胞聚集為1灶)有助于AIH的診斷,但漿細胞缺如不能排除AIH[10]。
3.3.2 小葉內表現 未經治療的AIH小葉內常出現中等程度炎癥。當炎癥明顯時,可見3區壞死/橋接壞死。肝細胞受炎癥細胞攻擊后出現水腫、變性、壞死,再生的肝細胞呈假腺樣排列,稱為“玫瑰花環樣”結構。穿入現象是指淋巴細胞進入肝細胞后在其周圍形成空暈樣結構,發生穿入的細胞主要為CD8+T細胞,可導致肝細胞凋亡[11]。
3.3.3 特殊類型AIH組織學表現 (1)急性AIH。急性AIH可分為兩大類:①無慢性肝炎病史,以急性肝損傷為首發癥狀的AIH;②以慢性肝炎表現的AIH急性發作或惡化甚至發展為肝功能衰竭。肝組織學上,前者可出現中央靜脈炎伴周邊壞死(3區壞死)、橋接壞死伴小葉內炎癥細胞浸潤;后者3區壞死相對較少,可有多核肝巨細胞、多灶融合壞死,甚至亞大塊或大塊壞死[12-13]。(2)AIH相關肝硬化。未經治療的AIH可進展為肝硬化,這一階段炎癥往往減輕或者耗盡,門管區/纖維間隔輕度非特異性炎癥伴有輕度界面性肝炎,診斷需要結合臨床。
3.4 診斷標準 國際自身免疫性肝炎小組(International Autoimmune Hepatitis Group,IAIHG)于1993制定了AIH描述性診斷標準和診斷積分系統,并于1999年進行了修訂(表2)[14]。1999年更新的積分系統根據患者是否已接受糖皮質激素治療分為治療前和治療后評分。
2008年IAIHG提出了AIH簡化診斷積分系統[15](表3)。簡化診斷積分系統分為自身抗體、血清IgG水平、肝組織學改變和排除病毒性肝炎等4個部分。我國一項總數為405例慢性肝病患者(其中1型AIH患者127例)的多中心臨床研究結果顯示[16],簡化積分系統確診AIH的敏感度為90%,特異度為95%,可較好地應用于臨床診斷。簡化積分系統容易漏診部分不典型患者,如自身抗體滴度低或陰性和/或血清IgG水平較低甚至正常的患者。因此,對于疑似AIH且采用簡化診斷積分不能確診的患者,建議再以綜合診斷積分系統進行綜合評估以免漏診。由于自身抗體檢驗方法的優化,近期歐洲學者提出基于ELISA的ANA和ASMA(F-actin)檢測也是AIH自身抗體評估的潛在可靠替代方法,建議將這些檢測方法納入AIH診斷的簡化標準[17]。
3.5 鑒別診斷 ANA和ASMA等自身抗體缺乏疾病特異性,低滴度的自身抗體也可見于其他多種肝內外疾病如病毒性肝炎、代謝相關性脂肪性肝病、Wilson病等肝病以及乳糜瀉、系統性紅斑狼瘡、類風濕性關節炎等自身免疫性疾病。因此,需進行仔細的鑒別診斷(表4)。
推薦意見1:對于擬診AIH的患者,應檢測自身抗體如ANA、ASMA、抗SLA/LP、抗LKM-1和抗LC-1等,并常規檢測血清IgG和/或γ-球蛋白水平。(B1)
推薦意見2:應對無禁忌證的擬診AIH患者行肝組織學檢查(可經皮或經頸靜脈)。界面性肝炎、淋巴-漿細胞浸潤、肝細胞玫瑰花環樣改變和淋巴細胞穿入現象等支持AIH診斷。(B1)
推薦意見3:應結合血清氨基轉移酶升高、血清自身抗體陽性和IgG升高及特征性肝組織學改變并排除其他病因后,進行AIH綜合診斷。(A1)
推薦意見4:AIH簡化積分系統可用于我國AIH患者的診斷,AIH綜合評分系統可用于非典型、復雜病例的診斷,或用于臨床研究。(B1)

表2 AIH綜合診斷積分系統(1999年)

總積分的解釋治療前治療后 明確的AIH≥16 明確的AIH≥18 可能的AIH10~15 可能的AIH12~17

表3 IAIHG的AIH簡化診斷標準
4 治療
AIH患者如不進行臨床干預,可迅速進展為肝硬化或終末期肝病。目前主要采用非特異性免疫抑制:潑尼松(龍)(prednisone/prednisolone)聯合硫唑嘌呤(azathioprine,AZA)治療或者潑尼松(龍)單藥治療作為AIH的標準治療方案。上述方案能顯著改善大多數中重度AIH患者的肝生化指標并延長生存期[18]。但至少有10%~15%的患者對標準治療方案應答不佳。另有部分患者因不能耐受藥物副作用或停藥造成復發。AIH的總體治療目標是獲得并維持肝組織學緩解、防止進展為肝硬化和/或肝功能衰竭,進而提高患者的生存期和生活質量,生化緩解定義為血清氨基轉移酶(ALT和AST)以及IgG水平均恢復正常。肝組織學緩解定義為肝內炎癥消失或輕微(Ishak評分系統HAI<4分或Scheuer分級系統G≤1)。
4.1 治療指征 所有活動性AIH患者均應接受免疫抑制治療,并可根據疾病活動度調整治療方案和藥物劑量。(1)建議中度以上炎癥活動的AIH患者[血清氨基轉移酶水平>3×正常值上限(ULN)、IgG>1.5×ULN和/或中重度界面性肝炎]接受免疫抑制治療。急性表現(ALT或者AST>10×ULN)或重癥AIH患者[伴國際標準化比率(INR)>1.5]應及時啟動免疫抑制治療,以免進展至肝功能衰竭。(2)對于輕微炎癥活動(血清氨基轉移酶水平<3×ULN、IgG<1.5×ULN和/或輕度界面性肝炎)的老年(>65歲)患者需平衡免疫抑制治療的益處和風險作個體化處理。暫不啟動免疫抑制治療者須嚴密觀察,如患者出現明顯的臨床癥狀,或出現明顯炎癥活動可進行治療。

表4 AIH的鑒別診斷
4.2 治療方案
4.2.1 一線治療 對于未經治療的AIH成人患者,若非肝硬化或急性重癥者,建議將潑尼松(龍)聯合AZA作為初始一線標準治療方案,即潑尼松(龍)用于誘導緩解,AZA用于維持緩解。該方案可顯著減少潑尼松(龍)劑量及其不良反應。潑尼松(龍)可快速誘導癥狀緩解,而AZA需6~8周才能發揮最佳免疫抑制效果,多用于維持緩解。聯合治療尤其適用于同時存在下述情況,如:絕經后婦女、骨質疏松、脆性糖尿病、肥胖、痤瘡、情緒不穩以及高血壓患者。潑尼松(龍)初始劑量為0.5~1 mg·kg-1·d-1(通常30~40 mg/d),誘導緩解治療一般推薦如下用藥方案:潑尼松(龍)30 mg/d 1周、20 mg/d 2周、15 mg/d 4周,潑尼松(龍)劑量低于15 mg/d時,建議以2.5 mg/d的幅度漸減至維持劑量(5~10 mg/d);維持治療階段甚至可將潑尼松(龍)完全停用,僅以AZA 50 mg/d單藥維持。需要強調的是,糖皮質激素的減量應遵循個體化原則,可根據血清ALT、AST和IgG水平改善情況進行適當調整。如患者改善明顯可較快減量,而療效不明顯時可在原劑量上維持2~4周。可在使用潑尼松(龍)2~4周后出現顯著生化應答后再加用AZA,初始劑量為50 mg/d,可視毒性反應和應答情況漸增至1~2 mg·kg-1·d-1。理想情況下潑尼松(龍)可撤藥,僅AZA單藥維持。伴發黃疸的AIH患者可先以糖皮質激素改善病情,總膽紅素水平恢復至較低水平(<50 μmol/L)時再考慮加用AZA聯合治療。
潑尼松(龍)單藥治療適用于合并血細胞減少、巰基嘌呤甲基轉移酶功能缺陷、并發惡性腫瘤的AIH患者。AIH“可能”診斷患者也可以單藥潑尼松(龍)進行試驗性治療。活動性AIH相關肝硬化失代償期患者在預防并發癥的基礎上可謹慎使用小劑量糖皮質激素(一般劑量為15~20 mg/d)口服,疾病好轉后應快速減量至維持量(一般劑量為5.0~7.5 mg/d)。來自我國的一項真實世界研究[19]顯示,小劑量糖皮質激素治療AIH肝硬化失代償期患者能獲得較高應答率(62.5%),接受治療者的生存率更高。此外,治療第7天的應答情況(血清總膽紅素水平的變化)可預測預后,有助于判斷是否繼續糖皮質激素治療或是需要其他治療。
布地奈德(Budesonide)作為第2代糖皮質激素,特點為肝臟首過清除率約90%,主要部位為腸道和肝臟,所以全身不良反應較少。布地奈德可作為AIH的一線治療方案,適用于需長期應用糖皮質激素維持治療的AIH患者以減少副作用。但不宜用于肝硬化患者,布地奈德可通過肝硬化患者門靜脈側支循環直接進入體循環而失去首過效應的優勢,同時還可能有增加門靜脈血栓形成的風險。來自歐州的多中心臨床研究結果表明,布地奈德和AZA聯合治療方案較傳統聯合治療方案能更快誘導緩解,而糖皮質激素相關不良反應顯著減輕,可作為AIH的一線治療方案[18,20-22]。布地奈德在急性重癥AIH或急性肝功能衰竭中的作用尚不清楚,因此不建議在此類情況下使用(圖1)。
4.2.2 二線治療 對一線治療應答欠佳或不耐受糖皮質激素或AZA副作用的AIH患者,可選擇二線治療方案,藥物包括:嗎替麥考酚酯(mycophenolate mofetil,MMF)、他克莫司(tacrolimus,FK506)、環孢素A(cyclosporine A,CsA)、甲氨蝶呤(methotrexate)、6-巰基嘌呤(6-mercaptopurine,6-MP)等[23-24]。MMF是一種與硫嘌呤類藥物分子結構和代謝不同的嘌呤拮抗劑,是在標準治療效果不佳患者中應用最多的替代免疫抑制劑。對于AZA和6-MP均不耐受的患者,可使用MMF作為二線藥物,可從250 mg每天2次的劑量開始,逐漸增加至500 mg每天2次口服。此外,膽汁淤積性AIH患者如糖皮質激素療效欠佳也可考慮加用小劑量MMF治療,以避免AZA誘導膽汁淤積的不良反應。雖然MMF的骨髓抑制等副作用顯著低于AZA,但使用MMF初期也需定期(每2周1次)監測血常規檢查。他克莫司在治療失敗、不完全應答和對AZA不耐受患者中具有補救治療價值。兩項關于成人AIH二線治療的Meta分析顯示,75%~94%的患者經他克莫司治療后血清氨基轉移酶改善或正常[25-26]。最常見的副作用是神經系統癥狀(震顫、頭痛)、腎臟并發癥(高血壓、腎功能不全)和脫發。
4.2.3 三線治療 對于一、二線治療無應答的AIH患者,應重新評估原診斷的準確性和患者的服藥依從性。三線治療藥物包括西羅莫司、英夫利昔單抗和利妥昔單抗等。小樣本量病例中報道過抗TNFα制劑(英夫利昔單抗)在難治患者挽救性治療中的作用。但也有研究發現抗TNFα藥物可致肝損傷,甚至可引起藥物誘導的AIH樣肝損傷。利妥昔單抗是針對B細胞表面受體CD20的單克隆抗體,在對6例成人AIH患者(3例AZA不耐受和3例糖皮質激素/AZA和MMF無效的患者)的治療中,所有患者血清轉氨酶和IgG水平顯著改善,67%的患者獲得生化緩解。
4.2.4 肝移植術 AIH患者進展至急性肝功能衰竭或終末期肝病時,應考慮行肝移植術。重癥AIH可導致急性或亞急性肝功能衰竭,如短期(1~2周內)的糖皮質激素治療效果不明顯時,需及時與肝移植中心聯系,以免失去緊急肝移植術機會。失代償期肝硬化患者的移植指征與其他病因導致的肝硬化相似,包括反復食管胃底靜脈曲張破裂出血、肝性腦病、頑固性腹水、自發性細菌性腹膜炎和肝腎綜合征等并發癥經內科處理效果不佳,終末期肝病模型(MELD)評分>15分或Child-Pugh評分>10分,或符合肝移植標準的肝細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選擇恰當的時間進行肝移植術十分關鍵,應盡早做好肝移植術準備。AIH肝移植預后通常較好,影響肝移植患者生存的主要因素是AIH復發和移植排斥。復發性AIH(recurrent autoimmune hepatitis,rAIH)的發生率約為23%,確診的中位時間為肝移植術后26個月[27]。HLA-DR位點不匹配是rAIH的主要危險因素。術前較高的血清IgG水平、移植肝的中重度炎癥與AIH復發有關,提示術前未能完全抑制疾病活動是復發的危險因素之一。因此,AIH患者在肝移植術后的免疫抑制方案應兼顧抗排異反應和防止AIH復發。由于長期應用糖皮質激素預防移植后排斥反應、移植物功能喪失或復發來改善AIH成人患者和移植物存活率的證據有限,2019年AASLD建議肝移植術后應考慮逐漸停用糖皮質激素[28]。少數(6%~10%)非AIH患者在肝移植后出現類似AIH的血清學和組織學表現,稱為新發AIH(de novo AIH)[29]。建議復查肝活檢、血清IgG水平和自身抗體來區分免疫介導性疾病和其他導致同種異體移植功能障礙的原因。AIH復發或移植術后新發AIH的肝移植患者建議在鈣調蛋白抑制劑的方案上加用潑尼松(龍)和AZA來聯合治療。

注:*建議有條件時在使用前檢測TPMT和NUDT15基因型和/或活性,啟動糖皮質激素2周后添加硫唑嘌呤(50~100 mg/d),并注意監測血常規。失代償期肝硬化患者不建議使用硫唑嘌呤。**對于經潑尼松(龍)治療后副作用嚴重者,布地奈德可作為替代藥物。但布地奈德在肝硬化患者中失去首過效應的優勢,有增加門靜脈血栓形成的風險,此外在急性重癥AIH或急性肝功能衰竭中治療作用未知,因此上述情況下不建議使用。圖1 AIH的藥物治療
4.3 藥物相關不良反應
4.3.1 糖皮質激素的不良反應 長期使用糖皮質激素可出現明顯不良反應,其中除了常見的“Cushing體征”以外,糖皮質激素還可加重骨質疏松導致相關骨病,并與2型糖尿病、白內障、高血壓病、感染(包括已有的結核發生惡化)、精神疾病的發生有關。應盡量采用聯合治療方案來減少糖皮質激素劑量,并最終過渡至AZA單藥維持治療方案。需長期接受糖皮質激素治療的AIH患者,建議治療前做基線骨密度檢測并每年監測隨訪。對于有骨質疏松癥危險因素的患者,應在基線時采用雙能X線骨密度儀(DEXA)對腰椎和髖部進行骨密度評估。此后每年復查1次。最常見危險因素為長期使用糖皮質激素、絕經后狀態、低創傷骨折史和老齡(女性>65歲,男性>70歲)。應在基線時測定患者血清25-羥基維生素D水平,此后每年復查1次。糖皮質激素治療期間,應補充鈣劑(1000~1200 mg/d)和維生素D(>400~800 IU/d),并根據臨床實際情況對維生素D不足的患者給予劑量補充。已有的臨床經驗支持在出現骨質疏松癥時,使用雙膦酸鹽治療。
4.3.2 AZA的不良反應 AZA最常見的不良反應是骨髓抑制導致的血細胞減少,可能與服用者的紅細胞內巰基嘌呤甲基轉移酶(thiopurine methyltransferase,TPMT)遺傳多態性和活性低有關。另外,Nudix水解酶15(NUDT15)基因變異也會導致活性物質6-硫代鳥嘌呤核苷酸(6-thioguanine nucleotides,6-TGN)水平顯著升高而引起骨髓抑制[30]。在有條件的情況下,治療前檢測TPMT和NUDT15基因型和活性可有助于預測接受AZA或6-巰基嘌呤(6-mercaptopurine,6-MP)治療時出現的嚴重骨髓抑制毒性。此外,加用AZA者需嚴密監測血常規變化,特別是用藥后的前3個月。如出現血細胞進行性下降,特別是外周血白細胞計數<3.5×109/L或者中性粒細胞絕對值<1.5×109/L時,應緊急停用AZA。AZA其他不良反應包括肝內膽汁淤積、靜脈閉塞性疾病、胰腺炎、惡心和嘔吐、皮疹等。少于10%的患者在接受AZA(50 mg/d)時會出現上述不良反應,一般均可在減量或停用后改善。
4.4 應答不完全的處理 應答不完全是指患者經標準治療后,其臨床表現、實驗室指標(血清AST及ALT、總膽紅素、IgG)和肝組織學等改善但未達到緩解標準。治療失敗是指經標準治療后,患者生化指標或組織學檢查仍在惡化。免疫抑制治療應答不完全或無應答者應首先考慮AIH診斷是否有誤和患者服藥依從性如何。IAIHG在AIH二線與三線治療立場聲明[31]中指出,應答不完全是指在免疫抑制治療的前6個月內患者未能實現完全的生化緩解。若臨床上對生化應答的解釋存在不確定性,則需根據肝組織學表現來評估應答情況。組織學緩解比生化緩解需要更長的時間,因此對應答程度的組織學評估可能需要延遲1年。對于一線治療藥物應答不完全的患者,建議檢測AZA代謝物6-TGN的水平。因為AZA本身無內在活性,需要經過體內一系列轉化后才能發揮藥理作用。對于那些6-TGN水平過低(6-TGN水平<220 pmol/8×108RBC)而6-甲基巰基嘌呤(6-methylmercaptopurine,6-MMP)水平過高的患者,可能是由于患者依從性良好的情況下藥物代謝發生改變導致療效欠佳。在這些患者中,AZA聯合別嘌呤醇可能有效,因為別嘌呤醇可阻斷6-MMP途徑。在不完全應答患者中,排除了其他肝病后,應考慮疾病活動度、并發癥和藥物副作用,加強標準藥物治療。若加強標準治療后患者仍未緩解,可考慮三線治療。建議在開始三線治療前進行肝臟活檢,以評估三線治療的必要性,排除其他診斷,并在開始這些試驗性治療前獲得疾病活動度(分級)和纖維化(分期)的詳細信息。
4.5 療程和停藥與復發的處理 免疫抑制治療一般持續3年以上,停藥前患者需維持血清AST、ALT和IgG水平降至正常范圍內(即獲得生化緩解)2年以上。停藥前進行肝活檢復查是首選策略,組織學緩解(HAI≤3分)可將復發率降低到28%。肝臟瞬時彈性成像能用于AIH患者纖維化進展的隨訪,但啟動免疫抑制治療后的最初6個月內肝臟硬度值的變化可能由于炎癥好轉導致[32-33]。患者在停止治療后的最初12個月應進行密切監測,之后至少每年進行一次實驗室檢查。最近,我國一項長期規律隨訪的705例AIH患者隊列顯示,經免疫抑制治療后569 例(80.7%)患者達到完全生化緩解。較低的血清IgG水平、診斷時肝組織纖維化程度輕以及對免疫抑制治療的快速反應是生化和組織學緩解的可靠預測指標,經3年免疫抑制治療并前后肝活檢患者(160例)中,約70%患者達到肝組織學緩解[7]。
復發是指經藥物誘導緩解和停藥(包括不遵醫囑自行停藥)后出現疾病活動加劇,可定義為血清氨基轉移酶水平>3×ULN,伴血清IgG水平不同程度的升高。復發的危險因素包括先前需使用聯合治療方案才能獲得生化緩解者、并發自身免疫性疾病和年齡較輕者。停藥后復發患者,建議再次以予潑尼松(龍)和AZA聯合治療,逐漸過渡至維持治療;而AZA不能耐受者可給予小劑量潑尼松(龍)(≤10 mg/d)或與MMF聯合長期維持治療。多次復發的患者更易出現肝硬化,預后不佳。
4.6 疫苗接種 AIH患者感染新型冠狀病毒的風險普遍增加,且感染新型冠狀病毒后病情重癥化及死亡的風險也會增加。盡快接種新型冠狀病毒疫苗是一項重要的保護措施。如果病情穩定、肝生化指標正常或基本正常,且無疫苗接種的其他禁忌證,可接種新型冠狀病毒疫苗。非急性活動性AIH患者,包括代償期肝硬化階段及病情穩定的失代償期肝硬化階段(無急性食管胃靜脈曲張破裂出血、肝性腦病、自發性細菌性腹膜炎及肝腎綜合征等嚴重并發癥)者可以接種新型冠狀病毒疫苗,且在接種期間不應該停藥。不建議高劑量免疫抑制劑治療者接種減毒活疫苗,滅活疫苗和重組疫苗相對而言比較安全。免疫抑制患者對疫苗的應答率較低,但仍可起到保護效果[34-35]。
推薦意見5:血清氨基轉移酶和IgG水平升高和/或肝組織學炎癥活動的AIH患者應啟動潑尼松(龍)聯合AZA治療方案或潑尼松(龍)單藥治療方案。(A1)
推薦意見6:潑尼松(龍)初始劑量為0.5~1.0 mg·kg-1·d-1(通常30~40 mg/d),并逐漸減量以誘導生化緩解。聯合治療時可在潑尼松(龍)基礎上再加用AZA 1 mg·kg-1·d-1(通常50 mg/d)。建議有條件時在加用AZA前監測TPMT和NUDT15基因型。(B1)
推薦意見7:在脆性糖尿病、高血壓病、嚴重骨質疏松等不能耐受潑尼松龍的非肝硬化患者可考慮使用布地奈德。對AZA不耐受或無應答的AIH患者,建議換用二線免疫抑制劑如MMF(常用劑量為500~1000 mg/d)或他克莫司等。(B1)
推薦意見8:AIH治療目標是獲得并維持生化緩解(血清氨基轉移酶和IgG水平復常)和肝組織學緩解(Ishak系統HAI評分<4分或Scheuer分級系統G≤1),以防止疾病進展。推薦維持免疫抑制治療療程在3年或獲得生化緩解后2年以上。(B1)
推薦意見9:建議在停藥前再次進行肝組織學檢查,獲得肝組織學緩解者方可考慮停藥。對于治療過程中反跳或停藥后復發者,可采用聯合治療方案進行治療。(C1)
推薦意見10:AIH相關肝硬化早期失代償期患者(無肝性腦病、頑固性腹水或細菌性腹膜炎等)可謹慎使用小劑量糖皮質激素(起始劑量為15~20 mg/d)口服,疾病好轉后應快速減量至維持量(一般劑量為5.0~7.5 mg/d),須嚴密監測感染的發生。(B1)
推薦意見11:肝硬化失代償期AIH患者如出現肝硬化并發癥無法改善或出現慢加急性肝功能衰竭時建議進行肝移植術。肝移植術后仍需注意AIH復發問題。(B1)
推薦意見12:建議所有接受糖皮質激素治療的AIH患者在基線時和每年進行骨密度檢測,并適當補充維生素D和鈣劑,骨質疏松嚴重者可使用雙膦酸鹽類藥物治療。(B1)
5 AIH特殊類型的處理
5.1 急性重癥AIH和急性肝衰竭 急性重癥AIH是指起病30 d內,出現黃疸及INR延長(>1.5,且<2.0),無肝性腦病表現且無既往慢性肝病基礎的AIH患者。目前對急性重癥AIH的黃疸水平定義尚有爭論,文獻報道的總膽紅素水平界定在45 μmol/L到升高5×ULN[36-37]。AIH相關急性肝衰竭是指在黃疸、出凝血異常(INR ≥1.5)的基礎上,于起病26周內出現肝性腦病且否認既往慢性肝病基礎。上述診斷需排除合并肝炎病毒感染、毒物,或者藥物誘導的肝損傷等誘發因素。急性重癥AIH患者有29%~39%為ANA陰性或弱滴度陽性,而25%~39%的患者血清IgG在正常范圍[38]。急性重癥AIH患者可在排除感染或敗血癥的基礎上進行糖皮質激素(甲潑尼龍 40~80 mg/d)治療,并同期進行肝移植術前評估,注意監測和預防感染特別是肺部感染的發生。急性重癥AIH患者在糖皮質激素治療1~2周內實驗室檢查無改善或臨床癥狀惡化者,應考慮停用糖皮質激素治療,并進行肝移植術。AIH相關急性肝功能衰竭患者應直接進行肝移植評估。
推薦意見13:急性重癥AIH患者盡早使用甲潑尼松(龍)(40~60 mg/d)試驗性治療,糖皮質激素治療1~2周內實驗室檢查無改善或臨床癥狀惡化者,建議進行肝移植評估。AIH相關急性肝衰竭患者建議直接進行肝移植評估。(C1)
5.2 藥物性自身免疫性肝損傷 米諾環素、呋喃妥因、英夫利昔單抗是目前最常報道的引起AIH樣肝損傷的藥物。免疫檢查點抑制劑在腫瘤患者中的應用也可引起免疫相關肝損傷,經糖皮質激素治療后通常得以緩解,但這類患者往往缺乏AIH實驗室及組織學特征,在診斷上需避免與AIH混淆[39-40]。對藥物誘導的AIH樣肝損傷患者,必須停用可能致病的藥物并持續隨訪。當癥狀或疾病活動嚴重或癥狀和肝生化指標在停藥后未能改善甚至惡化時,應啟動糖皮質激素治療。糖皮質激素撤藥過程肝生化指標持續好轉支持藥物誘導肝損傷的診斷。反之,若肝生化指標再次升高則提示AIH,并且需長期免疫抑制治療。
推薦意見14:肝組織學檢查對鑒別藥物性肝損傷和AIH具有重要作用。應立即停用可疑藥物,病情較重者可短期(3~6個月)使用潑尼松(龍)治療。若停用糖皮質激素后患者肝生化指標再次升高則支持AIH診斷,需進行標準化治療。(C1)
5.3 AIH合并病毒性肝病 目前常規推薦在進行免疫抑制治療前篩查患者的血清HBsAg及抗-HBc抗體和HBV DNA[41]。HBV DNA陽性者直接抗病毒治療,如HBV DNA轉陰后肝功能仍然異常并伴有血清免疫學異常者可考慮行肝組織學檢查,若明確AIH診斷可考慮在抗病毒治療的基礎上加用免疫抑制劑。對于HBV DNA陰性而HBsAg陽性的AIH患者在應用免疫抑制劑治療期間及治療后半年內,推薦服用恩替卡韋或替諾福韋預防性抗病毒治療。對于HBV DNA陰性、HBsAg陰性但抗-HBc陽性的低風險患者,建議密切監測血清學指標(血清HBsAg、HBV DNA),必要時啟動抗病毒治療。隨著糖皮質激素使用的劑量及維持時間增加,HBsAg陰性但抗-HBc陽性患者發生反向血清學轉化(血清HBsAg、HBV DNA出現陽性)的風險增加,潑尼松(龍)中等劑量(10~20 mg/d)到高劑量(>20 mg/d)使用超過4周將提高反向血清學轉化風險1%~10%[41]。推薦每1~3個月對HBsAg陰性但抗-HBc陽性的AIH患者進行血清學檢測(HBsAg、HBV DNA)。而高劑量糖皮質激素治療或應用B細胞敲除劑、細胞因子拮抗劑、鈣調蛋白抑制劑以及其他免疫抑制劑治療,可能提高反向血清學轉化風險,最好避免在HBsAg陽性或者HBsAg陰性但抗-HBc陽性患者中使用,如無法避免上述治療,則應啟動預防性抗病毒治療。我國學者也報道了一組慢性乙型肝炎合并AIH的病例,在抗病毒治療的基礎上進行免疫抑制治療取得了較好療效。因此,慢性病毒性肝病(HBV或HCV感染)在病毒成功治療后肝生化或肝組織學仍有炎癥活動需考慮排除AIH可能[42]。
推薦意見15:在進行免疫抑制治療前篩查患者的HBsAg和抗-HBc抗體以及血清HBV DNA,以評估HBV再激活風險以及啟動抗病毒治療的必要性。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在病毒得到完全抑制后仍存在肝炎活動者需注意排除AIH可能。(C1)
5.4 妊娠期AIH AIH患者妊娠期及產后12個月內發生各種妊娠并發癥的概率為38%。建議AIH患者在妊娠期或備孕期堅持治療,以降低發生復燃及肝臟失代償發生率。AIH復燃的風險在產后提高3倍左右,妊娠期復燃風險較低可能與胎盤植入物等因素有關。肝硬化孕婦隨著妊娠繼續,其血容量增加可能導致食管胃底靜脈曲張破裂出血風險加劇。考慮到β受體阻滯劑及特利加壓素對孕婦的不良反應,建議此類人群在孕前進行預防性曲張靜脈套扎術。目前沒有關于因使用AZA治療AIH而引起孕婦及胎兒不良事件的報道,早先對AZA致畸的依據來自于使用超過治療量的動物實驗研究。禁止有妊娠意愿的AIH患者服用MMF,因其可能與妊娠早期流產、出生缺陷(主要是耳、心臟、唇腭裂等)有關。
推薦意見16:在AIH患者妊娠過程中,可予小劑量潑尼松(龍)(5~10 mg/d)和(或)AZA(25~50 mg/d)維持治療,而在妊娠期間應避免使用MMF。分娩后6個月內需注意預防AIH復燃。(C1)
5.5 兒童AIH 兒童AIH年發病率為0.23/10萬~0.4/10萬,高峰年齡在10歲左右。兒童自身抗體的滴度比成人低,ANA和ASMA≥1∶20,或抗LKM1≥1∶10即有臨床意義。13%~38%的AIH兒童可檢測到抗LKM1。抗LC1主要發生在患有嚴重肝病AIH-2型患兒中。2018年ESPGHAN提出兒童及青少年自身免疫性肝病診斷評分標準[43],增加了外周抗核中性粒細胞抗體(pANNA)、抗LC-1和膽管造影的評分項目和權重,以提高AIH診斷的敏感性并排除合并自身免疫性硬化性膽管炎。兒童AIH的治療緩解標準較成人嚴格:當轉氨酶和IgG水平正常,AIH相關抗體陰性或低滴度時,認為病情完全緩解。歐美推薦的潑尼松(龍)起始劑量2 mg·kg-1·d-1(我國推薦的起始劑量為1 mg·kg-1·d-1,最大用量不超過成人劑量),在4~8周隨著轉氨酶水平的下降而逐漸減量,維持劑量為2.5~5.0 mg/d。在治療的前6~8周,應每周查肝生化指標,并相應調整藥物劑量。大多數AIH需要潑尼松(龍)聯合AZA治療。應用糖皮質激素治療2周后或出現嚴重糖皮質激素副作用及單藥治療轉氨酶水平停止下降時加用AZA,歐美推薦起始劑量為0.5 mg·kg-1·d-1,可逐步加至2 mg·kg-1·d-1;我國推薦劑量為0.5~1.0 mg·kg-1·d-1,最大用量不超過成人劑量。隨著AZA劑量調增,潑尼松(龍)的劑量逐漸降到最低甚至完全停藥。布地奈德聯合AZA可以考慮用于癥狀輕微或者擔心激素副作用而影響用藥依從性AIH兒童。布地奈德不適宜在肝硬化或急性重度AIH。環孢素的起始劑量為4 mg·kg-1·d-1,分3次使用,必要時每2~3天增加1次,以達到全血濃度(250±50)ng/mL持續3個月。如果在第1個月出現臨床和生化緩解,在接下來的3個月將環孢素濃度降低至(200±50)ng/mL。長期隨訪環孢素對兒童AIH的生化緩解效果良好[44]。兒童 AIH 患者對他克莫司長期耐受良好,在對標準治療不耐受或失敗的患者中大部分有效[45]。他克莫司的目標濃度為2.5~5.0 ng/mL。
推薦意見17:兒童AIH患者確診后即應啟動免疫抑制治療,推薦潑尼松(龍)1 mg·kg-1·d-1(最大劑量不超過40 mg/d)和AZA 0.5~1.0 mg·kg-1·d-1(最大劑量不超過50 mg/d)聯合治療方案或潑尼松(龍)單藥治療方案。(C1)
6 預后
AIH患者獲得生化緩解后預后較好,生存期接近同齡普通人群。預后不佳的危險因素主要包括診斷時已有肝硬化和治療后未能獲得生化緩解。我國研究顯示,合并其他系統自身免疫性疾病、肝內膽管損傷和診斷時MELD分數較高者與治療應答和預后不佳有關[46]。HCC發生在1%~9%的AIH相關肝硬化患者,年發病率為1.1%~1.9%。HCC危險因素是肝硬化≥10年、門靜脈高壓、持續性炎癥、反復復發和免疫抑制治療≥3年。一項系統評價及薈萃分析顯示,AIH患者中HCC合并發生率為3.06/1000人年,而AIH相關肝硬化患者中HCC的合并發生率為10.07/1000人年[47]。因此,臨床醫師在AIH肝硬化患者中需要密切監測HCC的發生。
推薦意見18:AIH相關肝硬化患者應每6個月進行一次肝臟超聲檢查和血清甲胎蛋白水平測定,必要時行上腹部增強磁共振或增強CT檢查。(C1)
執筆人:馬雄、王綺夏、肖瀟、苗琪、連敏、唐茹琦、尤紅、陸倫根、韓英、南月敏、徐小元、段鐘平、魏來、賈繼東、莊輝
指南制定專家(以姓氏拼音排序):蔡曉波(上海交通大學附屬第一人民醫院消化內科)、陳莎(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友誼醫院肝病中心)、陳煜(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佑安醫院肝病中心)、陳紅松(北京大學人民醫院肝病研究所)、崔麗娜(空軍軍醫大學第一附屬醫院消化內科)、董加強(空軍軍醫大學第一附屬醫院消化內科)、竇曉光(中國醫科大學附屬盛京醫院感染科)、段維佳(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友誼醫院肝病中心)、段鐘平(首都醫科大學附屬佑安醫院肝病中心)、郭長存(空軍軍醫大學第一附屬醫院消化內科)、郭冠亞(空軍軍醫大學第一附屬醫院消化內科)、韓濤(天津市第三中心醫院肝內科)、韓英(空軍軍醫大學第一附屬醫院消化內科)、侯金林(南方醫科大學南方醫院感染內科)、胡鵬(重慶醫科大學附屬第二醫院感染科)、宦怡(空軍軍醫大學第一附屬醫院放射影像科)、賈繼東(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友誼醫院肝病中心)、孔媛媛(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友誼醫院國家消化系統疾病臨床醫學研究中心方法學平臺)、李杰(北京大學醫學部基礎醫學院病原生物學系)、李軍(江蘇省人民醫院感染病科)、李淑香(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友誼醫院肝病中心)、李增山(空軍軍醫大學第一附屬醫院病理科)、令狐恩強(解放軍總醫院第一醫學中心消化內科)、劉家云(空軍軍醫大學第一附屬醫院檢驗科)、劉景豐(福建醫科大學孟超肝膽醫院肝膽外科)、劉燕敏(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佑安醫院肝病科)、劉迎娣(解放軍總醫院第一醫學中心消化內科)、陸倫根(上海交通大學附屬第一人民醫院消化內科)、羅新華(貴州省人民醫院感染科)、呂婷婷(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友誼醫院肝病中心)、馬雄(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仁濟醫院消化內科)、苗琪(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仁濟醫院消化內科)、南月敏(河北醫科大學第三醫院中西醫結合肝病科)、曲穎(上海交通大學附屬第一人民醫院消化內科)、任紅(重慶醫科大學第二醫院傳染科)、任萬華(山東省立醫院感染性疾病科)、尚佳(河南省人民醫院感染性疾病科)、尚玉龍(空軍軍醫大學第一附屬醫院消化內科)、時永全(空軍軍醫大學第一附屬醫院消化內科)、唐承薇(四川大學華西醫院消化內科)、王建設(復旦大學附屬兒科醫院感染科)、王婧雯(空軍軍醫大學第一附屬醫院藥劑科)、王綺夏(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仁濟醫院消化內科)、魏來(北京大學人民醫院肝病科)、吳浩(四川大學華西醫院消化內科)、徐小元(北京大學第一醫院感染疾病科)、閻明(山東大學齊魯醫院消化內科)、楊東亮(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附屬協和醫院感染科)、楊永峰(南京市第二醫院肝病科)、楊詔旭(空軍軍醫大學第一附屬醫院肝膽外科)、尤紅(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友誼醫院肝病中心)、張欣欣(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瑞金醫院感染科)、張躍新(新疆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感染科)、趙景民(解放軍總醫院第五醫學中心病理科)、趙守松(蚌埠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感染病科)、趙新顏(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友誼醫院肝病中心)、鄭林華(空軍軍醫大學第一附屬醫院消化內科)、周新民(空軍軍醫大學第一附屬醫院消化內科)、莊輝(北京大學醫學部基礎醫學院病原生物學系)
志謝(以姓氏拼音排序):安紀紅(內蒙古自治區人民醫院感染科)、鄧國宏(陸軍軍醫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傳染科)、黃燕(中南大學湘雅醫院傳染科)、黃緣(北京清華長庚醫院肝膽內科)、李榮寬(大連醫科大學附屬二院感染科)、李樹臣(哈爾濱醫科大學第二附屬醫院傳染科)、陸海英(北京大學第一醫院傳染科)、石荔(西藏自治區人民醫院感染科)、蘇明華(廣西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感染科)、溫志立(南昌大學第二附屬醫院消化內科)、吳彪(海南省人民醫院感染科)、徐京杭(北京大學第一醫院肝病科)、楊麗(四川大學華西醫院消化內科)、楊積明(天津市第二人民醫院感染科)、楊晉輝(昆明醫科大學附屬二院消化內科)、張繚云(山西醫科大學第一醫院傳染科)、周璐(天津醫科大學總醫院消化內科)、周永健(廣州市第一人民醫院消化內科)、祖紅梅(青海省第四人民醫院傳染科)參加本指南制定的討論,并提出了富有建設性的意見和建議。
利益沖突聲明:所有作者均聲明不存在利益沖突。

參考文獻見二維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