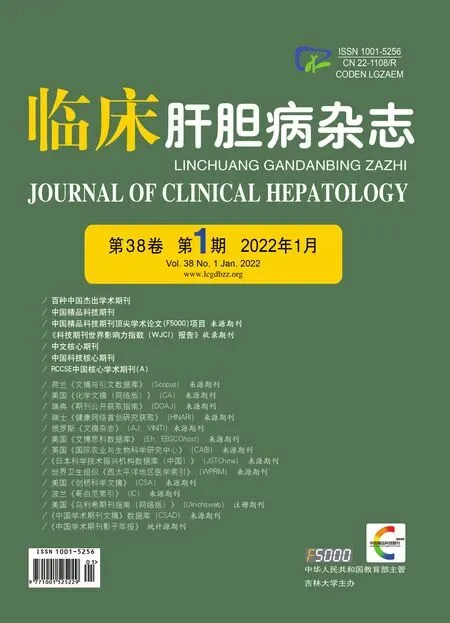原發性硬化性膽管炎診斷及治療指南(2021)
中華醫學會肝病學分會
1 概述
原發性硬化性膽管炎(primary sclerosing cholangitis,PSC)是一種多灶性膽管狹窄和進展期肝病為特征的少見疾病。PSC臨床表現多樣,病程多變,在排除其他病因后,PSC診斷主要依賴膽管影像學和肝臟組織病理學。PSC患者常合并炎癥性腸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IBD),且患膽管癌和結直腸癌風險顯著增加。目前尚無有效治療PSC的藥物,肝移植是唯一有效的治療方法。由于治療手段有限,PSC患者的早期診斷、評估和監測具有重要意義。
1.1 指南涵蓋的范圍和目的 2015年我國第一個《原發性硬化性膽管炎診斷和治療專家共識》發布。近年來,PSC的研究進展為該病的臨床診治提供了一些新的證據。中華醫學會肝病學分會自身免疫性肝病學組組織相關專家對近年來的研究證據進行評估,在2015年共識意見基礎上制定了本指南。本指南涵蓋的臨床問題包括:PSC的定義、流行病學、病理生理學、臨床診斷、治療、特殊情況處理、預后等問題,也包括IgG4相關硬化性膽管炎(IgG4-SC)的診治原則(附件1)。本指南旨在為我國醫務工作者在診治時提供參考和指導,不應作為患者診治的強制性規范。醫師應根據患者的具體情況、醫療資源可及性、患者的治療意愿等制定個體化合理診療方案。本指南不適用于無臨床醫學教育背景的普通公眾。
1.2 制定指南的人員和方法 參與本指南撰寫的專家專業領域包括:消化病學、肝病學、風濕免疫學、外科學、傳染病學、病理學及循證醫學等。指南制定過程未征集患者、醫療保險人士、社會公眾的觀點及意愿。本指南發布之前邀請國內消化病學、內鏡學、肝病學、免疫學、病理學、影像學、檢驗學、藥學以及循證醫學等專家進行了外部評審。
參與本指南制定的專家對2021年8月以前的PubMed、Medline、Cochrane、Embase等外文數據庫、中國知網(CNKI)、維普等中文數據庫進行了檢索。檢索采用英文主題詞為“primary sclerosing cholangitis,autoimmune pancreatitis,IgG4,autoimmune overlap syndrome,cholangiocarcinoma”等。流行病學、診斷、治療等方面的關鍵詞為“prevalence,incidence,ursodeoxycholic acid,serum marker,ERCP,MRCP,immunosuppressant,steroids,liver transplantation”等。中文關鍵詞為“膽管炎、硬化性膽管炎、IgG4”等。指南制定相關專家對檢索文獻進行了系統性評估。將Meta分析、隨機對照研究、非對照研究、觀察研究、隊列研究、病例報告、共識意見、專家觀點納入本指南的參考文獻。
指南制定過程遵循Appraisal of Guidelines for Research and Evaluation(AGREE)instrument Ⅱ(www.agreetrust.org)標準。證據等級評估采用GRADE標準(表1)。指南的推薦意見基于最高等級的研究數據。當無高質量研究或者研究結論不確定時,本指南的推薦意見基于已發表的專家共識意見和本指南制定專家組的一致意見,同時也結合我國臨床診治現狀,考慮了相關診療措施在我國的有效性和可及性。本指南的推薦意見主要基于歐美國家的資料,我國和亞洲其他國家的相關研究資料較少,因此具有一定局限性。臨床研究在不斷更新,新的藥物和臨床試驗結果將不斷出現,建議每5年左右對指南進行更新。

表1 推薦意見的證據等級和推薦強度等級
2 流行病學和發病機制
2.1 流行病學 PSC患病率和發病率存在區域差異性。最早PSC的流行病學資料來源于北美(1976年—2000年)發病率為0.9/10萬~1.3/10萬,其中女性0.54/10萬,男性1.25/10萬[1]。2019年英國胃腸病學會(BSG)報道北歐的PSC發病率與北美比較接近,為0.91/10萬~1.3/10萬,小膽管型PSC發病率約為0.15/10萬[2]。近年來的數據顯示,北歐和北美的PSC患病率達3.85/10萬~16.2/10萬,有逐年增高趨勢[3]。亞洲的流行病學資料來源于新加坡和日本,分別報道PSC患病率為1.3/10萬、0.95/10萬,低于歐洲和北美國家[4-5]。PSC好發于男性,約占2/3,PSC平均確診年齡為20~57歲,發病年齡呈雙峰性,兩個發病高峰分別為15歲和35歲左右[6]。我國尚缺乏PSC的流行病學資料。
2.2 發病機制及分類 PSC是一種以特發性肝內外膽管炎癥及膽管纖維化改變導致多灶性膽管狹窄、慢性膽汁淤積的自身免疫性疾病,發病機制尚不明確。目前認為,PSC是遺傳、環境、免疫、膽汁酸代謝及腸道菌群等多種因素共同參與所致[7-15]。PSC具有遺傳易感性,目前已經確定有20多個PSC遺傳易感位點,但遺傳因素對PSC發病的影響僅不到10%,環境因素的影響高達50%以上;腸肝軸的交互作用在PSC發病中也發揮一定作用,其中腸黏膜屏障障礙、菌群失調、免疫交互作用等參與了PSC發病;膽汁酸穩態失衡、膽管黏膜屏障受損、反應性膽管細胞激活等是膽管損傷的病理生理基礎;PSC患者膽管周圍存在反應性T淋巴細胞、巨噬細胞和中性粒細胞,以T淋巴細胞為主,免疫紊亂也是PSC的發病機制之一。以上多種因素導致膽管慢性炎癥、纖維化,肝臟星狀細胞、肌纖維母細胞激活,并與膽管細胞交互作用進一步加重膽管損傷和肝臟纖維化,膽管長期慢性炎癥可導致膽管狹窄、肝內膽汁淤積、肝臟纖維化、肝硬化甚至膽管癌。
依據膽管受損的部位可將PSC分為以下幾種。(1)大膽管型:損傷肝外較大膽管,約占PSC患者的90%;(2)小膽管型:損傷較小膽管,膽管影像學無異常發現,少數患者可發展為大膽管型PSC;(3)全膽管型:肝內外大小膽管均受損傷。
3 診斷
PSC是一種持續進展性疾病,從肝內外膽管炎癥、膽管纖維化、肝硬化、肝功能衰竭直至死亡。診斷主要依據影像學檢查:膽管系統呈多灶性狹窄、節段性擴張、串珠狀及枯樹枝樣改變,堿性磷酸酶(ALP)和γ-谷氨酰轉移酶(GGT)等相關肝酶指標升高和/或膽汁淤積癥狀等表現。對于經典PSC患者,肝臟組織學檢查并非必須。診斷小膽管型PSC需要肝臟組織學,病理表現包括小膽管周圍纖維組織增生,呈同心圓性洋蔥皮樣改變。
3.1 臨床表現 PSC臨床表現多樣,早期多無癥狀,部分患者體檢或因IBD進行肝功能篩查時診斷PSC。約50%患者表現為間斷右上腹疼痛、黃疸、瘙癢、乏力、發熱和體質量下降[2,4,16]。黃疸呈波動性、反復發作,可伴有中低熱或高熱及寒戰。
PSC臨床表現多樣,常見以下表現。(1)無癥狀,僅體檢時偶然發現ALP/GGT升高;(2)IBD患者行肝功能篩查時發現ALP升高;(3)膽汁淤積引起的黃疸、瘙癢等;(4)進展期肝病、肝硬化所致癥狀:可出現門靜脈高壓引起靜脈曲張出血、腹水等;(5)反復發作的膽管炎,表現為發熱、寒戰、右上腹痛、黃疸等;(6)肝衰竭:表現為進行性黃疸加重及凝血障礙;(7)癌變:PSC患者易患膽管癌,PSC確診后5年、10年、終生患膽管癌的風險分別為7%、8%~11%、10%~20%[17-18]。發生膽管癌的PSC患者肝功能迅速惡化、黃疸加重,可伴有體質量減輕。PSC合并潰瘍性結腸炎(UC)患者結直腸腫瘤風險增加,以右半結腸癌多見,可出現體質量減輕、不全腸梗阻等癥狀。
PSC可并發脂溶性維生素缺乏癥、代謝性骨病等,還可伴有與免疫相關的疾病,如甲狀腺炎、紅斑狼瘡、風濕性關節炎等。
3.2 實驗室檢查
3.2.1 血清生化學 PSC的血清生化異常主要表現為膽汁淤積型改變,通常伴有ALP、GGT升高,目前尚無明確診斷標準的臨界值。ALP升高是診斷的敏感指標,但無特異性。對于骨生長中的青少年患者,需血清GGT輔助診斷。出現血清膽紅素升高,提示疾病進展或預后不良。血清轉氨酶通常正常,部分患者也可升高2~3倍。轉氨酶顯著升高者需鑒別是否重疊自身免疫性肝炎(AIH)、并發急性膽管梗阻或藥物性肝炎等可能。疾病晚期可出現低蛋白血癥及凝血功能異常。
3.2.2 免疫學檢查 PSC缺乏特異性的自身抗體。部分患者血清中可檢測出多種自身抗體,包括抗核抗體(ANA)、抗中性粒細胞胞漿抗體(pANCA)、抗平滑肌抗體(抗SMA)、抗內皮細胞抗體、抗磷脂抗體等。但上述抗體一般為低滴度陽性,對PSC診斷無特異性。部分患者可出現高γ-球蛋白血癥,約半數伴免疫球蛋白IgG或IgM水平輕至中度升高。歐洲及美洲報道約50%的PSC出現IgM升高[19],而亞洲日本報道24%患者出現高IgM,且多出現于年輕患者[20-21]。
3.2.3 影像學檢查 PSC典型的影像學表現為肝內外膽管多灶性、短節段性、環狀狹窄,膽管壁僵硬缺乏彈性、似鉛管樣,狹窄上端的膽管可擴張呈串珠樣表現,進展期患者可顯示長段狹窄和膽管囊狀或憩室樣擴張,當肝內膽管廣泛受累時可表現為枯樹枝樣改變。
(1)腹部超聲:是用于對PSC疾病初步篩查的常規手段。其可顯示肝內散在片狀強回聲及膽總管管壁厚度、膽管局部不規則狹窄等變化,并可顯示膽囊壁增厚程度、膽汁淤積及膽管擴張情況。結合病史可協助進行肝內外膽管結石、膽管癌、繼發性膽管炎及術后膽管狹窄等疾病的鑒別。
(2)腹部CT:不是用于PSC診斷的常規手段。PSC患者腹部CT可出現膽管擴張、膽管內占位、脾大、門靜脈增寬、靜脈曲張等門靜脈高壓的表現以及腹腔淋巴結腫大等。CT主要用于疑似膽管癌患者的鑒別診斷和膽管癌分期。
(3)磁共振胰膽管成像(MRCP):在臨床及生化診斷證據存在時,MRCP對PSC的診斷具有非常高的特異性。已成為PSC診斷的首選非侵入性影像學檢查方法,準確性與ERCP相當,敏感性和特異性分別為80%~100%、89%~100%[2,22-24]。MRCP還可提供肝實質、靜脈曲張、肝癌和淋巴結等信息,但其對小膽管型PSC或早期疾病的診斷敏感性較低。
(4)經內鏡逆行胰膽管造影(ERCP):ERCP既往被認為是診斷PSC的“金標準”,但由于可能導致嚴重并發癥,如胰腺炎、膽管炎、穿孔、出血等,因此除非有治療需要或需膽管取樣,一般不行診斷性ERCP。存在以下情況可考慮行ERCP:①MRCP和肝臟組織檢查仍疑診PSC或MRCP存在禁忌時;②在MRCP檢查后可疑存在顯性狹窄且其臨床癥狀可能在內鏡治療后好轉,需行ERCP內鏡治療和膽管活檢(細胞刷檢、膽管組織檢查);③在疑似膽管癌的PSC患者,應考慮ERCP和膽管活檢(細胞刷檢、膽管組織檢查)。ERCP應由經驗豐富的內鏡醫師進行,建議ERCP前常規給予預防性抗菌藥物治療,既可以降低菌血癥的發生率,也可以預防膽管炎和敗血癥的發生。可在ERCP期間行膽汁取樣進行細菌培養,以指導膽管炎發生后抗菌藥物的選擇[25]。在無禁忌情況下,ERCP前后應立即直接給予100 mg的雙氯芬栓或吲哚美辛栓直腸給藥。此外,在ERCP術后胰腺炎風險較高的情況下,應考慮置入胰管支架預防術后胰腺炎。
(5)其他內鏡檢查:疑似肝外疾病和MRCP檢查發現不能確定的病例,超聲內鏡和彈性成像可能會有助于膽總管狹窄、管壁增厚和肝纖維化情況的判斷。導管內超聲檢查和激光共聚焦內鏡也有助于膽管病變的評估和鑒別診斷(詳見IgG4相關硬化性膽管炎部分,附件1)。
3.2.4 肝臟病理 PSC大體病理上可見肝外膽管管壁增厚,管腔狹窄。組織學上PSC表現為膽管系統的纖維化改變,可累及整個肝內外膽管系統,少數僅累及肝內或肝外膽管系統,后期肝實質細胞可受損。肝內膽管周圍纖維組織圍繞小膽管呈同心圓樣排列的“洋蔥皮樣”改變是PSC的典型病理學改變。但由于肝臟活檢較難獲取較大的膽管,當PSC無肝內小膽管累及時,PSC患者的肝臟組織學可表現為正常或者非特性的肝內膽汁淤積改變。僅有不足20%的PSC患者肝組織檢查發現這種典型改變[26]。一項對138例PSC患者的回顧性分析顯示,對于具有典型影像學表現的PSC患者,肝臟組織學檢查并不能獲取更多的診斷信息[27]。因此具有典型臨床和影像學特征的PSC患者,診斷無需肝臟組織學檢查。
PSC在病理組織學上可分為4期,分別為Ⅰ期(即門靜脈期)、Ⅱ期(即門靜脈周圍期)、Ⅲ期(即纖維間隔形成期)及Ⅳ期(即肝硬化期)。利用肝臟組織檢查可以對PSC患者進行分期,也可以進行肝臟炎癥和纖維化評分。兩項分別包括64例和119例PSC患者的回顧分析顯示,肝臟組織學評分系統對于PSC具有良好的預后評估價值[28-29]。
感染、缺血、中毒、腫瘤、遺傳、手術等導致的繼發性硬化性膽管炎影像學和肝臟生化檢查與PSC類似[30]。對不能確診的患者,肝臟組織學有助于鑒別。
極少數PSC患者病變只累及肝內小膽管,膽管成像無異常發現,此類患者被稱為小膽管型PSC。PSC患者可同時合并AIH,也有少數PSC合并原發性膽汁性膽管炎的報道,但非常少見。一項包括7931例PSC患者的多中心長期隨訪研究顯示,約3.6%的PSC患者為小膽管型PSC,6.6%為PSC-AIH重疊綜合征[31]。對于膽管影像正常的小膽管型PSC和重疊其他肝臟疾病的患者,肝組織學檢查對于診斷是必需的。
3.3 診斷標準 目前尚無公認的PSC診斷標準。2016年日本非感染性肝膽疾病小組制定了日本的PSC診斷標準,但該診斷標準未納入小膽管型PSC[32]。2021年,國際PSC研究小組的PSC共識意見分別制定了大膽管型PSC和小膽管型PSC的診斷標準[33]。
本指南推薦的大膽管型PSC診斷標準為:(1)膽管成像具備PSC典型特征;(2)以下標準至少滿足一條:①膽汁淤積的臨床表現及生物化學改變(成人ALP升高、兒童GGT升高);②IBD臨床或組織學證據;③典型PSC肝臟組織學改變;(3)除外其他因素引起繼發性硬化性膽管炎。對于膽管成像無PSC典型表現,如果滿足以上標準第2條中2條以上或僅有PSC典型膽道影像學特征可疑診PSC。
本指南推薦的小膽管型PSC診斷標準為:(1)近期膽管影像學無明顯異常改變;(2)典型PSC肝臟組織病理學改變;(3)除外其他因素所致膽汁淤積。如果患者膽管影像學無異常,但肝臟組織學具有PSC特點但不典型時,若患者同時存在IBD臨床或組織學證據及膽汁淤積的生物化學證據時,也可診斷小膽管型PSC。
3.4 鑒別診斷 PSC需要與繼發性硬化性膽管炎進行鑒別診斷,見表2[34-35]。PSC與IgG4相關硬化性膽管炎(IgG4-SC)膽管影像學表現相似,鑒別困難。由于IgG4-SC對糖皮質激素治療應答良好且具有更好的臨床預后,所以臨床上要特別注意PSC和IgG4-SC的鑒別。IgG4-SC的診斷主要根據典型膽管影像學改變、血清IgG4升高、同時存在膽管外IgG4相關疾病表現和典型的組織學改變[36]。雖然血清IgG4升高是IgG4-SC的特征性血清學改變,但約10%的患者血清IgG4處于正常水平。此外,9%~27% PSC患者也可以出現血清IgG4升高,血清IgG4升高的PSC患者比血清IgG4正常的PSC患者臨床預后更差[37-38]。因此,對于PSC患者檢測血清IgG4水平不僅有助于鑒別診斷,也有助于預后判斷。
推薦意見1:對疑診PSC的膽汁淤積患者,膽管影像學檢查應首選MRCP。(A1)

表2 繼發性膽管炎的病因分類
推薦意見2:對疑診PSC患者,應進行血清AMA和IgG4檢測,以除外原發性膽汁性膽管炎(PBC)和IgG4-SC。(C2)
推薦意見3:對診斷不明確、可疑小膽管型PSC或可疑重疊其他疾病的患者可行肝臟活組織檢查,不建議將肝活檢作為PSC的常規診斷手段。(B1)
推薦意見4:對于膽汁淤積并具有枯樹枝、串珠樣等典型膽管影像學改變的患者,排除繼發性膽管炎后可診斷為大膽管型PSC。(A1)
推薦意見5:膽管影像學無異常的膽汁淤積患者,若肝臟病理顯示典型“洋蔥皮”樣膽管纖維化或硬化,可診斷為小膽管型PSC;膽管影像學無異常的膽汁淤積患者,肝臟組織學提示小膽管纖維化,同時合并IBD者也可診斷小膽管型PSC。(B1)
推薦意見6:對于疑診PSC,MRCP聯合肝臟組織學仍不能確診、膽管狹窄需內鏡治療或需膽管活檢以排除膽管癌者,可行ERCP;ERCP術前應預防性使用抗菌藥物。(C2)
3.5 合并癥和并發癥
3.5.1 IBD PSC與IBD共患率的報道差異較大。薈萃分析顯示北美和歐洲PSC患者中IBD共患率分別為70%和63%[39]。日本的流行病學研究顯示34%的PSC同時伴發IBD,青年PSC患者IBD共患率為57%,基本接近歐美國家。老年PSC與IBD共患率則顯著低于歐美(12%)[40-41]。一般情況下,IBD的臨床癥狀先于PSC出現,但也有越來越多的患者在PSC診斷后才發現同時患有IBD。在伴發IBD的PSC中,80%以上的患者為PSC-UC,約10%患者為PSC-克羅恩病(CD),另有10%為不確定性結腸炎。PSC-UC的患者中全結腸炎、倒灌性回腸炎和直腸豁免更常見[42]。與單純的IBD相比,PSC-IBD患者常無明顯癥狀或癥狀輕微,內鏡下結腸黏膜表現可為正常,但腸黏膜活組織檢查常可發現顯微性結腸炎[43]。因此,結腸鏡下多部位多點活檢對于PSC患者的IBD篩查具有重要意義。與單純IBD患者相比,PSC-IBD共患者結腸癌風險顯著升高。最近的兩項薈萃分析[44-45]進一步證實了PSC-IBD與進展期結直腸癌的相關性。大樣本的回顧性研究顯示PSC-IBD患者肝膽系統腫瘤、肝移植及死亡風險也顯著升高[31,46-47]。定期進行結直腸癌篩查可以改善PSC-IBD患者臨床結局[31,48]。
推薦意見7:對于確診PSC的患者,建議行結腸鏡檢查并活檢以評估是否合并IBD(A1);對于PSC伴發IBD患者,建議每年進行1次結腸鏡檢查;PSC不伴發IBD者每3年復查1次結腸鏡。(C1)
3.5.2 脂溶性維生素缺乏、代謝性骨病 PSC所致的膽汁淤積可導致脂溶性維生素的吸收不良,以維生素A、D、E的缺乏最為常見[49]。應對PSC患者進行脂溶性維生素水平的檢測,如缺乏可予以相應補充。代謝性骨病是慢性膽汁淤積時常見的并發癥。PSC患者體內成骨活動降低,骨吸收增加,出現骨質疏松的風險是正常人群的24倍[50-51]。年齡較大、BMI較低及長期合并IBD時,骨質疏松癥的危險性增加[50-52]。PSC疾病的嚴重程度可能與骨質疏松的程度無明顯相關性,雙能X線在診斷微小骨密度變化時,比MRI等技術更具優勢[53-54]。合并骨質疏松的PSC患者可按照骨質疏松相關指南進行治療[55]。
推薦意見8:并發脂溶性維生素缺乏的PSC患者,可予補充脂溶性維生素治療。(C2)
推薦意見9:PSC患者應接受骨密度檢查并評估骨質疏松風險,必要時給予治療。(C1)
3.5.3 肝膽腫瘤 PSC患者易患各種肝膽惡性腫瘤,其中以膽管癌為主。3.3%~36.4%的PSC患者可發展為膽管癌,且有研究認為PSC確診后1年內膽管癌的發生率最高[31,48,56-57]。PSC患者發生膽管癌的危險因素主要包括年齡、性別及是否合并IBD等[31]。隨著年齡的增加,PSC發生膽管癌的風險顯著升高。年齡>60歲的PSC患者,其膽管癌的發生率是年齡<20歲患者的近20倍。且PSC患者中男性膽管癌的發生率明顯多于女性。此外,當PSC合并IBD,尤其是潰瘍性結腸炎時,膽管癌的發病率顯著升高[31]。
可用于監測膽管癌的影像學技術主要包括超聲、MRI/MRCP、CT和ERCP等。CA19-9是臨床上應用最廣的膽管癌相關腫瘤標志物。影像學檢查聯合CA19-9可提高膽管癌篩查的靈敏度[58-59]。因此,建議對所有PSC患者每6~12個月行超聲、CT、MRI/MRCP及CA19-9檢查來篩查膽管癌。考慮到ERCP術后胰腺炎、膽管炎、出血等并發癥的風險,不推薦將ERCP作為PSC患者篩查膽管癌的常規檢查手段。但對于出現嚴重膽管狹窄、占位改變、CA19-9漸進性升高的患者,可考慮行ERCP進行刷檢、活檢等,進一步判斷有無膽管癌[60- 61]。
約2%的PSC患者最終罹患膽囊癌,10%~17%PSC患者伴發膽囊息肉[61]。腹部超聲對膽囊息肉的檢出具有較高的靈敏度和特異度。曾有觀點認為PSC患者可考慮行膽囊切除,以預防膽囊癌的發生[62]。但有研究表明,將膽囊息肉超過8 mm作為標準,可準確區分膽囊良性及惡性病變[63]。故也有國外學會主張膽囊息肉超過8 mm的PSC患者接受膽囊切除治療[64]。由于尚缺乏更可靠的循證依據,PSC患者是否需行膽囊切除應結合患者個體情況,并充分考慮患者的獲益/風險比。
肝細胞癌(HCC)在PSC患者中的發病率較低。當疾病進展至肝硬化后,HCC的發生率是否升高也尚無定論。根據我國肝硬化診治指南,對于確診的肝硬化患者,應密切篩查和監測HCC指標,方案可考慮每3~6個月行B超聯合甲胎蛋白(AFP)檢測[65]。
推薦意見10:確診PSC的成年患者,可每6~12個月行影像學和/或CA19-9檢查,進行膽管癌和膽囊癌篩查。(B2)
推薦意見11:合并膽囊息肉的PSC患者,若息肉存在高危因素(>8 mm),可行膽囊切除術。(C2)
推薦意見12:對于進展為肝硬化的PSC患者,應每3~6個月行腹部超聲檢查和AFP檢測,進行HCC篩查。(C1)
4 PSC的治療
4.1 PSC的治療藥物
4.1.1 熊去氧膽酸(ursodeoxycholic acid,UDCA) 早期非對照臨床研究顯示,UDCA可以改善PSC患者的臨床和生物化學指標[66]。隨后的一些隨機對照臨床研究(RCT)進一步評估了UDCA治療PSC的效果[67-85]。這些臨床研究評估了不同劑量UDCA的治療作用,小劑量UDCA(10~15 mg·kg-1·d-1)可以改善患者的肝臟生化學指標,但無法改善患者的肝移植、死亡等長期臨床終點[73-74,79-85];大劑量UDCA不僅無獲益,反而增加死亡、肝移植風險,嚴重不良事件發生率明顯增加[69-71,78]。兩項中等劑量UDCA(17~23 mg·kg-1·d-1)治療PSC的RCT研究[72,77]顯示,中等劑量UDCA可以改善患者肝臟組織學,并有降低肝移植率、死亡率及膽管癌發生率的趨勢。但隨后的研究則顯示中等劑量UDCA不能提高患者的5年生存率。UDCA治療PSC薈萃分析也顯示UDCA雖然可以改善患者的肝臟生化指標,但不能提高患者長期預后[86-90]。在預防結直腸癌(CRC)和膽管癌(CCA)方面,RCT研究和薈萃分析顯示UDCA不能降低PSC患者的CCA和CRC的發病風險,高劑量的UDCA甚至會增加CRC發病率[68-69,76,90- 93]。最近一項包括161例PSC患者的多中心RCT研究[94]顯示norUDCA可以劑量依賴方式降低PSC患者的ALP,且安全性好,其長期臨床獲益還有待進一步研究確定。雖然UDCA不能改善PSC的長期預后,但一項前瞻性臨床研究則顯示已經使用UDCA治療的PSC患者UDCA停用3個月后,患者肝臟生化指標顯著惡化,部分患者瘙癢加重[95]。目前尚無法確定UDCA停用后患者的肝功能及臨床癥狀變化是否是停藥反彈效應,其長期影響也不能確定。
4.1.2 糖皮質激素和免疫抑制劑 糖皮質激素治療PSC的研究較少。單臂前瞻性臨床研究顯示布地奈德可以改善PSC患者的肝臟生化指標[96],而潑尼松和布地奈德的隨機對照臨床研究則發現只有潑尼松可改善PSC肝臟生化指標[79]。薈萃分析[97-98]結果無法對糖皮質激素在PSC的治療中做出推薦或反對。一項回顧性研究[99]和一項前瞻性研究[100]顯示部分合并AIH或者具有AIH特征的患者使用糖皮質激素治療可能會獲益。免疫抑制劑如他克莫司、嗎替麥考酚酯、甲氨蝶呤、英夫利昔單抗等在PSC治療中的研究多為小樣本研究[73,101- 105]。有研究顯示,他克莫司可以改善PSC患者肝臟生化學指標[102,105]。總之,薈萃分析顯示免疫抑制劑不能降低PSC患者死亡或肝移植風險[106]。
4.1.3 其他藥物 除上述提到的藥物之外,也有一些抗菌藥物治療PSC的臨床研究,包括萬古霉素、甲硝唑、利福昔明等[107-110]。萬古霉素可以顯著降低PSC患者的ALP、丙氨酸轉氨酶(ALT)等生化指標,并且可降低PSC患者Mayo PSC評分(MRS),薈萃分析結果顯示萬古霉素可能對PSC患者有益[111];甲硝唑的臨床研究結論存在差異;利福昔明則療效不明顯。近年來一些新的藥物如FGF19類似物、FXR激動劑等也被用于PSC治療,但目前臨床證據尚不充分。
推薦意見13:對PSC患者可給予UDCA 15 mg·kg-1·d-1治療。(C2)
推薦意見14:糖皮質激素不應作為PSC患者的常規用藥,僅可用于重疊AIH或具有AIH特征的PSC患者。(B1)
4.2 PSC瘙癢的治療 瘙癢是PSC患者最常見的臨床癥狀之一,20%~60%PSC患者可以出現瘙癢癥狀[112-114]。瘙癢嚴重影響患者的生活質量[115]。英國胃腸病學會PSC指南推薦的治療PSC瘙癢的藥物為考來烯胺,二線藥物為利福平和納曲酮,但是其推薦級別和證據等級都相對比較低[2]。一項包括14例PBC和14例PSC患者的隨機對照研究顯示考來維倫與安慰劑相比不能有效改善膽汁淤積患者的瘙癢癥狀,而考來維倫吸附膽汁的作用要比考來烯胺強7倍[116]。另外兩項小樣本包括PSC患者的RCT研究顯示舍曲林可以有效地改善PSC患者瘙癢,與利福平相比對肝臟生化指標影響更小[117-118]。最近的一項隨機雙盲安慰劑對照研究顯示苯扎貝特治療PBC或PSC患者瘙癢的效果優于安慰劑[119]。
推薦意見15:對于伴有嚴重瘙癢的PSC患者,可用舍曲林、利福平、納曲酮或考來烯胺等藥物治療。(C1)
4.3 膽管狹窄的內鏡治療 膽管顯性狹窄(dominant stricture,DS)的定義為:ERCP膽管造影時,膽總管直徑≤1.5 mm或左右肝管匯合處2 cm范圍內肝管直徑≤1 mm[25]。前瞻性研究顯示,44%的PSC患者隨著隨訪時間的延長會發生膽管顯性狹窄[120]。一項單中心25年的回顧性分析顯示,63%的PSC患者發生膽管顯性狹窄[121]。另外一項回顧性研究顯示,45%的PSC患者發生膽管顯性狹窄,但與無膽管顯性狹窄的患者相比,膽管顯性狹窄患者在診斷后2個月到1年的肝臟生化學改變與無膽管顯性狹窄患者無顯著差異,這提示膽管顯性狹窄對于患者短期預后無顯著影響[122]。長期隨訪則發現膽管顯性狹窄與膽管癌發生風險增加相關,膽管顯性狹窄患者生存期明顯短于無膽管顯性狹窄患者(13.7年 vs 23年),生存期差異主要原因是膽管顯性狹窄患者的膽管癌發生率更高[121]。PSC患者出現有癥狀或肝臟生化學惡化的膽管顯性狹窄可能是膽管癌的臨床表現,良性的膽管顯性狹窄也會增加PSC患者膽管癌的風險。
針對PSC患者膽管顯性狹窄的內鏡治療方式主要為ERCP下球囊擴張、支架置入或二者聯合。早期研究顯示,支架置入后2~3個月內患者支架堵塞發生率較高[123]。因此,后續的研究一般都采用短期支架置入(1~2周)。PSC患者膽管顯性狹窄內鏡下治療的研究多數為前瞻性或回顧性非隨機對照研究,且樣本量相對較小[121,123-126]。這些研究的結果顯示,球囊擴張或支架置入可以在短期內改善患者的癥狀及肝臟生化學指標,且根據預后評分模型評估可提高無肝移植生存。一項隨訪2年的多中心隨機對照臨床研究顯示,在膽管再通率方面,短期支架置入與單純球囊擴張相比無顯著差異,且嚴重不良事件發生率顯著高于球囊擴張(45% vs 7%)[127]。薈萃分析顯示,在癥狀改善、狹窄再發率、肝移植率、5年生存率方面,短期支架置入與球囊相比無顯著差異,支架置入后胰腺炎、出血、穿孔等不良事件發生率高于球囊擴張,僅在膽管炎/菌血癥方面優于球囊擴張[128]。雖然球囊擴張和短期支架相比在臨床效果方面無顯著差異,但是并非所有患者球囊擴張都能成功,對于球囊擴張失敗的患者,短期支架置入是合理的治療方式。目前球囊擴張的時機和間隔尚無統一的規范。一項286例PSC患者的回顧性分析顯示,對于膽管顯性狹窄的PSC患者定期ERCP下球囊擴張的長期效果優于按需ERCP下球囊擴張,患者無肝移植生存期明顯延長(17.8年 vs 11.1年)[129]。
PSC患者膽管癌風險顯著增加,大多數PSC相關膽管癌都是在膽管顯性狹窄的基礎上發生[17]。膽管癌早期或局部進展期患者臨床預后顯著優于晚期患者,而不可切除的膽管癌患者化療或不化療的平均中位生存期只有5~12個月[130]。多數PSC患者的膽管顯性狹窄是良性病變,約5%的膽管顯性狹窄者存在膽管癌[25]。膽管造影對于區分膽管癌和膽管顯性狹窄作用有限,ERCP下膽管刷檢細胞學、原位熒光雜交、膽管活檢組織檢查、激光共聚焦探頭、膽管鏡活檢等對于診斷膽管癌具有重要作用[131]。對于膽管顯性狹窄的PSC患者進行ERCP治療時,對膽管可疑部位取材進行組織學檢查有助于診斷或排除膽管癌。
推薦意見16:PSC患者發生膽管顯性狹窄,可以行內鏡下球囊擴張或者短期支架置入進行膽管引流治療,應首選ERCP下膽管球囊擴張。(B1)
推薦意見17:PSC患者行ERCP治療時,需對膽管可疑惡性病變取材進行組織學檢查以排除膽管癌。(A1)
4.4 肝移植 肝移植是PSC唯一有效的治療方法。肝移植廣泛開展之前,多數PSC患者因肝衰竭死亡,肝移植改變了PSC的臨床結局,目前PSC患者首位的死亡原因是膽管癌[31,48]。一般情況下,PSC患者肝移植后的長期預后良好,歐美國家PSC患者肝移植后的5年生存率可達到85%[132]。我國PSC患者肝移植術后的研究較少。一項15例PSC患者的回顧性研究顯示,肝移植治療PSC總體預后良好,但同時也伴隨著疾病復發、膽管并發癥、排異反應等影響預后的危險因素[133]。另外一項147例自身免疫性肝病(PSC患者14例)的研究也顯示自身免疫性肝病患者肝移植術可獲得良好的長期臨床結局[134]。部分PSC患者肝移植后可出現PSC復發。薈萃分析顯示10%~40%的PSC患者肝移植后復發,總體復發率為17.7%,復發的高危因素為合并IBD、膽管癌、高終末期肝病模型(MELD)評分等[135]。
PSC患者肝移植的適應證與其他慢性肝病類似,包括嚴重生活質量受損、門靜脈高壓并發癥和肝功能衰竭等。不同指南推薦的PSC患者肝移植的指征不同。2015年美國胃腸病學會推薦的PSC患者肝移植指征為:藥物或外科引流難以控制的膽管炎、失代償期肝硬化、MELD評分>14分[64]。2017年日本胃腸病學會推薦的PSC肝移植指征為:失代償期肝硬化患者Child-Turcotte-Pugh(CTP)評分C級、反復發作膽管炎(每月至少復發1次)、難治性腹水和無法控制的瘙癢[4]。2019年英國胃腸病學會推薦的PSC患者肝移植指征為:肝硬化和/或門靜脈高壓并發癥、英國終末期肝病模型評分>49分、終末期肝病模型評分>15分、頑固性瘙癢癥、復發性膽管炎[2]。我國衛生部2010年發布《中國人體器官分配與共享基本原則和肝臟與腎臟移植核心政策》規定應根據等待肝移植患者醫療緊急度和等待時間排序,除暴發性肝衰竭、原發性移植肝無功能、移植肝肝動脈血栓形成、急性失代償肝豆狀核變性等外,應該按MELD或/PELD評分進行排序[136]。美國一項大樣本調查顯示肝移植的PSC患者在等待期間的死亡率低于其他原因所致的終末期肝病,原因可能是患者門靜脈高壓并發癥較低,等待期間死亡的主要原因是膽管癌[137]。另一項回顧性分析顯示復發性膽管炎與等待肝移植的PSC患者的死亡風險無關[138]。本指南推薦對于MELD評分≥15或CTP評分C級的肝硬化失代償PSC患者進行肝移植評估。
推薦意見18:MELD評分≥15分或CTP評分C級的肝硬化失代償期的PSC患者應行肝移植評估。(A1)
推薦意見19:PSC患者肝移植術后仍應密切監測其疾病復發。(A1)
5 特殊情況
5.1 小膽管PSC 5%~13%的PSC患者表現為孤立的小膽管病變,稱之為小膽管PSC[31,139]。患者的膽管成像無特異性改變,但臨床癥狀及生化指標提示膽汁淤積表現。對于疑診小膽管PSC的患者,肝組織學檢查是必要的,可觀察到典型的膽管周圍洋蔥皮樣向心性纖維組織增生樣組織學改變。小膽管PSC在確診時間早的患者中更為常見[140]。同時,多項研究顯示部分小膽管PSC最終可發展為大膽管PSC[141-142],但其是否為大膽管PSC的早期階段或變異,目前尚無定論。只有極少數的小膽管PSC最終會出現膽管癌[139,141],其總生存期或無肝移植生存期均顯著長于大膽管PSC[31,139,141-142],這提示小膽管PSC可能是一類長期預后較好的PSC。
5.2 PSC-AIH重疊 1.4%~17%的PSC患者合并AIH,且多見于兒童及年輕人,稱為PSC-AIH重疊綜合征[100,143- 144]。PSC-AIH患者的膽管影像學通常表現為較為典型的PSC,但在臨床表現、生化指標及組織學上的表現提示AIH,包括顯著升高的轉氨酶和IgG以及提示自身抗體(ANA、SMA、肝腎微粒體抗體等)陽性。由于合并AIH,PSC-AIH患者對免疫抑制治療通常是敏感的,且其預后優于經典的PSC[100,144-147]。大膽管PSC-AIH似乎比小膽管PSC-AIH對免疫抑制治療更為敏感[147]。由于AIH需要肝組織學確定診斷,因此對于具有AIH特征的PSC患者,通常需行肝組織學檢查。一旦確診,即可啟動免疫抑制劑治療。
5.3 兒童PSC 由于兒童骨骼生長發育常出現血清ALP的升高,故可通過檢測GGT判斷是否存在膽汁淤積。絕大部分的兒童PSC合并IBD,尤以UC為主,在兒童PSC中重疊AIH也較為常見[148-153]。兒童PSC發生肝膽惡性腫瘤者非常罕見,故不常規進行膽管癌或膽囊癌監測。小膽管PSC或PSC-IBD的患者比大膽管PSC預后更佳[148]。確診時升高的膽紅素、GGT、天冬氨酸轉氨酶(AST)和血小板(PLT)比率指數(APRI)可提示疾病進展高風險[148,154]。兒童PSC的治療原則與成人PSC一致,目前尚無有效的藥物[155],合并AIH者可考慮糖皮質激素或免疫抑制劑治療。確診1年內GGT復常或較基線下降75%可提示更長的5年無疾病生存期[156-157]。
推薦意見20:對于疑似PSC的兒童患者,GGT可替代ALP作為膽汁淤積的生化指標;兒童PSC無需常規進行肝膽惡性腫瘤的監測。(B1)
6 預后
6.1 PSC的自然病史 PSC的自然病史多變,性別、發病年齡、是否合并IBD,膽管累及部位等都可能影響患者疾病進程[158]。與成人PSC相比,兒童PSC患者進展更慢,10年生存率也高于成人[148,159]。10%~60%的PSC患者初診時并無明顯的臨床癥狀,這些患者臨床預后相對較好,但也可能是由于疾病診斷階段早晚導致的差異。PSC患者的臨床進程異質性很高,一些患者很快進展至肝硬化等終末期肝病,而有些患者的疾病狀態則長期保持穩定。PSC患者可最終發展為肝硬化,出現門靜脈高壓、腹水、食管胃底靜脈曲張和肝衰竭。PSC患者從診斷到死亡或肝移植的平均時間為10~22年。荷蘭一項包括422例患者的回顧性分析顯示PSC患者從診斷到死亡或肝移植的平均時間為21.3年[48]。最近一項大樣本PSC患者的多中心觀察研究顯示PSC患者5年、10年、20年肝移植或死亡率分別為37.0%、52.3%和63.6%,平均無肝移植生存期為14.5年[31]。PSC患者的主要死亡原因為膽管癌、肝衰竭、靜脈曲張出血、肝移植并發癥和結腸癌。
6.2 預后風險評估 PSC患者病情進展速度差異很大,準確預測患者的臨床進程對于臨床實踐具有重要意義。以往研究根據患者年齡、血液生化學指標、肝臟組織學指標、膽管影像學特征、病史及并發癥等建立了一些PSC預后評估模型[7]。肝臟組織學在PSC中應用有限,且存在取樣誤差,因此包含肝臟組織學指標的預后模型(如:最初的MRS評分系統)逐漸被棄用。同樣,基于膽管ERCP影像學特征的預后評估方法也在PSC風險評估中應用受限。修訂的MRS評分去除了肝臟病理學指標,是目前應用最廣泛的非侵入性評估方法,可以在疾病早期階段預測PSC的臨床結局,但是在初次應用4~5年后預測準確度顯著降低。隨著PSC進展,患者的臨床生化指標會不斷變化,時間依賴的預后評估模型能更好地進行預后評估。近年來,多中心研究建立了一些新的時間依賴的非侵入性PSC預后模型,如UK-PSC風險評分模型、Amsterdam-Oxford Model(AOM模型)、PREsTo模型等[160-163]。其中UK-PSC風險評分可以用來預測PSC患者短期及長期肝移植和全因死亡率,其預測效能優于MRS和APRI評分。AOM模型可預測PSC相關死亡和肝移植結局,已被多中心大樣本研究驗證,該模型預測效能隨著時間延長而提高,但是在疾病早期其預測效能一般。PREsTo模型是基于機器學習建立的PSC風險模型。此模型調整了血清ALP的權重,可以準確預測肝硬化失代償風險,且優于MELD評分和MRS評分。
需要指出的是,PSC的臨床分期緩慢進展。各種臨床指標和評分模型在不同階段有不同的預測價值,應對患者進行長期的隨訪,在疾病不同臨床階段選擇不同的預后評估模型,以更好地對患者預后及風險進行預測。
推薦意見21:可采用UK-PSC、AOM、PREsTo等非侵入性評分模型對PSC患者的長期預后進行動態評估。(B1)
7 總結和展望
目前,PSC研究多為小樣本的非隨機對照研究,本指南的推薦意見僅基于目前的臨床研究證據,推薦證據等級仍有待提高。我國PSC的流行病學、疾病特征、長期預后仍缺乏足夠的資料。為提高我國PSC的診治水平,應盡早建立我國全國性的自身免疫性疾病數據庫并開展多中心隨機對照研究。PSC診治中需要進一步研究的問題包括:如何提高PSC的診斷準確度和特異度;PSC患者膽管顯性狹窄的最佳治療時機和方法;如何準確判斷PSC患者的臨床預后;尋找或研發PSC的治療藥物等。隨著我國自身免疫性肝病數據庫的建立和新研究的開展,這些重要臨床問題將會有更多的證據出現。期待國際、國內的研究為PSC的診治帶來新的和突破性進展,最終改善患者的臨床結局。
附件1 IgG4相關硬化性膽管炎的診斷治療指南
1 概述
在20世紀70年代,有學者報道合并慢性胰腺炎的硬化性膽管炎。隨后病例報道顯示合并胰腺炎的硬化性膽管炎雖然符合PSC的診斷標準,但是預后明顯好于PSC,此類硬化性膽管炎被命名為非典型PSC。非典型PSC的特點是老年高發,糖皮質激素或膽管引流反應良好,不合并IBD,常伴有慢性胰腺炎。此后又有孤立性硬化性膽管炎對糖皮質激素治療反應良好的病例被報道。隨著對IgG4相關疾病和自身免疫胰腺炎的認識,此類疾病被稱為IgG4相關硬化性膽管炎(IgG4-SC)。IgG4-SC是系統性IgG4相關疾病(IgG4-RD)的膽管表現,是一種自身免疫性硬化性膽管炎,對糖皮質激素治療反應良好,與PSC相比臨床預后相對良好。
2 流行病學和分型
2.1 流行病學 日本的流行病學資料顯示,IgG4-SC發病率為2.18/10萬;男女比例約為4∶1,發病高峰年齡為60~80歲[164]。IgG4-SC常伴有其他器官累及,約80%以上患者同時患有自身免疫性胰腺炎(AIP),僅約10%的IgG4-SC患者診斷時無AIP 表現[164-165]。Mayo診所的研究顯示,89例IgG4-SC患者中,81%為男性,中位診斷年齡為67歲[166]。我國缺乏IgG4-SC的流行病學資料。中國上海一項57例患者的回顧性研究顯示,IgG4-SC的發病年齡為(49.38±16.71)歲,男女比例為1.4∶1, 其中單純IgG4-SC患者比例為59.6%,合并AIP者為28.1%[167]。該團隊的另外一項回顧性分析顯示19例孤立性IgG4-SC患者的發病年齡為(46.06±19.03)歲,而合并AIP的IgG4-SC患者的平均發病年齡為(62.60±15.11)歲[168]。中國北京的一項回顧性研究顯示,39例IgG4-SC患者中80%為男性,且90%以上患者合并AIP[169]。以上研究的結果差異可能是由于取樣差別所致,我國IgG4-SC患者臨床特點仍需要大規模流行病學調查進一步確定。
2.2 IgG4-SC的分型 根據是否合并AIP,IgG4-SC可以分為孤立性IgG4-SC或合并AIP的IgG4-SC。孤立性IgG4-SC與膽管癌鑒別困難。
按照膽管影像學表現,IgG4-SC可以分為4型[170]。1型主要表現為膽總管下段狹窄,因此需要與膽管癌和胰腺癌鑒別;2型表現為肝內外膽管彌漫性狹窄,需要與PSC鑒別;3型主要為肝門部病變和膽管下段狹窄;4型僅表現為肝門部膽管狹窄。3型和4型也需要與膽管癌鑒別。一項針對12例病例報道的系統性分析顯示部分IgG4-SC患者可以表現為局限性的肝內膽管受累[171]。
3 臨床表現和疾病進程
IgG4-SC多見于60歲以上的老年男性,約20%的患者合并支氣管哮喘、鼻竇炎、藥物過敏等過敏性疾病。IgG4-SC臨床表現多樣,約75%的患者表現為慢性或反復發作的梗阻性黃疸,其他非特異性癥狀包括皮膚瘙癢、腹痛、體質量下降以及繼發膽管炎癥所致的發熱、寒戰等。約1/4患者可能無癥狀,因偶然發現肝功能或影像學異常,或因其他組織、器官IgG4-RD行系統性篩查時確診[164]。我國報道的IgG4-SC患者的癥狀主要為黃疸和腹痛。
IgG4-SC的自然病程尚不清楚。美國、英國、日本報道的IgG4-SC的臨床結局存在差異[165,172, 173]。美國和英國報道的進展為肝硬化患者的比例顯著高于日本(7.5%、5.2% vs 0.8%)。我國報道的IgG4-SC患者發生肝硬化的比例則高達35.1%,其臨床預后與PSC-AIH重疊綜合征患者相似[167]。英國研究顯示IgG4-SC患者的全因死亡風險增加,但是癌癥相關死亡風險未發生變化。Mayo診所的隨訪研究顯示IgG4-SC患者肝膽系統不良事件發生率低于PSC患者,總體生存狀況優于PSC[166]。最近日本包括121例患者的回顧性研究顯示IgG4-SC發生胰腺、膽管系統癌癥風險顯著升高[174]。以往研究報道的隨訪時間均相對較短,仍需要大規模的長期隨訪研究才能確定IgG4-SC的臨床預后。
4 診斷和鑒別診斷
4.1 實驗室檢查 PSC的血清生化異常主要表現為膽汁淤積型改變,多數患者血清膽紅素、ALP、GGT升高,但無明確界定標準,部分患者可以出現轉氨酶輕度升高[175]。
血清IgG4水平升高是IgG4-SC的重要特征,但約10%的IgG4-SC患者血清IgG4水平可無明顯升高[176]。需要特別注意的是部分與IgG4-SC影像表現相似的疾病,包括8%~14%的膽管癌、9%~22%的PSC血清IgG4水平也可見升高[40,176-184]。另外,5%的健康人可以出現血清IgG4水平升高[177,179,185]。因此,不能單獨依據血清IgG4升高診斷IgG4-SC。
其他血清學異常還包括:IgG 升高(60%)、高γ-球蛋白血癥(50%)、抗核抗體陽性(40%)、嗜酸性粒細胞和/或 IgE升高(30%)及類風濕因子升高(20%)等[186-188]。
4.2 影像學檢查
4.2.1 腹部超聲 腹部超聲多用于疑診IgG4-SC患者的初篩。可以顯示肝內/外膽管管壁增厚以及肝內膽管擴張。日本學者Koyama等[189]根據膽管壁增厚的超聲表現,將IgG4-SC分為兩種類型:三層型,明顯增厚的膽管壁呈高-低-高回聲超聲三層;實質回聲型,增厚的管壁占據整個膽管腔,在膽管內出現實質性回聲。腹部超聲還可以同時檢查胰腺,以明確是否合并AIP。但由于腹部超聲敏感性和特異性均較差,無法準確鑒別IgG4-SC與膽管癌和PSC。
4.2.2 超聲內鏡(EUS) 以往研究中,超聲內鏡主要用于IgG4-SC與膽管占位性疾病的鑒別。Du等[190]報道了18例IgG4-SC患者和10例膽管癌的EUS特征,結果發現與膽管癌相比,IgG4-SC患者膽管EUS特征主要以膽管壁增厚為主(94.4% vs 30%),膽管占位少見(5.6% vs 80%)。另外一項66例IgG4-SC患者和44例膽管癌患者的研究顯示IgG4-SC的EUS特點包括:膽管壁環形對稱性增厚(>1 mm);膽管壁內部回聲低于胰頭;膽管壁層次可見;膽囊壁增厚。以此為基礎建立的膽管炎癥評分鑒別IgG4-SC和膽管癌的敏感度、特異度和準確度分別為86%、95%和90%[191]。但EUS對IgG4-SC的診斷價值還需進一步研究。
4.2.3 CT和MRI CT和MRI可以顯示膽管壁增厚及膽管擴張,MRCP還可以顯示和重建膽胰管系統,發現膽管狹窄的部位和程度。IgG4-SC相關的影像學特征包括:(1)沿膽管長軸延伸的向心性膽管壁增厚;(2)平滑的內/外邊緣;(3)膽管狹窄處管腔存在,近端膽管輕度擴張;(4)肝內外膽管的連續性膽管壁增厚[36,192-195]。
4.2.4 ERCP 雖然MRCP可以提供膽管狹窄和擴張的信息,但ERCP仍然是診斷IgG4-SC最為有效的手段,同時還可以進行組織活檢確定診斷。
4.2.5 IDUS IDUS是一種將微超聲探頭置入膽管或胰管內,獲得高分辨率圖像,從而進行膽胰疾病診斷的方法。IgG4-SC 的 IDUS 表現為環形、對稱性的管壁增厚、內外邊緣光滑以及膽管狹窄處的均勻內部回聲[196-197]。最典型的表現是膽管非狹窄處的管壁增厚[196-197],有助于與膽管癌和PSC相鑒別。膽管癌表現為不對稱的管壁增厚、外緣有缺口、內緣粗糙和狹窄處膽管壁內部低回聲,在非狹窄部位觀察不到膽管壁增厚[196,198-203]。PSC的典型表現為不對稱的管壁增厚、內緣不規則、外緣不清、憩室樣外翻、內部回聲不均勻、管壁的三層結構消失[204-205]。非狹窄區域膽管壁厚超過 0.8 mm 高度提示 IgG4-SC(敏感度95.0%,特異度90.9%,準確度93.5%)[196]。IgG4-SC的管壁增厚與膽管壁間質中大量淋巴細胞和漿細胞浸潤和纖維化的增生有關,膽管上皮層完整無損。大多數 IgG4-SC的管壁增厚表現為從下向上的連續性增厚。IDUS 觀察到的非狹窄區域壁增厚明顯高于 EUS(80.9% vs 73.8%,P=0.045)[206]。
4.2.6 經口膽管鏡(POCS) 應用POCS可以對膽管黏膜表面的詳細結構進行觀察。當與窄帶成像相結合時,使用 POCS 觀察血管可以輔助診斷[207]。有研究比較了PSC、膽管炎和IgG4-SC的膽管鏡下表現,結果發現少數 IgG4-SC膽管可表現出特征性的膽管壁血管擴張和迂曲,大部分IgG4-SC患者膽管沒有纖維瘢痕組織形成[208],IgG4-SC膽管炎癥主要發生在黏膜下,炎癥相對較少的黏膜血管會出現肉眼可見的充血。而在 PSC 中,血管分布很差,并且經常看到具有假憩室樣變化的疤痕。在膽管癌中,經常觀察到不規則的黏膜變化和大的新生血管(特別是擴張的血管)[209]。僅基于 POCS 圖像難以準確鑒別膽管癌、PSC和IgG4-SC,但POCS下膽管活檢有助于排除膽管惡性病變。
4.3 病理診斷
4.3.1 膽管組織學 通過膽管活檢明確診斷 IgG4-SC 需要包含膽管黏膜下層或更深組織結構在內的樣本。由于內窺鏡下使用活檢鉗難以獲取含有膽管黏膜下層或更深膽管結構的樣本,因此,既往報道成功率差別極大(0~88%)[172,196,210-211]。IgG4-SC膽管的上皮組織通常是正常的,膽管的病理表現為從膽管黏膜延伸至漿膜的彌漫性淋巴漿細胞浸潤、IgG4陽性漿細胞>10個/高倍視野(HPF),同時IgG4/IgG陽性漿細胞比例>40%。席紋狀纖維化、閉塞性靜脈炎和嗜酸性粒細胞浸潤。同時,膽管活檢應注意排除膽管癌。
4.3.2 Vater壺腹部活檢 Vater壺腹與胰腺和膽管解剖上臨近。AIP診斷國際共識推薦對Vater壺腹部行內鏡下活檢及IgG4免疫染色用于輔助AIP診斷。Vater壺腹腫脹和 IgG4 陽性漿細胞大量浸潤等特征與AIP累及胰頭相關[212-214]。Kawa等[215]證實Vater壺腹的內鏡和免疫組化特征同樣可以用于輔助IgG4-SC的診斷。
4.3.3 肝臟組織學 肝臟組織學可以為診斷 IgG4-RD 提供有用的信息。日本IgG4-SC的臨床診斷標準[216]和IgG4-RD中國專家共識中,肝組織中IgG4陽性漿細胞>10個/HPF,同時IgG4/IgG陽性漿細胞比例>40%。19例IgG4-SC和 22 例 PSC 患者的肝組織學回顧性研究結果顯示,約 25% 的 IgG4-SC 患者存在小膽管的受累,并且在肝內膽管狹窄的 IgG4-SC 患者中,每個 HPF 的 IgG4陽性漿細胞數量顯著高于 PSC(13.4 vs 0.4 個/HPF,P<0.001)[30,203]。然而,大多數情況下,IgG4-SC患者肝臟組織學缺乏特征性,可表現為匯管區的淋巴細胞、漿細胞和偶見的嗜酸性粒細胞浸潤,有時伴有門靜脈周圍、小葉內和中央靜脈周圍炎癥細胞浸潤[30,203,217]。IgG4-SC患者肝臟匯管區也可出現基于門靜脈的纖維炎性結節,類似于 IgG4 相關炎性假瘤的表現,對診斷具有一定的特征性[217],但很少能觀察到。雖然在膽管癌中也可以觀察到一些 IgG4 陽性漿細胞,但在IgG4-SC 肝組織中 IgG4 陽性漿細胞的數量明顯更多。在肝組織樣本中,僅在 PSC 中可觀察到第 3~4 期的晚期纖維化,而在 IgG4-SC 中幾乎見不到,這也有助于二者鑒別[218-219]。
4.4 其他器官表現
IgG4-SC作為IgG4-RD累及膽管的表現類型,可以合并任何類型的IgG4-RD,最為常見的是Ⅰ型AIP,其他相對常見的合并疾病包括IgG4相關性淚腺炎/唾液腺炎(Mikulicz病)、IgG4相關的腹膜后纖維化、IgG4相關的腎臟病變(IgG4-RKD)。
4.4.1 Ⅰ型AIP Ⅰ型AIP是IgG4-SC最為常見的合并癥,87%~92%的IgG4-SC合并Ⅰ型AIP。反之,膽管也是Ⅰ型AIP最為常見的胰腺外累及臟器[165,170,172,210,220-221]。AIP表現為胰腺彌漫或局部腫大,可累及胰頭及整個胰腺,壓迫膽管導致梗阻性黃疸。局灶性病變需要與胰腺癌鑒別診斷。
4.4.2 IgG4相關性淚腺炎/唾液腺炎(Mikulicz病) 通常沒有癥狀,或僅有輕度眼干、口干。與干燥綜合征通常累及腮腺不同,IgG4相關性唾液腺炎多累及頜下腺。抗SS-A抗體和抗SS-B抗體通常陰性[222]。
4.4.3 IgG4相關的腹膜后纖維化 由于腹膜后及其周圍纖維結締組織的彌漫性增生和炎癥,腹部 CT/MRI圖像顯示腹膜后腹主動脈周圍軟組織腫塊。通常會導致輸尿管梗阻及腎積水[223]。
4.4.4 IgG4-RKD IgG4-RKD 組織學上通常表現為腎小管間質性腎炎,伴有輕度尿檢異常和低補體血癥,腎小球受累時可以出現蛋白尿。大多數 IgG4-RKD 通常不影響或僅輕度影響腎功能,但有可能發展為嚴重腎功能不全的晚期階段。增強 CT 的特征性影像表現包括腎實質病變,表現為多處增強減弱區域(小的外周皮質結節、圓形或楔形病變)、孤立性腫塊(血管不足)或腎盂壁增厚而無不規則管腔。平掃CT 也可能顯示彌漫性腎腫大[224]。
4.5 診斷標準 目前尚無公認的IgG4-SC的嚴格診斷標準。2008年美國學者提出了基于組織學、影像學、血清學、其他器官受累及對治療反應的HISORt診斷標準[172]。2012年日本提出了IgG4-SC臨床診斷標準,該標準納入了特征性的膽管影像學表現、血清IgG4水平、其他IgG4-RD以及特征性病理表現[225]。2020年日本學者對上述標準進一步修訂、細化(表3)[226]。
4.6 鑒別診斷
4.6.1 膽管癌 1、3、4型IgG4-SC需要與膽管癌鑒別,由于IgG4-SC和膽管癌鑒別困難,需要綜合影像、血清IgG4水平、并發疾病及組織學等結果綜合判斷。ERCP聯合CT或MRI診斷IgG4-SC的靈敏度和特異度分別為70%~90%和73%~87%[227-228]。增強CT 有明顯的優勢,動脈期膽管壁均勻強化、膽管內外壁光滑是IgG4-SC的重要特點。導管內超聲(IDUS)也是鑒別IgG4-SC和膽管癌的重要手段,非狹窄階段膽管壁增厚是IgG4-SC的重要特征,研究顯示非狹窄階段膽管壁厚度>0.8 mm診斷IgG4-SC的靈敏度、特異性和準確度分別為95%~100%、91%和94%[196,229]。POCS在膽管內發現扭曲擴張的動脈也往往提示IgG4-SC[208]。血清IgG4在IgG4-SC和膽管癌鑒別中的價值受截斷值的影響,以140 mg/dL為截斷值,診斷IgG4-SC的靈敏度和特異性分別為64%~100%和81%~88%[228,230],以560 mg/dL為截斷值診斷IgG4-SC的靈敏度和特異性分別為17%和99%[177]。同時合并累及其他臟器的IgG4-RD,特別是Ⅰ型AIP,多提示IgG4-SC。膽管活檢診斷IgG4-SC和膽管癌的靈敏度均較低,分別為18%~52%和55%~72%[196,211]。同時行膽管刷檢細胞學檢測可以提高診斷的價值。

表3 IgG4-SC診斷標準(2020版)
4.6.2 PSC PSC在發病年齡、血清IgG4水平、并發疾病、影像學特征、肝臟組織學改變、對糖皮質激素治療反應和臨床病程等方面與IgG4-SC存在明顯不同。IgG4-SC與PSC鑒別的要點見表4。
推薦意見1:對于黃疸、膽汁淤積、肝內外膽管擴張的患者,在排除結石和腫瘤后,應進行血清IgG4的檢測。(C1)

表4 IgG4-SC與PSC鑒別要點
推薦意見2:對疑診IgG4-SC者,應行CT、MRCP等影像學檢查,必要時可行EUS、ERCP、IDUS、POCS等。(C1)
推薦意見3:對擬診IgG4-SC者,應檢查患者是否合并膽管外其他器官IgG4-RD。(C1)
推薦意見4:對疑診IgG4-SC者,可行膽管、十二指腸乳頭(或Vater壺腹)和/或肝臟活檢;膽管活檢時需注意排除膽管癌。(C1)
5 治療
5.1 診斷性治療 目前尚無糖皮質激素診斷性治療 IgG4-SC的隨機對照研究。日本IgG4-SC診治指南推薦診斷性糖皮質激素試驗應在排除潛在惡性腫瘤后,由膽胰專科醫師進行[231]。合并AIP或其他IgG4-RD可以幫助 IgG4-SC 診斷,無需膽管的組織學證據[209]。對于不合并AIP和/或沒有其他器官受累的難以確診的 IgG4-SC 患者,可以進行診斷性糖皮質激素試驗。診斷性糖皮質激素試驗也適用于血清 IgG4 水平升高且膽管造影結果提示 IgG4-SC 的患者[170]。應用潑尼松診斷性治療的劑量一般為0.4~0.6 mg·kg-1·d-1,治療 1 或 2 周后通過ERCP/MRCP影像學來評估療效。Mayo診所[172]和 Iwasaki 等[232]應用糖皮質激素對IgG4-SC進行了診斷性治療驗證,建議在1周左右進行血清學評估,包括轉氨酶、膽紅素、ALP等指標,1~2周時評估CT和MRCP或ERCP影像結果。如沒有改善,應建議重新評估患者的診斷。
推薦意見5:難以確診但高度懷疑 IgG4-SC的患者,可行診斷性糖皮質激素治療,并在1周后進行血清學評估,1~2 周后進行MRCP等膽管影像學檢查評估。(C1)
推薦意見6:對擬診IgG4-SC者,應根據膽管影像學改變、血清IgG4水平、其他器官IgG4-RD、組織學檢查以及對糖皮質激素診斷性治療的反應進行綜合判斷。(B1)
5.2 誘導緩解治療 糖皮質激素是治療 IgG4-RD 的基石,亦是公認的一線藥物。日本 AIP 臨床指南[233]推薦的標準治療方案是口服潑尼松(0.6 mg·kg-1·d-1)作為初始治療,2~4周病情有效控制后可逐漸減量,每 1~2周減 5 mg,至維持劑量。Mayo Clinic的方案為:潑尼松40 mg/d,口服4 周,然后每周減5 mg,直到第 11 周停藥[172,234]。日本一項多中心研究結果顯示,達到緩解所需的時間與潑尼松龍的初始劑量(30 mg/d vs 40 mg/d)無關[235]。由于糖皮質激素有使糖尿病惡化的風險,有研究報道使用低劑量糖皮質激素(≤20 mg/d)也對IgG4-SC 合并糖尿病的患者有效[165,236]。也有報道如需要在短時間內獲得療效,靜脈糖皮質激素沖擊療法比口服糖皮質激素能更有效地早期改善膽管病變[237-238]。IgG4相關性疾病診治中國專家共識推薦的糖皮質激素常用起始劑量為中等劑量,相當于潑尼松30~40 mg/d,但需要根據患者病情、體重合并癥等適當調整劑量。
推薦意見7:IgG4-SC患者應口服糖皮質激素(相當于潑尼松30~40 mg/d)2~4周,用于誘導緩解治療。(B1)
5.3 維持治療 隨機對照試驗顯示,AIP患者誘導緩解后使用5.0~7.5 mg糖皮質激素維持治療3 年的復發率顯著低于維持治療26周(23.3% vs 57.9%),且未發生嚴重的糖皮質激素相關不良事件[239]。另一項510 例 AIP 患者的多中心回顧性研究顯示2.5~10.0 mg的糖皮質激素劑量維持治療組的總體復發率顯著低于停藥組(30.3% vs 45.2%),最低復發風險用量為 5 mg/d(26.1%),且5.0 mg、7.5 mg和 10.0 mg之間無顯著差異[240]。一項前瞻性研究納入了21例在維持治療3 年后停藥的 AIP患者,約48%的患者在43個月的隨訪期間疾病復發[241]。一項30例IgG4-SC患者的回顧性研究表明,初始口服潑尼松40 mg/d,共4周,隨后每周減量5 mg,直到第11周停藥,3個月的復發率為 53%,6 個月內的復發率可達71%[172]。英國一項IgG4-SC 前瞻性研究中,患者初始使用30 mg潑尼松治療2周,后每2周減量 5 mg,3~4個月后停藥,57%的IgG4-SC患者停藥后出現疾病復發[242]。最近,澳大利亞一項69例IgG4-SC患者的全國多中心回顧性研究顯示,47%的患者在停用糖皮質激素后疾病復發。基于以上結果,建議IgG4-SC患者應長期維持治療,且維持治療至少要超過 3 年。目前關于IgG4-SC患者是否可以停藥尚無充分的研究數據,但是長期維持治療可能存在糖皮質激素相關并發癥的風險。日本一項AIP患者糖皮質激素維持治療研究顯示,長期服用糖皮質激素10 mg患者感染風險增加,并且當糖皮質激素總劑量達到或超過 6405 mg時,糖皮質激素相關骨質疏松癥的風險顯著增加[240]。
推薦意見8:IgG4-SC患者糖皮質激素誘導緩解后應逐漸減量,但需要維持治療,糖皮質激素維持劑量應相當于潑尼松龍5~10 mg/d。(B1)
推薦意見9:IgG4-SC患者糖皮質激素維持治療3年后,若病情穩定,可考慮減停;長期小劑量維持治療可減少復發風險。(C1)
5.4 復發的治療 IgG4-SC 復發是指癥狀消失后再次出現,伴隨膽管狹窄的進展或加重,和/或影像學提示其他器官受累,和/或血清 IgG4 水平升高。單純血清 IgG4 水平再次升高而無癥狀或仍存在膽管狹窄但無進展或加重不應定義為疾病復發[243-244]。特別是在最初幾年,30%~57% 的 IgG4-SC 患者在糖皮質激素維持治療期間或停用糖皮質激素后復發[173,245]。一項對507例IgG4-SC患者的回顧性隊列研究顯示,104 例患者(19%)出現膽管狹窄再狹窄,1年、3 年和 5 年的累積復發率分別為 1.6%、7.6%和16.5%[165]。預測復發的已知危險因素包括診斷時的高血清 IgG4 水平、肝外/肝內近端或多處膽管狹窄的存在,以及初次發作時膽管壁較厚[172,243,245-246]。研究顯示,對于激素減量或維持治療過程中復發的患者,重新使用甲潑尼龍30~40 mg/d治療仍然有效[172,233,242]。
除單一使用糖皮質激素外,也可聯合免疫調節藥物如硫唑嘌呤、6-巰基嘌呤、嗎替麥考酚酯和甲氨蝶呤用于IgG4-SC 患者復發的治療。然而,增加免疫調節劑在減少進一步的復發方面,益處尚不確定。由于這些藥物具有嚴重的副作用,因此應謹慎考慮使用[38]。利妥昔單抗是一種導致B淋巴細胞耗竭的單克隆抗 CD20 抗體,其治療PSC的臨床研究較少,有限的數據顯示,80%~90%的IgG4-SC患者妥昔單抗治療有效,包括難治性疾病[247-249]。
推薦意見10:IgG4-SC患者在減停糖皮質激素治療后,仍應密切監測是否復發。如疾病復發可用初始劑量糖皮質激素再次誘導緩解(C1)。
雖然多數IgG4-SC患者對糖皮質激素治療反應良好,臨床預后優于PSC。但是,IgG4-SC患者的臨床病程有待進一步確定,預后仍需要較長時間的觀察。IgG4-SC患者的最佳藥物治療方案也需要更多深入研究確定。
執筆人:郭長存、時永全、尚玉龍、董加強、崔麗娜、郭冠亞、鄭林華、尤紅、陸倫根、馬雄、韓英、南月敏、徐小元、段鐘平、魏來、賈繼東、莊輝
指南制定專家(以姓氏拼音排序):蔡曉波(上海交通大學附屬第一人民醫院消化內科)、陳莎(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友誼醫院肝病中心)、陳煜(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佑安醫院肝病中心)、陳紅松(北京大學人民醫院肝病研究所)、崔麗娜(空軍軍醫大學第一附屬醫院消化內科)、董加強(空軍軍醫大學第一附屬醫院消化內科)、竇曉光(中國醫科大學附屬盛京醫院感染科)、段維佳(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友誼醫院肝病中心)、段鐘平(首都醫科大學附屬佑安醫院肝病中心)、郭長存(空軍軍醫大學第一附屬醫院消化內科)、郭冠亞(空軍軍醫大學第一附屬醫院消化內科)、韓濤(天津市第三中心醫院肝內科)、韓英(空軍軍醫大學第一附屬醫院消化內科)、侯金林(南方醫科大學南方醫院感染內科)、胡鵬(重慶醫科大學附屬第二醫院感染科)、宦怡(空軍軍醫大學第一附屬醫院放射影像科)、賈繼東(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友誼醫院肝病中心)、孔媛媛(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友誼醫院國家消化系統疾病臨床醫學研究中心方法學平臺)、李杰(北京大學醫學部基礎醫學院病原生物學系)、李軍(江蘇省人民醫院感染病科)、李淑香(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友誼醫院肝病中心)、李增山(空軍軍醫大學第一附屬醫院病理科)、令狐恩強(解放軍總醫院第一醫學中心消化內科)、劉家云(空軍軍醫大學第一附屬醫院檢驗科)、劉景豐(福建醫科大學孟超肝膽醫院肝膽外科)、劉燕敏(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佑安醫院肝病科)、劉迎娣(解放軍總醫院第一醫學中心消化內科)、陸倫根(上海交通大學附屬第一人民醫院消化內科)、羅新華(貴州省人民醫院感染科)、呂婷婷(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友誼醫院肝病中心)、馬雄(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仁濟醫院消化內科)、苗琪(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仁濟醫院消化內科)、南月敏(河北醫科大學第三醫院中西醫結合肝病科)、曲穎(上海交通大學附屬第一人民醫院消化內科)、任紅(重慶醫科大學第二醫院傳染科)、任萬華(山東省立醫院感染性疾病科)、尚佳(河南省人民醫院感染性疾病科)、尚玉龍(空軍軍醫大學第一附屬醫院消化內科)、時永全(空軍軍醫大學第一附屬醫院消化內科)、唐承薇(四川大學華西醫院消化內科)、王建設(復旦大學附屬兒科醫院感染科)、王婧雯(空軍軍醫大學第一附屬醫院藥劑科)、王綺夏(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仁濟醫院消化內科)、魏來(北京大學人民醫院肝病科)、吳浩(四川大學華西醫院消化內科)、徐小元(北京大學第一醫院感染疾病科)、閻明(山東大學齊魯醫院消化內科)、楊東亮(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附屬協和醫院感染科)、楊永峰(南京市第二醫院肝病科)、楊詔旭(空軍軍醫大學第一附屬醫院肝膽外科)、尤紅(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友誼醫院肝病中心)、張欣欣(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瑞金醫院感染科)、張躍新(新疆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感染科)、趙景民(解放軍總醫院第五醫學中心病理科)、趙守松(蚌埠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感染病科)、趙新顏(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友誼醫院肝病中心)、鄭林華(空軍軍醫大學第一附屬醫院消化內科)、周新民(空軍軍醫大學第一附屬醫院消化內科)、莊輝(北京大學醫學部基礎醫學院病原生物學系)
志謝(以姓氏拼音排序):安紀紅(內蒙古自治區人民醫院感染科)、鄧國宏(陸軍軍醫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傳染科)、黃燕(中南大學湘雅醫院傳染科)、黃緣(北京清華長庚醫院肝膽內科)、李榮寬(大連醫科大學附屬二院感染科)、李樹臣(哈爾濱醫科大學第二附屬醫院傳染科)、陸海英(北京大學第一醫院傳染科)、石荔(西藏自治區人民醫院感染科)、蘇明華(廣西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感染科)、溫志立(南昌大學第二附屬醫院消化內科)、吳彪(海南省人民醫院感染科)、徐京杭(北京大學第一醫院肝病科)、楊麗(四川大學華西醫院消化內科)、楊積明(天津市第二人民醫院感染科)、楊晉輝(昆明醫科大學附屬二院消化內科)、張繚云(山西醫科大學第一醫院傳染科)、周璐(天津醫科大學總醫院消化內科)、周永健(廣州市第一人民醫院消化內科)、祖紅梅(青海省第四人民醫院傳染科)參加本指南制定的討論,并提出了富有建設性的意見和建議。
利益沖突聲明:所有作者均聲明不存在利益沖突。

參考文獻見二維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