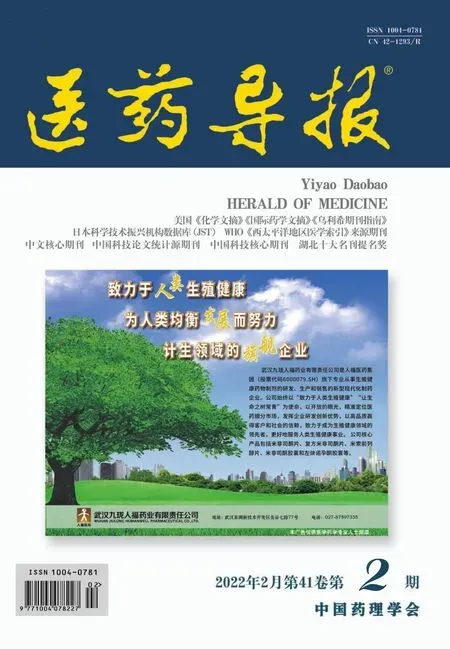肺動(dòng)脈高壓藥物治療新靶點(diǎn)及免疫調(diào)節(jié)治療策略*
李志勤,范媛,魏安華
(華中科技大學(xué)同濟(jì)醫(yī)學(xué)院附屬同濟(jì)醫(yī)院藥學(xué)部,武漢 430030)
肺動(dòng)脈高壓(pulmonary arterial hypertension,PAH)是一種進(jìn)行性、致命性疾病,其發(fā)生發(fā)展過(guò)程與肺血管結(jié)構(gòu)和(或)功能異常(即肺血管重構(gòu))密切相關(guān),表現(xiàn)為進(jìn)行性肺血管阻力增加,進(jìn)而導(dǎo)致右心功能衰竭甚至死亡,最新定義為靜息狀態(tài)下肺動(dòng)脈平均壓(mean pulmonary artery pressure,mPAP)≥25 mmHg(1 mmHg=0.133 kPa)[1]。PAH病理特征包括肺動(dòng)脈中膜肥厚、內(nèi)膜向心性或偏心性增殖和纖維化、外膜增厚纖維化、血管周?chē)装Y細(xì)胞浸潤(rùn)及管腔內(nèi)原位血栓形成等。目前PAH的發(fā)病機(jī)制尚未完全闡明,是多因素、多環(huán)節(jié)共同作用的結(jié)果,包括外因(低氧、煙草、粉塵等其他理化生物因素),內(nèi)因(遺傳、發(fā)育、結(jié)構(gòu)、疾病等)及交互因素(微生態(tài)、感染、免疫、藥物等),涉及多種血管活性分子(內(nèi)皮素、血管緊張素Ⅱ、前列環(huán)素、一氧化氮、一氧化碳、硫化氫及二氧化硫、雌激素等),多種離子通道(鉀離子通道、鈣離子通道、鋅離子通道及新型陽(yáng)離子通道),多條信號(hào)通路[低氧誘導(dǎo)因子/經(jīng)典型瞬時(shí)受體電勢(shì)通道(hypoxia inducible factor/canonical transient receptor potential channel,HIF/TRPC)通路、絲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MAPK)通路、Rho激酶(Rho-associated kinase,ROCK)通路、磷脂酰肌醇3-激酶/蛋白激酶B(phosphatidylinositol 3-kinase/ serine kinase,PI3K/AKT)通路、骨形態(tài)發(fā)生蛋白/轉(zhuǎn)化生長(zhǎng)因子β(bone morphogenetic proteins /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 beta,BMP/TGF-β)通路、核因子-κB(nuclear factor-κB,NF-κB)通路和Notch通路][1-3]。目前臨床上治療藥物有限,主要是肺血管擴(kuò)張劑和針對(duì)前列環(huán)素、內(nèi)皮素和一氧化氮通路的靶向藥物,其中肺血管擴(kuò)張劑只能改善癥狀,無(wú)法降低患者病死率。靶向藥物雖然帶來(lái)巨大希望,使我國(guó)PAH患者5年生存率從20.8%升高到>50%,但仍難阻止或逆轉(zhuǎn)PAH的病程進(jìn)展[4]。因此,開(kāi)發(fā)新的藥物治療靶點(diǎn)顯得尤為重要。最近免疫炎癥反應(yīng)在各種類(lèi)型PAH中的作用日益得到認(rèn)識(shí),PAH病程進(jìn)展必定伴隨著血管周?chē)难仔越?rùn),且免疫失衡和炎癥反應(yīng)在各種PAH實(shí)驗(yàn)動(dòng)物模型中的作用得到證實(shí),因此,免疫調(diào)節(jié)治療可能成為未來(lái)PAH治療的一個(gè)新方向[3,5]。筆者在本文就目前PAH藥物治療新靶點(diǎn),以及免疫調(diào)節(jié)治療的研究新進(jìn)展進(jìn)行綜述。
1 目前PAH藥物治療策略
根據(jù)2021年中國(guó)肺動(dòng)脈高壓診治指南[1],目前PAH治療策略包括一般性治療、支持性治療和特異性治療。其中特異性治療藥物即肺血管靶向藥物治療,主要涉及的通路是以下幾種。① 內(nèi)皮素受體途徑:主要包括非選擇性或選擇性?xún)?nèi)皮素受體拮抗劑,如波生坦、馬昔騰坦、安立生坦;②一氧化氮-環(huán)磷酸鳥(niǎo)苷(nitricoxide-cyclic guanosine monophosphate,NO-cGMP)途徑:主要包括可溶性鳥(niǎo)苷酸環(huán)化酶激動(dòng)劑(soluble guanylate cyclase stimulator,sGCs)(如利奧西胍)和5型磷酸二酯酶抑制劑(phosphodiesterase type-5 inhibitor,PDE-5i)(如他達(dá)拉非、伐地那非和西地那非);③前列環(huán)素通路途徑:主要包括前列環(huán)素受體激動(dòng)劑(如司來(lái)帕格)和前列環(huán)素類(lèi)似物(如依前列醇、曲前列尼爾、伊洛前列素、貝前列素鈉等)。
近年來(lái),PAH藥物研發(fā)逐漸深入,許多新治療靶點(diǎn),包括抑制血管重塑、改善右心功能、抑制細(xì)胞增殖分化、調(diào)控激素水平、抗炎、調(diào)控基因表達(dá)等新機(jī)制[2-6]已被動(dòng)物模型證實(shí),正由實(shí)驗(yàn)室轉(zhuǎn)化進(jìn)入臨床,部分新藥已開(kāi)始進(jìn)行臨床試驗(yàn),例如Rho激酶抑制劑法舒地爾[7]、內(nèi)源性血管舒張多肽愛(ài)帕琳肽[8]、激素類(lèi)去氫表雄酮(dehydroepiandrosterone,DHEA)[9]、二氯乙酸(dichloroacetic acid,DCA)[10]等。
2 炎癥因子與免疫反應(yīng)在PAH中的作用
免疫炎癥反應(yīng)與PAH的關(guān)系一直備受研究者關(guān)注。TUDER等[11]首次在PAH患者叢狀病損動(dòng)脈壁周?chē)鷻z測(cè)出T淋巴細(xì)胞、B淋巴細(xì)胞、巨噬細(xì)胞等炎癥細(xì)胞浸潤(rùn),開(kāi)啟了人們對(duì)PAH與免疫炎癥反應(yīng)相關(guān)性研究之門(mén)。近年來(lái)研究發(fā)現(xiàn)[2-3],PAH患者往往并發(fā)結(jié)締組織病,如系統(tǒng)性硬皮病、系統(tǒng)性紅斑狼瘡、POEMS綜合征、艾滋病等,且有研究發(fā)現(xiàn),病變血管周?chē)罅棵庖呒?xì)胞浸潤(rùn),涉及到T淋巴細(xì)胞、B淋巴細(xì)胞、巨噬細(xì)胞、肥大細(xì)胞、樹(shù)突狀細(xì)胞和中性粒細(xì)胞等,如特發(fā)性肺動(dòng)脈高壓(idiopathic pulmonary arterial hypertension,IPAH)患者受累肺動(dòng)脈的局部出現(xiàn)明顯增多的Th細(xì)胞和Tc細(xì)胞浸潤(rùn),而調(diào)節(jié)性T細(xì)胞 (regulatory cells,Tregs )數(shù)量減少,而靶向針對(duì)B淋巴細(xì)胞的抗CD20單抗可有效減少PAH患者循環(huán)血液中抗體和炎性因子釋放,從而達(dá)到治療作用,但目前各種免疫細(xì)胞之間存在的“cross-talk”關(guān)系較為復(fù)雜,在PAH病理生理過(guò)程中具體作用機(jī)制仍不清楚。同時(shí)多項(xiàng)研究[12-22]發(fā)現(xiàn)PAH患者血液中炎癥相關(guān)的細(xì)胞因子和趨化因子水平明顯變化,包括白細(xì)胞介素(IL)(如IL-1、IL-6、IL-8、IL-10),干擾素γ(IFN-γ),腫瘤壞死因子-α( TNF-α),基質(zhì)金屬蛋白酶-9 (matrix metallopeptidase 9,MMP-9),血管內(nèi)皮生長(zhǎng)因子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趨化因子(chemokine,CCL),IFN-γ誘導(dǎo)單核因子 (monokine-induced by interferon-γ,MIG),CXC趨化因子配體(C-X-C motif chemokine,CXCL),C-X3-C基元配體(C-X3-C motif ligand,CX3CL)等,具體見(jiàn)表1,均說(shuō)明免疫失衡早于肺血管重構(gòu)的發(fā)生,免疫炎癥反應(yīng)在PAH起始和形成過(guò)程中起著重要作用。免疫細(xì)胞及其分泌的細(xì)胞因子和趨化因子影響肺血管的收縮功能,調(diào)節(jié)肺血管內(nèi)皮和平滑肌細(xì)胞的生長(zhǎng)、遷移和分化,最終導(dǎo)致肺動(dòng)脈重構(gòu)。因此,靶向免疫炎癥的調(diào)節(jié)治療已成為目前PAH研究的一個(gè)熱點(diǎn)。

表1 PAH患者細(xì)胞因子/趨化因子的水平變化Tab.1 Change of level of cytokines and chemokine in patients with PAH
3 免疫調(diào)節(jié)治療藥物在PAH中的應(yīng)用
近年來(lái),許多免疫調(diào)節(jié)治療藥物減輕甚至逆轉(zhuǎn)PAH的作用在動(dòng)物模型中已得到證實(shí),部分藥物也在進(jìn)行臨床試驗(yàn),有望開(kāi)發(fā)成為PAH新型治療藥物。
3.1糖皮質(zhì)激素 糖皮質(zhì)激素是經(jīng)典的細(xì)胞免疫和體液免疫抑制劑,能有效降低合并結(jié)締組織病患者的肺動(dòng)脈壓力。在野百合堿誘導(dǎo)的PAH大鼠模型中,地塞米松可改善PAH,減少炎癥因子。PRICE等[23]研究顯示糖皮質(zhì)激素與免疫抑制劑聯(lián)合使用可有效減緩PAH的進(jìn)展,具有明顯的療效,但研究納入的治療方案不一致,設(shè)計(jì)存在一定限制,故無(wú)法排除血管擴(kuò)張藥物對(duì)降低PAH的影響。目前,少數(shù)回顧性研究和案例報(bào)道說(shuō)明糖皮質(zhì)激素聯(lián)合環(huán)磷酰胺治療結(jié)締組織相關(guān)肺動(dòng)脈高壓(CTD-PAH)是有效的[24]。MIYAMICHI-YAMAMOTO等[25]正在開(kāi)展CTD-PAH患者的隊(duì)列研究,患者接受12~18個(gè)月大劑量環(huán)磷酰胺和潑尼松,結(jié)局指標(biāo)肺血流動(dòng)力學(xué)和生存時(shí)間有一定改善,但該研究?jī)H僅為小樣本的觀察性研究,有待進(jìn)一步大規(guī)模的臨床試驗(yàn)證實(shí)其有效性和安全性。
3.2他克莫司 他克莫司是一種鈣調(diào)神經(jīng)磷酸酶抑制劑,可上調(diào)骨形成蛋白2型受體Ⅱ(BMPR-Ⅱ)的表達(dá)。小劑量他克莫司已被證明可逆轉(zhuǎn)野百合堿誘導(dǎo)和缺氧所致的PAH模型大鼠的疾病進(jìn)程,恢復(fù)肺動(dòng)脈內(nèi)皮細(xì)胞的正常功能。一項(xiàng)單中心隨機(jī)對(duì)照Ⅱ期臨床試驗(yàn)(NCT01647945)研究已經(jīng)完成,旨在評(píng)估他克莫司在PAH中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結(jié)果顯示少數(shù)患者表現(xiàn)出6 min步行距離和超聲心動(dòng)圖參數(shù)的改善,但這些變化并不顯著[26]。
3.3雷帕霉素(rapamyein) 雷帕霉素是一種強(qiáng)有力的免疫抑制劑,通過(guò)抑制T細(xì)胞和B細(xì)胞來(lái)發(fā)揮抗排斥作用,對(duì)多種自身免疫性疾病有顯著療效。不同于目前臨床常用的環(huán)孢素和他克莫司,雷帕霉素對(duì)刺激鈣依賴(lài)和非鈣依賴(lài)的信號(hào)傳導(dǎo)通道誘導(dǎo)的T細(xì)胞增殖具有明顯抑制作用,不僅能抑制IL-2、IL-4、IL-12、IL-7、IL-15介導(dǎo)的T細(xì)胞增殖,還能抑制IL-2和IL-6依賴(lài)的B細(xì)胞向產(chǎn)生抗體的漿細(xì)胞分化,從而降低IgA、IgM、IgG抗體的生成[27]。大鼠模型已證明雷帕霉素具有預(yù)防野百合堿所致PAH的作用,但無(wú)明顯治療作用[28]。目前雷帕霉素治療PAH的療效數(shù)據(jù)有限,僅有1例報(bào)道[29]。同時(shí)有一項(xiàng)開(kāi)放標(biāo)簽的I期臨床試驗(yàn)正在進(jìn)行,用于評(píng)估雷帕霉素在PAH患者中的治療作用(NCT02587325)[5]。
3.4利妥昔單抗 利妥昔單抗是一種抗CD20的單克隆抗體,可致B細(xì)胞耗竭。目前有2例病例報(bào)道關(guān)于利妥昔單抗用于治療系統(tǒng)性紅斑狼瘡和Still疾病所致的PAH[30-31]。同時(shí),一項(xiàng)多中心隨機(jī)對(duì)照、雙盲II期臨床研究正在進(jìn)行,旨在評(píng)估利妥昔單抗治療系統(tǒng)性硬化癥所致的PAH的有效性和安全性(NCT01086540)[5]。
3.5抗組胺藥和肥大細(xì)胞穩(wěn)定劑 增多的肥大細(xì)胞在PAH病程進(jìn)展中已被觀察到,但肥大細(xì)胞在PAH發(fā)病機(jī)制中發(fā)揮的作用尚未明確[32]。FAHRA等[33]研究一種H1受體拮抗劑非索非那定和一種肥大細(xì)胞穩(wěn)定劑色甘酸鈉對(duì)PAH患者的影響,12周后結(jié)果顯示,肥大細(xì)胞標(biāo)記物色氨酸酶、白三烯明顯減少,血管內(nèi)皮生長(zhǎng)因子下降,表明肥大細(xì)胞可能促進(jìn)血管重塑和內(nèi)皮功能障礙。同時(shí)結(jié)果還顯示PAH患者呼出的一氧化氮有所增加,提示肥大細(xì)胞可能參與PAH的肺血管重構(gòu)。
3.6他汀類(lèi) 他汀類(lèi)藥物除了具有明確的降膽固醇作用外,還發(fā)揮非調(diào)脂作用,包括抑制炎癥遞質(zhì)的釋放、改善血管內(nèi)皮功能、抗血小板聚集、穩(wěn)定動(dòng)脈粥樣硬化斑塊、抑制系膜細(xì)胞增生、免疫調(diào)節(jié)反應(yīng)等[5]。他汀類(lèi)藥物已經(jīng)在PAH的動(dòng)物模型中證明其有效性,能降低肺動(dòng)脈壓力,改善心室重構(gòu),逆轉(zhuǎn)PAH進(jìn)展,其中研究最多的是辛伐他汀。TANG等[34]構(gòu)建野百合堿注射所致合并右心衰竭的PAH大鼠模型,辛伐他汀2 mg·kg-1·d-1可改善大鼠肺動(dòng)脈壓力等血液動(dòng)力學(xué)指標(biāo),抑制心室肌和肺血管重構(gòu),促進(jìn)心肌能量代謝等,涉及的作用機(jī)制與miR-21-5p/Smad/TGF-β通路有關(guān)。2005年,KAO等[35]應(yīng)用辛伐他汀20~80 mg·d-1治療16例原發(fā)性或繼發(fā)性PAH患者,結(jié)果能明顯改善患者心功能,降低右心室收縮壓。然而,之后兩項(xiàng)隨機(jī)臨床對(duì)照試驗(yàn)未顯示辛伐他汀改善PAH患者的運(yùn)動(dòng)能力。SIPHT臨床試驗(yàn)結(jié)果[36]顯示,辛伐他汀80 mg,qd,短期能改善RV和pro-BNP水平,但6 min步行距離、心臟指數(shù)和肌酸激酶均無(wú)明顯變化,辛伐他汀對(duì)右心室(RV)和B型腦鈉肽前體(pro-BNP)的改善作用也是短暫的,持續(xù)應(yīng)用6個(gè)月后效果差異無(wú)統(tǒng)計(jì)學(xué)意義。同樣,ASA-STAT臨床試驗(yàn)[37]也未證實(shí)辛伐他汀對(duì)PAH運(yùn)動(dòng)耐力的改善作用。CHEN等[38]開(kāi)展Meta分析,共納入9個(gè)RCT研究657例患者,結(jié)果顯示他汀類(lèi)藥物可降低PAH患者的PAP,特別是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亞組,其他疾病亞組結(jié)果有待進(jìn)一步證實(shí)。
3.7其他 基于PAH的免疫調(diào)控機(jī)制,許多類(lèi)別的免疫抑制劑理論上應(yīng)該具有類(lèi)似治療效果,但目前尚無(wú)完善的臨床前和臨床研究證實(shí)其療效,僅有少數(shù)案例報(bào)道。
甲氨蝶呤:目前僅有1例病例報(bào)道描述甲氨蝶呤在PAH患者中的應(yīng)用[39],經(jīng)過(guò)小劑量甲氨喋呤和潑尼松龍免疫抑制治療1年,在未使用任何血管擴(kuò)張劑的情況下,患者肺動(dòng)脈壓力從47 mmHg下降到30 mmHg,同時(shí)臨床癥狀也有明顯改善。
霉酚酸酯:目前霉酚酸酯在PAH中研究數(shù)據(jù)非常有限,早期回顧性研究關(guān)于霉酚酸酯的療效不明確,近期MASAO等[40]報(bào)道1例抗磷脂綜合征所致PAH女性患者,使用大劑量激素和霉酚酸酯后癥狀改善較好。
曲妥珠單抗:是一種抗IL-6R單克隆抗體,已有少數(shù)病例報(bào)道用于治療結(jié)締組織疾病相關(guān)的PAH,KADAVATH等[41]首次報(bào)道曲妥珠單抗(8 mg·kg-1)聯(lián)合甲氨蝶呤和潑尼松治療1例成人Still病,結(jié)果顯示全身癥狀和實(shí)驗(yàn)室指標(biāo)均明顯改善,有望成為結(jié)締組織病所致PAH的新希望,但其有效性和安全性仍有待前瞻性臨床研究驗(yàn)證。
環(huán)孢素:目前已有動(dòng)物模型顯示環(huán)孢素有利于血流動(dòng)力學(xué)和血管重構(gòu)的改善,但迄今為止,筆者尚未見(jiàn)環(huán)孢素治療PAH的臨床試驗(yàn)研究[42]。
依那西普:筆者目前尚未見(jiàn)依那西普用于PAH治療的動(dòng)物和臨床研究報(bào)道[5]。
4 結(jié)論與展望
綜上所述,免疫炎癥反應(yīng)在肺血管重構(gòu)中必然發(fā)揮重要作用,通過(guò)調(diào)節(jié)免疫細(xì)胞、細(xì)胞因子和趨化因子等介入PAH的病理生理過(guò)程,但目前PAH免疫學(xué)機(jī)制尚未完全闡明[43],因此尚無(wú)批準(zhǔn)上市用于PAH 治療的的免疫調(diào)節(jié)劑,大多數(shù)治療藥物對(duì)PAH的治療效果驗(yàn)證還停留在動(dòng)物模型,僅少數(shù)藥物已經(jīng)過(guò)渡到臨床試驗(yàn),而對(duì)于已進(jìn)入臨床試驗(yàn)的藥物療效卻不甚理想,原因可能與現(xiàn)有PAH疾病分類(lèi)太復(fù)雜,不同類(lèi)型PAH發(fā)病過(guò)程涉及的免疫炎癥機(jī)制存在差異,臨床研究納入就必然存在明顯的異質(zhì)性有關(guān),因混雜因素過(guò)多,影響臨床試驗(yàn)結(jié)果。因此,為了進(jìn)一步推動(dòng)免疫調(diào)節(jié)治療藥物用于PAH領(lǐng)域的開(kāi)發(fā)上市,一方面應(yīng)借助前沿的免疫學(xué)和分子生物學(xué)研究方法和手段,逐漸闡明PAH病理生理過(guò)程中的免疫學(xué)機(jī)制,為PAH的免疫調(diào)節(jié)治療奠定基礎(chǔ);同時(shí)應(yīng)進(jìn)一步規(guī)范免疫調(diào)節(jié)治療藥物的臨床試驗(yàn),盡可能消除混雜因素,通過(guò)良好的試驗(yàn)設(shè)計(jì)保證結(jié)果的真實(shí)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