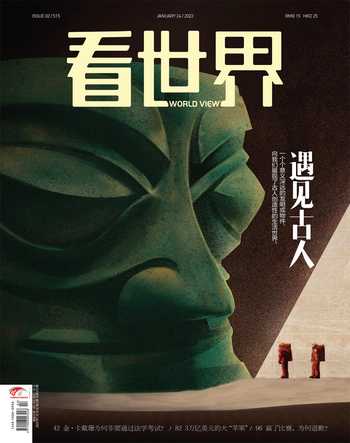八雷亞爾銀幣環繞地球
許諾

1545年,玻利維亞的波托西山發現了世界上最豐富的銀礦,西班牙征服者使用本地勞動力來開采白銀
電子支付高度普及的當下,實體的錢幣似乎已經悄然退出我們的生活,面額小重量大的硬幣更是絕少被人提及—人類貨幣史正在翻開嶄新的一頁。金屬貨幣仿佛是無言的旁觀者,見證了人類文明從稚嫩、孤立的鴻蒙初辟,走向成熟、聯合的全球化時代;又好似煞費苦心的導演,以財富和利益驅動著人類創造出復雜的組織,開拓出廣闊的天地,編排了一幕幕歷史劇。
而那位把所有演員調動在一起的偉大導演,促成了全球化雛形的世界貨幣,正是八雷亞爾銀幣。
八雷亞爾銀幣源自西班牙對美洲的殖民和開發。
1492年,哥倫比誤打誤撞地開辟了歐洲人的大航海時代,西班牙和葡萄牙最先揚起了探索新世界的風帆。拉丁美洲無窮的礦藏成為西班牙殖民者的囊中之物,而金銀被寄予了最大的希望。他們最想要的是黃金,但美洲給他們的是白銀。
墨西哥和安第斯山脈中分布著儲量豐富的金銀礦,西班牙人到來后擴大了開采規模。墨西哥的薩卡特卡斯和瓜納華托、玻利維亞的波托西,成為了產量驚人的銀礦基地。
1536年,墨西哥城造幣廠開始生產西班牙殖民地的第一種銀幣。此后幾百年,由于打造技術和印制圖案的變化,西班牙銀幣的形制分為多種樣式,直到18世紀晚期霸業衰落,西班牙銀幣的形制才穩定成大眾熟悉的樣子:正面刻西班牙國王頭像,背面刻王室盾徽和雙立柱,并配有相應裝飾圖案、文字、年份、面值等內容。

1776年造的西班牙卡洛斯三世八雷亞爾銀幣
八雷亞爾是單枚銀幣的最大面值,也被稱為Pieces of eight。
如1776年造的西班牙卡洛斯三世八雷亞爾銀幣,正面為國王半身胸像,銘文為西班牙文“DEI·GRATIA·1776·CAROLUS·Ⅲ·”,意為“蒙神恩寵,1776 年,卡洛斯三世”。背面紋飾為西班牙王室盾徽,徽內以橢圓圈為中心十字分割,徽上有皇冠,兩側有大力神赫克力斯立柱,柱身有卷軸纏繞,卷軸內有字,左書“PLUS”, 右書“VLTRA”,意為海外有天地。邊緣銘文“·HISPAN· ET·IND·REX·OM·8R·F·M·”,分別意為西班牙與西印度之王,墨西哥城鑄造,面值八雷亞爾,最后兩個字母為兩位鑄銀師姓名的縮寫。
雷亞爾(西班牙語Real,又翻譯為里亞爾)是西班牙的貨幣單位,八雷亞爾是單枚銀幣的最大面值,也被稱為Pieces of eight,類似于今日美元紙幣的最高面值為100美元,八雷亞爾也成為財富最直接的象征。
銀礦的開采,給殖民者帶來了無盡的財富,也給被奴役的礦工們帶來無窮的痛苦。
西班牙法律規定:殖民地的所有地下資源全部歸王室所有,任何礦區都必須把礦產品的1/5交給王室,并且嚴格限制私人礦的規模,大片礦產只能由王室開采。不過,因為有利可圖,大量的移民來到新大陸,小型白銀礦如雨后春筍般興起。
為了節省成本盡快牟利,小礦主們很少會采用科學的開采技術、購置昂貴的先進機器設備,而是殘酷奴役印第安人開采,甚至建立“委托監護制”強迫印第安人勞動。“殖民者認為把一個印第安人累死,再替換上另一個,比花錢照顧他便宜得多”。冶煉銀所用的汞齊化法,需要把銀礦砂和水銀攪拌,印第安人不得不冒著汞中毒的危險,光著腳來攪拌,直到18世紀末期騾、馬才代替了人工。
16—18世紀美洲白銀產量約占世界總產量的近八成,美洲白銀帶來的巨額財富,使西班牙國王擁有充足的儲備發動稱霸歐洲的戰爭。16世紀中期,西班牙帝國的領土在歐洲大陸從三面包圍法國,伊比利亞半島、尼德蘭、意大利和地中海的眾多島嶼均在囊中;大西洋的對面,帝國還統治著除巴西之外的中美洲和南美洲;在太平洋,它掌管菲律賓群島—全盛時期西班牙帝國領土面積達到了1054萬平方公里,超過古代羅馬帝國的兩倍。國王驕傲地宣稱:“白銀乃我王權穩定與強大之根基。”
僅建造無敵艦隊的費用就高達1000萬金幣,而一場戰爭就讓艦隊全軍覆沒。

16世紀西班牙的銀幣兌換商
窮兵黷武也把帝國拖入泥潭。西班牙幾乎和歐洲所有國家交戰,并且卷入了與伊斯蘭教和新教的曠日持久的宗教戰爭。為支持龐大的軍隊開銷,西班牙消耗了大量財力。殖民地運來的白銀再多,也不能填補財政漏洞。16世紀40年代,來自美洲的收入大約是20萬金幣,到80年代,達到了200萬金幣,但僅建造無敵艦隊的費用就高達1000萬金幣,而一場戰爭就讓艦隊全軍覆沒。國王不惜債臺高壘,將未來的收入都抵押給了外國的債權家。
然而,這還不是西班牙最大的麻煩。
大量白銀的輸入,解除了15世紀以來困擾歐洲的“貨幣金屬缺乏癥”,短期內的貴金屬貨幣過剩,導致白銀價格下降、貨幣貶值、物價上升,這場持續的通貨膨脹被稱為價格革命。從1540年代到1640年代,不僅僅是西班牙,整個歐洲的物價上漲了3倍,英國的生活費用則增長了7倍!
首當其沖的西班牙物價漲幅遠遠高于英、法等國,使得發展工業、出口商品變得不再可能,西班牙人不愿把資金投入工業生產,致使本國工業蕭條。同時,西班牙也并不發展殖民地的加工業,只把其作為原料產地加以嚴格控制,這也造成后來獨立的拉丁美洲國家缺乏工業基礎。
本國和殖民地的需求得不到滿足,只能進口外國的商品。學者的統計顯示:17世紀末,西班牙運往美洲殖民地的貨物,總值5100萬~5300萬埃斯庫多(葡萄牙前流通貨幣),其中25%屬法國、22%屬意大利、20%屬荷蘭、10%屬英國、10%屬佛蘭德斯、8%屬漢堡,只有5%來自西班牙。幾個世紀以來,西班牙用白銀培養了競爭對手的產業基礎。
在西班牙國內,王室和貴族占據了絕大部分財富,西班牙淪為了一個貧富極度分化、基礎生產受到打壓的“消費型社會”。依靠特權獲得財富者,不用白銀進行投資生產,反而投入“炫耀性消費”。社會也形成了鄙視勞動、追逐奢侈消費和投機的不良風氣。
白銀像水一樣從西班牙流過,卻并沒有給西班牙帶來財富,反而讓它變得一貧如洗。“西班牙像一張嘴、它進食、咬碎、嚼爛,立即送到其他的器官,除了一瞬即逝的味覺或者偶然掛在牙齒上的碎屑之外,自己什么也沒留下。”
在殖民地,由于宗主國的高壓統治和資源掠奪,大量白銀外輸,產地反而會出現白銀稀缺的情況。由于特權階級突出,殖民地經濟和社會高度分層,甚至形成了雙重貨幣體系。

往返于美洲和菲律賓的帆船(左)
東方的吞噬
在東方,西班牙白銀洪流浩浩蕩蕩地流向大明帝國。
一直以來,中國苦于貴金屬匱乏,缺乏能夠長期穩定有效供給的貴金屬貨幣充當一般等價物。直到明代中葉之前,白銀都未能取得本位貨幣的地位。隆慶元年(公元1567年)發生了兩項影響深遠的重大決策:一是買賣貨物值銀一錢以上的“銀、錢兼使”,一錢以下的,只許用錢(銅錢),說明國家從法權的形式上確立了白銀的主幣地位;二是宣布在漳州開海,允許民間私人出洋從事海上貿易,“準販東西二洋”。
明代中國,外來白銀的主要來源一是日本,由葡萄牙人充當中介,廣州—澳門—長崎的航線完成了中日之間的絲綢白銀貿易;二是美洲,以馬尼拉為基地進行貿易,白銀來自橫跨太平洋的美洲銀礦。學者粗估,1570—1644年,美洲白銀共約有12620噸流入了中國。在1540—1644年,從日本流入的白銀有7500噸左右。同時,占歐洲產量一半的白銀流入了中國,這些加在一起,總數極為龐大。
大量商品和白銀在東南沿海聚集,為商品市場的擴大和資金的周轉提供了有利條件,極大促進了商業發展、市場擴大和專業化生產,刺激了資本主義萌芽的迅速增長。百姓財富迅速增長,人們開始追逐物質消費,八雷亞爾銀幣“繪就”了多彩斑斕的晚明風情圖。這一切都成為晚明大變局的一部分,是中國近代化的先聲。

明朝中后期,歐洲產量一半的白銀流入了中國
輸入中國的白銀一段時間內劇烈下降,成為了壓垮大明的諸多稻草之一。
萬歷九年(公元1581年),張居正力主一條鞭法,白銀從此成為國家命脈,危機的種子也就此埋下。對海外白銀的嚴重依賴,使國家財政貨幣體系的風險性大增。在明代末年一系列外部事件的影響下,輸入中國的白銀一段時間內劇烈下降,成為了壓垮大明的諸多稻草之一。
17世紀中葉,美洲白銀產量開始下降,西方殖民者在東南亞的異動也造成了白銀輸入的短暫斷絕:1639年,西班牙人屠殺馬尼拉華人,導致福建與馬尼拉貿易陷于停頓;1640年,葡萄牙脫離西班牙統治獨立,澳門與西班牙之間的貿易基本中斷;1641年,荷蘭人攻占馬六甲,徹底改變了貿易體系格局。
白銀生產和流通都在縮減,社會動蕩加劇,百姓無銀納稅,朝廷發不出兵餉,明末危機的總爆發,與全球的白銀危機有著一種不可忽視的聯系。
“美洲金銀礦的發現,土著居民的被剿滅、被奴役和被埋于礦井,對東印度開始進行的征服和掠奪,非洲變成商業性的獵獲黑人的場所—這一切標志著資本主義生產時代的曙光。” 拉丁美洲殖民地白銀的輸入,極大地促進了歐洲資本主義的發展。
在東方,古老的中國在白銀和銀幣的吸引下,也卷入了初見規模的全球體系之中。這短暫的相遇,還不足以改變中國按照自身文明的慣性前進,但銀本位的確立,確實是一條無法斬斷的絲線,把中國和世界緊密相連,直到雙方下一次的碰面。在此之前,來自遙遠美洲的八雷亞爾銀幣,則一直默默陪伴中國度過漫長的銀本位時代。
特約編輯榮智慧 rzh@nfcma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