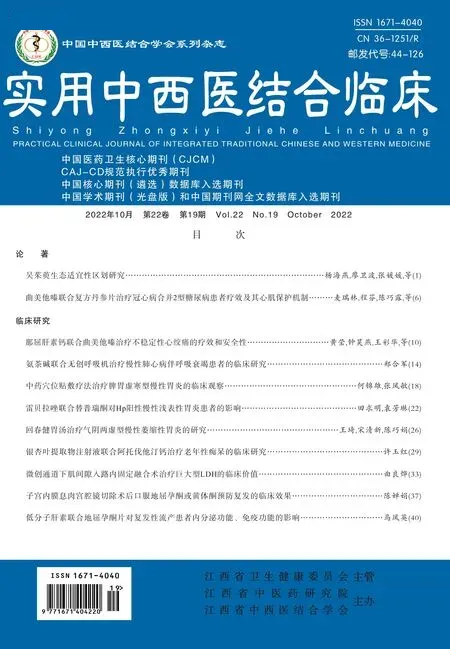微創通道下肌間隙入路內固定融合術治療巨大型LDH的臨床價值
曲良燁
(河南省南陽市中醫院脊柱三科 南陽 473007)
腰椎間盤突出癥(LDH)是骨科常見的一種腰椎疾患,通常是因腰椎間盤部分,特別是髓核部位發生退行性改變,受外力作用后纖維環破裂,髓核由破裂位置向椎管或是后方突(脫)出,造成鄰近脊神經根受壓或刺激,引起腰部疼痛、下肢麻木及疼痛等癥狀[1]。當突出椎間盤組織>腰椎椎管矢狀徑的50%時則屬于巨大型LDH,該病癥較為多見,部分患者發病急且伴一定程度的下肢神經癥狀,也有少部分患者的馬尾神經受到一定損傷[2]。手術是現階段臨床治療巨大型LDH的常用手段,且建議伴馬尾神經損傷者要盡快接受手術治療[3~4]。近年來,內固定融合術在LDH臨床治療中的應用日益廣泛,且取得了顯著成效。該術式早期常采用正中切口入路,雖有視野大、手術操作便捷等諸多優點,但也會對骶棘肌造成一定程度的損傷。微創通道下肌間隙入路方式可充分彌補上述缺陷,有效保護骶棘肌[5~7]。本研究探討微創通道下肌間隙入路內固定融合術治療巨大型LDH的效果。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2019年2月至2021年2月于南陽市中醫院行內固定融合術治療的90例巨大型LDH患者,按照隨機數字表法分為兩組,各45例。對照組男性、女性分別為21例、24例;年齡42~64歲,平均(51.33±9.20)歲;體質量指數(BMI)19~25 kg/m2,平均(22.30±2.08)kg/m2;病程5個月至6年,平均(3.77±1.60)年;病變節段:L3/L4節段11例,L4/L5節段27例,L5/S1節段7例。研究組男性、女性分別為19例、26例;年齡40~67歲,平均(51.46±8.15)歲;BMI 19~25 kg/m2,平均(22.34±2.42)kg/m2;病程7個月至7年,平均(3.82±1.78)年;病變節段:L3/L4節段13例,L4/L5節段26例,L5/S1節段6例。兩組基線資料(性別、年齡、BMI、病程、病變節段)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經南陽市中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批準(倫理字201901042號)。
1.2 納入與排除標準 (1)納入標準:有嚴重性腰部疼痛或腿部放射痛,經CT、X線或MRI等檢查發現椎間盤組織向椎管突出,且大于腰椎椎管矢狀徑的50%;單節段發病;伴神經根或馬尾神經損傷,且呈進行性加重,需盡早采取手術治療;經藥物、牽引及睡硬板床等非手術治療3個月后無效;對本研究內容知情,自愿參與并簽署知情同意書。(2)排除標準:有骨質疏松癥者;腰椎嚴重畸形者;病變節段椎板或椎弓根存在發育不良者;病變節段椎弓根出現峽部斷裂者;BMI超過25 kg/m2者;有腰椎部位手術史者。
1.3 治療方法 兩組手術均由同組手術醫師操作,均為靜脈復合麻醉,體位為俯臥位且保證腹部處于懸空狀態。對照組采用正中切口入路:將病變節段作為中心,從棘突部位對腰部正中位置行縱向切口,將皮膚及皮下組織依次切開,對存在神經癥狀側或病變較為嚴重側的骶棘肌予以剝離,借助橫突拉鉤牽拉骶棘肌,充分暴露椎板間隙、關節突關節,使用C臂X線機明確具體病變節段。將定位針通過椎弓根置于病變節段的上下椎體后,經椎間孔腰椎椎間融合術(TLIF)實施椎管擴張減壓以及髓核摘除等操作,對椎間隙展開深部植骨并放入融合器。借助瞄準器安裝對側椎板關節突螺釘,最后將定位針拔除并安裝椎弓根螺釘、連接棒等,對椎間進行適度壓縮處理。研究組采用微創通道下肌間隙入路:在存在神經癥狀側或病變較為嚴重側將病變節段作為中心,在棘突旁作腰部縱向切口,長度控制在2~3 cm。將皮膚、皮下組織依次切開直至腰背筋膜,對多裂肌肌纖維間進行鈍性分離,到達椎板以及關節突表層后,借助擴張套管逐步擴張,接著向其中放置帶有光源的通道給予縱行撐開,讓底部通道保持一種喇叭狀,促使通道處于外傾及頭傾并進行固定。清理椎板以及關節突表層殘留組織,將椎板間隙和關節突關節均充分暴露于術野,借助C臂X線機明確具體病變節段,后續方法與對照組相同。椎弓根、椎板關節突螺釘安裝均需借助C臂X線機。手術結束后對切口進行徹底性止血處理,生理鹽水沖洗干凈后縫合切口,借助引流管負壓引流。
1.4 觀察指標 (1)圍術期相關指標:對比兩組切口長度、術中出血量、術后引流量及術后72 h腰部切口疼痛程度,其中疼痛程度用視覺模擬評分法(VAS)評估,評分高疼痛嚴重。(2)影像學相關參數:術前、術后12個月時,通過X線、CT及MRI等影像學檢查,對比兩組腰椎矢狀面Cobb角、腰椎冠狀面Cobb角及病變節段椎間隙高度。(3)腰椎功能:術前、術后12個月時,通過日本骨科學會評估治療分數(JOA評分)[8]評估兩組腰椎功能,總評分為29分,評分高代表腰椎功能恢復好。(4)多裂肌面積與等級:術前、術后12個月時,借助寧波明天醫學影像系統不規則面積測量模塊對兩組多裂肌面積進行實時測量;參考相關標準對兩組多裂肌等級進行評估,1級代表正常肌肉狀態,2級代表肌纖維間散在分布一定量脂肪組織,3級代表肌肉、脂肪組織呈相當性分布,4級代表肌肉組織占比低于脂肪組織。(5)早期并發癥:對比兩組術中并發癥(椎弓根骨折、終板損傷等)及術后并發癥(馬尾神經損傷、切口皮膚部分壞死等)發生情況。
1.5 統計學分析 采用SPSS24.0軟件分析數據。計量資料(圍術期相關指標、影像學相關參數、腰椎功能、多裂肌面積)以(±s)示,行t檢驗;計數資料(多裂肌等級、早期并發癥)以%表示,行χ2檢驗;等級資料采用秩和檢驗。P<0.05表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兩組圍術期相關指標比較 和對照組相比,研究組切口長度更短,術中出血量、術后引流量更少,術后72 h VAS評分更低(P<0.05)。見表1。
表1 兩組圍術期相關指標比較(±s)

表1 兩組圍術期相關指標比較(±s)
?
2.2 兩組腰椎功能比較 術后12個月時,兩組腰椎JOA評分較術前提高(P<0.05),但組間比較無顯著性差異(P>0.05)。見表2。
表2 兩組術前、術后12個月時腰椎JOA評分比較(分,±s)

表2 兩組術前、術后12個月時腰椎JOA評分比較(分,±s)
注:與同組術前相比,*P<0.05。
?
2.3 兩組影像學相關參數比較 術后12個月時,兩組影像學相關參數均優于術前,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但組間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3。
表3 兩組術前、術后12個月時影像學相關參數比較(±s)

表3 兩組術前、術后12個月時影像學相關參數比較(±s)
注:與同組術前相比,*P<0.05。
?
2.4 兩組多裂肌面積與等級比較 術后12個月時,兩組多裂肌面積均縮小,但研究組大于對照組(P<0.05);術后12個月時,研究組多裂肌等級優于對照組(P<0.05)。見表4。
表4 兩組術前、術后12個月時多裂肌面積與等級比較(±s)

表4 兩組術前、術后12個月時多裂肌面積與等級比較(±s)
注:與同組術前相比,*P<0.05。
?
2.5 兩組早期并發癥發生情況比較 研究組早期并發癥發生率(17.78%)較對照組(4.44%)高,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5。

表5 兩組早期并發癥發生情況比較[例(%)]
3 討論
與LDH相比,巨大型LDH的病情特征及病理改變更為特殊:(1)大體積髓核脫出,且常伴終板軟骨剝脫問題;(2)硬膜、神經根均受到嚴重壓迫,可能與脫出的髓核出現粘連現象;(3)椎間隙高度已明顯低于健康人群;(4)病情進展快,多數患者出現下肢神經癥狀,也有少數患者出現馬尾神經損傷癥狀;(5)受髓核嚴重突出或脫出的影響,硬膜、神經根以及馬尾神經均受到嚴重壓迫,造成椎管內空間狹窄,不利于神經退讓,手術操作時易對神經造成進一步損傷[9~11]。正因巨大型LDH存在上述特殊病情特征及病理改變,導致術式選擇方面至今存在很大爭議,但也有諸多研究主張采用內固定融合術進行治療[12~14]。近年來,單側椎弓根螺釘聯合對側椎板關節突螺釘內固定并椎間植骨融合術因具有確切療效,在多種腰椎病變臨床治療應用日益廣泛,但目前臨床對于巨大型LDH可否通過微創通道下肌間隙入路進行內固定融合術治療尚無統一意見。
本研究對兩組患者均以相同的減壓、內固定以及融合術進行治療,結果顯示,術后12個月時,兩組病變節段椎間隙高度較術前明顯增加,且腰椎矢狀面、冠狀面Cobb角也均得到有效恢復,腰椎JOA評分明顯提高,但組間對比差異不顯著,提示該聯合術式治療巨大型LDH效果顯著,不會因入路方式不同產生明顯差異。本研究結果還顯示,和對照組比,研究組切口長度更短,術中出血量、術后引流量更少,術后72 h VAS評分更低,提示微創通道下肌間隙入路內固定融合術治療巨大型LDH有切口小、出血少、引流量少及疼痛程度輕等多種優點。究其原因在:(1)經多裂肌肌纖維入路可有效避免剝離大范圍肌肉組織,減少術中出血量;(2)微創通道沿著肌纖維撐開,保持喇叭狀,可發揮切口小、顯露大的作用;(3)通道內自帶光源,可為手術操作提供良好的照明條件;(4)術區可充分暴露于視野內,有效提高了手術操作的便捷性。術后12個月時,兩組多裂肌面積均縮小,但研究組較大;術后12個月時,研究組多裂肌等級優于對照組,與曾忠友等[15]的研究結果一致性較高,提示微創通道下肌間隙入路內固定融合術治療巨大型LDH可有效減輕對多裂肌的損傷,對患者術后康復有積極意義。
但本研究對兩組早期并發癥進行統計分析發現,研究組早期并發癥發生率(17.78%)較對照組(4.44%)高,提示相比于正中切口入路而言,通過微創通道下肌間隙入路行內固定融合術的早期并發癥發生風險較高。這可能是由于:(1)肌間隙入路術中的入路途徑、切口及手術操作空間等均異于傳統入路,若手術操作欠熟練將會增加早期并發癥的發生風險,以終板損傷、切口皮膚部分壞死等切口部位并發癥為主。同時,微創通道下進行手術操作還會在一定程度上增加馬尾神經、硬膜等損傷風險。(2)該入路方式難以暴露棘突基底部位,因此容易降低椎板關節突螺釘安裝的精準度,從而增加螺釘安裝位置不佳、硬膜或馬尾神經損傷等發生風險。(3)由于巨大型LDH的病情特征及病理改變較為特殊,而微創通道下肌間隙入路內固定融合術又屬于一種新學習且在狹小空間內操作的術式,因此硬膜、馬尾神經損傷等發生風險也相對較高[16]。
綜上所述,微創通道下肌間隙入路內固定融合術治療巨大型LDH具有切口小、出血少、引流量少及疼痛程度輕等優勢,可促進患者腰椎結構及功能改善,但存在早期并發癥發生風險高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