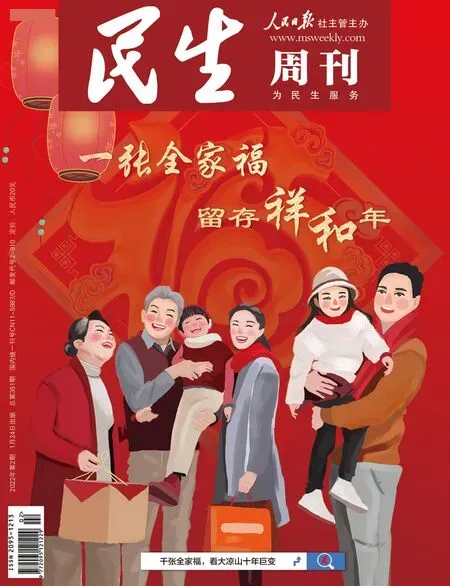紅絲帶港灣:33個艾滋病孩子共有一個家
□《民生周刊》記者 王迪

2021年10月11日,國際女童日,艾滋病健康基金會(AHF)亞洲局副主席鮑宇剛博士和臨汾紅絲帶學校的全體師生共同演出了美麗的童話故事—森林女童日之化妝舞會。
在山西臨汾堯東區郊外,有一個特殊的“大家庭”—紅絲帶學校。
這里的孩子們,稱呼校長叫“伯伯”,生活老師叫“阿姨”,年輕的老師叫“姐姐”,負責做飯的師傅叫“叔叔”。
這群孩子大部分是孤兒,由于母嬰傳播,生下來便攜帶艾滋病病毒(HIV),注定比普通孩子要承受更多的痛苦。
“除了服藥、病痛的折磨,他們還要承擔這個年紀本不該有的心理壓力,由于遭受周圍人的不理解和歧視,孩子們幼小的心靈受到了傷害。”作為臨汾紅絲帶學校的校長、孩子們心中的郭伯伯,17年來,郭小平為這里的艾滋病患兒成長傾注心血,與孩子們結下了近乎父子(女)般的深厚感情。
2017年,郭小平先后獲得“感動中國”2016年度人物、第六屆全國道德模范提名。在他的帶領下,紅絲帶學校孩子和老師的命運,也在悄然發生著變化。
是校長 也是家長
時鐘撥回到2004年,臨汾市傳染病醫院綠色港灣接收了第一批小患者,這也是郭小平第一次接觸艾滋病患兒。
彼時,郭小平還是臨汾市傳染病院院長,這個叫作“綠色港灣”的地方,是專門收治傳染病患者的病區。“遭受孤立,沒有玩伴,無法和當地同齡孩子一起上學,成了這批孩子共同的遭遇。”郭小平告訴《民生周刊》記者。
為了讓孩子有學上,郭小平在病區騰出一間房,擺上了幾張課桌和一個小黑板,就這樣,“愛心小課堂”成立了。醫護人員充當老師,輪流教孩子們讀書寫字。
然而,這種教學方式并非長久之計。“時間一長,孩子們會問,為什么別的小朋友都可以去學校,而我們只能在這里上課。”
在郭小平的堅持下,2006年9月1日,“愛心小課堂”變成了“紅絲帶小學”,專門為艾滋病患兒提供教學和食宿,郭小平兼任校長。
“沒想到的是,來上課的孩子越來越多,甚至有外地家長不遠千里把孩子送來。”
2011年12月1日,在臨汾市委、市政府支持下,該校被納入國家義務教育行列,并正式更名為“臨汾紅絲帶學校”,成了九年義務教育學校,也是目前全國唯一一所集艾滋病兒童少年的生活、醫療、教育于一體的全日制學校。
作為紅絲帶學校的創始人,郭小平深知肩上的重任。自2013年起,他先后辭去臨汾市傳染病醫院、第三人民醫院和中醫院院長職務,成為紅絲帶學校的專職校長。
面對外界的質疑,他說:“醫院不缺一名院長,而紅絲帶學校缺一名校長、一個家長。”在郭小平眼里,這里不僅是一所學校,更像一個家,而他要做的,是當好這里33個孩子和20余名老師的“大家長”。
功夫不負有心人。2017年,紅絲帶學校培養出第一批大學生。16名孩子參加高考,其中15名分別考取了專科及本科院校。
“當時,臨汾市在紅絲帶學校專門設置了標準化高考考場,也是中國首次為艾滋病感染者設立獨立的高考考場,具有劃時代的意義。”郭小平認為,這是全社會對這一特殊群體的關愛,是社會文明的進步。
從最初的病區小課堂,到如今的紅絲帶學校,這里見證了郭校長一路走過的10余年。
“這里是家,我喜歡這里”
2021年12月1日,是第34個世界艾滋病日。這一天,紅絲帶學校迎來了10周年紀念日。
11月28日,在該校舉辦的“世界艾滋病日”主題活動上,高一學生佳佳、文文把一首動人的《父親》演唱給她們最愛的“校長爸爸”郭小平。
孩子們唱得哽咽,郭小平也早已濕了眼眶。
唱歌的兩個女孩,佳佳今年18歲,從未見過自己的親生父母,被領養后發現感染HIV,2015年被送來臨汾紅絲帶學校;文文今年16歲,由奶奶撫養長大,2018年進入學校。
在日常相處中,郭小平發現,比起同齡孩子,這里的孩子更需要關愛和陪伴。“自卑、孤僻,不愛說話,也不合群,是這群孩子剛來時的共同點。”
女童玲玲,父親務農,偶爾靠打工修路掙點生活費,媽媽因為艾滋病過世。在家時,玲玲和父親幾乎沒什么交流。外界知道她有這個病,也比較排斥。玲玲剛來時,不愛和人交流。
“經常一天也說不到幾句話。”郭小平擔心孩子有心理問題,于是讓學校阿姨和姐姐輪流陪伴,幾個月的相處之后,玲玲逐漸打開封閉已久的心。“現在越來越愛笑了”。
“這里是家,我喜歡這里。”玲玲對《民生周刊》記者說。
坤坤,紅絲帶學校最讓人操心的孩子。8歲時,從山上玩耍時不慎跌下山撞破了頭,在醫院做手術時,查出體內攜帶艾滋病病毒。
隨后,當地疾控部門查明,坤坤是通過母嬰感染,生父是誰,至今不知。坤坤剛滿月時,繼父離家,10個月大時,母親也離開了,沒有血緣關系的爺爺,將他勉強帶大。
“不會說話,撿垃圾吃,基本沒啥認知能力和語言水平。”郭小平回憶道,坤坤剛來時,吃飯總愛往自己碗里扒菜,有一天,老師檢查寢室時發現,他在床底下藏了很多饅頭。
“因為之前老吃不飽。”現在,不缺吃穿了,坤坤開始懂得分享,會主動給同學夾菜。
為了讓坤坤回歸正常,教學老師一點點教他如何張口、發音、識字;生活老師手把手糾正他的日常習慣—餐前洗手,如何用筷子。
廣東省所強化監督做標準,不斷將藥檢創新力轉化為監管戰斗力。目前檢驗檢測能力項1733項,已參與金銀花、銀杏葉等應急檢驗案件30多起,涉案檢驗近200個品種,為行政監管提供了強有力的技術支撐。
如今,坤坤已經長成了14歲的少年,雖然智力還未達到同齡孩子水平,但是已經學會自己穿衣吃飯,還會和人親昵,會禮貌地跟人說謝謝。
進入青春期后,學校尤其注重對孩子性知識的傳授與引導。“這是對他們未來防止艾滋病傳播必要的基礎教育。”郭小平說,希望至少從他們這里,艾滋病不再傳播下去,孩子們也在履行著他們的承諾。
永遠的避難所
不只是孩子,紅絲帶學校的老師們也有一部分是HIV感染者或病毒攜帶者。
今年48歲的劉麗萍就是其中一位。1996年因宮外孕輸血,劉麗萍感染上艾滋病病毒,2005年因舌頭上長出一層白瘡,吃飯、喝水都疼,辛辣的東西一點兒不能碰,去市里做血液檢查時被確診。
2005年5月,劉麗萍開始在臨汾傳染病醫院接受治療,病情穩定后,她來到“愛心小課堂”做志愿者老師。后來,劉麗萍成了紅絲帶學校的正式老師,照顧孩子的日常起居,吃藥,定期跟孩子談心,孩子們親切地稱呼她為“劉阿姨”。

郭小平和孩子們在一起做游戲。
和劉麗萍一起留下的,還有因母嬰傳播攜帶艾滋病病毒的孩子—小雨。
作為紅絲帶學校第一批考上大學的學生,小雨畢業后,又回到這里,成了一名志愿者老師,給曾經與自己共度童年的弟弟妹妹分享大學校園生活,陪伴他們一起成長。
廚師老李,也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當年,他送孩子到紅絲帶學校上學,郭小平得知他之前在部隊當過廚師,就將他留了下來,給學校的孩子們做飯。2017年,老李的孩子考上了大學,而老李因為和孩子們感情太深,選擇繼續留在這里。
由于學校的特殊性,紅絲帶學校的老師都有著“雙重身份”:教學老師也管生活,生活老師也負責教學。
朱然,紅絲帶學校頗具人氣的年輕女教師。2014年9月,畢業不久的她回到家鄉,得知紅絲帶學校缺一名語文老師,她毅然報名。
“一開始,家人朋友也不理解,主要還是擔心。”后來,她將艾滋病傳播知識普及給家人,握手、擁抱、吃飯等日常接觸并不會感染艾滋病,并且將在學校的所見所聞、孩子們的無辜純真講給家人。最終,在她的堅持下,家人也決定支持她。
“情感豐富,懂事,知道感恩。”朱然告訴《民生周刊》記者,由于離開父母早,這群孩子比普通孩子成熟得更早。有一次,在學校舉辦的活動上,一個大孩子講到“最想感謝的人,還有李叔。一年四季都在給我們做飯吃,尤其夏天,高溫把廚房烤得像蒸籠,李叔依然說著沒事……”講到一半時,在場的孩子全哭了,仿佛積壓心底已久的委屈、不安、傷痛,在那一刻,全迸發了出來。“一路走來,他們記得每個人的好。”朱然說。
家人是什么?在朱然心里,家人就是每天在一起吃飯的人。“我和孩子們每天在一起吃飯,我們就是一家人。現在,是我離不開他們了。”
7年過去了,朱然用手中的相機,記錄著發生在這里的一切。
從生活起居到學習、治療、心理輔導,郭小平帶領學校老師,用愛和奉獻,為艾滋病患兒撐起一片藍天。對孩子而言,學校是他們溫暖的家,郭小平就是疼愛自己的“爸爸”。
郭小平對孩子們說得最多的一句話是:希望你們將來兢兢業業學習,干干凈凈做人,快快樂樂工作。
“10年來,通過與外界的接觸,孩子們的笑聲更多了,視野也更開闊了。”圍墻之外,還有人在關注、關心、關愛著他們,這里再也不是一座孤島。
今年59歲的郭小平,已接近退休年齡。談起紅絲帶學校的未來,他對《民生周刊》記者說:“如果有需要,我愿意繼續帶下去,將來孩子們無論走多遠,這里都是他們永遠的家。”
(為保護孩子隱私,文中學生姓名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