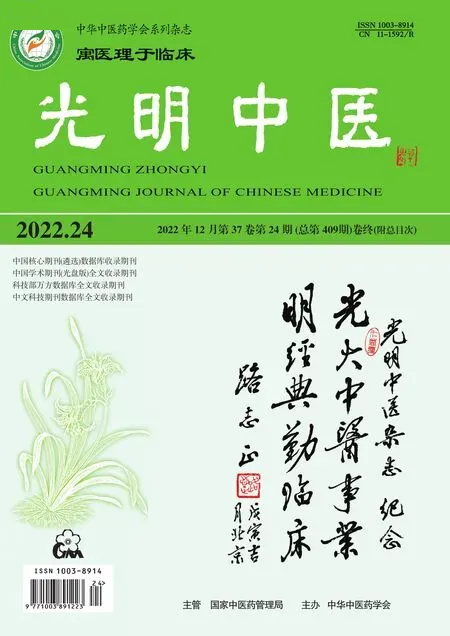張虹亞主任清補相施治療濕熱型脂溢性脫發經驗*
朱明娟 張虹亞
脂溢性脫發(SA)又稱雄激素性禿發(AGA),是一種發生于青春期和青春期后的毛發進行性減少性疾病,其發病機制與遺傳因素、雄激素水平、細胞因子等相關。臨床男性患者主要表現為前額發際后移和 (或) 頭頂部毛發進行性減少和變細;女性患者主要表現為頭頂部毛發進行性減少和變細,少部分表現為彌漫性頭發變稀,發際線正常[1]。此病在中國男性的患病率為21.3%,女性患病率為6.0%[2]。脂溢性脫發屬中醫學“蛀發癬”或“蟲蛀脫發”范疇,為皮膚科常見疾病,其嚴重影響患者的外在形象,給患者帶來嚴重心理負擔,影響患者的生活質量,然脂溢性脫發易診難治。
張虹亞主任系安徽省中醫院皮膚科學術帶頭人,江淮名醫,從事臨床工作30余年,在皮膚病診治方面具有較高的造詣,現將其清補相施運用中藥口服加外洗治療濕熱型脂溢性脫發的用藥經驗作簡要介紹。
1 病因病機
《素問·五運行大論》[3]言:“東方生風,風生木,木生肝”,頭為至陽之位,易受風邪所傷,其毛發脫落為風氣致病之象;《素問·五藏生成》言:“腎之合骨也,其榮發也”,頭發的生長脫落、澤榮枯槁,與肝腎精血的盛衰有密切的關系,精血盛旺則茂盛潤澤,精血虛少則枯槁脫落;《素問·五臟生成》又云:“多食甘,則骨痛而發落”認識到飲食肥甘厚味,易致脾失健運而致頭發油膩和脫落。歸納中醫學對脂溢性脫發病因病機的認識,病因可概括為“氣、血、濕、郁、虛”五字,而病機上可分為虛實兩綱:實者分濕疲郁,或因嗜食肥甘厚味,脾胃濕熱,熏蒸發根,漸成枯槁脫發,或瘀血阻礙頭部血絡,發失所養而掉落;或肝郁氣滯而頭發不榮,虛者則因血虛風燥,或肝腎不足(腎精虧虛),發無所養而枯萎脫落。 楊志波教授認為濕熱為其致病之因,胃腸濕熱向頭面部熏蒸,侵及發根而發病[4]。韓碧英教授認為脂溢性脫發多為本虛標實病,其標多為熱證,本為肝腎不足[5]。榻國維教授提出此病的病機要點為腎中陰陽失衡,腎陰虧虛于下,濕熱毒邪蘊于里,上泛巔頂所致[6]。鐘以澤教授強調脫發的致病因素以血熱與濕熱居多[7]。
導師張虹亞主任結合多年臨床經驗,通過對現代脂溢性脫發患者的臨床研究發現,脂溢性脫發患者大多病程長達數年,部分患者起病年齡尤其年輕,尚有未成年患者就診。結合當代人生活飲食習慣,及臨床表現,四診合參,張虹亞主任認為脂溢性脫發雖多表現為濕熱內蘊,實則病因虛實夾雜,濕熱多為其外在表現,脾虛濕蘊、肝腎不足是該病的重要病因。濕熱證脂溢性脫發患者多因平素飲食不節,偏嗜肥甘厚味,日久傷脾,一則脾虛至水濕內停, 郁而化熱,濕熱內生,熏蒸發根,則至脫發;濕熱日久則生瘀血阻礙頭部血絡;二者脾能散精,脾虛影響一身氣機和水液輸布運行,精微營血無法上達巔頂,導致毛發失榮而干枯脫落。張虹亞主任指出“人臥血歸于肝”,現代生活作息紊亂,日久出現肝郁血虛,血不歸肝的癥狀,發為血之余,肝血虛則不能滋養毛發孔竅,則會出現毛發枯槁、稀疏;肝血虛則傷陰,乙癸同源,水不涵木,則精不充盈;腎藏精,主骨生髓,其華在發,毛發的生長與脫落、潤澤與枯槁與腎精的盛衰密切相關; 肝腎互生、精血同源是為毛發生發的根本,肝腎不足、精血虧虛則至毛發失養。
2 清補相施
張虹亞主任結合脂溢性脫發病機,針對現代患者虛實夾雜特點,治療濕熱型脂溢性脫發以“清、補相施”,清代程鐘齡的《醫學心悟》中指出:“論病之原,則以寒熱虛實表里陰陽八字統之。而論治病之方,則又以汗和下消清溫補八法盡之”。其中“清”法是指通過藥物涼血、解毒、瀉火等作用,解除病證熱邪的治法。“清”者,是以“清解”之品祛其濕熱之邪,以“清行”之品祛瘀生新。“補”者,補其肝脾腎三臟,若脾健則運化有常,則濕熱無以內蘊,若肝腎充固,無本虛之因,則發無所脫;故“補”以“補肝”“健脾”“益腎”。自擬脂溢性脫發經驗方,臨床隨證加減療效顯著。藥物組成:茵陳20 g,石菖蒲10 g,薏苡仁30 g, 丹參15 g,當歸10 g,女貞子15 g,墨旱蓮15 g,五味子15 g,側柏葉10 g,羌活10 g。
方中茵陳味苦、辛,性微寒,苦降寒清,善清利脾胃濕熱;石菖蒲味辛,芳香化濕,醒脾開胃,尤宜用于濕阻中焦證,二者共為君藥;薏苡仁健脾補中,滲濕利水,使健脾與利濕同治,助脾胃運化、驅除濕邪,為臣藥。又因久病入絡,濕熱蘊結,致氣血運行不暢,日久生瘀,故清熱祛濕健脾的同時又適當佐以丹參、當歸等“清行”之品,丹參味苦、微寒,善活血祛瘀生新,以助濕熱清,瘀血除;“發為血之余”,當歸補血活血,既能助瘀血消退,亦能補血生發。女貞子苦甘性涼,善補肝腎之陰,藥性緩和,尤能烏須發,與墨旱蓮配伍,即二至丸,二者歸肝腎經,平補肝腎,使發有所養,促新發再生。五味子酸甘斂陰,可滋腎陰而澀精;側柏葉味苦、澀,性寒,歸肺、肝、脾經,有養肝涼血、生發烏發之功效。上方中所選補益藥均為清補之品,以防滋膩。另外張虹亞主任認為風邪善達頭部,為百病之長,虛受邪風,則發落頭禿,且《諸病源候論》曰“人有風邪在頭,有偏虛處,則發脫落”,故加以羌活祛風勝濕。上方諸藥合用,共奏清熱祛濕,補肝益腎,健脾生發之效。
此外,張虹亞主任注重臨證加減,肝郁則血瘀,故補益肝腎同時,若伴有心煩易怒,則加柴胡、香附等疏肝理氣;若氣虛乏力,舌淡苔薄則加白術、茯苓、黃芪、黨參等健脾益氣;若失眠多夢、夜尿多,舌淡苔白,加酸棗仁、柏子仁等補腎安神;若患者伴有面部痤瘡,皮膚油膩、毛孔粗大,舌紅苔黃膩,加黃芩、赤芍、枇杷葉、生山楂等清熱解毒,化濁祛脂。
3 現代藥理研究
脂溢性脫發的現代研究表明其發病機制與雄激素及5α-還原酶水平相關[8],研究顯示II型5α-還原酶在 AGA 真皮乳頭細胞中的表達高于其他部位的表達;二氫睪酮是睪酮的 5α-還原代謝產物,二氫睪酮刺激毛乳頭細胞中的轉化生長因子-β(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TGF-β) ,抑制角質形成細胞生長并誘導細胞凋亡,最終引起脫發[9];同時毛乳頭分泌各種細胞因子調控毛囊的自我更新,以及維持毛發生長與脫落的平衡[10],此外頭發中微量元素[11]、血液流變學[12]等也可加快脂溢性脫發的發生與發展。體外研究表明,女貞子醇提物可抑制5α-還原酶活性,同時促進毛囊對肝細胞生長因子的表達,從而促進毛囊的生長[13]。丹參的主要成分丹參酮,可以抑制皮脂腺細胞增殖、脂質合成或調控雄激素受體 mRNA 的表達,達到抗雄性激素及抗脂質的效果[14]。五味子可以通過調節 TGF-β的表達來促進毛發生長[15]。當歸提取物具有擴張皮膚毛細血管,加快血液循環,豐富微量元素的作用,能促進毛囊進入生長期,同樣可以增加毛囊數量[16]。側柏葉中含有雪松醇可激活毛母細胞和促進血液循環,使毛發生長能力衰退的毛囊復活[17]。
4 結合外治
張虹亞主任治療脂溢性脫發善內外合治,內服同時配合中藥外洗,中藥外洗可直接作用于脫發皮損處,使藥物直達病所,自擬脂溢性脫發外洗方,方藥組成:透骨草30 g,豬牙皂30 g,白鮮皮30 g,側柏葉30 g,黃柏30 g。方中透骨草味甘、辛,性溫,具有祛風除濕,解毒止癢功效,研究表明透骨草、豬牙皂外用均有抗炎、殺菌的功效[18,19];黃柏清熱燥濕,殺蟲解毒,具有抑菌、促進血管新生,改善局部微循環的作用[20];側柏葉性寒涼,可涼血泄熱《本草通玄》記載側柏葉能“除風冷濕癢,烏鬢黑發”;白鮮皮性寒,清熱燥濕、止癢,現代藥理學研究表明白鮮皮及其部分活性成分具有明顯的抗炎止癢抑菌作用[21]。
5 醫案舉隅
林某,女,26 歲,2021年4月8日初診。主訴: 脫發2年余,加重1個月余;查體: 頭發油膩,發質細軟,頭頂兩側發量明顯減少,伴頭皮瘙癢、頭屑增多,舌紅,苔黃膩,脈滑。拔法試驗7~10根。伴隨癥狀: 面部油膩,輕度痤瘡,性情煩躁、易怒,月經正常,平素喜食辛辣,納寐尚可,大便略溏,小便正常。中醫診斷: 蟲蛀脫發,濕熱證; 西醫診斷: 脂溢性脫發。以清熱祛濕,補肝益腎,健脾生發為基本治則,予以中藥處方:茵陳20 g,石菖蒲10 g,薏苡仁30 g,丹參10 g,當歸10 g,女貞子15 g,墨旱蓮15 g,五味子10 g,側柏葉10 g,羌活10 g,黃芩10 g,赤芍10 g,柴胡10 g。共 7 劑,日1劑,水煎2遍,每次煎取200 ml,早晚溫服; 并配合中藥外洗方:透骨草30 g,豬牙皂30 g,白鮮皮30 g,側柏葉30 g,黃柏30 g,艾葉30 g。共3劑,水煎外用,每日1次,每次1000 ml左右,浸洗10~15 min,用后可清水沖洗。用藥期間注意事項:①囑其清淡飲食,忌食油膩刺激性食物;②規律作息,起居有常;③調節情緒,保持心情舒暢;④減少使用清潔用品洗頭次數。
2021年4月15日二診:頭皮瘙癢好轉,頭部油脂溢出較前減輕,納寐可,大便溏較前緩解,舌質偏紅,苔黃膩,脈滑,訴服藥后食欲不振,原方加陳皮10 g,茯苓10 g。14 劑,煎服法同前。
4月29日三診:患者面部痤瘡未見新發,頭部油脂溢出較前明顯減輕,自覺洗頭時脫發較前明顯減少,食欲尚可,二便正常,舌淡紅,苔黃,脈滑。上方減黃芩、赤芍。14 劑,煎服法同前。外洗間隔時間延長至每3 d一次。
5月13日四診:諸癥較前好轉,拔法試驗(-),脫發處可見新生毛發,舌淡紅,苔薄黃,脈滑。原方繼服2周,服法同前,外洗方同前。
1個月后隨訪,頭部基本無油膩感,無瘙癢、脫屑,脫發處可見新生毛發。3個月后隨訪,毛發未見脫落,頭部油脂分泌正常,無瘙癢、脫屑,皮損處有新發長出,發色、粗細如同常發。
按:患者平素嗜食辛辣油膩食物,損傷脾胃,脾運不健,水濕停滯,郁久化熱,濕熱熏蒸,上泛巔頂,結合舌苔脈象,辨證為濕熱證。患者頭發油膩,發質細軟,肝腎不足、精血虧虛則無以滋養毛發,遂治療原則為清熱祛濕,健脾補肝益腎。患者平素情緒易怒,面部患有痤瘡,在基礎方上辨證加柴胡疏肝理氣,黃芩味苦性寒,有清熱燥濕解毒之效,為“清解”之品,赤芍味苦性微寒,清熱涼血散瘀,為“清行”之品,二者合用,既能清熱祛濕,亦可治療兼癥,消痤瘡。二診患者服藥后食欲不振,脾虛失運,加茯苓、陳皮理氣健脾。三診面部痤瘡未見新發,遂減黃芩、赤芍。
6 小結
張虹亞主任認為濕熱型脂溢性脫發除清熱祛濕外,考慮到肝腎互生、精血同源是為毛發生發的根本,脾虛精微營血無法上達巔頂,則毛發失榮而干枯脫落,故治療時切不可忽略肝脾腎三臟,應“清、補相施”。同時應注意內、外治結合,臨床應根據不同兼癥,辨證論治,隨證加減。脂溢性脫發病程較長,服藥周期較長,新發再生緩慢,應注重患者情緒疏導,及告知患者日常注意事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