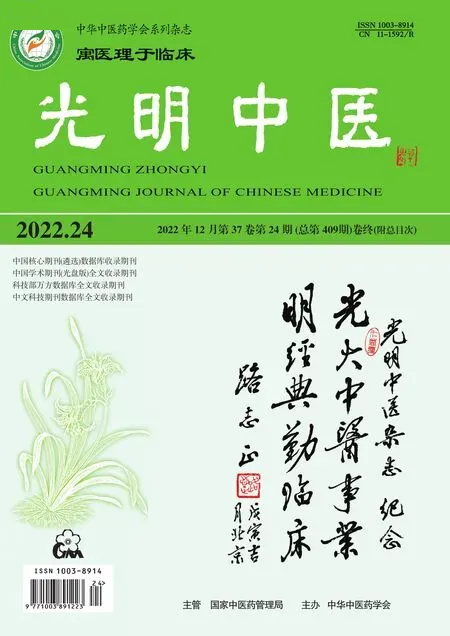朱世楷教授治療腸易激綜合征臨床經驗探析*
李 維
朱世楷教授,為第五批全國名老中醫藥專家學術經驗繼承指導老師,全國名老中醫,江蘇省名老中醫,曾任無錫市中醫院院長、無錫市中西醫結合學會副理事長,江蘇省中西醫結合學會理事,消化病專業委員會副主任,《無錫醫學雜志》編委等職。年輕時師從全國著名中醫肝病專家鄒良材教授,盡得其真傳,著有《鄒良材肝病診療經驗》一書。朱世楷教授從事消化科臨床工作50余載,臨床涉獵疾病甚廣,尤擅長治療慢性胃病、肝病、腸功能紊亂等疾病。筆者有幸能拜師朱老門下,長期抄方學習,感觸頗多,茲將朱老治療腸易激綜合征的經驗總結剖析,以饗同道。
現代醫學認為,腸易激綜合征屬于一類功能性疾病,以腹痛、腹部不適伴排便習慣和(或)大便性狀改變為主要癥狀,可伴有精神抑郁或焦慮、慢性疲勞綜合征等全身癥狀,其發病機制尚未完全明確,多考慮與遺傳、飲食習慣、內臟高敏性、腸道菌群紊亂、免疫失調、精神心理異常等因素密切相關[1]。治療上,強調飲食管理,避免進食高敏食物或食物剔除療法;針對腹痛、腹瀉、便秘對癥治療;使用抗抑郁、抗焦慮藥物[2]。但因需長期飲食控制、藥物治療,難以根治疾病,給患者身心帶來極大負擔,更有甚者加重病情。
中醫典籍上并沒有腸易激綜合征之病名,依據臨床癥狀不同,多將其歸屬于“腹痛”“便秘”“泄瀉”等范疇,依據《腸易激綜合征中醫診療專家共識意見(2017)》[3]將此病分為腹瀉型、便秘型、混合型和不定型,以腹瀉型多見,并認為先天稟賦不足或后天脾胃失養、情志失調、飲食不節、感觸外邪等因素為此病發病之因,脾虛肝郁為主要病機,所有變證均由脾虛、肝郁演變而來,并將腹瀉型分為肝郁脾虛證、脾虛濕盛證、脾腎陽虛證、脾胃濕熱證、寒熱錯雜證5個證型,將便秘型分為肝郁氣滯證、胃腸積熱證、陰虛腸燥證、脾腎陽虛證、肺脾氣虛證5個證型,治療上強調以益氣健脾、疏肝理氣為主。朱世楷教授認為腸易激綜合征本身屬于西醫病癥,臨床缺乏診斷金標準,以排他性診斷為要領,因此提出急性期以現代醫學診治為先,可合用健脾化濕、行氣解郁之法;慢性期以疏肝健脾為主,兼顧益腎溫陽、利濕化濁、行氣活血等治法,遷延期當以補益脾腎為主,化痰、活血為輔,充分利用西醫在此病早期診斷上的優勢及中醫藥在慢性病治療上的特色。認為此病發生的關鍵病機在于脾虛,或土不疏木,脾虛肝旺;或脾失健運,濕濁內生;或脾虛日久及腎,脾腎兩虛,治療上強調分期與辨證相結合,注重培補脾胃,急性期以健運脾胃為主,慢性期運脾、補脾兼施,遷延期以培補脾胃為主,具體經驗探析如下。
1 重視調補脾胃
《黃帝內經》有云:“脾胃者,倉廩之官,五味出焉”[4],脾主運化,胃主受納,二者互為表里,有腐化水谷,化生氣血精微,濡養五臟六腑之能,是為后天之本;如脾失健運,胃納不降,則百病皆生,正如《脾胃論》[5]中所言:“脾胃之氣既傷,而元氣亦不能充,而諸病之所由生也”,故治病當明辨調補脾胃之要,實為“百病生,調理中州,其首務也”[6]。朱老認為脾胃位于中焦,為水谷運化之樞紐,凡出入有異,皆因于此也,故在疾病治療中強調調補脾胃,推崇“胃氣無損,諸可無慮”[7]的治病原則。在具體應用中,朱老將其分為“虛則補之”“脾健不在補貴在運”[8]2個大方向。對于急性期患者,多因脾運失常,水谷難化,或積滯難行,或聚而成泄,《素問·痹論》有云:“夫飲食失節,寒溫不適,脾胃乃傷”,病因源于長期飲食不當,寒熱不忌,脾胃氣機凝滯,運化失常,治療當以理氣、化濕、消食、溫陽等法健脾助運,如選用陳皮、蒼術、豆蔻、砂仁、木香、枳實、山楂等藥,使得脾胃氣機調暢,脾運得健,方能無虞。對于慢性期,因氣滯濕阻難除,正氣日漸耗傷,治療時純用補益抑或單用芳香燥濕,均難獲全效,當補運兼施。而對于遷延期,因病程日久,脾氣已虧,水谷難化,元氣難以為繼,治療需大補元氣,脾腎同補,以后天養先天,可用白術、黨參、山藥、黃芪等益氣健脾之品。
2 注重肝脾和調
肝脾同處中焦,生理功能上相互依賴,《黃帝內經》云:“肝主藏血”,有疏泄氣機之能,“脾主統血”,司運化之職;脾胃運化水谷,化生精微,濡養五臟六腑,依賴于肝氣調暢、氣機疏泄如常,故謂“土得木而達”;反之,肝木賴脾土以養,肝體陰而用陽,肝體賴陰血之濡養,方能發揮疏泄氣血、調暢氣機之功能,而脾主運化,有化生氣血之能,故能養肝。朱老認為肝木、脾土在五行上相克,在功能上相輔相成,臨床用藥時,如不知調和二臟,純用補益,抑或疏泄太過,惟有徒傷氣血、壅滯氣機一途。在急性期,多有氣機郁滯,肝失疏泄之病機,雖脾運如常,如肝木橫逆克土,必有痛瀉也,正如《景岳全書·泄瀉》[7]云:“凡遇怒氣便作泄瀉者……蓋以肝木克土,脾氣受傷使然”,其治療以疏泄肝氣為主,兼顧健脾養陰;再如慢性期,脾胃已傷,氣血化生不足,肝體失養,氣機疏泄失常,脾土難以承受肝木克制,脾土必益衰,是為“土敗木賊”也,其治當健脾柔肝,兼理氣疏肝,是故疏肝不忘補脾,運脾不忘養肝,唯有肝脾調和,方能中焦氣機升降無虞,五臟六腑安和。
3 不忘痰濕瘀阻
部分腸易激綜合征患者病程較長,病情遷延難愈,中西醫藥物弗效,朱老將其歸為遷延期來論治,推薦在補益脾腎之余,合用“化痰、通絡”之法,認為久病不愈必有瘀血阻絡,如《臨證指南醫案》[9]所言:“初病在經,久痛入絡”,氣為血之帥,血為氣之母,營血、精液皆賴氣以行,其脾氣虧虛者,氣血化生不足,溫煦推動無力,日久必氣血凝滯不暢;肝氣郁結者,氣機升降失調,氣不行血,血停而瘀血內生也,是故“凡氣既久阻,血亦應病”,此時治療需摻入活血化瘀之品,如加用丹參、紅花、五靈脂、莪術、桃仁、延胡索、川芎等;對于病證復雜,焦慮明顯者,朱老多從化痰通竅入手,尊崇“怪病多由痰作祟”觀點,脾為生痰之源,脾虛日久,痰濕乃成,脾虛清氣不升,痰濁不降,隨氣升降出入,無處不到,故有性格多變,難以痊愈之證,臨床多應用燥濕化痰、清熱化痰、散結消癰等大法,常用藥物如法半夏、浙貝、皂角、黃連、黃芩、黃柏、萊菔子等。
4 臨床驗案
李某某,男,38歲。2020年7月24初診。主因“便溏間作數年”診治,就診前曾求治多位中醫、西醫專家,因難以獲得持續緩解,此次求治朱老,癥見:大便不成形,夾有黏液,日行3~4次,腸鳴,伴腹部不適,無腹痛,怕冷,胃納尚可,夜寐安。腹部CT未見明顯異常。腸鏡:慢性結腸炎,胃鏡:淺表性胃炎,外院診斷為腸易激綜合征,舌淡紅苔微膩,脈細,朱老診斷:泄瀉病-脾陽不足證,擬方健脾益腸。處方:炒黨參10 g,炒白術10 g,云茯苓15 g,廣陳皮6 g,炮姜5 g,川黃連3 g,黃柏10 g,辣蓼30 g,煨石榴皮15 g,煨訶子10 g,補骨脂10 g,炮附片6 g,炙甘草5 g,廣木香5 g。7劑,水煎服,每日1劑,每日2次。2020年7月31二診:患者腹瀉緩解,大便日行1次,基本成型,胃納增加,夜寐安,精神改善,舌淡紅苔薄,脈細,繼予前方鞏固治療。8月7日三診:訴癥狀持續緩解,食納可,前方去木香,繼進7劑,煎服法同前。3個月后電話隨訪訴癥狀未再反復。
按:患者中青年男性,腹瀉便溏數年,不論先天不足,抑或后天飲食失宜損傷脾胃,其脾虛已成,且因反復腹瀉,脾陽日衰,有脾虛及腎之趨勢,病程在慢性期,治療在辨證論治的基礎上突出補益脾胃,方以四君子湯益氣健脾,培補脾虛不足,加炮附片、補骨脂、炮姜溫陽益腎,一則溫補脾胃,補脾陽之不足,益火之源以消陰翳;二則溫腎益氣,《金匱要略》[10]有言:“見肝之病,知肝傳脾,當先實脾”。此見脾病益甚,為防脾病及腎,當先溫腎;加黃連、黃柏清熱燥濕,堅陰止瀉,既可防瀉痢日久傷陰,又可與炮附片、炮姜合用寒熱同調,辛開苦降,恢復中焦氣機升降;另有辣蓼、石榴皮、訶子收斂止瀉,此三藥為收斂固澀之品,臨床認為大凡酸澀收斂之劑或有斂邪閉門留寇之嫌,多用于純虛之證,朱老總結多年經驗發現,此三藥尚有苦泄降氣之功,可解氣機之郁滯,故無論虛證或虛實夾雜均可用之,是故諸藥合用,則脾陽得溫,脾運得健,瀉痢得止。
5 結語
腸易激綜合征為消化內科常見疾病,其發病率逐年升高與飲食習慣改變、社會生活節奏加快密切相關[11],在未來仍屬于常見病、多發病。隨著病患人數增多,人們對于治療需求的增加,社會醫療負擔的加重,中醫藥的優勢愈發顯著,其有效性、低廉性、低不良反應率更符合社會和人民的需求。朱老中西醫診療經驗豐富,因此能率先嘗試中西醫結合,分期聯合辨證論治的治法,認為中西醫各有優勢,臨床時當以患者為中心,充分利用一切資源減少患者的病痛,尤其是在此類慢性功能性疾病診治中,需要優先排查有無惡性疾病時,不能自詡醫術高明而讓患者錯失手術機會。強調急性期當以明確病因為先,治療上以健脾化濕行氣為主,慢性期治療當“扶正、祛邪”并行,遷延期治療以培補脾腎為主,兼以化痰、行氣、活血等。總之,在跟隨朱老抄方學習中,不僅體會到了朱老精湛的醫術,更感受到那高尚的醫德醫風,學習體會很多,卻難以完全闡述而出,難免有遺漏之處,可待往日學習交流。最后感謝全國名中醫傳承工作室的推廣,讓年輕中醫師有機會跟隨中醫大家學習、傳承,借以分享腸易激綜合征學習經驗,望有更多中醫從業者因傳承獲益、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