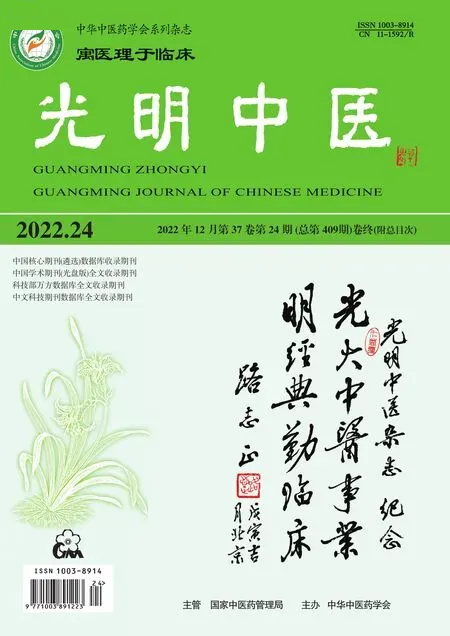烏梅丸方證探析
陳榮武 葉文彬 王雪萍
《傷寒論》第338條有云:“傷寒,脈微而厥,至七八日膚冷,其人躁,無暫安時者,此為臟厥,非蛔厥也;蛔厥者,其人當吐蛔,令病者靜,而復時煩者,此為臟寒,蛔上入其膈,故煩,須臾復止,得食而嘔吐,又煩者,蛔聞食臭出,其人常自吐蛔,蛔厥者,烏梅丸主之,又主久利”[1]。自從成無己在《傷寒論》第338條把烏梅丸做為治蛔厥、久痢的主方,后世對烏梅丸的臨床多局限于此,雖然柯琴[2]、章虛谷以及《醫宗金鑒》都強調烏梅丸為厥陰證治之主方,特別是柯琴提出“仲景此方,本為厥陰諸證立法,叔和編于吐蛔條下,令人不知有厥陰證治之主方,觀其用藥與諸證符合,豈止吐蛔一證耶”,但由于后世醫家對《傷寒論》厥陰病提綱即經文第326條:“厥陰之為病,消渴,氣上撞心,心中疼熱,饑而不欲食,食則吐蛔,下之利不止”[1]。有關病位描述前后不一致,導致臨床應用還存在諸多困惑,如1985年版《傷寒論講義》對“氣上撞心”中心的部位注解是泛指心胸的部位,在隨后的“心中疼熱”又說心指胃脘部,明顯的前后矛盾。馮世論教授在《經方傳真》中對烏梅丸的病機闡述為虛寒為本,虛熱為標的上熱下寒證,觀烏梅丸中黃連的用量達16兩,僅次于烏梅的用量,大大超過附片等溫熱藥的用量,顯然不支持馮氏等論斷[3]。黃煌在《黃煌經方使用手冊》[4]里闡述了烏梅丸適用于厥冷、腹部絞痛、煩躁、嘔吐腹瀉為特征的寒熱錯雜的病證,并提出有腹痛型、腹瀉型、反流型、煩熱型等不同臨床表現,拓展了烏梅丸的用藥思路,但是烏梅丸方證要點目前還不夠明確,四診綜合信息不突出。本文試以《傷寒論》第326條厥陰病提綱為核心,通過臨床對烏梅丸方證的實踐,進一步明確烏梅丸的方證特點和使用要訣。烏梅丸方證實踐具體如下。
1 從腰痛案辨烏梅丸病位拓展
陳某某,女,64歲。以反復腰痛5年,再發伴雙下肢冷1個月為主訴,2021年5月28日首診。經口服止痛、營養神經等藥物、理療等治療后癥狀改善不明顯。6年前有膽囊切除術史。刻診:面暗紅,雙側腰痛,勞作時明顯,雙膝酸軟,雙下肢冷,遇風尤甚,時值夏季炎熱氣候仍需穿厚褲子,不能臥涼席、吹風扇及空調,口干口苦,喜溫飲,寐差,大便溏,小便不黃,舌淡暗,苔薄黃,脈沉弦細尺弱。診斷:腰痛;辨證:上熱下寒證;以清上溫下為法,擬烏梅丸治療。處方:細辛 6 g,干姜10 g,桂枝10 g,附片10 g,黃連6 g,黃柏6 g,黨參15 g,當歸10 g,烏梅16 g,蜀椒5 g,白芍15 g。7劑,每日1劑,水煎分早晚2次溫服。2021年6月5日二診:證候改善,腰痛減半,可穿薄秋褲,吹風無明顯不適,守方同前續服7劑。6月12日三診:腰痛基本緩解,雙下肢怕冷明顯改善,可穿短褲,吹風無明顯不適,仍不能吹空調。前方續服2周,諸癥皆平,冬季未復發。
按語:腰痛關于肝腎的病位辨析:腰痛為常見病,須分病在肝與病在腎之區別,中間屬腎,兩側屬肝,不可不察,蓋兩側豎直肌筋膜發達,為肝主筋之分野,強力勞作、久坐傷骨,筋骨相連,皆可傷及筋骨,尤以傷筋多見,故腰痛在兩側需求之于肝。
厥陰經病寒熱、虛實探求:求之肝者,需分虛實兩端,以制補瀉之策,患者面暗、雙膝酸軟,大便溏瀉,可知下元不足,少陰厥陰并病,脈弦尺弱為疏泄不利、腎精虧虛的復合表現,口干口苦、寐差為火郁胸腑邪擾心神的表現,故診為上熱下寒,肝血不足。厥陰病提綱之心下再認識:病位是構成六經辨證重要元素,從本案可知烏梅丸的病位不局限在經文描述的心或心下位置,與厥陰經相關的臟腑、經絡、氣血病變都可以出現烏梅丸證。
烏梅丸+當歸四逆合方芻議:取烏梅丸合當歸四逆湯加減以溫補下焦元氣、清中上焦心膽之火、溫通血脈,清不傷正,溫不化熱,以達陰陽并調之功,故腰痛、下肢冷諸癥得愈。
2 從糖尿病酮癥酸中毒案辨消渴
劉某,男,72歲。以口干納差、消瘦乏力1周為主訴,2021年7月16日收治入院。隨機血糖 26.3 mmol/L,血β-羥丁酸陽性,pH 7.29。刻診:精神萎靡,面色暗紅,呼吸稍深快,口干多飲,心中煩,納谷不馨,喜食西瓜,大便干,小便頻、色白,舌質暗紅舌苔黃厚濁,脈寸關弦滑尺弱。診斷:消渴;辨證:上熱下寒證;以清上溫下為法;擬烏梅丸治療。處方:烏梅16 g,細辛5 g,干姜10 g,桂枝10 g,附片10 g,黃連10 g,黃柏6 g,黨參15 g,當歸10 g,蜀椒5 g。3劑,每日1劑,水煎分早晚2次溫服。常規使用胰島素降糖治療。服用3劑后口干明顯緩解,進食量增加至正常量的2/3,β-羥丁酸轉陰性,pH 7.38。效不更方,于2021年7月19日,守方再進7劑,口干基本緩解,進食量正常,大便軟、通暢,血糖平穩,辦理出院。
按語:從厥陰病辨消渴病機:厥陰風木與少陽相火互為表里,肝為風木之臟,以腎水為根,內寄相火,主疏泄,以升發為順,抑郁為逆。風木疏泄失常,相火失其蟄藏,風火合邪,津血耗傷,消渴之病乃成[5]。
辨識厥陰病之消渴證:從本案患者不能進食五谷卻喜食西瓜,通過烏梅丸治療后癥狀緩解,可知《傷寒論》提綱所提“消渴”不一定是飲食水谷增加,“饑而不欲食”不一定是什么都吃不下,可能存在飲食偏嗜,饑不欲食與利不止不一定同時存在,不一定要存在下利的表現,本患者表現為大便干;患者精神萎靡應辨清在少陰、厥陰之別,烏梅丸的根在少陰,相火不布,故有精神萎靡證候,易與“少陰之為病,但欲寐”相混淆,應再觀其舌脈象。
烏梅丸方證脈象特點:寸關弦尺弱。治法:經“清上溫下”之法治療后,陽氣復、津液充、邪熱祛,則諸證自除。
3 從胃食管反流病焦慮癥案辨心中疼熱
逢某某,女,67歲。以反復反酸、胸背痛5年,再發1個月為主訴,于2021年11月18日首診。在外院經抑酸護胃等治療后癥狀仍反復,卵巢惡性腫瘤術后5年。刻診:面色暗紅,善太息,一問一答,語速不快,反酸,上腹部、胸骨后燒灼感,口干口苦,喜溫飲,早飽,陣發性胸悶痛,痛連肩胛及背部,右側偏頭痛,夜間尤甚,難寐易醒,易疲勞,頭面部易汗出,大便溏,舌質暗紅舌苔黃厚,脈弦,兩脅內側按之有抵抗感。胃鏡檢查提示食管炎(B級),心電圖、冠脈CTA未見異常,肺部低劑量CT提示雙肺微小結節,診斷:吐酸病;辨證:膽熱脾寒證,以“和解少陽、溫脾散寒”為法,擬柴胡桂枝干姜湯加減治療,處方:柴胡16 g,桂枝10 g,干姜 10 g,牡蠣20 g,黃芩10 g,炙甘草6 g,天花粉15 g。7劑,每日1劑,水煎分早晚2次溫服。2021年11月25日二診:面色暗紅,口干口苦、右側頭痛稍減,減不足言,反酸、上腹部、胸骨后燒灼感、早飽、陣發性胸悶痛諸癥仍在,難寐易醒,易疲勞,頭面部易汗出,雙足底怕涼,大便溏,舌質暗紅舌苔黃厚,脈寸關弦滑尺弱,兩脅內側按之有抵抗感。癥狀無改善,調整治療方案,證屬:上熱下寒證,以清上溫下為法,擬烏梅丸治療,處方:細辛6 g,干姜10 g,桂枝10 g,附片10 g,黃連6 g,黃柏6 g,黨參15 g,當歸10 g,烏梅16 g,蜀椒 5 g。7劑,每日1劑,水煎分早晚2次溫服。12月2日三診:諸癥減輕過半,大便成形,苔薄黃微膩,療效佳,續方同前7劑。12月9日四診:反酸、上腹痛、胸痛、頭痛、雙足底怕涼皆平,進食量正常,每晚睡眠時間7 h,進食時頭面部稍有汗出,原方再服7劑,每2日服一劑,每劑水煎分早晚2次溫服,停藥后至今未在復發。
按語:《靈樞·經脈》曰:“肝足厥陰之脈……抵小腹,挾胃,屬肝,絡膽”[6]。《素問·水熱穴論》:“腎者,胃之關也,關門不利,故聚水而從其類也”[7]。肝腎同屬下焦,乙癸同源,下焦虛寒,胃失溫煦,故見胃脘痛;賁門失約,相火流竄,下焦寒飲攜相火邪熱上逆,故見反酸、上腹灼熱、胸痛,甚則痛連肩胛及背部;夜間疼痛、舌質暗紅符合病入陰分、血分的特點,烏梅丸適合治療血分的痛證。該患者焦慮合并胃食管反流病,疼痛從胃脘、心胸直到背部,范圍廣泛,可知厥陰病提綱所提“心中疼熱”“氣上撞心”可以從胃脘到心胸的廣泛區域,與肝經經絡分布有關。
烏梅丸方證與柴胡桂枝干姜湯方證辨識:①病位:烏梅丸上面的病位主要在心胸,柴胡桂枝干姜湯上面的病位主要在兩脅。②病性:烏梅丸主要是上熱及下寒,與太陰證相關,以寒熱的勝復為主,寒熱同時存在,此消彼長;柴胡桂枝干姜湯主要以寒熱往來為主,寒熱交替發生。③厥陰、少陽腹診的區別:烏梅丸偏在下,柴胡桂枝干姜湯偏在上。④烏梅丸的心中痛熱的表現常常不易透露(有苦說不出);柴胡桂枝干姜湯的情志表現常為郁郁微煩,常可表露于外(就診時主訴偏多)。⑤大便溏的辨識:烏梅丸方證上有心火,下移小腸,再傳大腸;柴胡桂枝干姜湯:太陰少陽合并,陽為結于上,陰不化于下,故大便溏。⑥本患者首診考慮卵巢癌術后焦慮軀體化癥狀使用柴胡桂枝干姜湯疼痛不能緩解,使用烏梅丸后癥狀緩解,可知柴胡桂枝干姜湯不使用當歸、烏梅等血分藥物,柴胡桂枝干姜湯是少陽太陰合病用方,偏向氣分,不是厥陰病方藥,厥陰以肝為基,肝主藏血,體陰而用陽,故厥陰經以血為體,以氣為用,其病亦不離此二端。
4 從便秘案辨下之利不止
胡某某,男,66歲。以反復便秘、下腹脹滿10年為主訴,于2022年3月10日首診。曾多次在外院就診,服用麻仁丸、牛黃解毒片等藥物,效果不佳。刻診:形體壯實,面色偏暗,胸悶心悸,咽干,大便先干后溏,3~4日一解,色偏暗,排便不暢,每次排便需半小時,苦不堪言,肛門瘙癢、墜脹感,下腹部脹滿感,肢端怕冷,冬季尤甚,舌暗紅,苔黃根厚,脈寸關沉弦尺弱,兩脅內側按之有抵抗感。排便造影提示:直腸黏膜脫垂I度;MRI提示:盆底肌肉痙攣綜合征。診斷:便秘;辨證:厥陰寒熱錯雜證。處以烏梅丸方:細辛5 g,干姜10 g,桂枝10 g,附片10 g,黃連10 g,黃柏6 g,黨參 15 g,當歸10 g,烏梅10 g,甘草6 g,野麻草15 g。7劑,每日1劑,水煎分早晚2次溫服。2022年3月17日二診:患者服藥后大便每日1~2次,軟成形,色黃,排便較前明顯順暢,每次約10 min,肛門瘙癢、下腹脹滿明顯改善,肢端轉溫,胸悶大減,心悸偶發。效不更方,守方同前,續服7劑。3月22日三診:大便每日一解,量色正常,排便順暢,每次5 min,余癥皆除,需方同前7劑,服法同前。電話隨訪至今未再復發。
按語:便秘主要與太陰、陽明轉輸失職有關,亦與少陰、厥陰精氣失調相關。命門藏真火為相火之根,肝行相火則疏瀉有權,升降有度,大腸傳導有權;腎藏先天之精,納后天之精為肝臟陰血之基,肝陰得養,陽用陰輔,陰血則濡潤大腸以行舟。
該患者大便先干后稀,排便不暢伴有肛門墜脹感、肛門瘙癢、下腹脹痛、舌苔厚濁,似乎為濕熱阻滯氣機之證,但同時有面色暗晦無澤、肢端怕冷,冬天尤甚,尺脈沉弱等真陽不足的表現,又有胸悶、心悸、苔黃等上焦陽氣郁結擾心的癥狀,可知其便秘在于真陽不足,相火不明,疏瀉不利。
清上溫下、調氣行津是便秘重要治法:便秘的治療常以通腑為主,結合不同的病機,或扶正或驅邪;通腑的關鍵在于調氣行津以行舟通便;肝陽不足,疏瀉失職,陰津敷布失序,則大便溏結不調;厥陰肝經繞陰器,循魄門,肝陽不足,肝氣不舒,氣機阻滯,排便不暢,甚至大便不通;故便秘之辨證,須分清寒秘、熱秘或寒熱錯雜之便秘。
烏梅丸使用苦寒藥與下之利不止是否矛盾?厥陰病提綱所提“下之利不止”是一種治療禁忌預告,該患者表現為排便困難,大便先干后溏,使用含有黃連、黃柏等苦寒藥物的烏梅丸后癥狀反而改善,提示厥陰病提綱所提“下之利不止”應該是指禁用攻下藥,并非禁用苦寒藥。
5 從失眠案辨氣上撞心
曾某,男,42歲。以“失眠3年”為主訴于2022年4月19日首診。既往服用中西藥效果均不佳。刻診:頭面部多汗,面部暗紅,難寐易醒、早醒,尤其凌晨 1:00—3:00 易醒,每晚睡眠時間約4 h,晝日疲乏感,餐后胃脘脹悶,夜間打鼾,大便溏稀、不黏,小便不黃,舌暗紅,苔黃厚,脈寸關弦滑尺弱。診斷:失眠;證屬:厥陰寒熱錯雜證,上焦有熱、中下焦有寒。處方:烏梅丸:細辛6 g,干姜10 g,肉桂10 g,附片10 g,黃連 10 g,黃柏6 g,黨參15 g,當歸6 g,烏梅16 g,木香6 g,芡實15 g。7劑,每日1劑,水煎分早晚2次溫服。2022年4月26日二診:患者服用烏梅丸方后服藥后睡眠明顯改善,每晚可睡8 h,夜間無驚醒,頭面部汗出大減,僅以額部少許汗出,大便正常,口不干苦,小便調。守方同前,續服7劑,半月后患者陪同家屬來診言患者二診服藥后諸證皆除,停藥后癥狀未復發。
按語:氣上撞心與失眠:陽化氣,陰成形,陰陽互生,如環無端,陰陽出入有序則睡眠如常,當今社會工作、生活壓力大,失眠的發生率高,緣于過勞耗傷腎精,腎精虧耗,命門火衰而相火不明,肝陽失用疏瀉失職,木不疏土而心包之火不能布散而擾心,陽難入陰而失眠;厥陰病提綱之“氣上撞心”可以產生“心中疼熱”癥狀,也可以產生邪火擾心的失眠癥狀。
從子午流注看厥陰病失眠:據子午流注,肝經經氣旺于丑時,故部分患者于凌晨1:00—3:00 或后半夜易醒;陰精不足,肝體失養,肝不藏魄而多夢。肝陽不足,木不疏土而瞋脹,故餐后胃脘脹滿。陽加于陰謂之汗,火曰炎上,故見頭面部汗出明顯;腎之陽氣以三焦為通路上溫脾陽,腎虛則脾失溫養,中焦脾陽不足,則見便溏,大便不黏滯;尺脈侯腎,故見尺脈弱;面色蒼暗帶紅為厥陰肝陽不足,陰霾凝滯,同時上焦郁火不散之象。
烏梅丸與梔子豉湯之心煩辨識:烏梅丸證之心煩是一種陰煩,可以表現為失眠,就診時被動應答為特點的煩,與梔子豆豉湯就診時心煩多語明顯不同。
烏梅丸黃連用法:烏梅丸證之失眠黃連使用是清心火的主要藥物,其使用劑量主要看舌苔黃厚與舌質暗紅為主,如果舌苔厚而微黃,或舌質暗而偏淡者,黃連的用量宜偏小,失眠之烏梅丸證,選肉桂配黃連以交通上下。
通過以上醫案,可知烏梅丸方證特點的共性:①面色暗晦或暗紅:符合厥陰經為陰盡陽生,陽氣不榮于面,肝血瘀滯的特點;②舌質暗紅舌苔黃濁:符合厥陰肝經為藏血之臟,體陰而用陽,命門火衰,相火不明,肝陽不展故疏瀉失職,肝血瘀滯故舌質暗紅;木不疏土,水濕運化不利,濁氣上泛故舌苔厚濁;③脈象共性:脈寸關弦尺弱為上盛下虛之象,上盛包括2個方面,一為厥陰相火內郁,心包之火不能布散,一為木不疏土,水濕濁氣上逆;下虛為命門火衰,肝血不足,尺脈不充;④腹診共性:厥陰肝經聯系胃肝膽,上貫于膈而布兩脅,故兩脅內側按之有抵抗感。
烏梅丸在臨床上廣泛運用,不能僅囿于蛔厥、久痢證候,應謹守厥陰陰陽寒熱錯雜之病機,熟知烏梅丸證的臨床證候,方能發揮其治療作用。寒熱錯雜證的臨床表現復雜,故用烏梅丸以雜治雜。烏梅丸對應厥陰寒熱錯雜證,病在血分、陰分故以烏梅為君。臣以附片、桂枝、干姜、細辛、椒目等辛熱之品以助其陽,溫以祛寒;黃連、黃柏苦寒之品, 共奏清熱燥濕、瀉火解毒之功,可使火去不復傷陰,起到以瀉為補的功效,烏梅丸方藥里黃連、黃柏的用量不是一成不變,必須根據舌苔厚薄、脈力強弱判斷寒熱比重而靈活處理用量;《傷寒論》從太陽病到少陰病,方藥里都沒有當歸,只有到了厥陰病烏梅丸及當歸四逆湯里有當歸,當歸甘潤,能養血、入肝,與烏梅合用,養肝陰,補肝之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