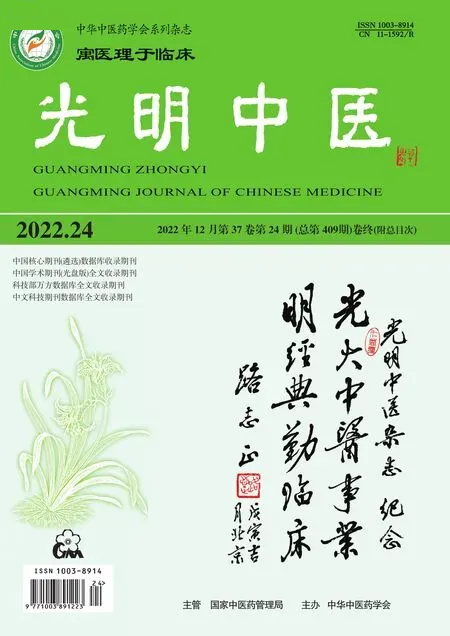巨刺法的研究現狀與展望
顧吉瑞
經絡在人體左右兩側對稱分布,通過奇經八脈相互貫通、連結,某些經脈在循行過程中左右相互交會,如大腸經“左之右,右之左,上夾鼻孔”。加之經別和經筋的循行分布特性[1],使得脈氣左右相通,故能“左病取右,右病取左”,由此衍生出巨刺法這一古典針刺療法。其臨床療效顯著,現代基礎研究也不乏從現代分子生物學、神經學及影像學等方面對其作用機制進行探索。
1 巨刺法的由來及針刺操作
1.1 巨刺法的由來巨刺針法首見于《黃帝內經》:“凡刺有九,以應九變……八曰巨刺。巨刺者,左取右,右取左”。闡釋巨刺可左右交叉取穴治病[2]。自古以來,各醫家流派對“巨刺”理解不盡相同,都試圖通過釋義來更好地服務臨床。古代醫家認為:“巨,大也,謂當以長針取之”。強調巨刺應以長針為針刺工具,“巨刺, 大經之刺也”,取大經脈而刺。當代醫家更是眾說紛紜:“巨”系“互” 字誤寫;“矩其陰陽”,陰為患側,陽為健側,當患側不適, 即在健側進行“刻識”找到與之對應的點, 給予針刺治療,這種觀點的臨床運用最為廣泛且沿用至今[3]。
1.2 巨刺法的操作病位有深淺之別,病中有經絡之分,根據所患疾病的具體特性,刺法也有深淺之別,中經中絡之分。回顧經典,“巨刺”“繆刺”均在《黃帝內經》中有所提及,既指出二者的共同之處,又詳盡了二者的區別。《素問·繆刺論》曰:“帝曰:愿聞繆刺,以左取右,以右取左,奈何?其與巨刺何以別之”?可見二者具有共同的“左取右,右取左”取穴原則;黃元御言:“繆刺, 即巨刺之淺者也”。可見二者的區別在于針刺深淺、中經或中絡。清楚二者的區別也為巨刺法的臨床操作規范提供了依據[3]。
2 臨床運用方面
2.1 巨刺法在中風偏癱方面的研究現狀明代醫者喻昌認為:“凡治一偏之病,治宜從陰引陽,從陽引陰,從左引右,從右引左”。提示巨刺針法是通過刺激健側肢體經氣從而激發患側殘余經氣即潛在的恢復能力的一種針刺療法,其廣泛運用于改善腦卒中后肢體運動功能障礙。陳立典等[4]通過臨床研究發現,由于偏癱患肢腧穴處于低功能狀態,針刺患側穴位影響得氣,從而使療效無法達到最理想狀態;此時若刺激健側腧穴,反而可促進得氣,提高療效,于是采用健側取穴、強刺激的方法促進偏癱早期上肢功能的恢復,取得了不錯的療效,并為良好的遠期療效打下基礎。林奕君[5]將42例腦卒中后上肢痙攣患者分成治療組和對照組,分別采用巨刺法結合康復訓練、患側針刺結合康復訓練進行治療,研究表明治療組在改善患肢運動功能、日常生活活動能力、緩解患肢痙攣等方面與對照組療效差異無統計學意義,說明“巨刺法結合康復訓練”在改善腦卒中后上肢痙攣狀態具有一定臨床可行性,值得一提的是,巨刺法還可避免針刺患側引起痙攣加重。葉祥明[6]發現,康復治療配合巨刺法能在偏癱早期加快肢體運動功能恢復,縮短病程。筆者對近10年文獻進行整理,發現巨刺法在調動肢體同經真氣、驅逐邪氣、快速提高患肢肌張力、恢復大腦皮層對運動的控制等方面具有一定的臨床療效。
2.2 巨刺(灸)法在消炎鎮痛方面的研究現狀巨刺法還在消炎鎮痛方面有一定的作用, 關于這方面的臨床研究不在少數。Zuo等[7]分別對福爾馬林誘導的炎痛小鼠足三里穴位進行患側灸和健側灸,發現無論灸哪一側,均可在一定程度上縮短小鼠舔咬痛處的時間,實驗數據顯示2組之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說明艾灸健側和患側均可用于緩解疼痛,且2組具有相當的鎮痛效力。Miurai等[8]根據“面口合谷收”經典理論,分別對福爾馬林誘導的唇周炎痛大鼠合谷穴位進行患側針刺、健側針刺及腹腔注射納洛酮鎮痛處理,研究發現針刺具有與納洛酮相似的鎮痛效應,明顯抑制了早期和晚期的炎性反應,且患側針刺組與健側針刺組之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說明2組具有相當的鎮痛效力。郭涵甄[9]將50例急性腰扭傷患者分為治療組30例、對照組20例,治療組采用三才巨刺導氣法進行治療,對照組采用常規針刺取穴進行治療,結果治療組總有效率達96.6%,對照組總有效率達50%,不難看出治療組療效明顯優于對照組。
2.3 巨刺法在改善關節活動限度方面的研究現狀有相關臨床研究表明巨刺法在改善關節活動限度方面有一定療效。Zhang等[10]對20例慢性肩痛患者條口穴分別進行患側針刺、健側針刺,發現2組患者在治療后,肩關節活動限度均有改善,且巨刺組肩關節功能的平均客觀改善優于患側針刺組。關于巨刺法能改善關節活動限度的臨床研究發現,筆者認為很有可能與其消炎鎮痛作用密切相關,即巨刺通過消炎鎮痛間接改善肢體關節活動限度。
3 作用機制方面
3.1 周圍神經肌肉系統有研究表明,脊髓不僅是針刺信號傳遞的中繼站,還是針刺效應產生的初級中樞[11]。周圍神經系統主要可以通過以下3種途徑產生“巨刺”效應:神經元的中介作用、后根纖維的直接作用、脊髓上行傳導束對高位中樞的直接或間接影響。有些后根纖維能跨過中線并止于對側后角,意味著針刺一側穴位可通過這類纖維,直接刺激對側后角神經元,從而在對側引發神經沖動。此外,針刺信號還可通過脊髓網狀束和舊脊丘束對腦干及上位的高級中樞產生雙側影響,從而發揮“巨刺”效應[12]。早在20世紀90年代就有研究發現[13],刺激健側肌力較強的肌肉產生隨意收縮后可使整個傳導中所涉及的運動性神經元產生興奮聚集效應,從而增強患側肌肉力量,借此促進恢復進程的起始、縮短病程,更有利于肌張力和肌力的恢復。所以,如果從運動生理學角度看[11],巨刺發揮效應主要與交叉遷移理論相關,即刺激一側肌肉帶動未受刺激一側的同源肌肉收縮[13];此外有相關研究表明[11],針刺結合康復療法在抑制炎癥反應、促進神經細胞再生及側支循環建立方面均有積極作用,并可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細胞凋亡。
3.2 中樞神經系統有研究發現[14],在中樞神經系統中腦干、網狀結構、丘腦非特異性投射系統以及大腦皮質等是“巨刺法”發揮效應所依賴的重要結構基礎。當針刺信號傳遞到腦干水平,刺激的傳導不僅是雙側的,更是彌漫、廣泛的,這一特性決定了“巨刺”不僅適用于疼痛性疾病,還適用于偏癱及某些運動系統疾病。CHEN等[15]對10例缺血性腦卒中左偏癱患者的右側曲池和右側足三里進行針刺治療,針刺前后均進行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檢查。采用ReHo分析法,用REST軟件比較針刺前后患者的腦區反應,結果顯示,針刺后患肢產生了明顯不同于針刺前的神經活動;同時顯示右側中央前回和額上回ReHo值升高,右側頂葉上小葉、左側梭狀回和左側輔助運動區ReHo值降低。這一現象說明單側針刺可刺激雙側區域。研究還發現針刺健側可喚醒腦回,這可能為巨刺法改善中風后運動功能提供客觀支持。另有研究發現[16],巨刺法可通過調節環磷酸腺苷-蛋白激酶A-環磷腺苷反應元件結合蛋白(cAMP-PKA-CREB)信號傳導通路改善腦缺血再灌注損傷,這條通路在腦缺血恢復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cAMP信號被激活后轉錄相關基因,進而表達某些蛋白分子,這些基因產物可以影響神經細胞膜蛋白的結構和功能,參與中樞神經系統突觸傳遞,調節著神經元在應激損傷后的再生、存活及修復等, 因此cAMP在神經系統損傷中發揮重要的調控作用,而cAMP的含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ATP、腺苷酸環化酶的影響。江一靜等[16]將大鼠分為針刺組和非針刺組,其中針刺組又分為巨刺組和非巨刺組,研究人員通過動物實驗發現,針刺組的大鼠體內AC、cAMP、PKA活性均高于非針刺組大鼠,針刺組中,巨刺組大鼠體內AC、cAMP、PKA活性較高,說明針刺尤其是巨刺對提高大鼠體內AC、cAMP、PKA活性有更強的效應。此實驗還觀察到針刺組的大鼠腦梗死體積明顯小于非針刺組,巨刺組大鼠腦梗死體積小于非巨刺組。
4 思考與展望
通過歸納中國古代典籍,研究梳理現代文獻數據,不難看出巨刺法作為中國針灸的古典特色針法之一,歷史悠久,療效確切,具有高臨床價值的特性和優勢。隨著科研進入到新的高度,多學科交叉融合已是常態,不論是從分子生物學角度探究巨刺法的作用機制,還是輔助影像學研究巨刺法作用下的腦功能成像,都在一定程度上為巨刺法確切的臨床療效提供了客觀可視化的數據理論支持。本文通過查閱相關文獻,梳理目前巨刺法涉及的部分臨床優勢及作用機制,希望為今后的科研方向提供參考價值,以期巨刺法得到更廣泛的認可,充分發揮其治療優勢,進一步減輕患者痛苦,提高患者生活質量,從而推動中醫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