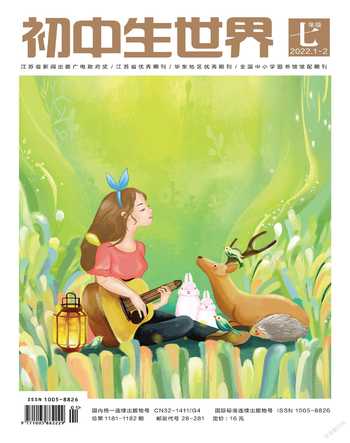天文界“90 后”葉叔華:天文是一輩子的浪漫事業
雨勻音

葉叔華,中國科學院上海天文臺名譽臺長,我國天文地球動力學的奠基人之一。在中國,大家習慣叫她“葉先生”;在浩渺的宇宙中,3241號小行星被命名為“葉叔華星”。
葉叔華的職業生涯,意味著對世界科學研究最高峰的不懈攀登。1958年,葉叔華挑起了籌建我國世界時綜合系統的重擔。20世紀70年代初,葉叔華提出了發展VLBI(very long baseline interferometry的縮寫,簡稱甚長基線干涉測量技術,就是把幾個小望遠鏡聯合起來,達到一架大望遠鏡的觀測效果)的計劃,推進該項目正式啟動,并在我國“探月”和“探火”等深空項目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這位天文界的“90后”也有不按常理出牌的可愛的另一面。比如,人們通常認為,小行星被命名為自己的名字是件浪漫的事,葉叔華卻覺得被命名毫無意義——反而認為小行星們長得像洋芋、山藥蛋,外形很丑,是宇宙空間的“廢物”。再比如,對于一些有關“水逆”之類的說法,葉叔華覺得很無聊,完全沒有科學道理。
有人稱贊葉叔華是中國天文界最亮的那顆星,她卻說:“我只是一粒小小的芝麻,在漫漫宇宙長河中,不值得一提。”
與天文結緣,主持建立中國世界時系統
1927年,葉叔華在廣東出生,同年12月,廣州起義爆發,革命的烈火迅速在這座城市蔓延。迫于戰爭和生計,葉叔華跟隨家人經歷了多次遷徙才完成學業。1945年,中山大學來中學招生。一門心思想學古文的葉叔華,遭到父親的阻撓。兩人三改志愿達成折中方案:數學系。由于當時的中山大學沒有單獨的數學系,只有數學天文系,葉叔華便被理學院以全區第一名的高分錄取。
葉叔華大一時,被鄒儀新教授講的天文課深深吸引了。到了大二,她便決定主修天文。1950年暑假,她和人生伴侶程極泰一起到南京紫金山天文臺求職。當時,工作人員回答她“天文臺只招一個男的”。吃了“閉門羹”的葉叔華很不服氣,提筆寫了一封長信給當時的臺長、天文學家張鈺哲,列舉五個“不應該不用自己”的理由,成功說服了臺長。1951年底,葉叔華進入當時紫金山天文臺所屬的上海徐家匯觀象臺工作。
這里恰恰是葉叔華天文事業的開始。當時全國就這么一家完備的時間工作站,條件艱苦,在半地下室辦公,員工就四個人。葉叔華說,進入觀象臺的第一項工作是觀測恒星,計算恒星時,再換算成世界時。觀測需要手眼并用、全神貫注,身材矮小的葉叔華只有站在一塊小平板上才方便操作。冬天,操作儀器時不能戴手套,葉叔華常被凍得手指發僵。
新中國成立之初,還沒有一份統一的全國地圖,這影響了大型的工程建設。很多省份還沒有精確測量,3萬名測繪工作人員奔波在全國各地。而測繪離不開天文授時——如果天文時間測得不準,地圖就拼不起來。國務院要求科學院首先做好時間工作。1958年,籌建我國世界時綜合系統的重擔,落在了葉叔華身上。“我衡量了一下,要做得和國際上一樣好,最主要是保持數據平穩,要搞一套自己的方法。”葉叔華說。他們最先遵循了國際時間局的原則,但后來發現,中國授時臺站的數量與國際時間局及蘇聯系統相差太遠,不能照搬,最后改用了自己的方案。葉叔華回憶,到了1964年,中國世界時系統達到世界第二名,1966年初正式作為我國的時間基準向全國發送標準時間,這就是后來的“北京時間”。葉叔華也因此有了“北京時間之母”的稱號。
拓荒“無人區”:VLBI的變革
熟悉葉叔華的人,都能背得出她的一句口頭禪:辦一件事,假設只有40%的把握,如果停在那里不動,就會慢慢變成20%的把握,最后變為零;但積極爭取,可以將其變成60%或70%的把握,最后將事情辦成。拓荒“無人區”,一直是她性格中的重要特質。
1970年,她恢復工作的第一件事,就是跑到圖書室看國外同行在做什么。葉叔華了解到,1966年,新出現的VLBI的分辨率比傳統觀測儀器提高了幾十倍,而且不需要電纜,各個天文臺站借助原子鐘就可以連接起來,相距可達幾千公里。更讓葉叔華振奮的是,這一技術利用空間射電源,銀河系外也能觀測到。由于VLBI是一項新技術,成本又比較高,即使在一些發達國家也鮮有人問津;但葉叔華敏銳地看到了它的應用前景。1973年,她提出了發展VLBI的計劃,從自己的隊伍里頭挑選了一批“骨干”出來,決定先試制6米望遠鏡。
“人很奇怪,先把難的吃掉,容易的就好弄。如果先做了容易的,難的就開展不起來。” 1981年10月,葉叔華擔任上海天文臺臺長,VLBI項目正式上馬。1988年起,國際天文學會和國際大地測量學會宣布,世界時測定全部采用VLBI、激光測距人造衛星和GPS等新技術。如果當初沒有預估到這一趨勢,我國的時間測量優勢將全軍覆沒。
20世紀90年代,本來一直用處不大的VLBI,恰巧趕上我國啟動“探月工程”。之前,我國航天器最遠只去過8萬公里遠的太空,而地月之間有38萬公里。當時面臨的一個棘手難題,即衛星飛到月球附近要改變軌道,需要非常精確的空間測量。“如果飛船沒有按照原定軌道走,要么撞上月球,要么飛到很遠的地方,這兩個都是‘大失敗’。”葉叔華和上海天文臺的同事跑到北京主動請纓,接受了任務。后來,在國際射電天文會議上,當她說出“10分鐘內把VLBI測軌結果報到北京總部”時,現場一片寂靜,有吃驚,更有懷疑。2007年,“嫦娥一號”衛星發射,由上海、烏魯木齊、北京和昆明4個站組成的VLBI聯測,從上海報到北京總部實際只用了6分鐘;到了“嫦娥四號”和“天問一號”發射時,四站聯測將VLBI測軌結果報到北京的時間更是縮短至1分鐘。
把天文當作一輩子的浪漫事業
葉叔華潛心于天文研究的同時,也是一名熱心社會科普的志愿者。她經常在百忙之中抽出時間為青少年指導科學實驗活動,做科普報告,在媒體上講課,并參與編輯了新版《十萬個為什么》等科普著作。她常說,科學工作者自身就是科普的最大受益者,自己從一張白紙成為天文學領域的專家,也是受到大量天文科普作品的啟發和影響。
2019年3月,耄耋之年的她和一群青少年到漠河觀測日全食。因途中受了風寒,她突發高燒。為了不讓孩子們失望,她仍然堅持出席最后一晚的聯歡會,滿面笑容地跟大家講話。她希望讓更多人了解這份浪漫。“年輕人,一定要努力學習,只爭朝夕。現在是科技發展日新月異的時代,稍不留神,機會就會溜走。身為科學家,總要在有限的時間里多做一些于國于民有意義的事情。”更讓葉叔華欣慰的是,在她和一些科學家持之以恒的推動下,上海天文館終于在2021年夏季正式開館,今后將成為天文科普和教育的重要場所。“作為一座國際化的大都市,上海一直沒有一座天文館,這是積壓在我心里40多年的一個結。”接下來,在她的倡導和推動下,上海又建成了65米射電望遠鏡(天馬望遠鏡),從而使我國VLBI網的靈敏度提高至2.6倍以上。
大可頤養天年的葉叔華,依舊每天到天文臺上班,從早上9點,一直工作到下午。“每個人把自己的工作做好,都是一份很珍貴的貢獻!”辦公室墻上,有一幅根據葉叔華語錄創作的書法,這是葉叔華的自勉,也是葉先生對忙碌在大小崗位上的你我,提出的期許。
(根據2021年第12期《新民周刊》文章《天文界“霸道奶奶”葉叔華訪談 我們從跟著跑,到并排跑》、2021年第10期《時代郵刊·下半月》文章《葉叔華:天文是一輩子的浪漫事業》綜合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