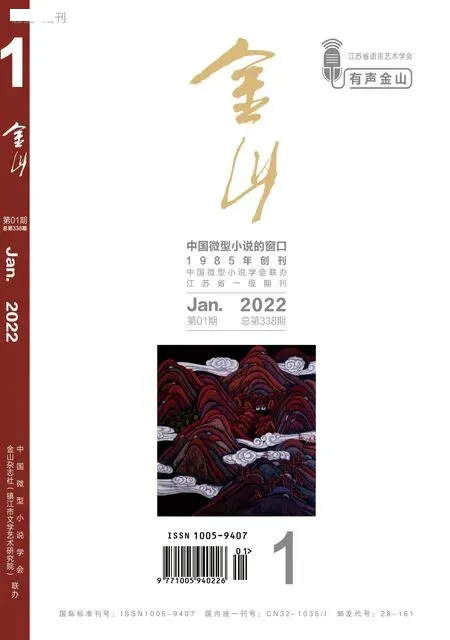當代詩歌
欄目主持人:雪 鷹 劉思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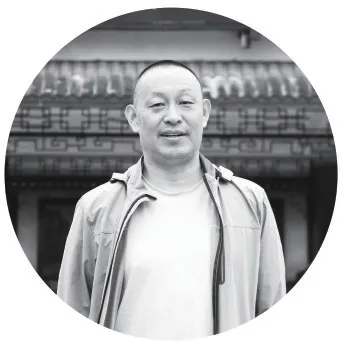

汪劍平的詩平實自然、舒緩而又迂回。蘊藉的內涵,如支撐靈魂的骨架,在柔和的語境里吐露自己內心的追求,向往的風骨便是自身的精神關照。
魯蕙的詩具有明顯的性別特征,女性的婉約和對愛的思考與追求,通過回顧、想象、預設的情境,通過順手拈來的意象展示出來。詩里裸露的不只是一顆柔軟而纏綿的心,更有現代女性的生活剪影與心靈律動。
金益的語言相對簡潔,從他詩里對歷史的鉤沉,可見其得益于文言的功底。新詩懷古,觸景生情,老題材若想寫出新意來也是不易的。
蘇金文的語言老練,想象豐富、新鮮,雖然是雪月之詩,但有諸多不可言說的深意蘊寓其中。
冬簫曾獲徐志摩詩歌獎,詩寫受徐氏的影響必不可少,那種回環往復的小令格調,唯美精致的敘述,若能融入詩人當下的深度思考,讀來也饒有興致。
張學宏的玄思相比之下更為深刻。語言創新的努力隨處可見,在相對傳統的詩寫中,他能靠意象組合出新鮮的閱讀感覺來。
許勤的詩很純凈,有秋天童話的色彩。
喬一水一直在走自己的詩歌寫作之路。追求詩性靠得住的手段,便是追求語言的獨特。可以看出,他在多年努力的基礎上,寫作之路越走越扎實,越走越自信。
楊孝洪詩歌風格已經形成,人如其詩的觀點,用于他的身上是極其熨帖的。善于觀察者必然善于歸結,必然善于從日常中看到他人無法窺探的哲理。風趣的秉性無論是在生活,還是在詩里都能自如呈現,達到合一。
對于毛文文來說,故土以及與故土密切關聯的那些記憶,已經是他詩歌的精血,是他生命里永不結痂的烙痕。“詩人的天職是返鄉”,南京溧水的那一片鄉土,給予他無盡的創作源泉,而鄉愁與懷舊的主題,往往與敘事嵌合得十分密切,如何能在敘事里生成詩,讓詩走出敘事的母體,是我們一生需要研究的課題。毛文文的詩寫之路已經鋪向了無想山,鋪向了石臼湖的深處。
張建祥在不到一年的時間里,詩歌寫作的脫胎換骨是有目共睹的。平靜舒和的語言基調,應該緣于他的處事風格,透過表層呈現的深邃的事理,則是他慣于沉思的體現。觀察、思考、想象與詞匯量,以及意象粘連與融合的能力,從他的詩行里我們都可看得清晰。
陳筱靜的努力已經產生了回報。她能在很短時間里基本擺脫幾十年延續下來的散文敘事方式,而重新打開一扇通往詩性的敘事之門,這不單是天賦或者追求的結果,只有二者的結合,才有可能在短時間內實現這樣的突破。而清新、通透的詩歌特點,則是她心靈的純凈與思考的深度所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