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我們正在重寫物種
文|胡安·恩里克斯 史蒂夫·古蘭斯
譯|郝耀偉
1959年,蘇聯動物學家、遺傳學家德米特里·別利亞耶夫來到了廣袤無垠的西伯利亞,那里既沒有實驗室,也沒有大學。作為一個骨子里流淌著實驗主義血脈的科學家,他手頭有什么資源,就會拿什么來做實驗。最終,德米特里選擇了飼養野生狐貍。
他不是隨意飼養,而是每一年都會根據溫順或暴戾的秉性來對每一只狐貍進行排序。只有那些在這些特質上趨于極端的狐貍才會被選來繁殖。1/5 最溫順的狐貍和1/5 最暴戾的狐貍會被隔離開,分別飼養,一代一代,循環往復。最終,德米特里的“去野性實驗”非常成功地改變了一個野生物種,這些狐貍中的一小部分變得像拉布拉多犬一樣,后來甚至被運到美國進行銷售,賣點是“溫和的家庭寵物,特別適合陪伴孩子”。由此可以看出,我們可以通過人工選擇快速增強或削弱一個物種的好斗性。
重寫物種一 馴化自我
我們的自我馴化速度很快,幾乎是在十幾代間完成的。
人類自身從一個“全天然”的物種進化而來,如今,我們已經快速且大幅度地消除了自己身上的野性。這是一個巨大的變化。
現在,我們會覺得居住在干凈、明亮、安全的城市中,水龍頭里流出潔凈的水,有馬桶沖掉排泄物是一件很正常的事。但事實上,人類歷史上99%的時間里這些條件都沒能實現。我們現在已經適應了完全非自然的、由人工設計的環境,認為一切理所當然。
我們的自我馴化速度很快,幾乎是在十幾代間完成的。
過去,我們并不會與數百萬個同類聚集在一起,秩序井然,和平共處。在之前的環境中,距離睡覺的地方幾十米之外就是野地,可以采集到大多數食物。人類祖先部落的規模只有150人左右,當個體多于這個數量時,就會出現紛爭,進而導致部落分裂。
我們所說的文明是伴隨著農業的出現才發展起來的,始于約500代之前。公元前2000年,世界人口總量只有幾千萬,而且絕大多數人都居住得非常分散。大型城市的萌芽出現于新月沃地、亞洲、北美洲,甚至歐洲,但城市并不多見。1300年,英格蘭僅有約5%的面積屬于城市。在整個工業革命時期,鄉村是常態。即使到了1910年,仍只有1/5的人口居住在城市。而截至2007年,世界大多數人口都住在城市。也就是說,大規模的全球城市人口遷移只花了不到100年,或者說5代人的時間。從歷史背景來看,從最早的古人類開始直立行走,到現在已經至少經過了12.5萬代人。
今天,城市化進程仍在加速。全球范圍內,城市人口到2030年估計會再增加1倍。在未來12年內,一些國家打算將2.5億人從鄉村遷往城市。要容納這些新的居民,需要建立的城市總面積等同于將幾十個特大型城市加在一起。
曾幾何時,非自然環境對人類而言是非常有益的。在馴化自己和周圍環境時,我們也在一點點移除阻礙人類延長壽命的絆腳石。
在人類的絕大部分歷史中,大部分人的生命中都充斥著營養匱乏、疾病和暴力。人類生活的一個嚴重威脅是被“敵人”吃掉,各類捕食者不時出沒。后來,我們消滅了這些大型食肉動物,改變了環境。現在,我們必須非常仔細地尋找,才可能發現這些一度很常見的巨型捕食者。灰熊在美國的大多數地方已經不再構成威脅,劍齒虎也已成為化石。我們擺脫了食物鏈的束縛,大多數人會在自家床上或者醫院里離世,而不是淪為另一種動物的果腹之物。我們還是有些擔心鯊魚,不過不幸的不是我們,而是鯊魚——它們出現時,可能會遭到捕殺或成為科教節目中的稀有研究對象。罕見的鯊魚攻擊會引發全球媒體的關注,每年野鹿撞上汽車導致的人員死亡數量,是鯊魚攻擊致死人數的11倍。在大多數城市里,毒蛇則更為罕見。盡管更加原始的飲食和生活方式漸成一種時尚,但理智的人仍會追問:“為什么有人會愿意回到洞穴人的時代?那時候可只有10%的人能活到40歲。”
到目前為止,最危險也最常見的“捕食者”仍舊是人類中的其他成員。平均而言,我們死于戰爭的可能性是死于鯊魚攻擊的11 000倍。盡管世界上時有騷亂和喋血事件發生,但人類馴化自身的趨勢仍是廣泛而深刻的。總體而言,戰爭和暴力現象在各個地方都在逐漸減少。我們不會認為暴力致死是一種常態。
重寫物種二 改變環境
對大多數陸生物種而言,應對極端溫度和天氣變化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們本已適應氣候波動的身體,僅僅一個世紀的光景,就適應了生活在恒定的環境中。
我們在馴化自身的同時,也在不斷改變著生活的環境。暴露于自然環境下曾經是一個主要的致死原因。隨后,我們發明了各種衣物和調節溫度的方法,家和辦公場所變得越來越舒適,我們對環境已經不再那么擔憂了。龍卷風、颶風、洪水和干旱,甚至“末日暴風雪”都可以提前預知,進而由媒體跟進報道。得到預先警告對我們來說已經習以為常,但在絕大部分的人類歷史中,天氣都是自然選擇最嚴酷且恒久不變的驅動力量。
除了極端天氣外,或許我們看到的最大變化就是無處不在、影響廣泛的溫度變化。對大多數陸生物種而言,應對極端溫度和天氣變化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們本已適應氣候波動的身體,僅僅一個世紀的光景,就適應了生活在恒定的環境中。我們待在有空調的大廈、居所、汽車和辦公室里,在20℃~24℃之間愜意地生活著,遠離寒風凜冽、暴雪肆虐、大雨滂沱。這種生活方式完全是非自然和非正常的,而且著實令人感到舒適。
對大多數國家的大多數人來說,獲取食物不再是事關生死的問題,除非涉及過多的卡路里攝取。確實,仍有很多人食不果腹、缺乏營養,但饑餓已遠不像從前那樣泛濫。直到不久前,即使在發達國家,尋找、收集和攝入足夠的卡路里都是人們每天的首要任務。而現在,饑荒已經不太常見,也遠不像以前那樣扮演大規模“殺手”的角色了。
重寫物種三 改變其他物種
達爾文認為,如果人工飼養者能夠將豢養環境中的單一物種操控改變到如此程度,那或許也可以操控改變野生的所有物種。
在過去的幾個世紀中,人類改變了足以促使其他物種快速進化的絕大部分因素。
即使相對微小的環境改變也會導致植物、動物的極度多樣化,但這種多樣化往往發生在同一地理區域內。如果把野綿羊圍進牧場,圈養幾代,你會觀察到綿羊的明顯改變。如果把一種動物、植物或細菌物種從鄉村環境遷移到城市環境中,在5代之后,可以預見該物種會發生極其迅速的基因變異,或者滅絕。一些鴿子物種,比如常見的廣場鴿,從住在懸崖峭壁上、性格驚怯的鳥類,變成了盤踞廣場的高空俯沖式害禽。與此同時,數十億計的旅鴿沒有適應變化,一直保持著易于親近的秉性而常被獵手捕殺,在短短一個世紀中即從比比皆是落得銷聲匿跡。
達爾文明白人類驅動的非自然選擇,及其后果和未來,因為當時人們已經將其應用于動植物的馴化了,他稱之為“人工選擇”。通過研究觀賞鴿的飼養,達爾文記錄了物種的快速變化。達爾文認為,如果人工飼養者能夠將豢養環境中的單一物種操控改變到如此程度,那或許也可以操控改變野生的所有物種。
達爾文只是沒有沿著這個邏輯繼續延伸,沒有預見到我們不久后掌握的巨大力量,直至改變這個星球,改變所有其他物種,改變人類自身。否則,他也會將非自然選擇視為進化的一種關鍵驅動力。
你可能會認為,我們現在習以為常的事情,比如壽命、智力和身高的顯著增長趨勢,好像是突然間發生的,其實不然。人們已經在漫長的時間中深刻地改變了周圍的環境,使其變得不再自然、不再隨機,不再那樣具有危險性;同時,我們也已經徹底馴化了自己,就像馴化貓和狗一樣,而這帶來了重大的進化后果。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個星球上的物種進化已經超越了臨界點,轉向了非自然選擇和非隨機變異,這甚至都不是真正的進化論2.0版,而是一種全新的、基于不同原則和機制的進化邏輯。這不再是單純的自然進化,而是人類驅動的進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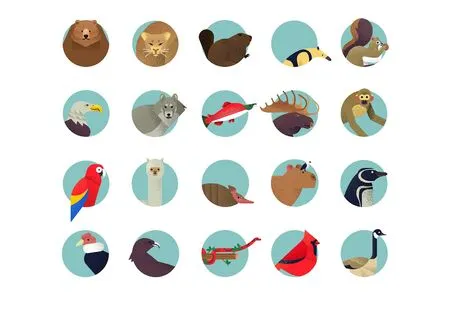
本文內容摘編自《重寫生命未來》一書,胡安·恩里克斯、史蒂夫·古蘭斯著,郝耀偉譯,浙江教育出版社,2021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