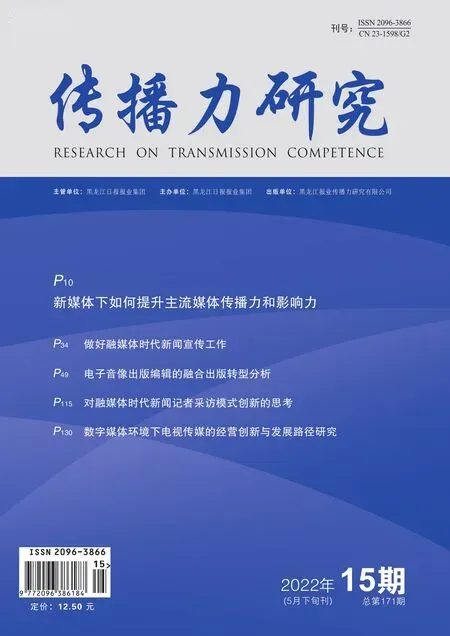從媒介發展視角看我國媒介功能的演變歷程
◎龔婷婷
(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四川 成都 610072)
媒介功能是指媒介的政治、經濟以及社會協調功能的總和。媒介功能的演變是指隨著社會和技術的發展,媒介功能不斷變化的過程。萊文森提出的“媒介進化”理論認為,媒介進化是媒介的自我選擇,也是人類出于自身需求的選擇,后出現的媒介并不會讓舊媒介消失或完全失去作用,新媒介是在舊媒介的基礎的升級,是一種包容狀態。因此,媒介功能的演變不是新功能替代舊功能的過程,也不是簡單的依次疊加的過程,而是新功能在舊功能基礎上的升級與整合。并且在社會變遷和媒介技術發展的每個階段,媒介的功能有主次之分,由于各種內外力的作用。
一、媒介功能及其演變研究現狀
近百年以來,隨著媒介,尤其是新興媒介的蓬勃發展,有關媒介功能的研究逐漸增多,在文化學、社會學、傳播學等學科均有大量涉獵,并形成了三種較為成熟的研究模式。一是從文化學出發的媒介功能批判理論,以法蘭克福學派的阿多諾、馬爾庫塞、霍克海默為代表。他們以媒介文化批判研究為起點,將大眾傳播媒介視作意識形態操縱的工具,并將大眾傳媒稱作“文化工業”,其產品“大眾文化”導致文化墮落與審美變質。霍克海默等人提出“社會水泥”的概念,斥責大眾文化的以悠閑娛樂的方式操縱社會心理的思想。二是基于社會學視角的媒介功能研究,以芝加哥學派的米德、帕克、布魯默為代表。他們注重探究傳播與社會影響之間的聯系,“結構功能論”將社會視作一個有機體,其中每一部分都對該體系的平衡做出貢獻,因此,媒介具有對社會的協調與平衡功能。三是基于傳播學角度的媒介功能理論,代表學者有拉斯韋爾、賴特、施拉姆。他們在社會發展的基礎上,首先指出媒介的社會協調和遺產傳承等基礎性功能,又依據環境的變化,逐步提出媒介在娛樂與經濟等附加功能。在國內,學者們普遍認為,新聞傳播媒介作為大眾傳播媒介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發揮社會功能的同時,其更重要的功能是傳遞新聞信息和反映輿情、監督社會。
學界對媒介功能演變的相關研究相對較少,大多從傳播學的媒介功能論視角出發,研究大眾傳播媒介,尤其是新聞傳媒功能在某一階段演變的特點、變化、規律及其與社會之間的關系,或者某一領域或事物伴隨著媒介歷史演變而變化和發展的過程。從第一種研究視角來說,例如,馮雋將新聞媒介作為社會大系統的子系統,認為其功能經歷了單一到多元、小眾到大眾、大眾到分眾、時空有限到無限、現實與虛擬并舉的過程。殷暢通過改革開放三十年間《半月談》雜志的國內十大新聞的分析,發現改革開放與媒體發展發揮著共同促進的作用。趙娜將文化形態的變化視作影響媒介功能的直接原因,認為媒介功能重心變化的外在體現是社會政治、經濟和社會關系的變化。從第二種研究視角看,周利榮通過論述傳播媒介的結構、特性以及媒介生產力的發展變化,以說明其對于文學文體的類型、文體功能以及新藝術形式的影響和作用。
綜上所述,現今關于媒介功能及其演變的論文或局限于新聞媒介,或已經落后于媒介的發展現實,因此,本文對媒介功演變進行梳理,探討其在各個媒介時代的地位、影響因素和表現形式,以期媒介能在當下和未來更好地揮發作用。
二、我國媒介功能的演變
蔡凱如、黃勇賢認為,媒介功能是媒介形態呈現的一部分。同時根據羅杰·費德勒在《媒介形態變化》一書中指出的引起傳播媒介形態變化的三種因素:一是可感知的需要;二是競爭和政治壓力;三是社會和技術革新。因此,通常所謂的媒介決定時代特征,同時時代也賦予媒介內涵和外延,也是媒介功能演變的依據和軌跡。美國媒介文化研究學者馬克·波斯特對從歷時性視野對媒介時代進行劃分,清晰地說明了這種演變,他在著作《第二媒介時代》中提出與“第一媒介時代”形成二元對立的“第二媒介時代”,前一種是指少部分信息制作者與大多數信息消費者的單向傳播的時代;而第二媒介時代是指一種去中心化的雙向傳播時代。李沁在此基礎是提出“第三媒介時代”,也是泛眾傳播的時代,依附于泛在網絡和大數據等物理基礎,具有沉浸傳播的特征。與此相對應,“前媒介時代”就是在出現大眾傳播之前的,原始傳播的媒介時代。
(一)前媒介時代:媒介功能的自然使用到簡單政治功能利用的過渡
前媒介時代是在第一媒介時代之前,是人類傳播的口語傳播時代和文字傳播時代,以及大眾報紙出現以前的印刷傳播時代,這些時期的傳播媒介呈現出以下特征:以口語為核心傳播媒介,文字和印刷為封建統治者和士大夫服務的原始傳播。因此,這一時代的媒介功能演變,主要是從平民對媒介的自然使用,到朝廷和士大夫對媒介政治功能的簡單利用的過渡。需要注意的是,這種過渡并非后者對前者的替代,而是后一種媒介在前者基礎上的疊加。
首先是對媒介功能的自然使用。在前語言傳播時代,口語是人類傳播的開端,雖受時空限制,傳遞信息的效率受限,記錄性較差,但口語傳播有其獨特的靈活性。于是逐漸出現了一些早期的體外化媒介,如巖洞壁畫、結繩記事、符號標記,然而由于使用的符號繁雜,且存在地域和人群的不一而導致符號使用的異同,極少有符號能沖破時空的結界。其次,封建統治者和士大夫將媒介作為一種宣傳工具。文字的出現將人類帶入更高文明的發展階段。文字不僅讓信息得以長久保存,人類文化的傳承也有了可靠的依據,如民間年畫具有傳播天文歷法知識、農業技能及其對農事活動的指導功能,碑刻的堅固耐久具有空間傳播特性,更是把消息傳遞到遠方,《邸報》加強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聯系,為鞏固封建統治階級的統治根基提供了一種可靠的方式。
在前媒介時代,文字和印刷術被廣泛使用,印刷技術也較為成熟,但縱觀整個社會,并未因此而形成相當規模的大眾傳播。一方面,以小農經濟為統治根基的君主專制政府不可能鼓勵信息傳播方式的改革,與當時的世界各國相比,中國的封建制度根深蒂固,統一的大國沒有太多外部勢力的威脅,儒家文化的發展使得歷代君王實行文化和思想上高壓政策,內部權力制度不斷自我完善,直至鴉片戰爭爆發;另一方面,與世界各國不同的是,中國在血緣紐帶解體不充分的情況下進入文明社會,形成了獨特的宗法制度和與此相對應的血親意識,并在歷代統治者的有意改造下形成法律條文,轉化為宗法式的倫理道德,左右著當時人們的心理和行為。因此,這仍是一個以口語為主的社會,信息無法大范圍傳播,人們將過去的、既成的東西視為學習和效法的對象,在經驗式的積累下代代相傳。在這種社會下,生產、溝通、合作在主體共同在場情境下進行,每個人的社會活動都處于相互監視之下,依靠身體的人際交往就可以表達意向、情感來實現目的。所以早期的傳播媒介的時間性決定了其功能是儲存信息,幫助加強記憶,作為一種人體生理結構的表達工具,帶有局限性,是對媒介功能的自然使用。
(二)第一媒介時代:媒介由政治功能向多功能轉變
馬克·波斯特對第一媒介時代的劃分依據是傳播模式是單向型占主導,即少部分的信息傳播者和大量的受眾,以傳統媒介為代表,少數精英與知識分子占有更多的傳播話語權,受眾被動地接受信息,形成了單向傳播體系,決定了這一時期的媒介具有極強的政治性,因此,也被統治者們重視。大眾傳播取代了人際傳播的位置,成為人們獲取信息的主要途徑,人際關系和生活方式也因此發生了改變,媒介由政治功能實現向多功能的轉變
從封建社會末期到改革開放以前,中國社會的傳播媒介主要是作為一種宣傳工具被使用。鴉片戰爭后,近代報刊作為西方傳入中國的文明之一,內容上以宣傳西方宗教、文化和近代科技為主,雖然也在客觀上具有促進了中西文化交流,但其本質上是殖民主義的文化侵略活動,具有極強的政治性。在新中國成立以前,中國處于動蕩的社會變革期,國人的辦報活動和廣播事業活躍頻繁,維新變法、五四運動、抗日戰爭等一系列的政治活動,歷史的發展和國人在動亂中求新求變的精神,使得這一時期的傳播媒介的政治功能得以凸顯,尤其是在促進社會變革中的作用。改革開放以后,社會生活走向多元化,政治的民主化、法制化程度不斷提升,新聞媒介內部的改革也促進了媒介功能的轉向,媒介的多功能得到繁榮。
隨著工業社會結構的建立,社會的經濟生產方式、社會關系和活動規模都發生了質的變化,促使媒介功能發生變化。交換與分工高度發達,人們能親身參與感知的部分越來越小,共同體之間的功能性以來增強,橫向聯系變得愈加重要,大眾媒介因此成為個人與社會的重要聯系方式,并且工業社會的動態性要求人們主動使用媒介,及時了解外部世界的最新變化,導致了對媒介的依賴。大眾傳播代替人際傳播,媒介逐漸轉向功能的多元化,其他功能均建立在信息傳播的基礎上,媒介從單一的政策宣傳者回歸到環境的監測者與社會的守望者角色。
(三)第二媒介時代:媒介多功能的拓展與異化
隨著信息技術、衛星技術的快速發展,在技術與電視、電腦、電話的結合中產生了一種集制作者、銷售者、消費者于一體的雙向去中心化交流模式,即第二媒介時代。在信息化時代,媒介的各項功能得到更多拓展,其衍生功能或派生功能日益凸顯。也有學者認為,媒介功能的異化對人們獲取信息產生了干擾,甚至對經濟社會發展產生了不良影響。
隨著新媒體的普及、新技術的發展,媒介傳播方式和渠道愈加多樣化和便捷,媒介的多元化功能也得到進一步的拓展,主要體現在以下四方面。第一,表達功能。網絡的出現打破了傳播的時空限制,實現了信息在真正意義上的及時與同步,任何終端之間都能及時互動,無限擴大了網民在終端自主選擇權,民眾的表達空間在新媒體平臺得以拓寬,一些政務微博、政務微信、官方抖音號陸續開通,不僅民眾的表達權得以實現,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也在與時俱進中行進。第二,公共參與功能。網絡的去中心意味著扁平化和通透性,這一特性使得哈貝馬斯“公共領域”模型在互聯網群體傳播時代,通過網絡多元群體的結構重新建構起來。第三,社會協調功能。網絡將我們帶進信息社會,因此,信息和知識都成為重要的生產力。公眾的價值觀每天在數以萬計的信息中振蕩,公眾總感到傳統價值觀的漂移,又感受到新生價值觀的模糊,他們經常面臨著“合群”與“邊際人”的兩難抉擇,關于是非對錯的判斷,也屢屢受挫。因此,暗含著特定的社會價值規范和行為準則的大眾傳媒逐漸在消解公眾價值觀碰撞的過程中,成為有利于解決社會問題的“輿論場”。第四,經濟功能。在第二媒介時代下,媒介的經濟功能隨社會發展繼續發揮作用,并在注意力經濟下加劇了競爭,新媒體建構了一個線上市場交易環境——電子商務,虛擬網絡成為真實利潤實現的中介。
媒介的麻醉功能、“把關人”迷失、群體極化已經在第一媒介時代初見端倪,進入網絡信息社會,不僅這些異化的功能得到了強化,而且還衍生出一些新的負功能,對經濟社會發展產生諸多不良影響,如信息泛濫干擾準確信息的獲取,媒介傳播的時效性讓新聞媒介缺失厚度,以及媒介協調功能的異化。
(四)第三媒介時代:媒介的多功能融合與娛樂至死的憂患
第三媒介時代,也被稱為泛眾傳播時代,媒介以泛在網絡和大數據為物理基礎,具有沉浸傳播特征。其媒介與媒介技術基礎,即新的媒介形態就是沉浸媒介,如VR、AR和人工智能等,其本質是以人為中心,時刻環繞,隨取隨用,集媒介形態和內容于一體。時至今日,沉浸媒介雖被廣泛使用,但還并未成為人們的日常,更多被用于公共領域,因此,本文在此處對于媒介功能的演變更多是對既有媒介使用呈現的一種推測。
第三媒介時代將實現媒介的多功能融合。沉浸媒介的首要特征就是以人為中心,以滿足人的需求為發展前提,不僅如此,沉浸傳播讓人成為媒介的延伸,一方面是媒介改變人類,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等技術讓機器擬人化,人與機器深度學習、互相沉浸。沉浸媒介無時不在,人類時刻都在現實與虛擬兩個世界中漫游。傳播效果無處不在,人、媒介與環境彼此相融,人沉浸在其中,達到一種身心一體的愉悅體驗。沉浸傳播無所不能,娛樂、工作和生活的邊界消失,云計算和大數據整合人們生存的一切。基于此,人既融于媒介之中,呈現出沉浸生存特征,又能隨時隨地從繁雜的社會與信息中抽離出來,與自己對話,人內傳播回歸,媒介實現了多功能的融合。
與此同時,沉浸媒介提供的工作、娛樂一體化的設計,不禁產生了對媒介娛樂功能的憂患。工作與游戲不區分,工作就是游戲,游戲同時也成為工作,人們一邊沉浸在虛擬社會中,進行著娛樂與社交,一邊又將虛擬世界的物與情感帶入物理世界,娛樂、社交、工作和生活之間的界限逐漸相融,人們的工作、娛樂和社交相互交融,彼此關聯,而娛樂至死也將成為必然的趨勢,所以沉浸的人生也是一種娛樂的人生。此外,關于沉浸媒介的負功能還包括沉浸技術帶來的“前臺”生活與信息,它將暴力、災難、血腥、恐怖等場面呈現在人們眼前,這種臨近真實觸摸帶來的感受,對人們心靈的觸及,遠高于二維平面的呈現。
三、結語
媒介是功能性產物,作為對社會環境的反映,必然帶有時代和民族的印記,也必然在時空上存在著偏移,并體現在延伸主體與壓縮外部世界兩個方面,這種時空偏移的特性決定了媒介在功能上各不相同的時空特性。因此,作為中國社會背景中的傳播媒介,必然帶有鮮明的社會烙印,伴隨著中國社會結構的轉變,與此同時,伴隨著媒介技術的革新和演變,在不同的社會歷史時期,在媒介的不斷進化之中,媒介的功能也隨之變化、拓展與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