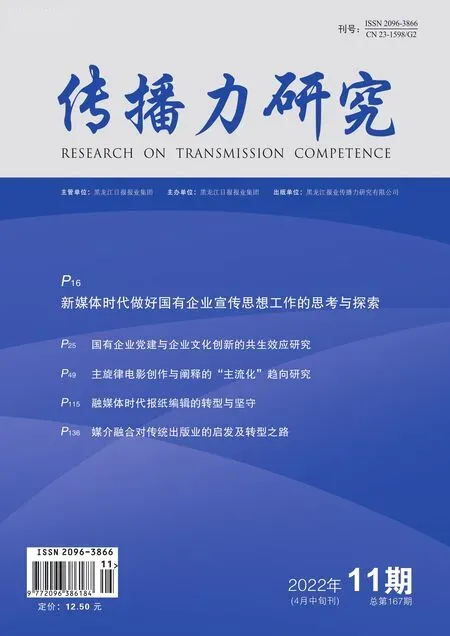書籍史寫作的新探索
——以《書的大歷史:六千年的演化和變遷》為例
◎胡群英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北京 100010)
在數字化時代,閱讀方式和習慣正悄然發生著變化。人們越來越多地通過屏幕(網絡在線閱讀、手機閱讀、電子閱讀器閱讀、平板電腦閱讀等)而不是紙質媒介進行閱讀。紙質書籍的地位和它的未來受到前所未有的質疑。書籍過時了嗎?書籍會消亡嗎?這樣的話題每每都會引起熱烈的討論。
在眾聲喧嘩中,一些學者和愛書人士開始回頭去盤點紙質書籍的歷史,探究書籍如何成為人類文明的最強搬運工,以及書籍是如何誕生和延續至今的。這樣的熱潮也相應催生了書籍史研究的新視角,以及書籍史寫作的新探索。本文即以《書的大歷史:六千年的演化和變遷》為例,嘗試從研究范式、謀篇布局、書寫模式、寫作視角四個方面對書籍史類圖書的寫作做一些探討和分析。
一、從傳統書籍史到新書籍史
書籍有自身的歷史。書史悠久的中國和歐洲都有著豐富的書史資源,中西文獻學研究各自具有深厚的傳統。自20世紀中葉以來,西方學術界興起了文獻學與史學、社會學等其他學科相結合的書籍史研究。它“以書籍為中心,研究書籍創作、生產、流通、接受和流傳等書籍生命周期中的各個環節及其參與者,探討書籍生產和傳播形式的演變歷史和規律,以及與其所處社會文化環境之間的相互關系”①。為區別傳統書籍史研究,學術界把這種書籍史稱為新書籍史,或書籍社會史。作為突破傳統文獻研究樊籬的一個跨學科研究領域,新書籍史既代表了現代學術的新范式,又帶有明顯的西方學術印記。
中國書籍史研究也興起于20世紀上半葉。1917年,葉德輝用文言文寫出了中國書史的發軔之作《書林清話》。1931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了陳彬龢、查猛濟二人合撰的《中國書史》,收入《萬有文庫》叢書。這是我國第一部用白話文撰寫的、以“書史”命名的著作。根據文獻學者的考證,《中國書史》實際上是抄錄葉德輝《書林清話》和袁同禮相關論文拼湊成的。②因此,中國書籍史研究一開始就受到傳統版本目錄學以及近代圖書館學的影響,多采取古典文獻學、目錄學、版本學、校勘學等路徑,“關注的焦點是書籍本身的發展史,即書籍的形制演變、編纂、出版、流通、收藏等等”③。
比較國內外的書籍史研究,兩者在研究內容、研究范式、史料選擇、文本分析等方面,存在著明顯的文化差異。④傳統書籍史和新書籍史研究之間也存在諸多類似的差異。就關注的焦點而言,傳統書籍史更注重就書談書,將書籍看作由紙張、墨水、硬紙板和膠水制作而成的物理客體,一件藝術品。新書籍史則更注重由內而外進行擴展,將書籍看作具有廣泛社會聯系的、活躍的、有生命的主體,“歷史中的一股力量”⑤。
基于對語言、符號和古籍的濃烈興趣和探究成果,基思·休斯敦(Keith Houston)結集出版的《書的大歷史》體現了對書籍史寫作的新探索。《書的大歷史》以實體書籍本身為探究對象,立足于傳統書籍史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新書籍史的影響,是一部縱觀古今、橫越東西的書籍制作史,也是一部理解人類如何傳承知識的文化史。基思·休斯敦在前言中即指出:“本書探討的是文明進步中安靜的最強知識載體,它淘汰了泥土書寫板、莎草紙卷軸、蠟制書寫板,將人類的歷史代代相傳。”⑥
二、從線性敘事到非線性書寫
為了探究書籍最初的模樣,以及書籍在幾千年中是怎樣延續至今的,無數愛書人士對書籍的歷史非常感興趣。關于書籍的歷史,普洛斯佩爾·馬爾尚(Prosper Marchand)在《印刷術的歷史》一書的序言部分感嘆道:“或許,從沒有一個主題被這么多人或偶然或有意地研究過;然而,也從沒有一個主題如此不為人知。”⑦
此類研究成果中,有的從文字的從無到有講起,有的從紙張的從無到有講起,有的只從紙張傳入歐洲開始講起,有的甚至是從印刷術的出現開始講起。許多書都按歷史的發展階段,“根據似是而非的時間標志進行章節劃分”⑧,籠統地介紹書籍全面的歷史(諸如版本學、校勘學、編輯史、印刷史、出版史、發行史、藏書史、閱讀史)和演變進程。實踐證明,如果只是簡單地羅列“資料的歷史”,無論是從宏觀上進行縱向的通史性研究,還是深入地進行多類型、多角度的專題性研究,都是非常挑戰讀者耐心的。要讓內容讀起來輕松愉悅,非常考驗作者謀篇布局、取舍史料的功力。
蘇聯科普作家伊林所著《書的故事》文筆通俗曉暢,是一本介紹書籍歷史的入門讀物。伊林認為,在文字出現之前,“這世界上第一本書,一點不像現在我們所有的書。這第一本書是有手有腳的。它并不放在書架子上面。它能說話,也能唱歌。總之,這是一本活的書:這就是人”⑨;文字出現之后,永久的書(載體為石頭、黃銅、磚塊等)、帶的書(載體為卷軸)、蠟的書(載體為蠟板)、皮的書(載體為羊皮紙)、紙的書(載體為真正的紙張)相繼以不同的載體展開了自己的命運。
在基思·休斯敦看來,載體的變化無疑也是梳理書籍的歷史時不可忽視的一條主線,《書的大歷史》第一部分即追溯了莎草紙的發明、羊皮紙的問世,以及現代紙張的起源和走向全球的歷程。但是基思·休斯敦并不滿足于單線敘述,而是廣泛搜集文獻資料,并抽絲剝繭地提取出了構成“書”的四個重要方面——紙張、文字、插圖、形制,分別從造紙、文字、插圖和裝幀四大元素追溯書籍的發展脈絡,將制書技藝的變遷化為躍然紙上的動人故事。這四個方面在時間上有重合,在內容上卻不重復,這樣的非線性書寫結構清晰、有機融合,實現了歷時性研究和共時性研究的均衡布局,體現了書籍史寫作的新探索。
三、從板正“求真”到趣味科普
“書寫歷史,也即要對過去進行梳理和界定,要羅列諸多材料,目的是為當今建立起一種理性;另外,在書寫歷史的過程中,應力圖消除口述性,拒絕不實之詞。”⑩在這種書寫建構下,書寫真正全球意義上的“書”的大歷史,有賴于對海量中西書籍歷史資源和文化資源的巧妙梳理,以及深入展開的比較研究。
基思·休斯敦不是把做書(出版)視為一種冷冰冰的行業去“求真求實”,而是致力于講述六千年來人類做書的故事,以及人類在做書這一件事情上所展示出來的聰明才智和瘋狂之舉,從而為讀者呈現出一個內涵豐富而又生動的書史世界。這種講故事式科普的寫作方式,觸及許多有趣的“知識盲區”,也關注到一些前人所忽視的細節。
在書中,作者分享了一些令人悚然的冷知識:美國人曾進口埃及木乃伊用于造紙和當柴火燒;一些既沒錢又沒底線的人,為了制作上等“象牙墨”而竊取墓中的人骨;一些書的封面居然是用人皮制作的,至今保存完好,收藏在圖書館;有彈性的莎草紙卷軸居然有致命風險,年邁的羅馬元老院成員維吉尼烏斯·魯弗斯就是在取莎草紙卷軸的時候,受到彈性襲擊摔倒而最終喪命,等等。
此外,作者也講述了不少做書歷史上的趣事,包括一些不成功的嘗試或者不經意的發明,如馬克·吐溫投資“佩奇排字機”、《美洲鳥類》以眾籌方式出版、塞內費爾德偶然發現石版印刷術等等。當然,這些故事并非是故意博人眼球的“不實之詞”,而是有史為證的。它們不光提升了閱讀的趣味,還為嚴謹的學術研究提供了一些啟發。(11)
細節呈現方面,《書的大歷史》所做的探索尤為可圈可點。圍繞如何制作書籍,以及制作工藝、加工方法、制作材料和所用工具在六千年中經歷了怎樣零敲碎打的改良,基思·休斯敦平實仔細的文字描述,幾乎達至了視頻、影像的效果,讀者一看就懂,甚至可以如法炮制。以泥金裝飾手抄本的制作工藝為例,畫線、繕寫文字、裝飾、涂色等工序都有精彩的介紹,尤其上底漆、貼金、打磨、固定、繪圖、上色等裝飾工作如在眼前,中世紀手抄本的生產線細節一目了然。又如,書籍裝幀部分,涉及開本、尺寸、折頁等技術性比較強的知識,讀者甚至可以跟著書中的文字介紹,動手折一折、裁一裁,感受不同開本的大小,“見證”書籍形態從卷軸、折本到分頁的演進。
四、從技術視角到文化視角
“書籍史乃至出版史,某種程度上也是關于人類或人類文明的歷史,而其除展示人類改造自然與社會等的事功,更深層意義則是展示人的思想智慧的發展軌跡以及人性等問題。”(12)文化史的視角,無疑是書籍史研究中最為重要的視角之一。以《書的大歷史》為例,這一視角上的寫作嘗試值得關注。
基思·休斯敦固然對制書技藝的歷史非常感興趣,但他并不局限于狹隘的技術決定論。在書籍技術史的梳理中,蔡倫、畢昇、谷登堡等毋庸置疑是閃亮耀眼的明星,但驅動著“書”不斷向前發展的,還有更多不太為人看重的邊緣人物。他們是眾多“以失敗告終”的發明者或投資者、默默無聞的工匠、普通的抄寫員、心高氣傲的出版商等等。
就書寫材料而言,中國的造紙術傳到阿拉伯世界、北非以及歐洲之后,默默無聞的造紙工匠們因地制宜,不斷對造紙工藝進行著看似“一點也不復雜”(13)的改良,如用機械驅動的漿輪替代巨大的攪拌棒,以水力驅動的錘子取代沉重的大石頭。這些改良大大提高了生產效率,卻帶來了一個意想不到的問題:造紙原材料的短缺。在歐洲和美國,廢舊亞麻布料短缺的問題越來越嚴重,一直延續至現代。各路好事者嘗試過用石棉、玉米殼、海草、玉米、稻草、棕櫚葉以及其他奇奇怪怪的材料作為破布頭的替代品。在中國,蔡倫最初利用的麻、構樹皮等傳統原材料也逐漸不能滿足生產需要,人們先后嘗試用竹子、蘆葦、麥草、蒲草、蔗渣等進行造紙。19世紀中期,使用木漿造紙的想法在歐洲落到實處,以木材為原料的機械化造紙廠在世界各地迅速發展起來。至此,造紙商們終于擺脫了原材料不足的束縛,圖書行業急劇發展壯大。
“從任何角度來說,這都是一場革命。”(14)為了讓讀者一窺這一關鍵片刻,基思·休斯敦注重從人性、從個人生活史的角度切入并展開,講述了法國博物學家雷奧穆·費雷爾特·德·雷奧米爾、德國鄉下織工弗里德里希·戈特洛布·凱勒、薩克森造紙商海因里希·弗爾特、法國造紙廠普通職員路易斯-尼古拉斯·羅伯特等人的故事。首先,是使用木漿造紙這一想法的提出:1719年,雷奧米爾觀察到黃蜂用咀嚼過的木漿制作出質地像紙一樣的巢穴,提問人類能不能模仿這些勤勞的昆蟲制造出真正的紙張。其次,是受這一想法啟發而誕生的發明:1844年,凱勒制造了一臺用石輥碾碎木材的破碎機,利用生成的木漿制作出了紙張,并成功申請到專利。然后,是這一發明的落地開花:1846年,為了從自己的發明中獲利,凱勒與造紙商海因里希·弗爾特合伙;1852年,因流程不夠成熟,工業化生產未能實現,凱勒無法支付專利續展費,此項專利歸弗爾特一人所有;1859年,弗爾特攜手工程師約翰·馬休斯·福伊特,大規模生產凱勒發明的碎木機。于是弗爾特一夜暴富,福伊特成為現代造紙業的先驅,可憐的凱勒卻什么也沒得到。
書籍制作技術每一次或大或小的創新,背后都可能存在著凱勒這樣不得志的發明家、默默無聞的工匠、追逐利潤的投資者。腦洞大開的發明家專注于發現與突破,卻不一定是優秀的商人,難以獲得預想中的經濟回報,甚至還因此而窮困潦倒。追逐利潤的投資者有可能如海因里希·弗爾特眼光獨到、一夜暴富,也有可能像投資排字機的馬克·吐溫那樣屢戰屢敗、血本無歸。但也正是靠了這無數人六千年中的不懈摸索,書籍這一最悠久的知識儲存工具才能得以成形并持續至今。
以上所做的種種新探索,既與作者基思·休斯敦的研究志趣和關注重點密不可分,也奠基于中西書籍史研究的學術傳承。《書的大歷史》更致力于面向大眾普及新知,在有趣的故事背后“為當今建立起一種理性”,揭示出驅動這些技術進步的主要原因,是人類或基于追求經濟利益,或基于求索新知的欲望,或基于信仰宗教的虔誠而不斷產生的新需求。數千年來,從莎草紙到羊皮紙,從黏土泥板到刻字蠟板,從雕版印刷到凹版印刷,從卷軸到分頁,書籍制作技術始終受到文化、政治、宗教的牽動。
今天,電子書在一定程度上構成了對實體書籍的威脅。但根據艾瑞咨詢發布的《2021年中國圖書市場研究報告》,紙質書、電子書、有聲的用戶閱讀時長在2020年均實現增長,且紙質書和有聲的時長較電子書的增長更多。統計數據表明,紙質書依然表現堅挺,書的大歷史仍在繼續,對書籍史寫作的探索也還會繼續。
注釋:
①[英]戴維·芬克爾斯坦、阿里斯泰爾·麥克利里著,何朝暉譯:《書史導論》,商務印書館2012年版,第6頁。
②江曦:《陳彬龢、查猛濟<中國書史>考辨》,《圖書館雜志》2018年第6期。
③何朝暉:《為了將來多元書文化的溝通和對話——<書史導論>譯者前言》,《中華讀書報》2012年3月28日10 版。
④郭平興:《不一樣的書籍觀:論中西方書籍史的差異》,《出版科學》2015年第4期。
⑤[美]羅伯特·達恩頓著,葉桐、顧杭譯:《啟蒙運動的生意:<百科全書>出版史(1775—1800)》,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年版,第2頁。
⑥[英]基思·休斯敦著,伊玉巖、邵慧敏譯,《書的大歷史:六千年的演化與變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0年版,第3頁。
⑦[法]呂西安·費弗爾、亨利-讓·馬丁著,和燦欣譯:《書籍的歷史:從手抄本到印刷書》,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19年版,第1頁。
⑧[法]呂西安·費弗爾、亨利-讓·馬丁著,和燦欣譯:《書籍的歷史:從手抄本到印刷書》,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19年版,第6頁。
⑨[蘇]伊林著,胡愈之譯:《書的故事》,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版,第4頁。
⑩[法]米歇爾·德·塞爾托著,倪復生譯:《歷史書寫》,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26頁。
(11)張正萍:《“書感”的來源——讀<書的大歷史>》,《書城》2021年第5期。
(12)馬曉翔、王宏波:《書史理論:以社會視角觀照書籍的歷史》,《出版廣角》2018年22期。
(13)[英]基思·休斯敦著,伊玉巖、邵慧敏譯,《書的大歷史:六千年的演化與變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0年版,第58頁。
(14)[英]基思·休斯敦著,伊玉巖、邵慧敏譯,《書的大歷史:六千年的演化與變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0年版,第6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