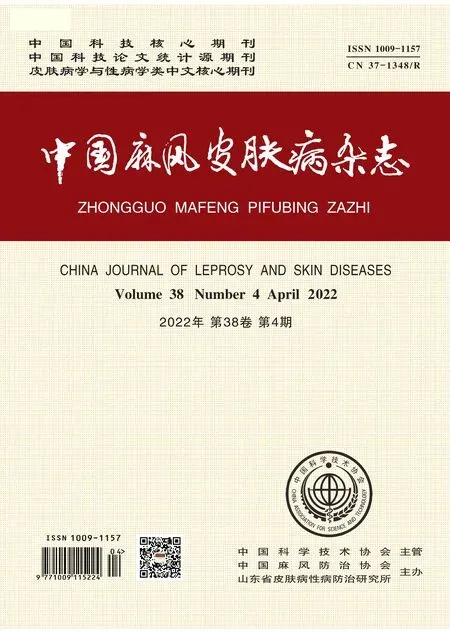外用磷酸二酯酶4抑制劑軟膏治療斑禿一例附文獻復習
張 帆 糜自豪 孫勇虎
山東第一醫科大學附屬皮膚病醫院(山東省皮膚病醫院),山東省皮膚病性病防治研究所,濟南,250022
1 臨床資料
患者,男,35歲。因毛發片狀脫失5天就診。患者5天前頭皮出現斑狀毛發脫失。自訴發病前工作壓力較大、睡眠質量差。個人史:從事科研類工作。家族中無類似病史。皮膚科檢查:頭部一直徑2 cm的圓形毛發脫失斑,局部皮膚光滑發亮,無炎癥浸潤現象(圖1)。皮膚鏡檢查:鏡下可見斷發、黑點征(圖2)。治療:外用磷酸二酯酶4(PDE-4)抑制劑(克立硼羅軟膏),每日2次(患者拒絕使用糖皮質激素類藥物,經與患者充分溝通并簽署知情同意后應用克立硼羅軟膏)。治療1個月后,患者出現約40%新生發,色澤黑,鏡下可見短毳毛,拉發實驗陰性。2個月后患處痊愈,斑禿區毛發完全再生,分布密度、粗細及色澤與周圍正常毛發相似。

圖1 1a:治療前可見患者頭部一橢圓形毛發脫失斑片,表面皮膚光滑,無炎性浸潤;1b:治療1個月后部分毛發再生;1c:治療2個月后毛發完全再生

圖2 2a:治療前鏡下見黑點征、斷發及多發點狀凹陷(點陣激光治療后);2b:治療1個月后鏡下見少量直立新生發,可見線狀分支狀血管結構,未見明顯黑點征;2c:治療2個月后鏡下見多發直立新生發,頭皮見大量線狀分支狀血管結構,未見空毛囊
2 討論
斑禿(alopecia areata,AA)是較為常見的非瘢痕性脫發,全球患病率為1/1000。斑禿嚴重程度不一,常表現為圓形或卵圓形非瘢痕性毛發脫失斑,嚴重者可出現全禿或普禿。斑禿除累及毛囊外,還可影響指甲,可造成甲脆裂、點狀凹陷、甲粗糙等,約發生在10%~20%的患者中[1]。
斑禿發病機制包括遺傳易感因素、免疫因素、環境因素。斑禿更容易發生在有家族史的患者中。我國學者對1032例斑禿患者研究發現,斑禿具有明顯的遺傳傾向[2]。小鼠模型同樣顯示出斑禿是一種復雜的多基因疾病。全基因組關聯研究發現了許多控制免疫表型的單核苷酸多態性。包括編碼調節性T細胞、細胞毒性T細胞的活化和增殖,控制白細胞介素的表達及抗原提呈的基因。HLA基因已經被確定為決定該疾病表型的主要基因。除此之外,位于6號染色體上負責編碼自然殺傷細胞受體D及其配體NKG2DL3和維甲酸早期轉錄1L蛋白的基因,已被發現僅與斑禿有關,與其它自身免疫性疾病無關,表明該基因在本病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3]。
T細胞介導的自身免疫反應也已被證明在斑禿中發生。在受脫發影響的人類和小鼠的皮膚生長期,CD4+T細胞與CD8+T細胞及IFN-γ和IL-15等細胞因子被發現一起位于毛囊中。在慢性斑禿小鼠模型中,去除CD4+和CD8+細胞的單克隆抗體可以促進毛發再生。此外,斑禿患者體內存在抗毛囊IgG抗體,減少抗體后頭發再生[4]。以上都導致了毛囊的免疫豁免機制被破壞,隨后毛囊在炎性細胞浸潤、細胞因子釋放及細胞毒性T細胞的作用下被破環,最后導致毛發脫落。在8%~27%的斑禿患者中可合并甲狀腺炎。斑禿患者中白癜風的發病率在4%~7%之間[5]。而在對患者隨訪過程中,斑禿痊愈后患者由于不明原因發熱被診斷出甲狀腺炎。這也從另一方面說明,自身免疫改變是斑禿發病的一個重要原因。
心理應激也被認為與斑禿的發生有關。從生物學的角度來看,免疫細胞如T細胞、B細胞,樹突狀細胞和巨噬細胞可以與膽堿能系統相互作用。在急性應激狀態下,乙酰膽堿等激素的上調可導致免疫細胞功能的調節以及腫瘤壞死因子-α、干擾素-γ和白介素-6的分泌上調[6]。環境因素例如病原體感染、幽門螺旋桿菌等微生物的感染、其他慢性炎癥等均可能通過不同機制導致斑禿。綜上來看,斑禿的發病是一個多因素綜合致病的一種復雜自身免疫性疾病。
發病機制的復雜性及慢性復發性導致斑禿的治療并不樂觀。目前已發展了多種治療手段。2018年澳大利亞發表的治療指南指出,持續6個月以上的孤立性穩定斑禿、活動性斑禿及多發斑禿都是治療適應癥。一般將兒童局部使用高效糖皮質激素,成人每4~6周皮損內注射糖皮質激素作為一線治療。對以上治療無效的患者應考慮進行局部免疫治療、米諾地爾或全身治療。局部免疫治療的藥物包括二苯基環丙烯、二硝基氯苯等。全身治療包括口服糖皮質激素,80%的患者可以取得臨床反應,而至少11%的患者對大劑量糖皮質激素治療仍無效。50%的患者會在減藥過程中或停藥后復發。其他免疫抑制類藥物可選用甲氨蝶呤、環孢素、硫唑嘌呤聯合糖皮質激素治療[7]。面對局部應用糖皮質激素帶來的皮膚萎縮、毛細血管擴張等不良反應,一些新興藥物或技術手段也開始應用。JAK抑制劑是選擇性抑制JAK1、JAK2、JAK3和酪氨酸激酶2的新興生物靶向藥,可以阻斷IFN-γ等細胞因子與其受體的結合,從而干擾STAT與JAK的信號傳導及接下來的基因轉錄,最終抑制炎癥的發生[8]。在經過外用JAK抑制劑涂抹的小鼠模型中,4周的時間便觀察到毛發的再生,并發現皮損處的炎性細胞浸潤明顯減少。JAK抑制劑在人類斑禿患者應用的研究中,口服劑型效果顯著,但長期大量使用不可避免出現一定的不良反應。由于人類皮膚與小鼠皮膚相比更厚、穿透性更差,外用劑型始終沒有找到很好的配方比例。這限制了此類藥物在斑禿中的應用[9]。除此之外,脈沖激光、光療等物理療法也在一些斑禿患者中取得療效[10,11]。但此類多作為糖皮質激素治療的輔助用藥,治療費用及要求患者定期治療等問題限制了其廣泛應用。
磷酸二酯酶-4(PDE-4)主要分布于免疫細胞、上皮細胞和腦細胞,是一種調節炎癥和上皮完整性的細胞內非受體酶。其通過對cAMP的降解作用增加了致炎細胞因子,如IL-4、IL-5、IL-10、IL-13以及前列腺素E2產生,導致T細胞活性失調,調節T細胞減少而輔助T細胞(Th2)增加。體外研究表明,PDE-4抑制劑可以減少IFN-γ、TNF-α和IL-2的分泌[12]。2014年開展的一項體內研究,在成功開發的兩組斑禿小鼠模型中,提前注射PDE-4抑制劑的實驗組中僅15%出現脫發,而未作處理的對照組86%出現脫發。這從一定程度上證明了PDE-4抑制劑可以對抗炎癥因子從而有效改善斑禿[13]。印度學者[14]一項關于阿普斯特(口服PDE-4抑制劑)治療15例斑禿患者的回顧性研究發現,阿普斯特治療有效率達到100%,但高達73.3%的患者出現惡心、嘔吐和腹瀉等胃腸道不良反應。為了避免毒副作用,外用PDE-4抑制劑開始被研制使用。新型制劑克立硼羅是一種以硼為基礎的苯并硼唑(benzoxaborole)PDE-4抑制劑,已被嘗試用于特應性皮炎、銀屑病、白癜風、脂溢性皮炎、炎性線狀表皮痣等皮膚病并取得了令人滿意的臨床效果。我們推測外用PDE-4抑制劑可以直接作用于應用區域,局部起到抑制炎癥產生的作用,在避免胃腸道反應的情況下達到與口服相同的效果。
斑禿雖有較為特征性的臨床表現,但尚不明確的發病機制給治療帶來一定困難。對于輕度亞型多以糖皮質激素軟膏為一線治療,難治型及中重度患者可以多種方案聯合治療。在我們的患者外用PDE-4抑制劑治療的1個月后,可見明顯新生毛發,2個月后痊愈,尚無復發,顯示出PDE-4治療斑禿快速、有效的特點。國內外關于外用PDE-4抑制劑治療斑禿缺少相關報道,目前國外一項關于外用克立硼羅治療斑禿的2期研究正在開展(臨床試驗注冊號編碼NCT04299503)。尚需更充分臨床證據檢驗PDE-4抑制劑的安全性及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