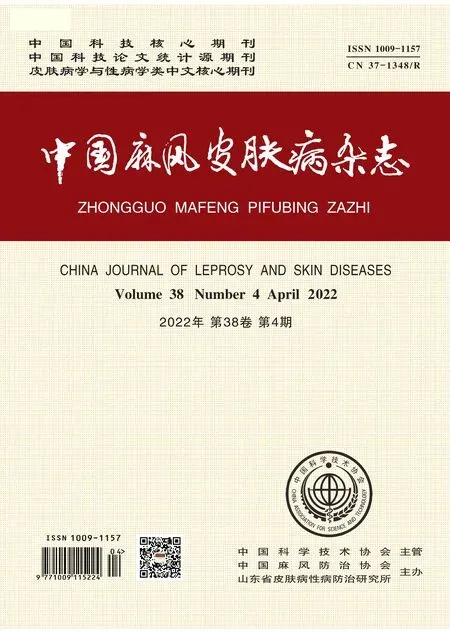硬化性苔蘚合并扁平苔蘚、硬斑病一例并文獻復習
呂嘉琪 常建民
1 北京醫院皮膚科 國家老年醫學中心 中國醫學科學院老年醫學研究院,北京,100730;2 北京協和醫學院研究生院,北京,100730
硬化性苔蘚(lichen sclerosus, LS)、扁平苔蘚(lichen planus, LP)和硬斑病是三種病因不明的皮膚病。已有多篇文獻報道LS可與硬斑病并存[1],亦有報道硬斑病或LS合并LP的案例[2,3]。更為少見的情況下,患者可同患LS、LP和硬斑病,目前未見國內有相關報道。本文報道1例LS合并LP和硬斑病患者,并對國外已報道的類似病例進行回顧性分析。
1 資料和方法
1.1 資料來源 北京醫院于2021年5月接診的LS合并LP和硬斑病1例,根據臨床表現及皮膚病理結果確診。從 Pubmed檢索并篩選出1985年1月至2021年6月報道的LS合并LP和硬斑病7例[4-7],結合本文1例患者,共8例(表1)。

表1 LS并LP、硬斑病8例分析匯總
1.2 方法 以“lichen sclerosus”或“lichen sclerosus et atrophicus”組合“morphea”或“scleroderma”或“lichen planus”為關鍵詞檢索Pubmed,排除未同時合并LS、LP與硬斑病的患者,共有7例LS合并LP和硬斑病的報道。以“硬化性苔蘚”組合“硬斑病”或“硬皮病”組合“扁平苔蘚”為關鍵詞檢索中國知網、萬方、維普、SinoMed數據庫,未見報道。收集所有入選病例資料,包括性別、年齡、三種疾病發病順序、病變部位、臨床表現、病理特點、實驗室檢查結果、既往史與家族史、治療方案及轉歸。
2 結果
2.1 一般資料 男2例,女6例,男女比例為1∶3。年齡39~76歲,平均(60.3±15.1)歲。6例患者LS與硬斑病幾乎同時發生,2例硬斑病發病早于LS且發病時間相差兩年之內,3例LS、LP與硬斑病的發病彼此之間均相差一年之內。4例在最初發病3年內被診斷出患有全部三種疾病。3例患者LP發病早于LS和硬斑病,3例患者LP發病晚于LS和硬斑病。
2.2 病變部位 3例LS發生于生殖器皮膚,5例LS發生于生殖器外皮膚。5例硬斑病累及軀干,4例硬斑病累及四肢,5例為泛發型硬斑病。例2的LS和硬斑病發生于同一皮損處。3例LP局限于口腔黏膜,4例LP累及軀干、四肢,3例LP累及生殖器。
2.3 臨床表現 8例患者中,生殖器LS皮損主要表現為生殖器皮膚萎縮性色素減退斑伴局部硬化,其中患者5見小陰唇融合,本例見小陰唇與陰道有紅斑、糜爛;生殖器外LS和硬斑病主要表現為硬化性斑塊伴有萎縮和色素沉著或色素減退,部分皮損可見紫紅色邊緣,臨床上難以將兩者區分開。4例有詳細的LP相關臨床表現的描述,外陰LP主要表現為外陰糜爛伴灼痛感,皮膚LP表現為多發性紫羅蘭色多角形丘疹伴脫屑,其中患者1可見口腔黏膜糜爛、潰瘍性色素脫失斑,患者2可見軀干多發表淺性潰瘍。
2.4 組織病理 患者2肩部、腹部、足踝硬化性斑塊的病理改變均同時符合LS和硬斑病,表現為角化過度,表皮萎縮,皮突變平,基底層灶狀液化變性,真皮淺層均質化,真皮中下層膠原纖維腫脹,可見附屬器擠壓現象,真皮血管周圍可見少許淋巴細胞為主的炎細胞浸潤。其余患者均在不同切片下分別可見典型的硬斑病或LS病理改變。8例患者LP皮損均見基底層液化變性,真皮淺中層淋巴細胞帶狀浸潤。
2.5 實驗室檢查 7例完善了三大常規、自身抗體等檢測及胸部X線片、腹部B超等系統篩查并報道了異常結果,其中白細胞計數減少2例,抗甲狀腺抗體升高2例,嗜酸粒細胞百分比升高和抗核抗體(ANA)陽性各1例,多克隆性IgM升高1例,梅毒非特異性血清學試驗陽性1例,輕度肝功能異常1例;2例用酶聯免疫吸附法檢測了伯氏疏螺旋體抗體,均為陰性。
2.6 既往史與家族史 6例患自身免疫性疾病,其中斑禿1例,橋本甲狀腺炎2例,白癜風1例,系統性硬化癥1例,2型糖尿病1例。1例有白癜風和硬斑病家族史。
2.7 治療與轉歸 4例報道了治療方案,其外用藥均以強效糖皮質激素為主,3例聯合系統用藥,包括灰黃霉素、羥氯喹和糖皮質激素和積雪苷片等,多數皮損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
2.8 典型病例 患者,女,67歲。背部斑塊7年,外陰色素減退伴瘙癢5年。7年前背部出現瓷白色丘疹,無明顯自覺癥狀,皮損逐漸增多、融合,未診治。5年前外陰出現色素減退斑,伴瘙癢,曾外用藥膏于外陰皮損處(具體不詳),療效不佳。3年前小陰唇出現紅斑,伴輕微疼痛和燒灼感,未診治。既往患2型糖尿病。家族史無特殊。體格檢查:系統檢查未見異常。皮膚科檢查:背部一約5 cm×5 cm瓷白色斑塊,表面萎縮,觸之有皮革樣硬度,周邊見瓷白色丘疹、輕度色素沉著;大、小陰唇及前、后聯合散在白斑,大、小陰唇及陰蒂局部萎縮,小陰唇內側、陰道散在紅斑、糜爛(圖1)。口腔黏膜未見異常。背部皮損組織病理示:真皮全層膠原纖維增生硬化,可見灶狀淋巴細胞浸潤,符合硬斑病;陰唇前聯合組織病理示:棘層萎縮,真皮淺層均質化,其下方淋巴細胞呈苔蘚樣浸潤,符合LS;陰道皮損組織病理示:棘層萎縮,基底層液化變性,真皮淺層淋巴細胞為主的炎細胞苔蘚樣浸潤,符合LP(圖2)。血、尿、便常規及肝腎功能、血糖、血脂、免疫球蛋白、補體均正常,抗核抗體譜、類風濕因子均為陰性。心電圖、胸部X線片與肝膽胰脾雙腎B超均正常。給予積雪苷片口服,鹵米松乳膏外涂于外陰患處;鹵米松乳膏與多磺酸粘多糖外涂于背部患處。治療1個月后背部斑塊稍軟化,外陰癥狀緩解。目前患者仍在隨訪中。

圖1 1a:背部約5 cm×5 cm萎縮性瓷白色斑塊,周邊見瓷白色丘疹、色素沉著;1b:大、小陰唇及前、后聯合散在白斑,大、小陰唇及陰蒂局部萎縮,小陰唇內側、陰道散在紅斑、糜爛

圖2 2a:背部皮損病理示真皮膠原纖維增生硬化,灶狀淋巴細胞浸潤(HE,×40);2b:陰唇前聯合病理示棘層萎縮,真皮淺層均質化,其下方淋巴細胞呈苔蘚樣浸潤(HE,×40);2c:陰道皮損病理示棘層萎縮,基底層液化變性,真皮淺層淋巴細胞為主的炎細胞帶狀浸潤(HE,×40)
3 討論
LS和硬斑病發病均涉及免疫系統的活化與失調、自身免疫、感染、膠原代謝異常等,Thomas等[8]報道357例女性LS中有10例患硬斑病,Kreuter等[9]報道472例局限性硬皮病中5.7%患LS。LS和硬斑病可共存于同一皮損處,從同一部位多次活檢的病理結果中亦可觀察到LS轉變為硬斑病,關于LS是否為淺表性硬斑病目前仍有爭議[10]。發病順序上,文獻報道LS的發病與局限性硬皮病同時發生或晚于局限性硬皮病[6,9],與本文結果相符。LS和LP臨床上均可見同形反應,病理上均可見基底細胞液化變性和淋巴細胞帶狀浸潤,病情早期兩者在病理上很難區分,故有學者認為它們可能屬于同一病譜[11]。本文中,1例患者的同一切片并存LS和硬斑病病理特點,預示LS和硬斑病亦可能屬同一病譜,且其可出現在LP患者中,這表明三者可能有相似的病因或相關的病理過程。
LS、LP和硬斑病發病機制均與輔助性T 細胞(helper T cell,Th 細胞)浸潤相關。LS和LP均為T細胞介導的針對鱗狀上皮基底細胞未知免疫表型的炎癥性皮膚病,其共同免疫學特征是大量Th1細胞浸潤及Th1特異性細胞因子水平(干擾素-γ、腫瘤壞死因子-α、白細胞介素-1α、白細胞介素-6、白細胞介素-8)升高[12],microRNA-155表達增強[13],IFN-γ 受體、CD25、CD11a 和 細胞間黏附分子1上調[12],這可能表明這兩種疾病是對相似觸發因素的不同反應。硬斑病初期炎癥階段以Th1細胞浸潤為主,同時伴Th17細胞浸潤;在疾病晚期,Th2細胞出現,CD4+Th2淋巴細胞產生的白細胞介素-4可上調T細胞和其他細胞產生的轉化生長因子-β[14],進而能夠刺激成纖維細胞合成膠原和其他細胞外基質蛋白,故Th2細胞水平與纖維化程度相關[15];與LS和LP類似,硬斑病中亦可見血管黏附分子的表達上調,包括血管細胞黏附分子-1、細胞間黏附分子-1及E-選擇素,其可促進T細胞募集,進而促進硬化發生[14,16]。
慢性移植物抗宿主病(graft-versus-host disease,GVHD)是具有免疫能力的移植細胞對抗原性異種宿主組織產生的免疫反應,最常累及皮膚,其不同階段可產生類似于LP、LS和硬斑病的臨床表現:病情初期可見經典的LP樣皮疹,20%的患者在初次接受慢性GVHD的系統性治療后3年內出現了皮膚硬化[17]。當硬化累及淺表真皮時,病變類似于LS,呈白色或灰色薄斑塊伴皮膚紋理加重,好發于上背部;當硬化累及真皮中深部時,皮損表現為硬斑病樣[18],呈色素沉著過度、色素沉著減少或皮色的質硬斑塊。嗜酸粒細胞增多、多克隆性IgG或IgM水平升高、自身抗體陽性和肝功能異常是慢性GVHD的常見的實驗室發現[19],本研究中4例患者亦存在類似的實驗室異常結果,由此發現GVHD這種由單一誘發因素(器官或組織移植)引起的形態學和實驗室檢查的異常與本研究中各患者的疾病表現相似。GVHD是一種醫源性疾病,研究其皮膚病變的發病機制可能有助于加強對LS合并LP、硬斑病發病機制的認識。
本研究中所有病例均存在異常免疫反應,患斑禿、白癜風、系統性硬化癥、自身免疫性甲狀腺疾病、2型糖尿病或存在白細胞減少、嗜酸粒細胞增多、梅毒血清學試驗假陽性等實驗室檢查結果提示患者存在免疫細胞或自身抗體異常,故臨床上對LS、LP合并硬斑病患者應注意行實驗室檢查和系統篩查以除外潛在的相關系統疾病。
通過適當用藥,多數患者的病情可在3個月內得到控制[5]。LS和糜爛性外陰LP患者鱗癌的發生率均增加,需警惕惡變可能,定期隨訪。對于LS合并LP、硬斑病患者,治療方案應視個體情況而定,三者的一線治療為局部外用或皮損內注射糖皮質激素,皮損嚴重、難治或泛發時可全身應用糖皮質激素或免疫抑制劑,但系統治療證據有限。
所有患硬斑病和生殖器外LS的患者,尤其是女性,都應檢查其生殖器以除外生殖器LS和LP[8]。外陰LS合并外陰LP并不罕見,臨床上疑診其中一種病時應同時評估有無另一疾病存在可能[3]。本文暗示LS、LP和硬斑病間可能存在關聯,這可能為探索這些疾病的發病機制提供有價值的觀點,且繼續研究它們的發病機制亦有助于進一步了解三者可在同一患者中共存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