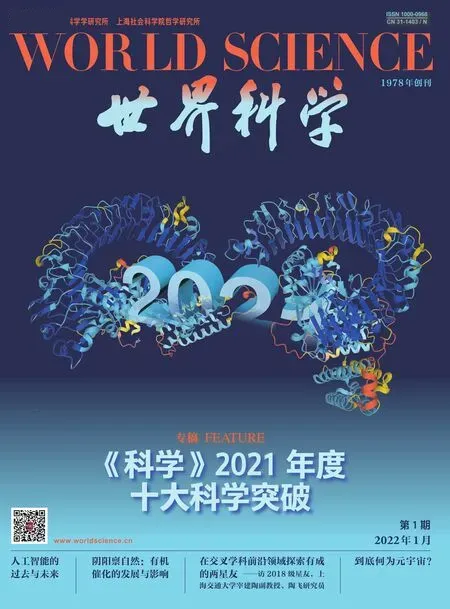交叉學科實踐及感悟
在今天這樣一個鼓勵創新,且基礎研究得到從未有過的重視程度的今天,很多人都會覺得走交叉學科之路勢在必行。但是這方面的成功案例并不多見。本次同時采訪宰建陶、陶飛兩位星友,也是因為他們在交叉學科探索方面已經有所成就、有所心得。他們談到了開展交叉學科的必要性,以及如何有效地推進交叉學科研究。希望這些觀點和建議能傳遞到有關科技管理部門并惠及更多星友。
兩星友交叉合作開新路
宰建陶:2013年我在賓州大看《半導體物理學》時,也在思考電子的能量等概念。啟明星交流會的那個晚上,當陶老師與我討論時,我馬上想到縈繞在腦海里的這樣一些概念。
陶 飛:2014年從麻省理工媒體實驗室回來后我一直心存一念——學會的蛋白質手藝不用就浪費了。1914年,科學家亞歷山大?貝爾(Alexander G. Bell)曾說:“除非你能測量出它們的相似和不同之處,否則就不可能有氣味科學。如果你雄心勃勃地想找到一門新的科學,那還是測量一下氣味。”這是因為氣味只能主觀描述,很難定量刻畫,譬如聞到蘋果味,你很難去告訴別人它的具體特征(如強度和類型)。那天和建陶見面,當我聊到這一節時,我們彼此都覺得可以在氣味傳感方面做點什么。例如,手機可以聽、看,可以感知,但它無法感知氣味,因為沒有氣味傳感器。當時還有報道說可以訓練狗去聞患者、老人的尿液,經過訓練的狗可以大致辨出氣味的不同組分,并且用來檢測癌癥。我們的氣味傳感器如能實現,就應該可以做到比狗更精準。氣味傳感是我倆交叉合作的第一個項目。這個項目的研究結果已經證實這一設想是可行的,而且效果是好的。
宰建陶:初次合作產出結果后,我們雙方找到了合作的感覺,建立了無話不談的合作關系。這就引出與雙碳和節能相關的第二個合作項目,也是這次準備在啟明星論壇上交流的內容。第三個是智能代謝重編研究的這個新的發展方向,陶飛團隊主要出課題研究框架和實施路徑,我的團隊提供高通量數據采集和解決電極的特殊要求。
陶 飛:還有一個正在醞釀籌備的合作是在學校致遠學院開設融通課程,培養生命、醫學、納米材料的交叉人才。想做這件事也是基于我們在合作中迫切需要培養一大批具有交叉學科意識、具備交叉學科探究知識儲備能力的人才。這一段時間我倆已經就具體如何落實商量了多次。
宰建陶:事實上海交大已在探索如何重構本科生培養體系,使他們能適應學科交叉發展的大趨勢。我在給醫學院拔尖人才班設計融通課程時,就提出要把氣味傳感器識別與大健康、人工智能結合起來開設一門課的想法。為這些未來的醫生開設這樣一種新型課程,可以讓他們提前介入交叉學科,為未來職業開闊思路。當然我們這個項目也有培育潛在的交叉學科合作者的用意。我正在擬寫建設 “化學生命融通實驗”這門課的計劃書,軟硬條件都要準備好,還需要申請場地資源、爭取經費。順利的話,2023年可以開課。
開展交叉學科應具備的能力和方法
宰建陶:就開展交叉學科應具備的能力而言,一種是個人的學科背景本身具有一定的跨度,有多學科背景,這樣自己跟自己交叉比較容易;第二種是不同合作者的雙方互補,如果只是單向的需求就很難持續。這種合作,首先是要能找到一個契合點。這對合作者的心胸、為人也都是有要求的,包括你愿不愿意與人分享自己的想法,愿意花時間并找到這樣的機會。其次,合作起點不能太難,不能一開始就需要雙方投入很多精力在一個未知的方向上,否則只會止步于想法。由易到難,合作雙方都做各自擅長的事,能夠很容易地解決對方或交叉課題的需求。如我們首次合作時,陶飛需要的納米材料在我們實驗室很容易就可以獲得。有了良好的開端,相互之間信任和默契也提升了,大家也愿意投入(或一起申請)更多的資金、資源去解決更深層次的科學問題。合作過程中雙方團隊之間會有很多的交流。這種交流有時就是一起出差的路上,或在實驗室里,學生也會一起介入,我們為此建了一個名為“生物納米交叉”的群。大家交流多了,深入了,自然而然就會產生更多的興趣點。
基礎研究要走精英路線,科研人員應該聚焦科研
宰建陶:現在國家對基礎研究的重視大家都感受到了,而且還在不斷升溫。這對從事科學研究的人來說是好事。但是我認為不應該是“撒胡椒面式”的資助,不是所有的高校和老師都適合做基礎研究。事實上現在不少研究低水平重復率太高了。基礎研究還是要走精英路線。國外大學的功能是有區分的,有些側重科研,有些側重教學。對主要承擔基礎研究的機構應該給予足夠的支持,少受干擾,生活上給予保障。現在國內很多高校和科研單位還在實行類似“數工分”的年末和聘期考核制度。這使得很多科研人員疲于奔命,分心不少。這與國家要求的沉下心來,十年磨一劍的要求是相悖的。很多科研人員更多的是承擔項目經理或者說包工頭的角色,至少一半的精力要去做學術研究之外的事。如買一個烘箱的錢是放在A項目上還是放在B項目上需要反復考慮斟酌,否則審計通不過。因此,我的建議是科研人員應該就關注科研,只要他努力干活就可通過考核;具體項目上的事還是要找一些職業經理人,負責這些日常事務。從事交叉研究的人也要調整好心態,因為國際上對跨度很大的學科交叉項目也難以認可,而且學科交叉的東西在一開始時的關注度是不高的,好的雜志也不會給予關注,只有到了一個成熟期才會受到關注。
陶 飛:宰老師以上講的關于基礎研究的觀點和看法,我也感同身受。創新分兩種,一種是原創性基礎理論創新,一種是技術創新。基礎研究應該走精英路線,應該選擇有科學志趣、科學情懷,對人類、對國家、對科學有追求的精英科學家去實施,這種在前沿探索的科學家有些可能是位怪脾氣的人。對這種另類的科學家的管理機制可能不同,社會要能提供足夠的包容。基礎理論研究能做出成績的,必然都是在真問題上愿意下功夫的,都是在啃硬骨頭。沒有前面所說那種走精英路線的開拓者就很難實現,靠鞭子驅趕的人是基本上做不出來原始創新的。
建立鼓勵學科交叉的機制,嘗試階段性資助,鼓勵探索
陶 飛:技術發明創新的源頭很重要的一個因素是學科交叉,另外一個比較重要的因素是要鼓勵探索和冒險。前者在社會已形成一定共識,但后者得到的認可和支持還不夠。需要有一套相應的激勵機制,不是只靠引導和勸說。比如現在設立的交叉研究項目,如果管理部門覺得風險大,無法承受,可以嘗試階段性資助的方法。例如,從有個想法到要做成這件事總經費大概需300萬,可以先給30萬,把事情啟動起來,根據實施情況做評估后再給第二批資助,然后第三批、第四批直至全部完成。一步步推進的資助方式更靈活多樣。按照現在的評審機制,如果這個項目的總量是300萬,那肯定有很多人去搶,而評審強調可行性,要求穩,那么就只有業內知名團隊可以拿到,很難真正去資助那些有顛覆性的創新。分期資助的方式既可以規避大的風險,也可以讓好的想法得到資助,30萬探索一條路,試錯,相當于天使投資模式。具體操作上也希望可以靈活多樣,什么時候有想法隨時可以申報,不要一年只有一個時間可以申報,及時給創新的想法以支持,也可以避免在最后期限時慌忙拼湊項目的情況。此外,在項目申報指南設置上應鼓勵交叉學科。現在很多項目申報更愿意接受學科內、領域內的項目,而不太愿意或者根本就沒有接受跨學科的項目。目前上海自然科學基金有原始創新項目申報,但每個單位(學校)限一項。很多學院的項目申報都出不了學校。
宰建陶:關于如何有效推動交叉學科研究,我覺得應該更多鼓勵兩個人(團隊)之間的合作。但這種合作往往是一方為主,另一方配合。現在國家基金委也有交叉科學部,目前這種交叉學科項目的標書和其他項目一樣都是只有一個負責人。為了鼓勵大家合作應該設立雙負責人或共同負責人的角色,肯定交叉雙方的作用。此外,我記得上海市科委自然科學基金里面有一個探索類項目: 20萬資助經費,限40歲以下的年齡,只要在所列的四大方向中都可以申報。我2017年申報了這個項目并獲得支持,我們開拓了一個新的材料體系,現在還在探究其他的應用。現在這個探索項目變成了50萬的原始創新項目,且一個學校只能申報一項。現在的項目申報更像是獎勵,已經做成功了才給資助。希望能恢復之前的探索類研究項目,激勵更多的年輕人勇于探索和冒險,促進創新。
江世亮采寫于2021年1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