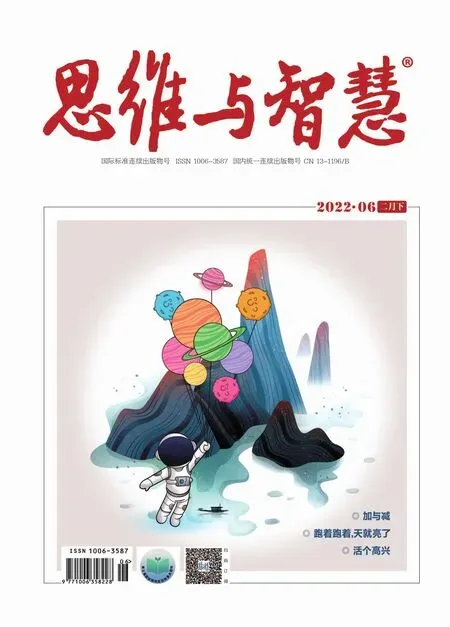靜悄悄的善良
◎ 孟祥菊

月底返鄉探母,空閑之際,我帶著8歲的冬冬去剛收獲完畢的花生地去“撿秋”。夜降微雨的緣故,地面有些潮濕,一些散落的花生露出地面,看著令人歡喜。我索性蹲在地上,把自己當作圓心,耐心地邊耙邊撿。冬冬太貪玩,專挑個頭肥大的去撿,每撿到一粒,都會雀躍著送到我的籃子里,一會兒工夫便忙得熱汗直淌。
正撿在興處,隔壁的張嫂趕了過來。她笑盈盈地和我打過招呼,又問了問冬冬的學習情況,隨后利用撿花生的間隙,一本正經地和我聊起她家孩子未來的就業問題。我對張嫂的家庭狀況很熟悉,近兩年她丈夫的腿病犯得厲害,不能下地干重活,家里家外全靠她一個人忙活,好在兒子爭氣,去年考到省城的一所大學就讀,各門功課都很優秀。張嫂說現在的大學生遍地都是,就業幾率越來越小,她擔心兒子畢業后找不到穩定的金飯碗,并問我是否有好的建議或辦法。見張嫂如此坦誠,我便很有耐心地勸慰起來:當今時代,黨和國家越來越重視教育,社會對人才的需求也不拘一格,只要孩子肯努力,夠優秀,將來定會找到理想的工作,做家長的完全不必擔心。聽完我的話,張嫂抿嘴笑了,轉身將剛撿的半袋花生倒進一旁的白鐵桶里。
小半天的時間過去了,我和冬冬的收獲很大,整整撿了多半簍花生。離開花生地時,冬冬逞強地將筐籃拎在手里,并趁我不注意,將里面的花生全部倒進張嫂的白桶中。望著冬冬所做的一切,我贊許地點點頭,同時拉過他的手,樂顛顛地往家的方向走去。
入夜不眠,望著一旁酣睡的冬冬,我的腦海里想起一則舊事。我10歲大時,家里發生一場變故,溫飽問題一時難以解決。當時的隔壁住著一位獨身的老倔爺,他身材不高,性情古怪,村里的小孩子遇見他都要繞著走。老倔爺家境很好,吃穿不愁,經常一個人悶在家里讀書看報。他對種田知識也不在行,只曉得在村頭的口糧田里成片種紅薯,說是好管理,吃用也方便。“寒露摘山楂,霜降刨地瓜”,每年的霜降未到,老倔爺總是找來鍬鎬,提前將地里的紅薯囫圇收回家中,然后虎著臉喊我去他家“開圈”的地里翻紅薯。時間一長,經驗也來了,我會專找地頭或壟溝的邊角處挖,因為那里的紅薯最多,有的甚至連翻動的痕跡都沒有。當我將翻出來的成堆紅薯用筐簍運回家的那一刻,我看到的,除了母親的笑容之外,還有殘留在她臉上的越擦越多的淚痕。多年后,我才從母親口中獲知事情的真相:老倔爺的成分不好,是個落魄的知識分子,他家田里遺落的紅薯都是他故意“賞”給我的,就是為了默默幫襯我家渡過難關。歲月流轉中,我按部就班地完成了學業,最終在大城市安了家。兒子冬冬略通人事后,我便將老倔爺施薯助人的故事多次講給他聽,小小的他總是百聽不厭,悄悄地將一顆樂善好施的種子埋入心中。
真正的善良都是靜寂無聲的,無須轟轟烈烈,也無須大聲點贊,但里面藏匿的小美好,則是可以傳遞的,便如當年老倔爺默默贈我的那些“放圈”紅薯,不僅填飽了我的胃,還滋養了我的靈魂,并最終以傳承的形式,引領我的下一輩知足感恩,揚善前行。
(常朔摘自《團結報》圖/槿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