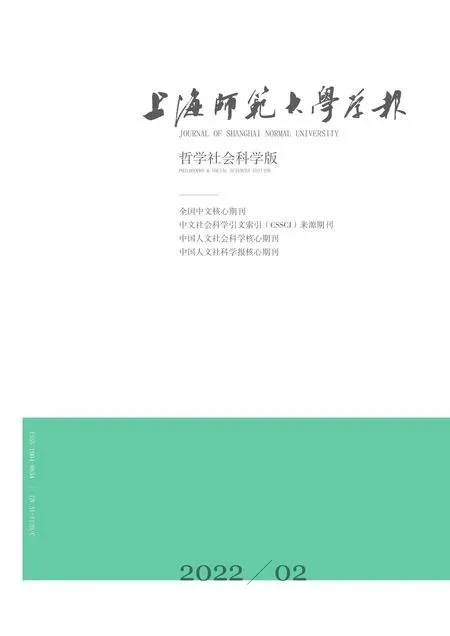勞動權利原則
——解答“馬克思與正義”難題的鎖鑰
鄭小偉
“馬克思與正義”難題之所以陷入僵局,根本在于這場爭論遮蔽了羅爾斯關于正義是為了保護權利的實質告誡和自由主義正義敘事實質為權利價值主題辯護的理論傳統。唯有切入權利范式才能真正掌握這場爭論的實質向度,同時在對作為權利之根據的勞動自我所有原則的考察與前提批判中,把握馬克思與自由主義在勞動權利原則上的根本區別以及會通性,從而內在地解答“馬克思與正義”難題。
勞動權利原則是會通馬克思正義理論與洛克開創的自由主義正義敘事的理論坐標,也是二者的原則性區別所在。馬克思勞動權利原則是在唯物史觀范式下,通過深入“現實的人”的現實社會歷史及其生產領域,實現了對洛克勞動自我所有權原則的前提批判與根本超越。以洛克勞動自我所有權原則作為理論根基的“權利”,是彰顯近代以來自由主義正義敘事實質的旨趣性、主題性價值。
一、權利:“馬克思與正義”難題的實質向度
自羅爾斯《正義論》問世以來,似乎形成了一個學界定式,一談到政治哲學就得談正義命題或者講政治哲學,不以正義命題展開就好似旁門左道、非“政治正確”。在這一巨大的理論效應影響之下,英美學術界和中國學術界逐漸形成了“馬克思與正義”這一學術理論難題,即馬克思到底有沒有正義理論、是否支持正義、是否運用正義理論批判過資本主義等理論問題。爭論的雙方各執一詞,在對“馬克思與正義”這一理論難題爭論了近半個世紀之久后,乃至當下,這一理論難題仍舊陷入無解的“僵局”。①李佃來:《全面理解〈資本論〉中的正義問題》,《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6期,第41頁。一方堅稱,馬克思拒斥正義,因為作為馬克思整個理論立場地基的“科學”歷史唯物主義拒斥“價值”規范性的正義訴求,在馬克思的經典文本中,隨處可見馬克思對訴諸“公平”“正義”等道德價值規范的蒲魯東、吉爾巴特、拉薩爾等學者的抨擊,指斥他們的這類言說和行為是“空洞的廢話”,并聲明“共產主義者根本不進行任何道德說教”等。①《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75頁。另一方反駁說,馬克思并不拒斥正義,反而擁有鮮明無產階級立場的正義理論,馬克思基于“公平”“正義”等道德價值規范曾斥責資本主義剝削雇傭勞動者為“搶劫”“盜竊”等。還有一些學者試圖調和上述對立的雙方,提出“雙重維度”說,即認為對“馬克思與正義”難題反映的“拒斥正義與支持正義的經典論述之間的矛盾”“堅持科學的歷史唯物主義與形塑道德價值規范性正義理論之間的矛盾”,要從“歷史維度”和“規范維度”進行“截然不同且并行不悖”的理解,簡言之,就是要對正義的社會歷史基礎和規范價值內涵進行絕對平行且互不相干的分析。②李旸:《馬克思論述正義問題的雙重維度》,《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2018年第6期,第25頁。
在筆者看來,上述對“馬克思與正義”難題的理解或破解研究,之所以長達近半個世紀之久地使這一理論難題陷入“僵局”,根本原因是上述研究大多是對這一理論難題的外部反思,并沒有切入對這一理論難題的內在機理進行解答的實質向度。筆者認為,對“馬克思與正義”難題的內在機理進行解答的實質向度,是能夠原則性地“界分”馬克思正義理論與羅爾斯正義理論的問題。如果筆者的這些判斷具有一定道理的話,那么關鍵就是要解答羅爾斯正義理論的實質與根基、馬克思正義理論的實質與超越,而勞動權利原則是貫穿性解答這兩個問題的一把鎖鑰。
對“馬克思與正義”難題內在機理的解答,首先需要回到產生這一難題的理論效應源頭進行“理解”,即回到羅爾斯《正義論》政治哲學語境原初地理解這一理論難題。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在關于馬克思的學術研究中,英美學術界引入羅爾斯《正義論》政治哲學語境的“正義”概念,被習以為常或不加反思地定義為一種分配制度德性,即指導社會分配的倫理規范或分配正義。這一對正義范式的限定,既一度是“馬克思與正義”命題產生爭議的緣由,也一度是限定這一爭論之深度與廣度的緣由。因為如若對“馬克思與正義”難題的探討僅僅停留于“分配”“正義”層面,就不能根本性地觸及羅爾斯正義理論和馬克思正義理論的實質向度與理論根基及其原則性區別,也就很難深入這一理論難題的內在機理而內在解答這一理論“僵局”。
那么,羅爾斯本人對自己正義理論的實質向度或主旨,到底是如何定義的呢?對這個問題的梳理,或許是我們解答“馬克思與正義”難題的一個關鍵切口。如果對羅爾斯語境的正義進行政治哲學史的追根溯源,我們會發現,即便是在羅爾斯的《正義論》政治哲學語境中,“正義”也不過是一個最終保障“權利”這個一階價值的二階價值。《正義論》開篇明確道出:“在一個正義的社會里,平等公民的各種自由是確定不移的,由正義所保障的權利決不受制于政治的交易或社會利益的權衡。”③羅爾斯:《正義論(修訂版)》,何懷宏、何包鋼、廖申白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3頁。《正義論》的開宗明義,旨在澄明正義是為了保障權利,權利才是正義的實質性價值目標即實質向度,權利是正義的目的性、旨趣性價值,正義的最終目的、內在傾向是為了保障權利。遺憾的是,就是這樣開宗明義式的關于羅爾斯正義理論實質向度即保障權利的鮮明闡述,竟然在人們長達近半個世紀的“馬克思與正義”爭論中被遮蔽而不能充分彰顯,致使“馬克思與正義”爭論陷入“僵局”。盡管直到羅爾斯,“正義”作為政治哲學概念、術語,才被學術界廣泛運用并引起巨大的理論效應,但羅爾斯本人還是在正義與權利的內在關系上,遵從了近代以來自由主義政治哲學為權利價值主題辯護的理論傳統立場。
自近代洛克開創自由主義理論傳統以來,就形成了一個以權利為實質向度、為權利的現代價值主題辯護的理論傳統,即實質性地開顯了一種為以私有財產權或所有權為軸心的權利價值辯護的規范性正義敘事邏輯。正如馬克思所指明的那樣,“洛克是同封建社會相對立的資產階級社會的法權觀念的經典表達者”。④《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冊,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3頁。權利之所以會成為近代以來自由主義政治哲學、政治經濟學的現代價值主題,是因為商品經濟和現代市民社會的發展為其積淀了社會歷史條件。馬克思恩格斯曾對此指出:“社會的經濟進步……把擺脫封建桎梏和通過消除封建不平等來確立權利平等的要求提上日程。”①《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1頁。為以私有財產權或所有權為軸心或基礎的權利進行辯護,構成了洛克以降自由主義政治哲學、政治經濟學的價值主題,“洛克哲學成了以后整個英國政治經濟學的一切觀念的基礎”。②《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冊,第393頁。隨著時代的演進和現代商品經濟的發展,即便到了19世紀穆勒和20世紀羅爾斯的政治哲學、政治經濟學,盡管人們對權利的理解發生了諸多變化,如對權利類型的擴展、對理解權利視角的調整等,但以私有財產權或所有權為軸心或基礎理解權利并開展正義敘事,仍然是自由主義永恒的理論傳統。對此,馬克思在《論猶太人問題》中早已指明:“自由這一人權的實際應用就是私有財產這一人權。……私有財產這一人權是任意地(à son gré)、同他人無關地、不受社會影響地享用和處理自己的財產的權利;這一權利是自私自利的權利。”③《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41頁。
至此,我們借助羅爾斯開宗明義的論述發現了羅爾斯正義理論的實質向度即保障權利,我們也從近代以來自由主義為權利價值主題辯護的理論傳統中捕捉到以權利為實質向度的自由主義正義敘事邏輯,從而把握了正義與權利的內在關聯,為破解“馬克思與正義”難題打開了一個具有實質向度的關鍵切口。但如果就此止步,那么,我們對“馬克思與正義”難題的解答仍舊停留于外部反思階段,并未真正觸及這一難題,羅爾斯正義理論的實質即其權利理論的內在機理也未得到破解。為完成這一艱難的理論解答工作,我們還需要對羅爾斯正義理論溯源至近代以來自由主義政治哲學史的開端,從探尋其權利理論傳統的內在機理或根基中,真正“內在”地掌握其實質或本質。
二、洛克勞動權利原則:權利的“內在機理或根基”
從近代以來的自由主義政治哲學史來看,洛克的勞動自我所有權原則無疑奠定了自由主義權利理論的“內在機理或根基”,成為近代以來自由主義為以私有財產權或所有權為軸心的權利價值進行辯護的“理論根據”。
洛克在《政府論》中闡述勞動權利原則即勞動自我所有權原則時指出:“雖然自然的東西是給人共有的,然而人既是自己的主人,自身和自身行動或勞動的所有者,本身就還具有財產的基本基礎。”④洛克:《政府論》下篇,葉啟芳、瞿菊農譯,商務印書館1964年版,第28頁。“每人對他自己的人身享有一種所有權,除他以外任何人都沒有這種權利。他的身體所從事的勞動和他的雙手所進行的工作,我們可以說,是正當地屬于他的。所以只要他使任何東西脫離自然所提供的和那個東西所處的狀態,他就已經摻進他的勞動,在這上面參加他自己所有的某些東西,因而使它成為他的財產。”⑤洛克:《政府論》下篇,第19頁。洛克的勞動自我所有權原則認為,原初的自然狀態或自然世界是人類共有的,人對自身、自身行動或勞動擁有排他性的所有權,通過自身勞動作用于自然并使自然滲入自身勞動的部分,就轉化為個人的私有財產,即“勞動”構成私有財產權或所有權的正當根據及基礎。洛克的勞動自我所有權原則開創性地為私有財產權或所有權進行自然法權的論證,在他看來,原初的自然世界屬于人類共有,人對于自身、自身行動或勞動具有先在于政治國家的自然法權,那么,由勞動作用于自然形成的私有財產權或所有權就是“不必經過全體世界人的明確協議”的自然法權。⑥洛克:《政府論》下篇,第17頁。歸根結底,這實質上是一種基于人身或人格(Person)行動即勞動的自然法權,正是勞動,即人身或人格(Person)對自然資源的行動或“滲入”,才產生私有財產權或所有權歸屬于勞動行為者的正當性或正義性問題。同時洛克指出,為了保護私有財產權或所有權,人們依據“契約”設立了政治國家及其法律制度,“人們聯合成為國家或置于政府之下的重大的和主要的目的,是保護他們的財產”。⑦洛克:《政府論》下篇,第77頁。這就奠定了近代以來自由主義的主要理論傳統和核心訴求:以勞動權利原則為私有財產權或所有權辯護的理論傳統。以亞當·斯密為代表的英國政治經濟學,在洛克的勞動自我所有權原則基礎上創立了勞動價值論,以勞動創造價值的勞動權利原則論證了私有財產權或所有權的正當性或正義性、合法性根基。眾所周知的黑格爾《法哲學原理》,更是以勞動所有權為理論邏輯基點來展開其法哲學原理正義敘事。《法哲學原理》以所有權這個抽象法為開篇主題,直到“倫理”的第三篇,在“市民社會”語境中深化了這一主題。當然,黑格爾對私有財產權或所有權本質性、正義性、合法性的界定也是基于勞動。黑格爾認為,“構成所有權的規定”即“把某物變為我的東西”,是勞動即“自由意志”的對象化,“作為自由意志的我在占有中成為我的對象,因而也才初次成為現實的意志,這一方面卻構成占有的真實而合法的因素”。①黑格爾:《法哲學原理》,鄧安慶譯,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97頁。
基于勞動權利原則為私有財產權或所有權進行自然法權證明的理論傳統,洛克以基于自身人格行動的勞動自我所有權原則,在為私有財產權或所有權進行自然法權證明時,示范性地為其以后的自由主義開辟了在自然法權范式內理解私有財產權或所有權的自由主義理論傳統。在自由主義權利學說看來,私有財產權或所有權是先于政治國家的自然權利,是“天賦人權”,是基于勞動即人格行動、自由意志對象化的“永恒”自然權利,不可被強制掠奪,但經權利人的“同意”,可以進行私有財產權或所有權的“讓渡”。這即是說,由于私有財產權或所有權作為自然權利的“神圣性”,政治國家只能保護私有財產權或所有權而無權掠奪它,但在商品經濟的市場交換中,出于權利人之間的自由意志,權利人可以自由“讓渡”自己的基于勞動的私有財產權或所有權以及作為其物質載體的勞動產品(蘊含勞動價值)。這形成了依據“契約”的現代商品經濟交換原則,也奠定了為資本主義私有制的雇傭勞動制度辯護的“理論根據”。在自然法權范式下,在超現實的先驗抽象的理論邏輯推演中,近代以來自由主義政治哲學家、政治經濟學家只關注人對自身、自身行為或勞動擁有占有、支配、讓渡的自然權利,只看到生產領域生產的產品包括剩余勞動的產品,在資本所有權名義下進行契約性的商品等價交換,以及商品所有權規律向資本主義占有規律轉化的“合法性”“正義性”。在他們看來,基于勞動自我所有權原則的私有財產權或所有權,是先于政治國家的自然權利,政治國家及其法律制度的建設,主要是為了保護私有財產權或所有權;在商品交換中,只要基于所有權并遵循平等自愿的等價交換的契約精神就是合法的、正義的,就是對人格及勞動能力的尊重,而不問作為交換基礎或前提的所有權或私有財產權的“合法性”“正義性”。這基本形成了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圣經”原則和資本主義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正義敘事邏輯。
對于勞動自我所有權原則展現的自然法權屬性,洛克曾注解道:“所有的人生來都是平等的,卻不能認為我所說的包括所有的各種各樣的平等。……高超的才能和特長可以使另一些人位于一般水平之上。”②洛克:《政府論》下篇,第34頁。這即是說,勞動自我所有權原則既強調私有財產權或所有權是天賦的自然權利、人人享有天賦的自由平等權利,又承認高超才能、特長可以獲取更多權利或默認才能、特長的“天然特權”。勞動自我所有權原則強調人的主體性、天賦自由平等和基于勞動能力的分配原則,對于解放人的主體性和釋放勞動潛能、推動生產力發展以及克服以往社會基于身份等級的分配原則,具有歷史進步性。但自由主義政治哲學家、政治經濟學家在自然法權范式下論證私有財產權或所有權的“天然正義”中,遮蔽了對其“合法性”“正義性”問題的前提性、根本性的追問。③王新生:《馬克思政治哲學研究》,科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239頁。馬克思對此批判地指出,“從私有財產的事實出發。它沒有給我們說明這個事實。……它把應當加以闡明的東西當做前提”,④《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55頁。無法真正回答資本主義“現代社會”中勞動自我所有權原則與“異化勞動”之間的悖論。
三、馬克思勞動權利原則:“馬克思與正義”難題的根本解答
馬克思盡管沒有專門以正義或權利為題進行系統全面的研究與著述,但他在研究人類活動的歷史發展時,闡述了大量有關正義或權利問題的理論觀點,尤其在對資本主義現代社會及其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正義敘事的前提性、根本性批判中,內在地、歷史辯證地構建了基于唯物史觀范式勞動權利原則的正義理論。
其一,馬克思對洛克的勞動自我所有權原則的邏輯前提進行了唯物史觀范式的批判性分析,尤其是通過對勞動力商品化歷史過程及條件的批判性分析,揭示了作為自由主義勞動自我所有權原則邏輯前提的勞動與勞動者分離的歷史性和強制性。
檢視洛克的以自身勞動為根據的勞動自我所有權原則,我們會發現,其基本規定是人(勞動者)對自身人格行動即勞動及其產品擁有所有權,而實現這一基本規定的邏輯前提是人格行動(勞動)與人(勞動者)的分離,即人格行動(勞動)及其對象化的產品獲得相對獨立于人(勞動者)的對象地位。對于這一邏輯前提,自由主義理論家在自然法權范式下,看到的只是人們在“契約”精神下“自然”“自愿”地占有、支配、讓渡自身人格行動(勞動)及其產品的“自然權利”,卻從未內在地反思過這一邏輯前提——人格行動(勞動)與人(勞動者)的分離,到底是自然的狀態還是歷史的產物,是自愿的選擇還是迫不得已的無奈。對此,馬克思基于唯物史觀范式揭示,在資本主義社會,勞動與勞動者分離實際是勞動力與勞動者分離、勞動力商品化。因此,馬克思主要是通過對資本主義社會勞動力商品化的歷史及條件的批判性分析而予以澄明:勞動與勞動者分離、勞動力商品化是社會歷史發展的產物而并非“自然狀態”,是迫不得已的無奈而并非自愿的“同意”。
在《資本論》及其手稿中,馬克思在對雇傭勞動與勞動力商品化的內在關系的揭示中指出,資本主義雇傭勞動、勞動力商品化的社會歷史前提條件有二:一是能夠進行市場自由等價交換的“自由勞動”的出現;二是“自由勞動”同實現自身的“客觀條件相分離”。①《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5頁。歷史地看,所謂法律上能夠進行市場自由等價交換的“自由勞動”也并非“自然狀態”的存在,而是歷經奴隸社會“奴役勞動”、封建社會“徭役勞動”,才在資本主義社會歷史條件下形成的。在“奴役勞動”歷史階段,勞動者不被承認具有獨立人格而是作為奴隸主的私有財產,“自由勞動”無從談起,勞動自我所有權原則在此階段無成立的邏輯前提;在“徭役勞動”歷史階段,勞動者人身依附于地主或領主,被嚴密捆綁于土地上,無自由支配自身勞動的權利;到了資本主義社會,現代商品經濟等價交換的普遍性、內在性要求,呼喚在法律上普遍承認交易主體的平等、自由意志和商品所有權,致使勞動者在法律形式上支配自身勞動的“自由勞動”得以產生。另外,“自由勞動”同實現自身的客觀條件的分離,也是歷史發展到了資本主義社會,勞動者與勞動資料發生了決定性分離才實現的。在原始社會,實行人們共同占有勞動資料、共同勞動、共享勞動成果;在封建社會,農民或農奴的人身依附于地主或領主,與租種的作為生產資料的一小塊土地緊密捆綁在一起,可以支配租種土地的農業生產,并自負盈虧風險;只有到了資本主義社會,才出現“自由勞動”同實現自身的客觀條件的決定性分離。這樣,我們通過對作為勞動力商品化二重條件的歷史性分析,前提性地呈示了勞動力商品化即勞動與勞動者分離的歷史性,折射了自由主義勞動自我所有權原則的歷史性,同時揭露了其自然法權范式的虛幻性。
馬克思進一步指出,勞動者與勞動資料的決定性分離、勞動力商品化不僅是“歷史的”而且還是“強制的”。這種決定性的分離造成了勞動的主體性條件——勞動力與勞動的客體性條件或客觀條件——勞動工具、勞動對象即勞動資料的根本性分離,造成了勞動者對勞動資料的依賴和“一無所有”唯有靠出賣自身勞動力才能維生的雇傭勞動者,致使勞動對資本無奈的“屈從”。但是,陷入資本主義私有制意識形態“勞動幻象”迷霧中的自由主義理論家,不僅將勞動自我所有權原則認定為先在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自然法權,而且認為勞動者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交換自身勞動力商品是完全出于自己自由意志的“自愿”讓渡,并且勞動力商品化即勞動力的買賣關系完全是基于“所有權”和“契約”的自由平等交換。對此,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指出:“勞動力的買和賣是在流通領域或商品交換領域的界限以內進行的,這個領域確實是天賦人權的真正伊甸園。……一離開這個簡單流通領域或商品交換領域……劇中人的面貌已經起了某些變化。”②《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04—205頁。在《資本論》第三卷中馬克思進一步說:“生產當事人之間進行的交易的正義性在于:這種交易是從生產關系中作為自然結果產生出來的。這種經濟交易作為當事人的……共同意志的表示,……表現在法律形式上,這些法律形式作為單純的形式,是不能決定這個內容本身的。這些形式只是表示這個內容。這個內容,只要與生產方式相適應,相一致,就是正義的。”①《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379頁。馬克思的這兩段話引起了學術界的極大爭議,據此,有的學者認為,馬克思的確“白紙黑字”地在商品交換領域將雇傭勞動者與資本家之間的勞動力買賣關系,即勞動力商品化界定為一種“正義”關系,并且指出馬克思的這個界定與當時占主流的、基于所有權和契約原則界定“正義”的西方自由主義理論傳統是基本一致的。這種理解其實是一種莫大的誤會,是一種對“馬克思與正義”難題的外在反思。其實,馬克思的這兩段關于“正義”的經典論述,既是在描述當時社會“流行”的勞動力商品化交換關系及其原則,更是在將這一論題的實質引向現實的生產關系和生產方式領域。在馬克思看來,固然勞動力商品交換在國家強制性的法律形式保障下基于自由、平等和所有權而進行,但實際上,這種交易的正義性并非取決于外在的法律形式,而是由生產方式內在決定的,是生產關系的自然結果。這正如馬克思所指明的那樣,一旦離開商品交換和流通領域,“劇中人的面貌”就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馬克思通過對以暴力強制分離勞動者與勞動資料的資本原始積累生產方式以及以生產剩余價值為實質內容的現代資本積累生產方式的歷史分析,在唯物史觀范式中推進了對勞動力商品化、勞動與勞動者分離的實質理解,揭示了作為自由主義勞動自我所有權原則邏輯前提的勞動與勞動者分離的歷史性和強制性,揭露了自由主義所謂基于所有權和契約的勞動者“自愿”讓渡勞動力的虛假性,同時也揭露了勞動力商品化的實質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規定:生產剩余價值。
其二,馬克思對洛克的以自身勞動為根據的私有制與后來自由主義的以剝削他人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進行了原則性的界分,并深入生產領域對所謂基于“所有權”和“契約”的勞動力商品化“正義”展開實質分析,根本性地揭批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本質以及作為其法權意識形態的自由主義正義敘事的虛假性、欺騙性。
在《資本論》及其手稿中,馬克思指明:“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的資本主義占有方式,從而資本主義的私有制,是對個人的、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的第一個否定。”②《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74頁。這句話里的“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是指洛克的以自身勞動為根據的私有制,即洛克的勞動自我所有權原則,它本來是資本主義原初時期的小資產階級所有制,內在蘊含的是商品所有權規律;這句話里的“資本主義占有方式”就是后來自由主義理論家辯護的以剝削他人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是資本主義機器大工業時期勞動力普遍商品化條件下的資本主義私有制,內在蘊含的是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決定的資本主義占有規律。這兩種私有制生產方式,在基礎、性質、時空等方面本來不同,但卻被“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理論”不加深刻反思地“混為一談”。③《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44頁。在勞動力普遍商品化的資本主義大工業時代,在遵循“契約”原則的現代商品經濟等價交換外在形式下,商品所有權規律堂而皇之地遮蔽了以剝削他人勞動為基礎的資本主義占有規律。后來自由主義理論家在普遍的遵循“契約”原則的現代商品經濟自由等價交換“外衣”的遮蔽下,誤以為資本主義占有規律是由商品所有權規律轉化而來的。于是,在對遵循“契約”原則的現代商品經濟即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及其所有制辯護的時候,訴諸以自身勞動為根據的商品所有權規律,這便生成了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意識形態“勞動幻象”——“在意識形態和法律上,他們把以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的意識形態硬搬到以剝奪直接生產者為基礎的所有制上來”。④《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第144頁。這即是說,后來自由主義理論家訴諸洛克的勞動自我所有權原則,為時空錯位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私有制辯護,是對這一理論原則非歷史的外在堅持和抽象性誤用,不僅未能實質性地貫徹這一理論原則,反而在為實質性地破壞這一理論原則進行虛假的意識形態辯護。造成這一虛假理論效應的后果,與自由主義理論家沒能內在反思貫徹這一理論原則的邏輯前提和社會歷史條件以及自然法權理論傳統也不無關系。
馬克思對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生產剩余價值的內在規定或本質屬性說道:“活勞動被對象化勞動所占有……這種包含在資本概念中的占有,在以機器為基礎的生產中,也從生產的物質要素和生產的物質運動上被確立為生產過程本身的性質。”①《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85頁。在馬克思看來,以機器大工業生產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本質屬性,就是資本對活勞動的占有、支配、宰制、剝削。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中,這主要表現為資本家“不付等價物”而“無償”占有由雇傭勞動者活勞動的使用價值轉化的剩余價值,并“不斷”基于這種“無償”占有活勞動的方式進一步去剝削雇傭勞動者的活勞動,②《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673頁。為“不支付等價物便占有他人勞動的權利”或占有剩余勞動的資本“所有權”進行轉化和積累。③《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06—107頁。資本家之所以購買勞動力,是因為勞動力的使用即活勞動能夠生產、創造出比自身勞動力價值(資本家所謂等價交換支付給工人的工資)大得多的價值,能夠在資本主義占有規律下源源不斷地創造出超過自身勞動力價值的剩余價值被資本“無償”占有或轉化為資本“所有權”。這樣,基于唯物史觀范式,馬克思深入生產領域,揭開了資本主義勞動力商品化的虛假“外衣”,根本性地揭示了資本主義占有規律取代商品所有權規律的實質,根本性地呈現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中資本無償占有雇傭勞動剩余價值的“剝削”性本質,根本性地揭露了作為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敘事和理論前提的所謂基于“所有權”和“契約”的自由主義“正義”的虛假性、欺騙性,實現了對資本主義的根本性正義批判。
一言以蔽之,基于唯物史觀范式,馬克思對作為自由主義正義理論根基的勞動自我所有權原則進行了前提性批判,即通過揭示作為勞動自我所有權原則邏輯前提的人格行動(勞動)與勞動者分離的歷史性與強制性,揭露自由主義正義理論邏輯前提的真實歷史內容;通過深入生產領域,對自由主義正義理論所謂基于“所有權”和“契約”的勞動力商品化的實質進行分析,根本性地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中資本無償占有雇傭勞動剩余價值的邏輯性質,從而實現了對資本主義的根本性正義批判,也揭示了作為資本主義法權意識形態的自由主義正義理論的虛假性根源在于以生產剩余價值為本質規定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或資本主義私有制。
其三,馬克思基于唯物史觀范式的勞動理論,立足于勞動作為人的現實存在方式與自由解放本質需要,主要通過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或所有制的變革,在科學性與規范性、手段性與目的性、現實性與理想性的統一中構建超越自由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勞動權利原則。
馬克思在其社會形態演進邏輯中,考察了“奴役勞動”“徭役勞動”“雇傭勞動”等勞動方式及其勞動權利關系與狀態,揭示了勞動權利原則的社會歷史條件制約性和根本受制于生產方式或所有制的規律。在《哥達綱領批判》中,馬克思指明:“權利決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發展。”④《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435頁。在馬克思看來,有什么樣的生產方式和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就會有什么樣的勞動方式與勞動權利原則,勞動權利原則是具體的、歷史的。他針對性地指出,雇傭勞動及其權利原則的性質根本上取決于以生產剩余價值為目標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則根本上決定了雇傭勞動及其權利狀態。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指出,通過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根本變革或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在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社會主義階段)實行真正“按勞分配”的勞動權利原則,即實行“生產者的權利是同他們提供的勞動成比例的”⑤《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435頁。勞動權利原則。這是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不再屈從于生產剩余價值和資本增殖的資本邏輯,而尊重勞動能力、貢獻及其分配的權利原則,正如《共產黨宣言》中所指明的那樣,“共產主義并不剝奪任何人占有社會產品的權力,它只剝奪利用這種占有去奴役他人勞動的權力”。⑥《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47頁。這是真正以勞動者為主體、為目的,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和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向往的勞動權利原則。但是由于共產主義第一階段剛剛脫胎于舊社會,勞動權利原則及其法權關系難免還存在舊法權印記或“弊病”,還存在基于才能等不同而造成的事實差異或對“天然特權”的默認問題,但這與自由主義屈從于資本邏輯而對才能、特長等天然特權的默認存在根本性質的不同。同時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生產能力還不充足還需要極大發展,特別是需要通過高質量發展來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以支撐勞動權利原則的圓滿實現。在這一社會歷史階段,勞動是進行生產與擴大再生產、積累社會物質財富的主要手段,也是實現人生價值和美好生活需要、積累社會精神財富的根本方式,是手段與目的的有機統一。
同時,馬克思基于勞動作為人的存在方式與自由解放本質的需要,指出“人類社會或社會化的人類”,還將在勞動實踐偉大變革力量的推動下,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辯證運動與高度發展中進入共產主義高級階段(共產主義社會),將實行“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勞動權利原則。這是在普遍聯合起來的勞動者共同支配高度發達的社會生產能力的基礎上,勞動真正成為人的第一需要和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勞動權利原則。這是對共產主義第一級階段“按勞分配”勞動權利原則的根本推進,是尊重人的才能、人人各盡其能,又對可能事實差距或“天然特權”等問題的根本克服,是真正徹底實現勞動解放與勞動正義。①劉同舫:《馬克思唯物史觀敘事中的勞動正義》,《中國社會科學》2020年第9期,第22頁。正如《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所指明的那樣,在共產主義社會“勞動上的差別不會引起在占有和消費方面的任何不平等,任何特權”。②《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38頁。
馬克思基于唯物史觀范式的勞動理論,以人的勞動自由解放本質需要為旨趣,從“現實的人”的勞動實踐出發,通過對自由主義正義理論之根基或原則的前提批判,而深入生產領域揭示作為自由主義制度載體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性質和本質——以生產剩余價值和資本增殖為目標的“資本正義”,從而根本性地對資本主義及其自由主義正義敘事進行了批判。同時,在對生產方式或所有制進行根本和前提性的變革中,歷史辯證地構建了超越資本主義及其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正義敘事的科學社會主義勞動權利原則——以人的生存發展和自由解放為目標的“勞動正義”。至此,我們以勞動權利原則為中心線索和鎖鑰,為內在地梳理和回應“馬克思與正義”難題探尋了一個具有實質向度的學理切口或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