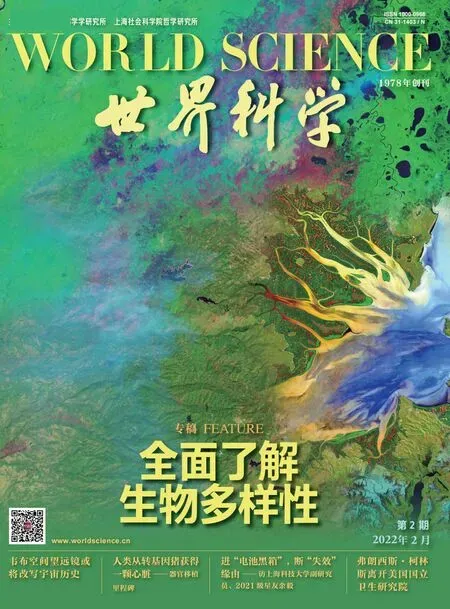有用知識的無用性
編譯 高斯寒
人工智能是不是新一代的煉金術?也就是說,控制著我們大部分生活——從網絡搜索到社交媒體推送——的強大算法是不是現代版的點石成金術?進一步的問題是,那是不是件壞事?
根據著名人工智能研究者阿里·拉希米(Ali Rahimi)及其他人的說法,現今流行的神經網絡和深度學習技術是建立在眾多花招之上,再添加大量樂觀主義,而不是系統分析。按照這個講法,現代工程師匯編代碼時懷著一廂情愿的念頭和誤解,恰似古代的煉金術士混合魔力藥水時的內心所想。
確實,我們對于自我學習算法的內部工作機制和算法應用的局限之處缺乏基本理解。這些人工智能的新形式與傳統的、能夠逐行理解的計算機代碼截然不同。相反地,這些算法在黑箱內運行,它們對于人類甚至是對于機器本身都似乎是不可知的。
人工智能界內的這番討論已經對所有科學門類造成后果。當前,深度學習沖擊了如此多的科研分支——從新藥發現到智能材料設計,再到粒子碰撞的分析——科學本身也許面臨被概念的黑箱吞噬的風險。讓計算機程序上化學課或物理課會很困難。但我們如此遵從機器,是否等于拋棄早已被證明十分成功的科學方法,回頭轉向煉金術一般的黑魔法?
先別這么快下結論,法國科學家楊立昆(Yann LeCun)這么說道,他憑借神經網絡上的開拓性工作而成為2018年圖靈獎共同獲獎人之一。他主張,當前人工智能研究的狀況在科學史上一點也不新鮮。這僅僅是一段必然出現的“青春期”,許多領域早已經歷過這種階段,以反復試錯、混淆、過度自信和缺乏總體理解為特征。我們一點也不用懼怕,還能從接受人工智能中獲益良多。只是,我們顯然對它的對立面更加熟悉。
畢竟,很容易想象知識順流而下,從抽象概念的源頭,經歷實驗的百轉千回,抵達代表實踐應用的廣闊三角洲。這就是著名的“無用知識的有用性”論斷,由亞伯拉罕·弗萊克斯納(Abraham Flexner)在他發表于1939年的文章中提出(這個論斷本身是對啟蒙時代出現的美式概念“實用知識”的文字游戲)。
這種知識流動的一個典型例證是阿爾伯特·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一切起始于“物理學定律應當對于所有觀察者都有效,且獨立于觀察者的舉動”的基本想法。接著,愛因斯坦將這個概念轉譯為彎曲時空的數學語言,再應用于引力和宇宙的演化。若是沒有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我們手頭的智能手機中的GPS會每天漂移偏離大約1公里。
但是,或許這個“無用知識的有用性”范例正是丹麥物理學家尼爾斯·玻爾喜歡稱為“偉大的真理”的東西——它的對立面也是偉大的真理。也許,正如人工智能所演示的,知識也能從低往上地逆流。
如楊立昆所暗示的,在廣闊的科學史中,我們能發現這一作用的許多例子,而且這大概能冠名為“有用知識的無用性”。從漫長的一系列逐步改進和嬉戲般的實驗中,能誕生影響廣泛、極其重要的想法。比如說,從弗里德里希·福祿貝爾(德國教育家)幼兒教育思想的誕生再到阿爾弗雷德·諾貝爾發光發熱的過程。
或許,最好的例證是熱力學定律的發現,熱力學定律對于所有科學分支來說都是基礎。那些優雅的公式描述了能量守恒和熵增原理,是自然定律,所有物理現象都要遵守。但這些普遍概念直到一連串漫長而讓人困惑的實驗之后,才變得像是顯然如此。實驗的起點要回溯至18世紀時建造出第一臺蒸汽機并逐步改進設計的時候。在實務考量的濃霧中,數學法則徐徐現身。
要看另一個例子的話,我們可以轉向流體動力學的歷史。如何在各種水路上運輸東西?這是一個出現在早期人類面前的緊迫問題,人類祖先盡其所能克服難題,毫不擔心甚至是毫不關心流體動力學的基本理解。在隨后的一千年中,人類建造船只,駕船遠航,單單依靠從經驗得出的知識和經驗,就打造出更具效率的船身。
直到19世紀時,我們才碰巧發現著名的納維-斯托克斯方程,該方程以精準的數學語言描述了流體的運動。即便在那時,盡管機械發動機和更高速度的出現抬高了對理論思考的需要,知識依然一直由下向上流動。如今,這些復雜精妙的方程的性質構成了千禧年大獎難題中的一個未解難題,獎金有一百萬美元之多,可以說,納維-斯托克斯方程進入了基礎數學的前沿領域。
我們甚至可以主張,科學本身早已遵循這條由下向上的路徑。在17世紀現代科研的方法和實踐誕生之前,科學研究大多被認為是非系統的實驗和理論歸納。這些古代實踐長久以來被認為是學術的死胡同,在近些年卻受到重新評估:煉金術如今被認為是現代化學的一個有益的或許甚至必不可少的先驅——它更像原始科學,而非花哨的騙術。
修修補補是一條通往宏大理論和見解的富有成效的道路。這點認識對于當前以新穎方式結合先進工程學和基礎科學的研究特別切題。納米物理學家受到技術突破的驅策,正在修修補補,在分子層面上構建蒸汽機的現代對應物,操縱個別的原子、電子和光子。CRISPR之類的基因編輯工具允許我們剪輯生命的代碼。我們正在以復雜得難以想象的結構,推動自然進入現實的新角落。我們有這么多探索物質和信息的新配置的機會,能夠邁進現代“煉金術”的黃金年代。
然而,我們永遠不該忘記那些來之不易的歷史教訓。煉金術不僅僅是一門原始科學,也是一門“大話連篇”的學問,做出過高的許諾,履約時卻差得好遠。占星術的預言曾經被信以為真,以至于人生得要去適應占星術,而不是占星術來適應人生。遺憾的是,現代社會并未免除這類虛幻想法,過于信任那些無所不能的算法,而沒有批判地質疑算法的邏輯基礎或道德基礎。
科學一直遵循著自然的節奏,擴張與收縮交替出現。未系統化的探索時間過后,是一段沉淀鞏固的時期,讓新的知識以基本概念為基礎。我們只能盼望,當前人工智能、量子設備和基因編輯領域的創意修補期——再加上多種多樣的有用應用——最終會通往人類對世界的更深刻領悟。
資料來源 Quanta Magaz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