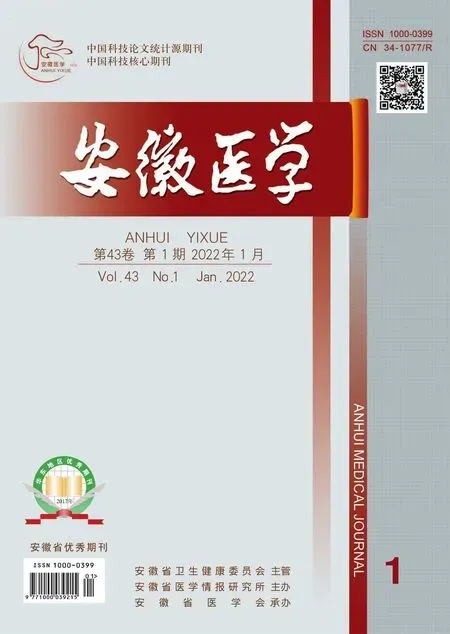78例腦膠質(zhì)母細(xì)胞瘤術(shù)后同步放化療患者的生存影響因素
方金梅 趙于飛 龍騰飛 劉 云 方 晶 吳愛林
高級(jí)別膠質(zhì)瘤(high-grade glioma,HGG) 是成人最常見的顱內(nèi)惡性腫瘤,其中以膠質(zhì)母細(xì)胞瘤(glioblastoma,GBM)惡性程度最高,呈侵襲性生長,預(yù)后差[1],病因尚不明確。目前認(rèn)為GBM的病因和電離輻射相關(guān),同時(shí)與基因的遺傳易感性有密切聯(lián)系。主要治療手段是在安全的前提下盡可能的切除腫瘤組織,術(shù)后進(jìn)行同步放化療及輔助化療。但GBM呈浸潤性生長,與周圍腦組織分界不清,手術(shù)通常無法完全切除,而殘存的腫瘤對(duì)放化療不敏感,新型治療手段如靶向治療、免疫治療及腫瘤電場(chǎng)治療尚處于探索階段。盡管治療方法不斷發(fā)展, GBM患者總體療效并不理想,復(fù)發(fā)率高、預(yù)后差,中位生存期僅為15個(gè)月[2]。目前絕大多數(shù)研究的對(duì)象為HGG,極少對(duì)GBM進(jìn)行單獨(dú)分析,導(dǎo)致對(duì)GBM患者的預(yù)后評(píng)估存在一定誤差。本研究針對(duì)GBM患者,根據(jù)其臨床特征及治療方案,探討其預(yù)后影響因素,旨在更準(zhǔn)確的評(píng)估GBM患者的預(yù)后。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回顧性分析2015年6月30日至2017年12月13日中國科學(xué)技術(shù)大學(xué)附屬第一醫(yī)院(安徽省腫瘤醫(yī)院)西區(qū)收治的78例GBM患者的病例資料,其中男性47例,女性31例;年齡5~75歲,平均54.33(49,63)歲。納入標(biāo)準(zhǔn):①所有患者術(shù)后病理檢查證實(shí)為GBM;②手術(shù)前、放療前的磁共振影像資料完整;③術(shù)后完成同步放化療,和至少1周期的輔助化療。 排除標(biāo)準(zhǔn):①病理診斷不確切;②合并其他惡性腫瘤的患者。
1.2 體位固定、CT掃描及靶區(qū)勾畫 所有患者均使用頭部熱塑膜及頭枕(E型號(hào))固定頭部,仰頜,高壓注射器經(jīng)肘前靜脈注射碘海醇,CT模擬機(jī)進(jìn)行2.5 mm的頭顱CT薄層掃描,掃描CT資料通過網(wǎng)絡(luò)傳輸至Philips Pinnacle39.0工作站,并將術(shù)前、術(shù)后的頭顱MRI掃描資料通過工作站CT-MRI互相關(guān)算法自動(dòng)融合,根據(jù)腫瘤瘤腔位置由放射物理師與臨床醫(yī)師共同進(jìn)行修正,融合后勾畫的靶區(qū)能在CT和MRI圖像上自動(dòng)映射。靶區(qū)勾畫如下:大體瘤腔體積(gross target volume of tumor bed,GTVtb)定位為術(shù)后MRI掃描上存在T2或FLAIR異常區(qū)域,包含術(shù)后MRI所有增強(qiáng)對(duì)比T1的異常和手術(shù)腔;臨床靶區(qū)(clinical target volume,CTV)定義為GTVtb向外擴(kuò)放2 cm邊緣,可因阻礙瘤體浸潤的自然屏障,諸如顱骨、腦室、大腦鐮等而適當(dāng)減少外放。在FLAIR相(首選)或T2加權(quán)成像中持續(xù)水腫的所有區(qū)域,CTV可向外擴(kuò)放超過2 cm以包括水腫區(qū)域。GTVtb外放3 mm定義為臨床瘤腔靶區(qū)(planning target volume of tumorbed,PGTVtb),CTV外放3 mm為計(jì)劃靶區(qū)(planning target volume,PTV)。
1.3 放療劑量及方法 處方劑量如下:95%PTV 45~68 Gy。Philips Pinnacle39.0工作站設(shè)計(jì)放療計(jì)劃,美國瓦里安公司Trilogy型號(hào)醫(yī)用直線加速器6 MV-X射線實(shí)施治療。殘存腫瘤或者瘤腔劑量95%PGTVtb 50~68 Gy,95%PTV 46~60 Gy。常規(guī)分割照射:單次劑量1.8~2.0 Gy,每天1次,每周5次。放療方式采用調(diào)強(qiáng)放射治療(intensity-modulated radiation therapy,IMRT)或者容積弧形調(diào)強(qiáng)放射治療(volumetric intensity-modulated arc therapy, VMAT)技術(shù),對(duì)于瘤腔靠近腦干、海馬、視神經(jīng)、視交叉、眼球等的患者,為保護(hù)正常組織,均采用VMAT技術(shù),余應(yīng)用IMRT技術(shù)。
1.4 化療方案 從放療第1天至放療結(jié)束持續(xù)給予替莫唑胺(temozolomide,TMZ)同步化療,75 mg/(m2·d),連續(xù)口服42~48 d;放療結(jié)束后采用TMZ輔助化療,具體方案如下:第1周期TMZ 150 mg/(m2·d),連服5天,從第2周期開始,TMZ 200 mg/(m2·d),連服5天,28天為1周期。
1.5 隨訪 放療結(jié)束后4周及12周復(fù)查頭顱MRI平掃、增強(qiáng)及灌注成像(perfusion imaging, PWI),以后每隔3個(gè)月復(fù)查一次,2年以后每隔半年復(fù)查一次,期間如出現(xiàn)頭痛、視物模糊等癥狀,縮短復(fù)查時(shí)間。所有患者均采用門診及電話隨訪,隨訪時(shí)間為2~56個(gè)月,中位隨訪時(shí)間為15(10,16)個(gè)月。所有患者隨訪至死亡或至截止日期2020年5月16日。
1.6 療效評(píng)價(jià) 記錄所有患者的疾病無進(jìn)展生存時(shí)間(progression-free survival,PFS)和總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OS)。PFS定義為手術(shù)之日至最早發(fā)生基于神經(jīng)腫瘤反應(yīng)評(píng)價(jià)(response assessment in neuro-oncology, RANO)標(biāo)準(zhǔn)[3]的疾病進(jìn)展或者復(fù)發(fā),以及任何原因?qū)е禄颊咚劳龅臅r(shí)間間隔。OS定義為自手術(shù)之日起到患者死亡或者最后一次隨訪的時(shí)間間隔。
1.7 統(tǒng)計(jì)學(xué)方法 采用SPSS 21.0軟件對(duì)數(shù)據(jù)進(jìn)行分析;用生命表法繪制PFS及OS生存曲線;用Kaplan-Meier評(píng)估生存率的差異,Log-rank檢驗(yàn)法進(jìn)行單因素生存分析;將單因素分析中具有統(tǒng)計(jì)學(xué)意義的變量納入多因素Cox比例風(fēng)險(xiǎn)模型篩選生存影響因素。以P<0.05為差異有統(tǒng)計(jì)學(xué)意義。
2 結(jié)果
2.1 78例患者的隨訪結(jié)果 78例患者隨訪率100%,均完成同步放化療,輔助化療周期1~24周期,隨訪時(shí)間為2~56個(gè)月,中位時(shí)間為15(10,16)個(gè)月,隨訪至患者死亡或截止2020年5月16日,其中10例患者存活,存活病例中 7例患者出現(xiàn)病情復(fù)發(fā)。78例患者1年、2年及3年OS分別為62.82%、30.77%、12.82%。見圖1。

圖1 78例膠質(zhì)母細(xì)胞瘤患者總生存曲線及無進(jìn)展生存曲線
2.2 單因素分析 在單因素分析中發(fā)現(xiàn),患者的性別、年齡、放療劑量、IDH-1突變情況、MGMT狀態(tài)、Ki-67表達(dá)情況所致的OS及PFS差異無統(tǒng)計(jì)學(xué)意義(P>0.05),而不同KPS評(píng)分、術(shù)中切除情況、輔助化療周期數(shù)的患者PFS及OS比較,差異有統(tǒng)計(jì)學(xué)意義(P<0.05)。見表1。

表1 78例膠質(zhì)母細(xì)胞瘤患者單因素分析
2.3 多因素Cox回歸分析 結(jié)果顯示,KPS評(píng)分、術(shù)中是否全切、輔助化療療程數(shù)對(duì)患者生存情況的影響具有統(tǒng)計(jì)學(xué)差異(P<0.05)。將在單因素分析中有統(tǒng)計(jì)學(xué)意義的3個(gè)變量納入多因素Cox回歸分析,賦值:KPS評(píng)分≤60分=0,>60分=1;未全切=0,全切=1;輔助化療≤6周期=0,>6周期=1;結(jié)果顯示KPS評(píng)分、術(shù)中是否全切、輔助化療療程數(shù)均是影響患者OS的獨(dú)立預(yù)后因素(P<0.05),而輔助化療療程數(shù)非PFS的預(yù)后影響因素(P=0.109)。見表2、圖2。

表2 78例膠質(zhì)母細(xì)胞瘤患者多因素分析

續(xù)表2

注:A.KPS≤60分與>60分患者的OS曲線;B.KPS≤60分與>60分患者的PFS曲線;C.化療周期數(shù)≤6周期與>6周期患者的OS曲線;D. 化療周期數(shù)≤6周期與>6周期患者的PFS曲線;E.手術(shù)全切與未全切患者的OS曲線;F. 手術(shù)全切與未全切患者的PFS曲線。
3 討論
膠質(zhì)瘤是顱內(nèi)常見的惡性腫瘤,其中以GBM惡性程度最高,影響其預(yù)后的因素極其復(fù)雜。本研究發(fā)現(xiàn),患者放療前KPS評(píng)分、術(shù)中腫瘤是否全切以及輔助化療療程與患者預(yù)后密切相關(guān),而性別、年齡、放療劑量、分子表型如IDH1、Ki-67、MGMT與預(yù)后無關(guān)。
KPS評(píng)分最常被臨床用來評(píng)估患者身體功能狀態(tài),評(píng)分越高,體能越好,對(duì)各種抗腫瘤治療更能耐受。Teo等[4]發(fā)現(xiàn),GBM患者KPS評(píng)分越高,則預(yù)后越好,本研究結(jié)果與之一致。目前GBM首選治療仍為手術(shù)切除,術(shù)中腫瘤是否全切與患者生存預(yù)后直接相關(guān)[5]。本研究中腫瘤全切的患者死亡風(fēng)險(xiǎn)明顯降低,且PFS及OS均優(yōu)于未全切者。GBM侵襲性生長的生物學(xué)特性致使其全切困難,故而術(shù)后放化療對(duì)改善患者預(yù)后尤為重要。而放療劑量并非越高越好,因?yàn)樵诳刂颇[瘤的同時(shí),放射線對(duì)神經(jīng)組織的損傷也顯著影響患者的預(yù)后及生存狀態(tài)。靶區(qū)勾畫不論“RTOG法”還是“EORTC法”,總照射劑量均不超過60 Gy。本研究也證實(shí)放療劑量提高到60 Gy以上,患者的生存時(shí)間并無延長。而增加輔助化療療程,則可以明顯的延長患者的OS,同時(shí)藥物不良反應(yīng)無明顯增加[6]。本研究中長療程化療總生存曲線明顯高于短療程化療。而對(duì)于PFS,生存曲線雖然分開,但P=0.109,考慮評(píng)估過程中存在假性進(jìn)展,而繼續(xù)服用TMZ仍然有效所致。由此可見對(duì)于GBM預(yù)后除了以上因素,分子分型也是重要因子。①IDH。IDH突變型GBM是2016年中樞神經(jīng)系統(tǒng)腫瘤WHO分類中正式提出的亞型,是以星形細(xì)胞分化為主要成分的高級(jí)別膠質(zhì)瘤,伴IDH1或IDH2突變。由于由彌漫型星形細(xì)胞瘤( WHO Ⅱ級(jí)) 或者間變型星形細(xì)胞瘤( WHO Ⅲ級(jí))惡變而來的膠質(zhì)母細(xì)胞瘤與IDH突變有關(guān), 也稱作 “繼發(fā)性膠質(zhì)母細(xì)胞瘤”[7]。目前IDH狀態(tài)主要通過活檢或者術(shù)后病理確定,但已有放射免疫學(xué)模型利用多參數(shù)MRI建立多區(qū)域特征來檢測(cè)IDH1狀態(tài)[8],這對(duì)無法取得腫瘤組織的患者預(yù)后評(píng)估有重要指導(dǎo)意義。GBM伴有IDH突變預(yù)后較好[9],劉競(jìng)輝等[10]的研究也顯示, IDH無突變是GBM患者預(yù)后不利的分子表型之一。②Ki-67。Ki-67是應(yīng)用最為廣泛的增殖標(biāo)志物,其在多種實(shí)體腫瘤的臨床進(jìn)展和預(yù)后判斷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準(zhǔn)確和標(biāo)準(zhǔn)化的Ki-67評(píng)分尤為重要[11],王艷敏等[12]發(fā)現(xiàn),Ki-67指數(shù)與GBM患者的總體生存率明顯相關(guān)。然而本文卻未顯示出以上結(jié)果,考慮為78例中僅42例術(shù)后病理完善了該標(biāo)志物的檢測(cè),存在一定的偏倚。③DNA修復(fù)蛋白O6-甲基鳥嘌呤DNA甲基轉(zhuǎn)移酶(O6-methylguanine-DNA methyltransferase,MGMT)。MGMT能從O6烷基-鳥嘌呤位置去除烷基團(tuán),修復(fù)烷化劑類化療藥物造成的DNA損傷,MGMT啟動(dòng)子的甲基化狀態(tài)可預(yù)測(cè)腫瘤對(duì)替莫唑胺化療的反應(yīng)[13]。特別是在IDH野生型患者中,約40%的患者M(jìn)GMT啟動(dòng)子的甲基化表達(dá)過高,這些患者對(duì)TMZ或TMZ和卡莫司汀的組合有更好的治療反應(yīng)[14]。因腫瘤呈侵襲性生長,經(jīng)過積極治療后仍難免復(fù)發(fā),所以急需一種針對(duì)侵襲環(huán)節(jié)中效應(yīng)分子的靶向藥物來改變GBM的預(yù)后。李化龍等[15]應(yīng)用貝伐珠單抗聯(lián)合TMZ對(duì)復(fù)發(fā)膠質(zhì)瘤進(jìn)行治療,與單純TMZ組對(duì)比,PFS延長5周,6m-PFS增加22.5%(P=0.030)。Jawhari等[16]研究發(fā)現(xiàn),40%~60%的GBM顯著表達(dá)EGFR,而單純采用 EGFR磷酸化抑制劑并不能有效抑制GBM的惡性增殖,或許是由于存在多個(gè)信號(hào)轉(zhuǎn)導(dǎo)通路,潛在的反應(yīng)性突變耐藥機(jī)制或者大腦對(duì)常規(guī)劑量的酪氨酸激酶抑制劑吸收有限造成的。
目前對(duì)GBM臨床預(yù)后因素的相關(guān)研究增多,越來越多的預(yù)后因素被不斷的發(fā)現(xiàn),本研究綜合患者的一般情況、治療方式以及基因或者分子分型,發(fā)現(xiàn)患者放療前KPS評(píng)分、術(shù)中切除情況、輔助化療周期數(shù)是影響GBM術(shù)后的獨(dú)立預(yù)后因素,KPS評(píng)分越高、術(shù)中全切、延長輔助TMZ化療周期數(shù)可以顯著延長患者的OS,其中KPS評(píng)分高低及術(shù)中全切與否明顯影響患者的PF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