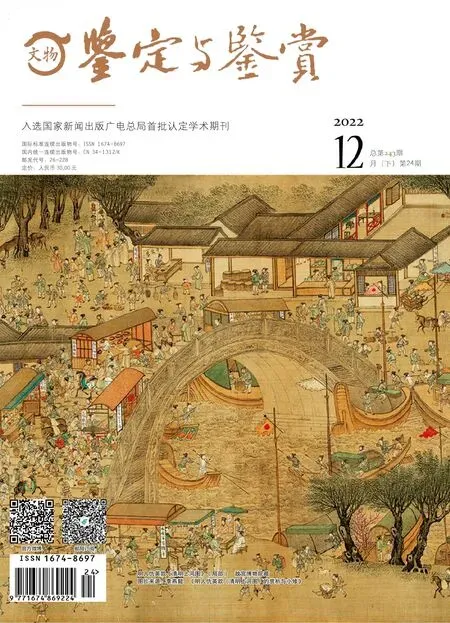古代長江三角洲地區的水運交通
陸曄 巫驍
(南京市博物總館,江蘇 南京 210000)
長江三角洲地區位于長江流域下游,由于這片區域河道縱橫,自古便有“舟楫之國”的說法,這里農業發達,物產豐富。長江三角洲地區因眾多的沿江沿河港口、豐富的水道以及先進的造船工藝,成了我國古代南方地區水上交通最為繁忙的區域。
1 長江三角洲的水文特征對于航運的優勢
徑流條件:鄱陽湖和洞庭湖為長江流域上游兩大湖泊,因洞庭湖、鄱陽湖等湖泊的蓄水能力強,有削峰補枯的調節作用,使得長江三角洲地區的河網即使在枯水期也擁有較大的徑流,使其擁有通暢的航道和深水岸線。同時長江流域含沙量相對較小,除金沙江中游、嘉陵江中上游等局部河段含沙量在1~10千克/立方米外,大多數河流在1千克/立方米以下,長江年平均含沙量僅0.54千克/立方米。河流的含沙量會直接影響船舶的吃水量,船舶吃水大小反映了船舶的大小,繼而影響其裝置貨物的容積。即吃水越大,船體越大,所載貨量也越多,航運價值也就越高。長江三角洲地區河段含沙量小,航道深,河道不易淤積,有利于船舶航運。據測繪數據,從吳淞口至南京的長江水道可以保持10米水深,基本暢通。
潮汐條件:由于受天體運行的影響,長江河口的平均潮汐差能達到2.5米,通航中可利用的水深條件良好。
避風條件:相比東南部沿海地區,長江三角洲所處地域受臺風影響并不頻繁,且河口內風浪小,可以獲得良好的避風條件。
地形氣候條件:長江三角洲是平原地區,地勢平坦,水流平緩,降水豐富均勻,流量季節變化小,地區氣候溫暖,雨量充沛,汛期時間長,冬季最低氣溫在零下4攝氏度左右,無結冰期,航運條件優越。
2 古代港口
2.1 揚州
東周末年揚州建城,始稱廣陵。公元486年(周敬王三十四年),吳國在邗江(《水經注》稱韓江)旁建邗城挖河溝,使長江和淮水相連,大致從今天的揚州市南長江北岸起,到今淮安清江市淮水南岸為止,是我國最早的人工運河,今天的運河段即是古邗溝。揚州的繁榮離不開大運河的開鑿,大運河雖以東都洛陽為中心,但是連接大運河南北的揚州因處于通航能力好的長江流域成了焦點,因此大運河的開鑿使得揚州成為僅次于兩京(長安,洛陽)的大都市。
由于揚州處于大運河與長江的交匯點,成為重要的物資集散中心。古書記載:“維揚萬貞者,大商也,多在于外,運易財寶以為商。”“揚州地當沖要,多富商大賈,珠翠珍怪之產”。揚州物產極為豐富,據《新唐書》記載揚州所產土貢有:“金、銀、銅器、青銅鏡、綿、蕃客袍錦、被錦、半臂錦、獨窠綾、殿額莞席、水兕甲、黃米、烏節米、魚臍、魚魚夸、糖蟹、蜜姜、藕、鐵精、空青、白芒、兔絲、蛇粟、括姜粉。”揚州更是歷代鹽鐵轉運之地,總匯東南財稅,政府也會在此開設店鋪進行貿易,使之成為重要的商業中心。揚州除了商業興盛,手工業也相當發達。除了江南常見的紡織業外還有銅器、木器制品、制糖、制鹽、釀酒、鑄錢以及其他手工業。其中以青銅鏡最為著名,在唐代被列為貢品,“唐于揚子江心鑄銅鏡,宋尚入貢,今無”。1998年,在印度尼西亞勿里洞島海域的一塊黑礁石附近,德國人發現了一艘唐代沉船并成功打撈,這艘黑石號沉船上足足有6萬多件珍貴文物,其中出土的一面銅鏡上刻有“唐乾元元年戊戌十一月廿九日于揚州揚子江心百煉造成”的銘文,由此認為黑石號沉船是從揚州起錨出發,滿載中國貨物前往伊朗的希拉夫港。
在唐朝中后期,經濟越發繁榮,隨著揚州等貿易港口的設立,造船工藝逐漸精湛,推動海上絲綢之路逐漸替代絲綢之路成為對外貿易的主要通道,把各種陶瓷制品運往國外乃至非洲,同時帶回各種香料、獸角和黃金,揚州成為重要的貿易港口。
2.2 南京
公元472年(周元王),越國滅吳,范蠡筑越城成為南京最早建造城池的記錄,此后自吳大帝孫權建石頭城于此,到“中華民國”建立,南京一直是江南地區最為重要的政治中心之一,這使得南京擁有著“六朝古都,十朝都會”的美譽。雖然南京缺乏揚州發達的工商業與漕運交通的便利,但是其重要的政治與軍事意義也使得其成為長江口地區的重要港口。
由于南京是南方地區的經濟政治中心,導致其不可避免地成為軍事重鎮,加之毗鄰長江,水軍的駐扎使南京造船業獲得發展。據史料記載,孫權在建業建造了巨大的五層海船,能容納萬人。公元230年,孫權稱帝的第二年,派衛溫、諸葛直兩將率兵士萬余人自建業出海航行至夷洲(臺灣)及亶洲,除了向東以外,孫權還向南、向北大規模派出海軍:向北方向船隊航行至遼東朝鮮半島;向南方向,吳國憑借海軍實力在越南北部設置交趾郡,以此為基地與南洋、西洋各國的海上來往和貿易進一步發展。到了明代,南京更是成為全國造船與管理中心。據《明史》記載:“洪武初,于都城南新江口置水兵八千。已,稍置萬兩千,造舟四百艘。”可見位于南京新江口的造船廠,最早是用于建造戰船抵御海上匪寇的,屬于軍事用途。《龍江船廠志》中又提到:“洪武初年,即于龍江開設廠造船,以備公用,統于工部,而分司于都水。”龍江船廠統轄于工部名下而不是兵部,很明顯其建造船只的用途不會是軍事,而應該偏重于政府運輸和對外活動。由此可見,在明朝初年南京就已經具備建造各種大型海船的能力,也為永樂時期能建造寶船完成下西洋的壯舉提供了堅實的基礎。直到現在南京依然保存著龍江船廠遺址與寶船廠遺址。
2.3 上海
上海位于長江口南岸,西部在6000年前形成陸地,東部則形成于2000年前。唐開元初年(713)在此修捍海塘,土地淤積,人口增加。公元751年設華庭縣。1260—1274年(南宋景定、咸淳年間)形成重要港口,因以此地出海,得名上海。康熙二十四年(1685),清政府在上海設立海關,成為“江海之通津,東南之都會。”是我國最早設立的海關之一。
2.4 太倉
瀏河貫穿太倉進入長江,是長江口地區的江防重鎮和漁港,古稱瀏家港,始興于隋唐時期。元朝,政府實施漕糧北運,在瀏家港沿線建大型碼頭泊位,建立海運倉儲和海事機構,自此長江中下游地區、浙江溫臺等沿海地區以及日本、琉球、高麗、安南等國的商船都集結于瀏家港,瀏家港成為“六國碼頭”“天下第一碼頭”。明朝,瀏家港作為鄭和七下西洋起錨地,發展達到鼎盛,成為當時世界上重要的樞紐港。明以后,由于種種原因,港口逐漸沉寂。
2.5 南通
南通位于長江入海口北岸,宋元時代因淮南鹽場鹽業生產而發展,運鹽河通暢促進了南通古港的興旺。明代成了棉花、土布的集散中心。
3 航運水道
3.1 河運交通
河運交通(圖1)一直是古代水上交通的最基本方式,其特點在于借助自然或人工形成的河網水道運輸,其優勢在于運輸工具制造的要求較低。劣勢也很明顯,受制于河道水深,單艘船只的運力有限,枯水季甚至無法通航。長江三角洲地區最具代表性的河運水道就是大運河。據史料記載“大業元年(605)三月辛亥,命尚書右丞皇甫議發河南、淮北諸郡民,前后百余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谷、洛水,達于河,復合板諸(河南汜水縣東北)引河,歷滎澤入汴(河南開封)。又自大梁之東引汴水入泗,達于淮。又發淮南民十余萬開邗溝,自山陽(江蘇淮安縣)至揚子(揚子津)入江。”“大業四年(608)春正月乙已,詔發河北諸軍百余萬穿永濟渠,引沁水南達于河,北通涿郡。”“大業六年(610)冬十二月已末,敕穿江南河,自京口(江蘇鎮江)至余杭(浙江杭州),八百里”。作為連接南北的大運河,其使得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五大水系連接在一起。于是長江流域的物產可以直接通過水運運輸到揚州、鎮江兩地再分散到南北各地,南北各地的物資也可通過大運河匯聚到這里,使得揚州、鎮江以及其周邊城市成為商業貿易的中心。

圖1 河運交通
3.2 海運交通
海運交通發展要遠遠晚于河運交通的發展,但其具備的能力也是河運交通無法達到的。首先海運根本不會受到河道的限制,其航行范圍極大。其次在掌握水文和氣象條件的前提下,海運交通可全年進行。最后,海船遠大于河船,其運力很強。同樣海運交通也存在對船只建造要求高、遠洋航行風險大等弊端。最為著名的古代海運水道便是元代海上漕運(圖2)。

圖2 元朝海運交通
元朝疆域是中國歷史上最為遼闊的,其定都于大都(北京),由于大都地處北方,農作物成熟周期長,加之作為國都以后,人口迅速膨脹,元朝統治者對于農業生產并沒有足夠的重視與鼓勵措施,所以元帝國的北方地區依舊依賴南方的糧食漕運。但是京杭運河由于失修與黃河“奪淮入海”造成中段河道阻塞,原本依靠大運河的漕運無法正常運行,加上漕運船只運輸量不大,難以維系需求。至元十九年(1282),元政府采納朱清、張瑄的建議,建造海船60艘,自昆山郡瀏家港(江蘇太倉)運糧4萬石到直沽(天津),最初海運要分為春夏兩次,后來隨著新航線的開通與運力的提升,只需要一次就能完成,運能最高時可達350萬石。元代全國稅糧總數大約是1200萬石,因此漕糧海運成為維系元政府國家機器運行的重要的命脈,為確保這條海運航線的安全,元政府更是安排了戰艦護航,長江口地區就在太倉、崇明兩地設置兵站,派遣水兵與哨船巡邏。盡管元代海運屬于近海航運,但是卻打破了自隋代開始了700余年的漕運模式,積累了豐富的造船與航海經驗,極大地推動了南北交流與對外交流。
4 航運船只
長江三角洲地區作為中國古代重要的水運交通中心,至今仍然發揮著重要的作用。船只作為水上交通的重要工具,也成了古代長江三角洲航運繁榮的佐證。1960年3月,在江蘇揚州邗江區施橋鄉夾江內發現了一只古代大木船和獨木舟。這艘楠木制揚州施橋古船為唐船,用料厚實,結構堅固,制作精良,非一般民船。出土時船身正面朝上,船艄破損殘缺,船長18.4米,中寬4.3米,型寬3.6米,底寬2.4米,艙深1.3米,船板厚13厘米。全船殘留部分分作5個大倉,艙壁間隔約1米,且沿艙壁頂端一線。據推測,大木船有可能為唐中期往來長江和運河的官用運輸貨船。獨木舟則由整棵大楠樹干當中刳空制成,船頭尾微翹,用檀香木膠合釘板而成,船尾為樹根,船頭為樹梢,圓底。船體全長13.65米,寬0.75米,深0.56米,呈長條狀,造型與現代龍舟相似,船舷和船底板厚6厘米。拴繩子的木扣在船頭右側,船尾有兩個方形的穿孔。據唐代史料記載,揚州風俗中,每年端午節要在江邊支流上舉行“競渡采蓮龍舟之戲”,觀眾數萬,熱鬧非凡,而揚州制作的舟不僅遠銷各地,還進貢京師,可見造船工藝之精湛(圖3)。

圖3 唐代競渡船(龍舟)
1978年揚州“七八二”工程施工時,發現南北向的河流和木橋遺跡,出土殘獨木舟兩只。其中一個獨木舟在橋墩南被發現,為楠木鑿成,呈東低西高,兩頭高度相差1.4米。獨木舟殘長6.3米,寬0.7米,口寬0.52米,呈“U”字形,內部發現對稱的隔艙凹槽及隔艙板,腐爛殘破嚴重,形狀大體可見,尾部齊平,頭部尖翹。另一只獨木舟東高西低,高差約0.45米,全長6.1米,寬0.6米,兩端平齊。獨木舟上有一排小木樁和木板,其中有三根木樁打穿舟底伸入舟下0.13米。史料記載,唐揚州城是“水上都會”,獨木舟的出土佐證了揚州作為唐代四大港口城市之一,水上交通極為便利。
1999年揚州文昌閣附近又發現了一只獨木舟,可惜船身被破壞無法清理出土。根據出土物品及相關考證,此舟由一根巨木制成,發現時殘留部分為5米,艙口朝上呈傾斜狀,另一端有隔艙板,可能為唐中期之前的木船,因意外沉沒水中。在同期的地層中,發現了文蛤殼,說明唐朝揚州百姓能吃到海貝,海運貿易便捷。
1973年南通如皋縣蒲西鄉馬港河旁出土唐代單桅運輸木船(圖4)。考古資料顯示,這艘如皋唐代木帆船是一只載重約20噸的運輸船,船長17.32米,船面最狹處1.3米,最寬處2.58米,船底最狹處0.98米,最寬處1.48米,船艙深1.6米。這樣窄長的單桅木船速度快,非常適合在江面上行駛,同時船體容積大、倉位多,又適合運輸貨物,如皋木船的出土也再次印證了長江三角洲地區古代水上交通運輸工具的發達。

圖4 如皋木船出土照片
此外,1975年常州武進縣在建設農田水利工程時發現漢代古船。1978年上海嘉定疏通封浜河,在河底挖掘出南宋木船。上海橫沙島海床下的清代“長江口二號”木質沉船,是我國現存的水下考古發現的保存最完整、體量最大、文物最多的木質沉船。這些沉船展現出的工藝無一不體現了我國古代精湛的造船水平,以及對長江三角洲地區水運利用的悠久歷史。
5 結語
長江三角洲地區依靠眾多的沿江沿河港口、豐富的水道以及先進的造船工藝,成為我國古代南方地區最為優秀的航運中心,長江三角洲地區人口稠密,經濟發達,對航運的需求量大,人們重視航道治理以及港口建設,良好的區域交通條件為區域發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環境,加速了各地方之間的商品貿易往來,從而帶動了古代長江三角洲區域的社會發展,延續至今仍然是現代航運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地區發展中仍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