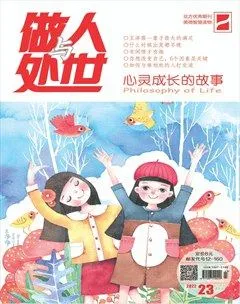告別孤獨
朋余
獨自的狂歡只是為了掩飾寂寞
哲人這樣描述“孤獨”:“孤獨是一種隱疾。”進而給出了一種告別孤獨的場景:“我們天天生活在喧鬧當中,接觸很多的人,所以我們經常希望可以找一個清靜的地方,因為我們對人產生了疲勞,喧鬧剝奪了我們跟自己對話的時間,剝奪了我們的閑情,只有你有時間跟自己對話,你才能自我反思。”每個人都會經歷孤獨,孤獨像是人生的伴侶,可在不同的人生階段,人對待孤獨的態度和感受往往不同。
大學剛畢業,又經歷失戀,身邊的好友陸續升學和工作,我也入職一家新公司,由于不善言談,和同事的關系一般,我一個人蝸居在出租屋里,那段時光是我最孤獨的時候。一個人的時候最容易放縱自己,我開始報復性地熬夜,長時間地打游戲,也常常一個人在被窩里偷偷回憶美好時光,然后自怨自艾,黯然神傷。有時也會立個深情文藝的人設,在朋友圈曬曬自己的憂傷,自揭傷疤企圖博得別人的同情,可終究是徒勞,得到的只是別人的一笑而過。其實,哲人早就點破了這種孤獨的實質:“孤獨并非是在自己心情壓抑或者是失戀的時候出現的,那種感覺只是空虛和寂寞,稱不上是孤獨。”
有一張《國際孤獨等級表》,“一個人去吃飯、看電影”這樣的初級孤獨對于我來說已是家常便飯;“一個人去看海、游樂園”這樣級別的孤獨,我沒體驗過,因為沒錢沒時間,也懶得去;最高等級的孤獨是“一個人做手術”,我的身體挺好,也沒有經歷過。而對于我來說,最孤獨的感受是,一個人在出租屋里,突然手機不見了,卻找不到一個人來打一下我的電話。不知道這算是什么等級的孤獨?
后來,我讀了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內容很長也很雜,可給我的精神慰藉是真實的。其中有句話這樣說:“人世間沒有任何理想值得以這樣的沉淪作為代價。”我也一直在思考生活的意義,現在的生活是我想要的嗎?
一天,我接到母親的電話,疲憊的聲音沿著電波傳來,告訴我外公不在了,還叮囑我不用回去,請假來回跑不容易。可我不能不回去,比起外公故去的悲痛,我更擔心母親,我能想象母親拿著電話強作鎮定的樣子,我知道從此以后我就成了她僅存的依靠。此時,我突然明白,生活不只有詩和遠方,還有眼前的傷,而背后永遠都有父母深情的凝望。不管未來怎樣,哪怕為了日漸蒼老的親人,我也該振作起來,迎著風雨而上。
我不再自我懷疑,利用工作之余開始備考教師資格證、普通話證,周末和節假日也不再悶在出租屋里,而是外出去游覽美景,探尋美食,用腳丈量城市的每一個角落,用心去感受生活的美好。一年后,我順利考下兩證,應聘到一所學校做了受人尊敬的辛勤的“園丁”。我也走遍了城市的每一個角落,貪戀一個人趕回大學食堂嘗一口酸湯鍋的暢快,享受一個人在圖書館里待上一天的充實。這時我發現,擺脫了煩惱的束縛,心變得自由而充實。一個人可以過得很好,一個人也更應該過得好,因為這世間不只有痛苦和煩惱,多彩和幸福才是生活的真實面目,我們要勇于去探索,善于去發現。
尼克·胡哲在給自己的信中寫道:“每個優秀的人,都有一段沉默的時光。那一段時光是付出了很多努力,忍受了很多孤獨和寂寞,不抱怨不訴苦,只有自己知道,而當日后說起時,連自己都能被感動的日子。”那段時光痛苦與否取決于我們的心態,試著去告別孤獨的感覺,讓自己深深地在幸福的土壤里扎根。當我們熬過那段孤獨的時光或旅途,就會發現,前方早已是一片蔥蔥的原野,而所謂的孤獨之苦只是路邊的一處殘景,走過了就是柳暗花明。
我一直相信,所有生活賜予我們的挫折、困惑、煩惱、風雨都是來幫助我們成長的,孤獨恰是它們的集合體,一種糾纏在一起的產物。所以,學會去告別孤獨,用心去體會告別時的快樂,這種感覺像是一種新生。
(責任編輯/劉大偉 張金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