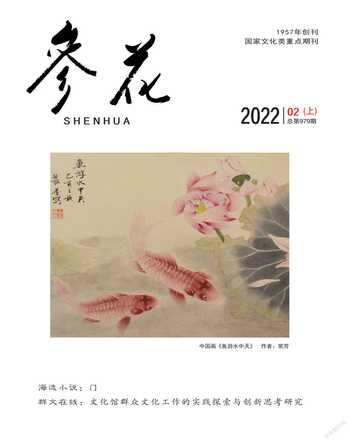小扁舟里搖出的歡情(外一篇)
有遠路而來的朋友登門,我除了請其品嘗正宗湖鮮之外,有時間就會引領其到依山傍水而居的朋友船上一游。遠方的客人不約而同地愛上主家這條住宅船,因為主家把這里面裝潢得跟岸上的商品房別無兩樣,會客室、衛(wèi)生間、空調(diào)、洗衣機一應俱全,主家好客,登船一坐,一杯綠茶,太湖邊秀麗風情、煙波浩渺,盡覽眼中。于是剛剛才謀面的你、我、他,恰似早已傾心密友般,聊天說地起來。主家有各式船只五條,住宅大船、汽艇、小木船,客喜大船,我獨好小木船。
此情此景常常讓我想起父親曾經(jīng)擁有的小木船,用小扁舟來定名似乎更為貼切,兩頭尖尖,中間如人的眼球般弧狀突出,那是父親用來放鴨的必需品。父親,一名師范速成班畢業(yè)的老師,大隊里需要知識分子來當大隊長,所以總在中山裝上口袋插支筆的父親就大隊長兼會計,幫社員抓生產(chǎn)了。上有寡母下有我們姐弟仨的父親,后來就想到放鴨這條路。
我至今不曉得父親的船究竟是買的二手,還是請別人在外面打造的,反正就看到在那船下水前一陣日子,父親邊哼著“日落西山紅霞飛”,邊用桐油把它擦過三遍。父親的放鴨還是和別人不同,他不走遠,沒有像別人那樣搖著小木船趕著鴨子,游過陌生的天空、陌生的水面、陌生的面孔。他就趕著鴨子在我們家獨戶小屋旁的小河里,約兩公里的路程來回吃食。因為社員們幾乎每天都有這樣那樣的事情來找他,我記得連著三天傍晚時分,有個女的鼻青臉腫的,坐在我們家大門口的羊隆溝上一把鼻涕一把淚,吼著“魏會計呀,他又打我了,你一定要幫幫我啊”。
父親的船上沒有拱起的蘆席棚。不去遠處,自然也無須別人放鴨船上備用的小泥爐。船艙內(nèi)一個熱水瓶、一只搪瓷杯,倒是有一個物件,父親必帶無疑,如寶貝般用一根細鉛絲綁在一張帶靠背的小板凳上。那是一只寬三十厘米、高二十五厘米,外板殼上有波浪條紋、表面為藍色塑料盒的收音機,父親說:它可太重要了,聽聽一天不落的天氣預報、時事新聞,并且歌曲一響,有它相伴就沒有個“累”字,跟著哼,渾身是勁。
來找父親有事的人,碰上父親正在這兩公里的水路上歡騰,他們就會很樂意地沿著岸路順方向?qū)とァP闹凶允菦]有燥意,因為走一會兒,能聽到喇叭聲,那父親就一定是在不遠處了。如今回想起來唯一有點遺憾的是,我全程坐過父親的小扁舟總共只有一次,瘦小的父親努力地撐著一支長竹篙,鴨子們乖巧地在前面排成一個倒置的扇形,小河兩旁的岸地卻原來都是別人家的自留地,一路過去,總有人向父親打招呼:“魏會計,明天天氣怎樣,我的腳有點酸,天氣預報是不是有雨呀?”“魏會計,你把那喇叭聲音開響一點啊。”“魏會計,我剛割了幾棵青菜,你要不要帶點回家?”父親一臉的燦爛朗聲一一答應著。我想我那時就應該明白,為什么如今父親去世好幾年了,但凡村中認識他的人只要提起他,第一句話總是:“魏會計,隨便嗲辰光都是笑嘻嘻。”
父親的放鴨雖說與眾不同,卻也非常成功,父親的鴨鴨生了那么多的蛋蛋,晚飯就可以有下飯最靈的菜絲:大蒜炒蛋。一時吃不掉那么多鴨蛋就腌腌,沿途送給人家還個人情。全家圍在一起喝白粥就咸蛋時,我和妹妹還可以光吃黃去白,因為母親肯定不會因為這個舉止罵我們浪費,當然去掉的白最后必然是父母親的腹中物。另有一件連那時尚年幼的弟弟都記著的成功之舉:父親用二十六個鴨蛋放在雞窩里孵出了二十三只小鴨。全家一致斷定,這絕對與父親放鴨時用收音機放歌及他哼歌從這小扁舟中搖出的歡情有關。
真的想不起來給父親、給我們家?guī)砟敲炊鄳涯睢⒛敲炊鄽g情的小扁舟最終去了哪里,但是我對小木船的情結(jié)卻是永遠也抹不去的。每當有我的一個朋友、我的知己能在太湖邊木船上多一份歡笑、溫情,自是作為營造者的我心中一大快事。
又陪母親看春晚
今年春節(jié)最值得期盼的是又可以陪著母親一起看春節(jié)聯(lián)歡晚會了。
一九八三年第一屆春節(jié)聯(lián)歡晚會,父親領著全家在鄉(xiāng)政府大院坐在條凳上全神貫注,如癡如醉,圍著那臺電視機,認識了能說相聲還能和李谷一對唱《劉三姐》的姜昆,知道了那個演《吃雞》小品的王景愚非常滑稽。我不知道當時父親是如何知曉有關春晚這個消息,更沒問父親是用什么方法,可以讓全家都能在政府大院看電視、看春晚。總之,父親對于我們只有一個概念,父親是全家的天,有父親在,天就不會塌。跟著父親就會有驚喜。而現(xiàn)在回想起來,父親骨子里原本就有那種崇尚文藝的根苗,無論生活有多少磨難,他始終都沒有放棄讓日子增添色彩的機緣。而母親做姑娘的時候演過小戲,我們慶幸,這方面,我們遺傳了他倆很多。
從一九八三年春節(jié)開始,每年除夕等待春晚就成為我們必不可少的目標。我們只是真的很喜歡那一個個文藝節(jié)目,主持人掀起的服飾潮流,也是我們愛臭美的小女生熱衷的緣由。當然條件還是有限,一九八四年年末,我們家還沒有電視機,為了能再次看到春晚,父親花一百五十元的“巨資”從常州知青朋友那兒組裝了一臺黑白電視機,搬到了街上外婆家,全家又在外婆家圍著春晚度過了除夕。
這以后的除夕,其實為了能看春晚還頗費周折,我家的祖先是從常熟搬過來的,祭祖習慣在除夕,每年在老家做完這些儀式之后,要看春晚的話,就必須再摸黑騎車三公里,趕到街上外婆家。于是,好多年除夕夜晚,父親的自行車龍頭前座帶著弟弟,我坐后座,踩在羊腸小道前面,嘴里喊著:“當心,這邊小石子多”,母親帶著妹妹在后邊跟著“哦”。
后來我家有電視機了,接著又有彩色的了,看完春晚后我們還會對每個類型每個節(jié)目都說出我們個人的點評。爆笑處甚至全家搶毛巾,我覺得那是全家都在盡情釋放的時刻。父母親釋放一年的辛勞,我們釋放學習壓力。
再后來,我和妹妹出嫁了,我們有了我們的家。弟弟在外創(chuàng)業(yè)成功,有幾次除夕之夜居然是他出差法國、美國的日子。父親在的時候是父母親倆人一起看春晚,現(xiàn)在父親過世,母親看春晚的時候又和誰去“眉飛色舞”呢?
春晚有著母親永不凋謝的記憶,作為老大“魏一”的我決定,號召“魏二”“魏三”,二〇二一年除夕,帶上我們的家人、孩子陪我們的母親一起再次感受這飽含溫情的春節(jié)聯(lián)歡晚會。
作者簡介:魏平,女,系無錫作家協(xié)會會員,江蘇省殘疾人作家協(xié)會理事。作品散見于《宜興日報》《無錫日報》《江南晚報》《西南作家文學》《中國作家》等報刊,數(shù)十篇文章入選《至味宜興》《陶都走筆》《激蕩與回望》等合集。
(責任編輯 王瑞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