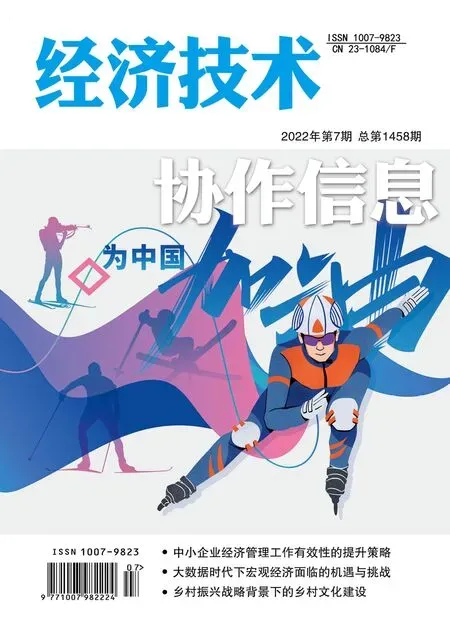有限責任公司章程限制股權轉讓條款效力研究
◎高悅函
一、章程限制股權轉讓的理論
(一)條文梳理
1993年的《公司法》因公司發展歷史較短,體現公司自治方面的權限較少。第三十五條是對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權轉讓規定,該規定將股權轉讓區分為股東內部轉讓和向外部轉讓兩種情形。此外,股權轉讓的規定還體現在第二十二條和第三十八條中,但結合三條規定來看,第三十五條是強制性法律規范,但第二十二條又對轉讓出資做了其他限制;第三十五條體現股東的意思自治,但第三十八條的股東會決議又將出資轉讓歸為公司意思決定的事項。2005年《公司法》修訂,公司自治的幅度和權限增大,加入了章程自治條款。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權轉讓的相關規定編為第三章,調整成為第七十二條四款內容。與1993年的《公司法》相比較,與公司章程有關的規定即是增設第四款“公司章程對股權轉讓另有規定的,從其規定”。此時七十二條的前三款由強制性法律規范轉變為任意性的法律規范,可以排除適用,只有在當事人沒有依據第四款制定其他規定是才被推定適用。“另有規定”賦予了有限責任公司很大的自治權限,也使得公司章程比裁判法優先使用。2013年《公司法》修訂,雖然降低了公司設立的難度,但對有限公司股權轉讓的規定并無改變。
從以上梳理中可見,我國公司法現代化逐漸發展,公司自治呈現逐步擴大的趨勢。在有限公司股權轉讓方面,從強制性規定到任意性規定,從依照法律規定到章程可以另行約定,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自治都是合理的,章程限制條款效力的問題自然產生。
(二)限制股權轉讓的正當性
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將股權自由轉讓這一規定作為該國公司法的基本原則之一。但這種自由不是絕對的,各國公司法對股權轉讓往往做了一些限制。而有限責任公司因其資合性與人合性兼具的特點,便會存在更多的限制。股東之間的信任是公司持續良好發展的一個關鍵,股東為了相同的目的選擇值得信任的伙伴,高效地運營公司、增加收益。人合性使有限責任公司在股權轉讓上自然比股份公司更為嚴格,一方面股權的內部轉讓會使股東之間持股比例發生變化,而另一方面股東向外部第三人轉讓股權則會帶來公司股東之間的信賴和合作關系的變動,深刻影響著公司的經營狀況和發展前景。股東對公司進行投資出資或者轉讓股權,是以獲得收益增加資本為主要目的的,如果過于重視有限責任公司的人合性而對于股東轉讓股權的限制過于苛嚴,不僅阻礙資本的流動,也會使股東獲得增益的目的難以達成,對于投資者來說是一種束縛。
二、章程限制股權轉讓的實證分析
章程自治使限制性條款生效具有正當性,但限制是否有邊界、限制應達到何種程度是法條中未清晰確立的,下文將通過對章程條款限制股權轉讓糾紛的司法實例的研究,分析各地法院的裁判思路及對該條款效力的態度。
(一)裁判文書的篩選
借助“中國法律資源庫”搜集相關案例,以“公司章程對股權轉讓另有規定的,從其規定”、“公司法第七十一條”搜索,將判決時間限定于2014至2021年,案由為“與公司、證券、保險、票據等有關的民事糾紛”,共搜集到判決書135份,除去無公司章程內容和沒有規定股權轉讓限制條款的,以70份裁判文件為研究基礎。
(二)統計與分析
從審判程序上來看,涉及再審的案件5件,占樣本數的7.1%,進入二審程序的案件27件,占樣本數的38.6%,一審案件38件,占樣本數的54.3%。進入二審和再審的案件數量不在少數,可見對于章程條款限制股權轉讓案件的審理還是存在一些爭議。具體統計情況如下表:

?
從涉及案由來看,涉及案由較多,涵蓋股權轉讓糾紛,股東資格確認糾紛、公司決議糾紛、與公司有關的糾紛等案由,具體統計情況如下圖:

圖1案件樣本的案由分布
從章程限制股權轉讓條款的類型來看,涉及禁止股權轉讓的案例有11件,占案件樣本的15.7%,涉及強制股權轉讓的案例有26件,占案件樣本的37.1%,涉及增加同意限制的案例有33件,占案件樣本的47.2%。具體統計情況如下表:

?
根據上述數據可以看出,在案例樣本中的各地法院對限制股權轉讓的章程條款認定還是持寬容的態度。案例樣本共70件,高達91.4%的限制股權轉讓的章程條款被認定為有效。但在章程條款效力的認定中仍存在一審和二審法院對章程效力認定截然相反的情況,也有部分法院的說理不夠充分,論證過程較為粗糙。依前文所述,認定限制股權轉讓條款效力的標準還未達成統一,下文將會對表2中列出的具體的限制股權轉讓條款類型進行分析。
三、章程限制股權轉讓條款類型化
(一)禁止股權轉讓
禁止股權轉讓的類型一般有以下幾種:一、禁止股東在一定期限內轉讓股權,如在中章程規定了股東在公司成立三年之內不得轉讓股權,三年期滿之后經其他股東同意才可進行股權轉讓;二、禁止股東向股東之外的第三人轉讓股權,如在章程規定了內部職工所持股份不得在社會上流轉,僅能在內部職工之間轉讓;三、禁止股東之間轉讓全部股份,如章程規定,在股東股權轉讓時不得將其所持有的股權全部轉讓給其他股東,以此來確保公司有一定數量的股東。
司法實踐中對于禁止股權轉讓條款的效力認定存在同案不同判的現象,在“張某與高某、紅河縣東興百貨有限責任公司股權轉讓糾紛”一案中,審理法院認為涉案公司章程中規定的“國家安置股不能轉讓”同公司法中“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東之間可以相互轉讓全部或者部分股權”的規定相違背,屬于無效條款。而在“岳某、李某股權轉讓糾紛”中法院以《公司法》第七十一條第四款的規定為依據,認為章程中“董事、監事、經理人員在任職期間不得轉讓其股份”的條款符合法律規定,對其效力予以認可。
公司章程中禁止股權轉讓條款是否有效,存在肯定和否定兩種學說。肯定說以公司合同理論作為其觀點的論據。公司的參與者以自由的意愿形成合意,當事人是判斷自身利益的最佳人選,既然股東排除了《公司法》的適用做出了不同規定,對自己所享有的權利進行限制形成了合意,就應當尊重股東的合同。德國對于章程條款禁止股權轉讓也持肯定態度,公司法規定公司章程完全可以禁止股東轉讓,但應為股東退出保留通道,即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股東繼續留在公司已不合理,那么股東有退出公司的權利。否定說認為禁止股權轉讓條款無效,因為股權被視為可以自由支配的“個人財產”,故阻礙其自由轉讓的限制是不合理的。禁止股權轉讓違反了財產自由流通的公共政策,不利于資源的優化配置。英國公司法認可章程可以限制股權轉讓,但是不能禁止股權進行轉讓,并且對限制股權轉讓條款的認可態度必須以該條款的規定應是明確清晰為前提,否則法院將在解釋股份轉讓限制條款的時候,傾向于認定股東有最大限度的自由轉讓股份的自由。
筆者認為禁止股權轉讓條款的效力應當結合具體案情去判斷,既要考慮有限責任公司的人合性,又要保證財產自由流動的特性。對于沒有任何預設條件的完全禁止轉讓的條款,應對其效力不予認可。章程可以規定禁止股權轉讓條款,但也要規定股東退出或者獲得救濟的途徑使其不會陷入困境。
(二)強制股權轉讓
根據案例樣本中的強制股權轉讓條款的統計,強制股權轉讓往往出現于特定的情形,如股東離職、離崗、被辭退、被除名、被開除、退休、死亡、不再與公司有勞動關系等。此時該股東和其他股東之間的信賴關系消減,公司的人合性降低。在這種情況下,轉讓人的股權一般由公司回購或者其他股東受讓。在強制股權轉讓的同時還會對股權的價格、股權轉讓的程序、轉讓順序、轉讓的期限等作出具體規定。這類條款的設定一般是為了保護股東的共同利益,維護公司的人合性。很多公司以職員購買公司股權的方式來吸引人才、激勵人才、,提升公司競爭力,同時借此強化職員同公司之間的聯系公司的人合性,而“人走股留”的規定也是公司在面臨人才流失時將損失降至盡可能低的方法。
在“徐某等與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公司決議效力確認糾紛”一案中,一審法院認為章程中新增加的內容沒有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行性規定,是公司意思自治的體現,應該認定有效。而二審法院改判,將條款效力認定無效。二審法院認為涉案公司的決議內容是修改公司章程,通過修改的章程條款對股東資格進行限制,以此來強制不符合資格的股東轉讓股權。而作為認定股東身份的基本條款卻并未取得現有所有股東的同意,那么小股東自由處分自己股權的權利必將受到阻礙。該條款損害了不同意公司決議股東的權益,違法剝奪了這些股東處分自己股權的意思自治,違反民法總則中的公平和自愿原則,故決議內容無效,強制股權轉讓條款無效。
對于強制股權轉讓條款的效力,也存在肯定和否定兩種態度。肯定者認為公司章程的強制股權轉讓條款是合同附帶的條件。股東們協商對限制自己的權利達成合意,該條款對所有參與制定的股東有約束力。而股東離開公司以后,與股東身份相伴的股東權利也應不復存在,股東在公司的權益也將由公司按照章程收回或者轉讓給其他人。而認為強制股權轉讓條款無效的否定觀點,則是基于目前大多數國家都在立法中認可的股權自由轉讓原則。英國大法官格林在一個著名判例中指出——股東的正常權利之一就是自由地處理財產,并轉讓股東給選擇的任何人。股權自由轉讓是《公司法》賦予股東們的法定權利,除非股東自己有同意轉讓的意思表示,否則任何人不能剝奪股東的股權,包括公司章程。
筆者認為強制股權轉讓條款的設置要具有合理性,不僅要考慮到公司的獲益和發展,也要注意不能侵害股東的個人利益,避免出現股東沒有選擇的余地的情形。不應違反公序良俗原則,使得強制股權轉讓條款變成大股東“合法”排擠小股東的手段。應兼顧有限責任公司的人合性和公司作為商事活動主體進行商事活動的必要。
(三)增加同意限制
這種條款是在《公司法》第七十一條的前三款的基礎上設置更嚴格的要求。在案例樣本中33件增加同意限制條款中,轉讓股權須三分之二的股東同意的案例有3件,占該類案例的9%;轉讓股權須全體股東同意的案例有9件,占該類案例的27.3%;轉讓股權須董事會同意的案例有12件,占該類案件的36.4%;轉讓股權須股東會同意的案例有9件,占該類案例的27.3%。從案例樣本的數據中看,各地法院對增加同意限制條款的效力基本是肯定的。
在司法實踐中,對于增加同意限制條款的效力認定,有不同理解。在“周某與某置業有限公司股東資格確認糾紛”中,涉案章程規定當出現股東向股東之外的第三人轉讓其出資,必須經過全體股東的同意,審理法院認為該章程內容并未違反《公司法》的規定,故對該條款效力予以認可。在“某集團有限公司與呂某股權轉讓糾紛”一案中,審理法院認為有限責任公司股權轉讓的法律規范是強制性規定,章程及合同不可以出現放寬條件的情形,但涉案股權轉讓合同嚴于公司法規定,應認可其效力。
而美國對于增加同意限制條款的態度一直相對保守,它更嚴格地限制了股權的轉讓。到1920年左右,美國法院還是幾乎無一例外地宣布股權轉讓過程中的同意限制是無效的。因為完全依賴于有權表示同意的股東的意思表示,如果其隨意表示同意或者不同意而不受到任何約束,對轉讓股東來說是不公平的。
四、總結
《公司法》第七十一條第四款有很大的彈性,而實踐中公司章程對于限制股權轉讓的情形又較為復雜多樣,應當結合具體案例具體分析,要處理公司利益和中小股東利益的沖突,平衡股權轉讓自由和公司章程自治的價值等。
對于完全禁止股權轉讓條款應設立禁止轉讓的期限。雖然注重人合性的有限責任公司禁止股權轉讓,在理論上具備合理性。但這類條款使得公司將公司置于停滯狀態,股權難以自由流動。如果不加期限約束該條款,那么就構成對股東轉讓股權以及退出公司權利的根本剝奪,其效力不予以認可。
對于強制股權轉讓條款須預設轉讓條件,這是基于股東利益和公司利益之間需要進行平衡的考量。在特定股東行使轉讓股權的自由時,對于可能威脅到公司及其他股東的利益的情況發生時,應將公司和其他股東的利益放在優先考慮的位置。因此,對于章程中沒有預設任何條件的強制股權轉讓條款,不僅使離開公司轉讓股權的股東沒有保障,也不利于公司對效率價值的追求,故其效力不予以認可。
此外股東應有退出公司的通道,通過案例樣本可見,無論是何種類型的限制股權轉讓條款,都不能造成使股東無法退出公司,股東權益無法保護的局面。這與《公司法》的立法目的相悖,也不符合股權自由轉讓的原則,如果該條款會帶來這樣的后果,應當認定為無效條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