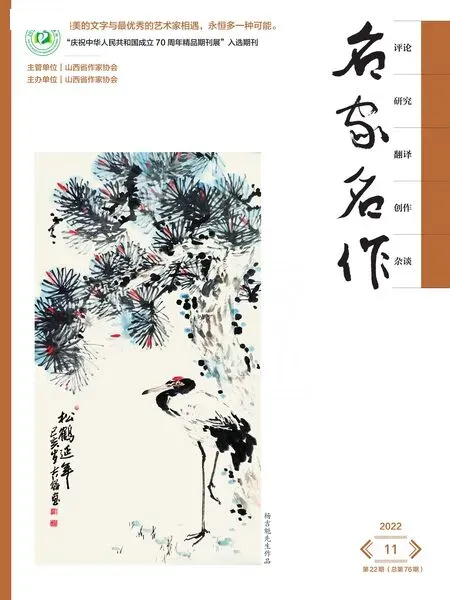分析張愛玲小說語言的修辭特點
宋 虎
文學是語言的藝術,語言修辭手法的運用是對語言藝術性表達的重要體現。張愛玲作品中,語言優雅的表達與深刻的描述,樹立了其小說語言獨特的修辭風格,也奠定了張愛玲小說大師不可動搖的地位。在張愛玲小說中,獨具匠心的語言修辭運用,使其作品呈現出鮮明的語言特征,不僅有對人物、事件的傳神描繪,更是將作者的態度、思想、情感淋漓盡致地表達出來。由此可見,張愛玲小說語言修辭運用的高度,對張愛玲小說語言修辭特點的研究具有較高的價值。通過對張愛玲小說進行分析探究,總結了張愛玲小說中的獨特性、音樂性、色彩性等語言修辭特點,呈現了張愛玲小說語言的修辭藝術魅力。
一、獨特性
張愛玲的語言天賦充分展現于其小說語言表達中,新奇、生動、獨特的語言修辭技巧,推動了故事情節的發展,引領讀者發現并感悟文字背后所蘊含的廣袤天地。這是張愛玲小說語言表達中最具特色的語言修辭特點。
(一)新奇的變異修辭
變異修辭是一種與常規語言規范不同的,通過語言表層與深層含義錯位的語言材料運用方法,能夠產生獨特且新奇的修辭審美效應。異化的詞語更契合特定語境的表達需求,通過賦予詞語與常規不同的新的內涵,使語言變得更加意味深長,語言效果也更為新奇。在張愛玲小說中,作者充分掌握了這種變異修辭的功能,利用特定的語言環境,實現了語言表達方式的改進與創新,從而使常見的詞語語義發生了異化或錯位,產生了新的語言視野。例如,在《傾城之戀》中,“寶絡沉著臉走到老太太房里,一陣風把所有的插戴全剝了下來,還了老太太,一言不發回房去了。”這一句是對寶絡相親之后的心理狀態的描述與反映。當全家人用各種穿戴物件將寶絡打扮得花團錦簇去相親,卻不想最后成了流蘇與范柳原親近了解的機會,寶絡的心中自然有怨言。為了表達出寶絡相親失敗的心理狀態,作者用一個“剝”字,替換了常用的脫、摘等詞語,使得寶絡失落、怨憤的心理生動地呈現了出來,語言表達也展現出了獨特性和新奇性。
(二)獨特的比喻修辭
比喻是一種在文學作品中常用的修辭手法,其不僅廣泛應用于書面語言中,在大眾日常口語中也經常出現,以使語言更加靈活生動。同時,比喻辭格也需要讀者將自己的想象與聯想充分調動起來,去感知比喻,從而讓語言說理更為清晰。在張愛玲的小說語言修辭運用中,比喻修辭的使用非常多,且使用數量在現代小說中并不常見。在比喻修辭使用中,張愛玲非常重視比喻的技巧性,大量的比喻修辭都不是隨手隨意用之,而是其獨特手法的呈現。一方面,張愛玲小說語言中,比喻的本體和喻體選擇具有很強的獨特性,在保持了比喻原有的修辭特色的基礎上,又實現了開拓創新,達到了非凡的語言表達效果。例如,在《紅玫瑰與白玫瑰》中,“屋子里水氣蒸騰,因把窗子大開著,夜風吹進來,底下的頭發成團飄逐,如同鬼影子。”在這里,作者用“鬼影子”來比喻被夜風吹亂的頭發,喻體具有強烈的抽象性,反而更真實地呈現了振保心中的蠢蠢欲動與煩躁紛亂的心情。同時,這種比喻方式將靜態的“頭發”賦予了動態的靈動,充分展現了作者高超的比喻手法,構建了神奇的語言境界。
另一方面,比喻辭格的運用以讀者的想象與聯想為基礎,因此在感悟比喻表達的內涵時,通常會調動讀者的各種感官因素,兼顧通感辭格。在張愛玲小說中,紅,實現了比喻與通感的完美結合,從而將作者的豐富情感與思維模式準確地表達出來,使語言的表達更具有新意。例如,在《傾城之戀》中,“她的聲音灰暗而輕飄,像斷斷續續的灰塵吊子。”這里用“灰塵吊子”作為喻體來比喻聲音,是作者緊緊抓住了兩件事物的相似之處,來形容白流蘇失望到極點、跌落至谷底的心情,通過聲音表達就像是灰塵吊子一樣,灰暗、寂寥、沒有任何依靠。這種比喻方法將聽覺與視覺感官聯系在一起,使讀者能夠從多重感官體驗中,體悟主人公的心情,同時對語言表達也有更新奇的感受。
二、音樂性
語言表達中,整齊的節奏、和諧的韻律通常能夠呈現出聲音之美,發揮著增強語氣和美感的作用。在張愛玲小說中,大量運用疊字、摹聲詞、反復等修辭,將語言的音樂之美呈現出來。
(一)疊字
疊字修辭也稱為“疊音”“重音”,在詩歌文學作品中較為常見,是一種漢語修辭手法與音韻用法,能夠協調音調、強化語意,使語言表達具有節奏性等。在小說中,疊字修辭可以使語言表達生動形象,具有深化主題的效果。在張愛玲小說中,對疊字修辭的運用既多且廣,更重要的是做到了巧用,使語言變得更加具有節奏感,增添了韻律美。例如,《沉香屑·第一爐香》中,“黑郁郁的山坡子上,烏沉沉的風卷著白辣辣的雨……”作者連用三個ABB型的疊詞,營造出一種非常急促不安的氛圍,來充分反映主人公的內心,同時語言表達也更加暢快,語感強烈,節拍明顯,使讀者在閱讀時充分感受急促緊迫的感覺。
(二)摹聲詞
摹聲詞是一種語音修辭手法,是運用語言將聲音節奏生動形象地展示出來的一種方法。在張愛玲小說中,有很多對生活場景、客觀事物的描寫,都是運用摹聲詞來構建讀者與所描述事物的聯系,使讀者能夠更好地通過語言來構建場景畫面,達到預期的語言表達效果,使讀者有身臨其境之感,獲得良好的審美體驗。例如,在《紅玫瑰與白玫瑰》中,“風吹著兩片落葉踏啦踏啦仿佛沒人穿的破鞋,自己走上一程子。”作者用“踏啦踏啦”描摹真實聲音,使讀者通過獲取聽覺感受,引發感官想象,在腦海中勾勒出具體的生活場景,加深對語言描述的印象,同時使語言表達更為傳神和生動。
(三)反復
反復修辭是通過同一語句的反復使用,以此一再表現強烈的情思。當人們在獲得深刻感觸或者對某件事進行強調時,常常會采用反復的方式。在文學作品中,反復修辭能夠構成和諧的語言節奏,強化語氣、強調內容,營造情境氛圍。在張愛玲小說中,有很多詞、句的反復應用都達到了這種效果。例如,在《茉莉香片》中,“‘聶傳慶,聶傳慶,聶傳慶’,英俊地,雄赳赳地,‘聶傳慶,聶傳慶。’”作者用“聶傳慶”的反復,表達了主人公急切、激動、期盼自己成為有錢人的一天,是對其心理活動的淋漓展現。又如,在《金鎖記》中,“七巧用尖細的聲音逼出兩句話道‘你去挨著你二哥坐坐!你去挨著你二哥坐坐!……’”作者用句子的重復,來表現這時候七巧激動的情緒,反映了其對當時生活狀態的失望與哀怨,同時也側面描繪了人物的痛苦掙扎,為后期人物性情扭曲的轉變作出了鋪墊。
三、色彩性
色彩語言在故事描述中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是對故事文本的重要渲染手段。在張愛玲小說的語言中,對色彩語言的運用是其語言表達的重要風格特色。她善于運用色彩詞對平凡的事物進行裝點,使其具有豐富的情感內涵,透露故事的情節發展,營造渲染故事氛圍,對主人公內心進行描繪。
(一)顏色詞的情感融合
張愛玲本身對色彩有難以忘卻的情懷,在她的小說中多次出現“藍綠色”,靜是其念念不忘的色彩,包含了其對母親的親切回憶。在張愛玲小說語言中,對顏色詞的運用融入了情感,將其內心的感受運用色彩進行調配,使文章呈現出獨特的藝術效果。一是張愛玲推崇對色彩的參差對照,善于運用色彩視覺上的落差,使文章的表達更具有層次和張力,與真實更加相近,從而通過對比來觀照人性。例如,在《紅玫瑰與白玫瑰》中,有關于紅玫瑰“蚊子血”“朱砂痣”,白玫瑰“明月光”“飯粒子”的經典描述,運用紅與白兩種顏色的對照,對振保在外人眼中正面形象和在情感世界中的肆意妄為的畸形雙重人格進行了映襯,同時也是對紅玫瑰與白玫瑰依附男人、毫無尊嚴的生活的可悲可嘆。在整個故事中,都夾雜著溫情與自信、真心與虛偽的荒誕交互,淋漓盡致地展現了人性的蒼涼。二是通過人物用色,進行人物內心情感變化與命運的勾勒,從而描繪出逼真的人物形象,使人物更具血肉情感。例如,在《沉香屑·第一爐香》中,“一件磁青薄稠旗袍,給他那雙綠眼睛一看,她覺得她的手臂像熱騰騰的牛奶似的,從青色的壺里倒了出來,管也管不住,整個的自己全潑出來了。”作者通過“磁青”的旗袍、喬琪的“綠眼睛”、白色的“牛奶”、“青色”的壺,將青綠與白色搭配起來,沒有說這時的薇龍有多美,但是卻淋漓盡致地表達出了她的秀色可餐。同時,“綠眼睛”也將喬琪的貪婪虛偽和色迷心竅表現出來,而白色的牛奶從青色的壺中全潑了出來,也體現了薇龍對誘惑的不能把持,使其最終淪為了喬琪的盤中餐。通過顏色詞的運用與變化描寫,將人物的內心與命運細致地表現出來。
(二)色彩詞的艷彩美
張愛玲在對色彩詞的運用中,會按照不同的事物來著色渲染,最終使語言呈現出艷彩之美,達到良好的表達效果。一是運用色彩詞的豐富層次感來體現故事情節的發展變化。例如,在《沉香屑·第一爐香》中,有關紅色的描寫包括了“鮮亮的蝦子紅”“巴黎新擬的‘桑子紅’”“大紅綾子”的椅墊、窗簾、“猩紅的厚嘴唇”“一朵一朵挺大的象牙紅”等,按照故事情節的發展,紅隨著薇龍初到姑媽房前花鮮亮美好的“蝦子紅”,到越發濃艷的“桑子紅”“大紅”,再到后來世俗的“猩紅”“象牙紅”,多層次的色彩詞承載了故事發展中主人公內心世界的變化,體現了故事的走向,表現出作者對色彩強烈的感知力和深邃的觀察力。二是運用復合式的色彩詞構造,達到更強烈的語言表達效果。例如,在《傾城之戀》中,“那車馳出了鬧市,翻山越嶺,走了多時,一路只見黃土崖,紅土崖,土崖缺口處露出森森綠樹,露出藍綠色的海。”作者除了運用黃、紅、綠等常規顏色外,還運用了“藍綠”的復合式顏色詞,相較于單純的顏色詞的表達,對事物的描繪更加清晰,表達效果更為強烈。因此,色彩詞的構造對于客觀事物的描繪具有重要作用,能夠在提高語言表達生動形象性的同時,帶給讀者強烈的視覺體驗,達到良好的表達效果。
四、結語
作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極具傳奇色彩的女性作家,張愛玲小說的文學和藝術魅力不僅體現于其所創作的獨特故事情節,同時還有其在語言表達中所展現的藝術成就。通過對張愛玲小說語言修辭特點的分析,可以看出她的小說融合了多種修辭藝術手法,將語言的獨特性、音樂性和色彩性淋漓盡致地表達出來,在我國文學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