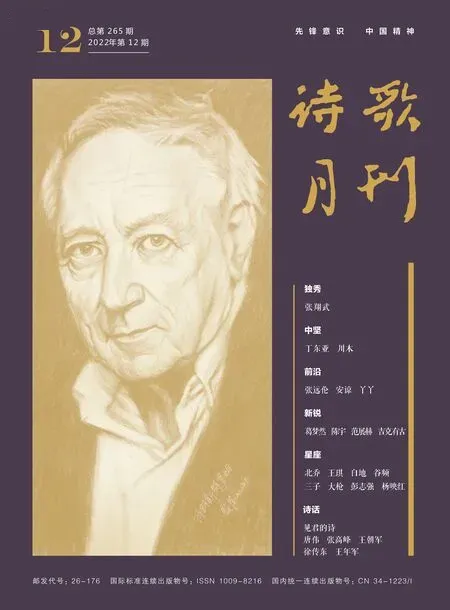箋日疏(組詩)
川木
1
這個冬天,語言結成了冰
仿佛天空散落的時光紙屑
被一雙手歸攏在河流上
晶瑩的星光沿著大地鋪展
你在黑夜行走,我遠望著你
蹣跚的腳步叩響書脊里
沉睡的文字。那些詞語
漫長歲月里撞身取暖的
孤獨而焦灼的孩子
向您發出沉默的問候
2
在永恒的包抄中,我們練習
突圍的技藝。這是游戲的一環
緊扣著人生的陣地。風從對面
斜插過來,刺中了你的影子
仿佛夢中的樹林,發出一陣陣
窸窣之聲。那是你的手腳沿著
生活的巉巖攀爬,留下的勒痕
時間的痕跡清晰可辨,即使在
冬夜。我見到了你滄桑的臉
3
從冬日的北運河遠望
天空的紋理邏輯清爽
烏鶇在語詞的推演中
上下翻飛,它的翅膀
扇動那片晚霞的霓裳
夕光與冰河一起涌來
小徑退隱于先輩的眠床
萬物都為澄明之境歌唱
4
他在酒后的失憶里
觸摸那張沉醉的臉
濕滑、謙卑、柔軟
幽暗詞語里的一抹苔蘚
每一寸都值得反復摩挲
他的身體在扭曲、旋轉
血液沸騰,浪濤般涌過
歲月沖積扇的河口沙灘
在黑夜的阡陌上層層鋪展
5
早安! 朋友
早安! 走失的祖先
早安! 窗外的烏鶇
以及你們溫柔的盤旋
早安! 從東方升起的
裊裊晨光。她們裙裾翩躚
仿佛大海有翼飛翔的歌唱
喚醒那棲息在港口的點點白帆
6
如果詞語能夠把這個冬天
帶回那棵核桃樹上,回到
春雪吐綠的夜晚。我一定
答應你,鑿開冰封的北運河
讓流水復活,讓時間的
羅盤重新校準我們約定的星辰
指向幽暗世界里那抹初現的微光
7
我時常在睡夢里
拼裝身體的積木
有著濃密的黑發
溫暖濕潤的軀體
然后,把瑣碎的絨線
縫進你的裙裾,或者
用生活的針尖刺穿
阡陌交錯的隱秘血管
直到大地一陣痙攣
泥土壓得我心口疼
8
午后,我在一首詩歌里
探尋她的臉,玫瑰的冊頁
綴著一顆美人痣。我命令
她再開一次。寒冷的冬季
人跡稀疏,烏鶇凝神不語
連同漸漸枯萎的柳枝
萬物之美紛紛凋敝
生活的邏輯就此折斷
我依然愛你
9
人到中年,談論愛情
既可恥也顯得幼稚
我們還能談些什么?
比如天氣,已是隆冬
北運河結滿厚厚的冰
你在冰上滑翔,宛如
盛開的玫瑰。這陳腐的
比喻,不該用在你身上
可是,可是,它的突刺
依然新鮮,保有錐心的疼痛
10
我要為出生向母親道歉
她十月懷胎喪失尊嚴飽受折磨
我要為青春向南方道歉
她慷慨接納被廢黜的愛情草坡
我要為生活向愛人道歉
她長發待嫁如今已是兩鬢斑駁
我要為寫作向詞語道歉
她病蚌成珠卻被詩人奪走光澤
我要為死去的時間向大地道歉
恰如北運河上靜靜飄落的白雪
11
清晨,白石橋的落葉又厚了一層
過不了多久,這些樹木將摘下面具
在寒風中抖動著赤裸干枯的虬枝
鳥雀還在盤旋,發出一陣陣叫聲
它要告訴你:每天,人都在時間面前停下
而大自然只不過是個開頭
紫竹院的臘梅正含苞欲放
12
那是誰?
隔窗對我耳語
宛如絲綢卷起的一抹月光
13
我們每個人走向和到達
我們所能到達之所
——荷爾德林《面包和酒》
通靈者醒來!
我已穿過你的睡眠
帶走你的前世和來生
逡巡在黎明前的高山之巔
14
我在清晨向你發出問候
這是我們約定的儀式
有一天群山不再醒來
大風依然在霧靄中行走
15
知我久慵倦
起我以新詩
——蘇軾《寄李邦直》
不要在陽臺上種植貓草
試圖引誘那只加菲貓
讓它吐出蠕動的往事
糾纏腸胃的陳年絨毛
它對生活的教義不太感冒
只是傾心于午后的時光
在慵倦的新詩里伸了個懶腰
16
午后,落葉翻動寂靜時光
風從身體穿堂而過,發出
幽暝的私語。仿佛血流的
冰骨在咬嚙中傾吐著回憶
更大的風在胸口盤旋,拍打
被遺棄的渡船:這無主之舟
飽經滄桑的心臟已經腐爛
而四肢的木槳依然在劃動
伴著午后落葉翻動的時光
17
思想的齒輪開始剝落,時針
沿著生活的鈍角走走停停
仿佛冬日的陽光拂過山谷
在銀杏的金葉上隨風飄零
虬枝交錯的巉巖下,鼴鼠
儲藏著食物,忽略了腳步
漸進的聲音。我們就這樣
說著話,看著傍晚的大霧
緩慢升起。然后互相道別
保重! 愛人! 好夢在今夜
18
在風中,詩歌打開了沉默的缺口
傾訴糾結的枝葉,以及枝頭的露珠
那些鳥已經飛走,羽翼劃過紙上的
天空,留下一陣陣戰栗。仿佛詞語
受傷的身體,在某種感覺中等待撫摸
你創造了它們,必須治療它們
那些飛翔的精靈,抑郁癥患者
甚至來不及感嘆,就消失在風中
19
什么時候? 詩人戴上面具
把豢養的詞語喂得又白又嬌
就像那只加菲貓,沉醉于舔舐
濃密的軟毛。不遠處工字廳角落
橘貓一陣陣低語,刺破寒風
20
從冬天剖開一個詞
你看到的是什么——
是元音輔音緊緊依偎的鴛鴦
還是意義斷裂時驚飛的寒鴉
是細節被封凍的一堵冰墻
還是韻味回旋的粒粒細沙
我不能確定詞根衰敗的白楊
能否在春天到來時枝葉煥發
正如詞典里那副姣好的臉龐
睡夢中有一滴淚水悄悄落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