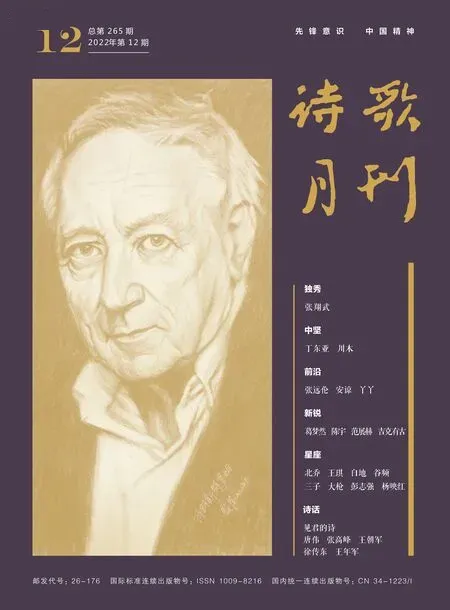時間經驗的追溯與聲音世界的呈現
張高峰
詩人簡·赫斯菲爾德曾在《十扇窗:偉大的詩歌如何改變世界》一書中談到:“我們內心渴望更多的事物——更寬廣,更深奧,更豐富的感覺;更多的聯想自由,更多的美;更多的困惑和更多的利益摩擦;更多形形色色的悲傷,更多無法抑制的喜悅,更多的渴望,更多的黑暗。”正是詩歌語言不可讓渡的神秘奇跡,而使得唯其所是的詩性存在,得以向我們持續性地敞開,它關乎詩人主體情感經驗,也溝通起無邊的他者存在,由此而反身凝神于生命體驗的瞬間開啟。可以說,一個詩人詩歌語言的精神載力之中,是否存有一個獨特的聲音世界,已然成為詩歌寫作能否有效處理復雜生命經驗的體現。當我讀到詩人見君的《風平浪靜》《回憶》《結怨》《四月的平淡》等詩作,再一次印證了這一詩學觀念。
他的詩作呈現出深緩而內斂、沉湎而幽邃的語言奇境,生命的張力卻于詞語間向我們不可回避地襲來。他執意打開的是作別青春激情退去后,日常生活經驗里中年心態的沉靜幽寂,平靜之下難抑生命的渴望,時間的境域里幽幽地跳動著焰心的光亮。我們會被他詩行間氤氳的音調深深地打動和吸引,這也正是他不可替代的詩性語質根源所在。他的詩歌寫作不以獵奇化景觀取勝,而是切入真切的個體生存境遇,力抵那無以名之的情感深處,微妙而豐饒地省察自我的存在,進而加深我們感受生命和世界的可能性。正如楊慶祥所評價的,詩人見君是一位有著“強烈自我意識和高度內在精神縱深的詩人”,他在對物象觀照的過程中,緩緩地呈現的是情感細膩的紋理與痕跡,其間都已“一切風平浪靜”,都已“清晰、明了、冷靜,沒有是非”,撫慰心靈的唯有時間經驗的沉積。由此詩人朝向了幽深的回憶,那是屬于每一個人的生命中,不可磨滅的情感體驗,難以捕捉的回憶無形,以詩性的呈現而見出難度。我們看到詩人承負著白發的惆悵寫下《記憶》,打開“時已過午”的心窗,“高處的交談”,自此將向內心的對話展開,由之追憶猶如“倒流過來的水”,優柔不舍地繾綣而來;細密的痛楚與歡欣相交織,無處告慰而暗自于詩性的述說之中生長;他深情款款地寫下《結怨》,當然這是時間境域里的饒有意味的“結怨”,欲說還休而永無完結,在反向的愛的拉開之中;而《風平浪靜》則將筆觸深入到暗自驚心的“風平浪靜”,那是已逝與將至的“時間一滴滴掉進去”,而不再泛起“任何激情”的中年情態,宛若那被端起的“慢慢變淡的茶水”,品味出的將是時間的鋒芒自在其中,從而連向生命的博大寬闊亦在其中。
詩人見君的詩作往往融豐盈的情感與生命的探詢為一體,他的詩之道在于生活的體察,在于生命全然的本真,通向不可割舍的心象對話,時間經驗中由記憶與想象來重構精神的維度。尤為可貴的是,他的詩歌經由個體情感,聯結起的是生命深切的普遍共鳴與靈魂振蕩,由此他的寫作無形之中構成心靈的“事件”,越是平易和緩,越是見出更深的悲哀之感,觸發并加深我們的詩性感知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