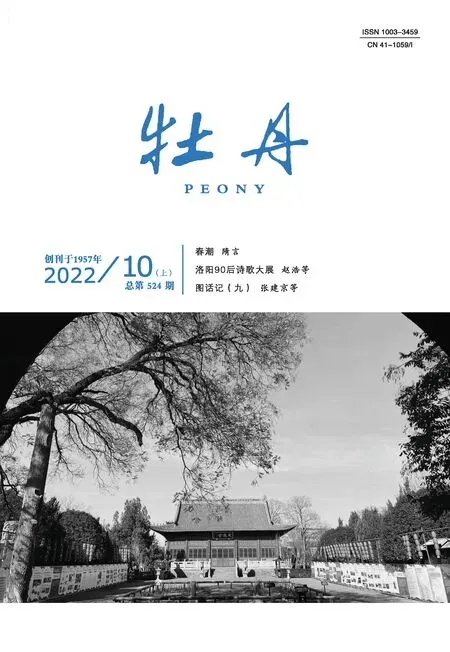酸棗樹
屈 皓
一
作為灌木科的植物,酸棗樹一簇簇,一叢叢,粗不過碗口,高不過幾米。一般情況下,它很難長成參天大樹,偶爾才會發現那種修行千百年“成了精”的酸棗樹。
這么矮小的酸棗樹,它既不能為人們遮風擋雨,又不能送人們一片陰涼。千百年來,人們卻稱其為“樹”,這是為何?
酸棗樹堪稱植物界的“刺猬”,模樣兇惡,總是一副張牙舞爪的樣子,不會主動攻擊人類,但渾身的長刺足矣讓人避而遠之。
從酸棗樹身旁經過,一不小心,衣服就會被它掛住;你一著急,胡亂拉扯,衣服立馬就是一個口子,千萬不要著急上手,否則長刺就會扎進皮肉里……面對這樣的情景酸棗樹,最好用兩個指頭謹慎地提起它的枝條,慢慢和它和解,才是正途。
一茬一茬的村民,生前在村莊里被生活磨平了棱角,大都與酸棗樹打過交道。他們有的人已經埋進了土里,而崖畔的酸棗樹依舊不卑不亢,對抗著歲月無情的鋒刃,直至枯死,它們依舊保持著高傲的姿態。
人們敬畏酸棗樹,僅僅因為它的長刺嗎?不然。
在本質上,如何構建國有資產共享機制的過程就是公有制下如何配置國有資產,如何進行科學分配的過程,因此,構建行政事業單位國有資產共享機制有利于推動我國公有制穩步發展,為鞏固社會主義體制打下基礎,更好地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
在故鄉,果園是蘋果樹、梨樹、柿子樹、石榴樹、山楂樹的舞臺,村莊是白楊、梧桐、國槐、榆樹、椿樹的世界,峭壁、崖畔才是酸棗樹的地盤。酸棗樹將生命的活力和希望統統種進了峭壁和崖畔。
酸棗樹看似卑微,但它是天生的“樂天派”,堪稱植物界的“蘇軾”。沒有人給它澆水施肥、除草打藥,也沒有人給它修剪枝條,在充滿一切可能性的自然界,自力更生更是卑微物種生存的法寶。
崖畔堅硬如石,常年干燥,酸棗樹悄無聲息地將根須竭力扎進去,努力汲取著有限的養分。它不會放過大自然賜予它的任何一次鍛煉的機會,長年累月的日曬雨打、風吹雷擊、沙襲霜砍、雪壓冰凍下,它淬煉出一身的硬骨頭。目送夕陽,身迎星月,日復一日重復著單調的生活。
一場皚皚大雪之后,太陽露出紅臉蛋,北風呼嘯著,而赤條條的酸棗樹剛洗了個雪水澡,刺骨的寒風中,不時秀出堅硬的骨頭。裸露在土崖外面的根,就像彎曲的鋼筋一樣。
土崖上面,多半是村民的旱地,酸棗樹會把擴充地盤的野心寫進去。但看到冒出的酸棗枝,人們立刻會用鋤頭除去。但沒過多久,新生的枝條又像春筍一樣冒了出來……哪怕挖到半晌午,也沒能徹底挖掉它們。就這樣,酸棗樹用毅力和人類做著斗爭。
滴水成冰的三九天,調皮的孩子不慎將蒿草點燃,也捎帶著燒著了酸棗樹,放心,來年春天,看似焦枯的酸棗樹依舊會抽出新的枝條來——這就是酸棗樹,倔強的酸棗樹。
二
年復一年,酸棗樹順著土崖橫向延伸的方向慢慢擴張,好像要鋪滿渭北高原的峁、塬、溝、坡、嶺、坎。
遠遠望去,數不清的酸棗樹像是土崖的頭發,又像戴在土崖頭上的綠色花環,還像是勒在土山腰身上的寬大的皮帶。有了酸棗樹的裝點,土崖有了伴兒,有了生機,有了詩意。
春末,酸棗樹揉揉惺忪的睡眼,仿佛才聽見春姑娘的呼喚,開始抽芽、拔節。卵圓形的葉子邊緣,很快長滿鋸齒,不幾日便撲撲啦啦滿樹青綠。
夏天,酸棗樹開花了,就像放飛了滿樹希望。那黃花,小巧、精致,細看有五只花瓣,像散落人間的小星星。花謝了,圓形或橢圓形的酸棗就出世了,果子顏色開始是深綠色的,經過時光的搓洗,逐漸變得發白。
秋天,是酸棗樹的高光時刻。時值中秋,棉絮般的云朵一次又一次將天空擦得湛藍,遠山日漸黯淡,酸棗樹毫無拘束地釋放著自己的熱情,熱烈而奔放,崖畔跟著火了似的。
一顆顆酸棗似珍珠,如瑪瑙,也像微型的燈籠,密密麻麻地掛滿枝頭。陣陣秋風吹過,渭北高原的峁、梁、塬、坡,被這紅色的海洋再一次淪陷。
三
酸棗樹在植物界,算得上是個“硬茬兒”。
“木秀于林,風必摧之”,暴雨或狂風能將白楊、梧桐等大樹連根拔起,卻很難折服那些緊密團結在一起的酸棗樹。看來,個子小有個子小的優勢。
崖畔有了踏實的酸棗樹,就像有了忠誠的守護者。酸棗樹不嫌土崖貧瘠,就像恪盡職守的一方諸侯。任憑狂風如何肆虐,不管雨水怎樣沖刷,都無法攻破酸棗樹組成的這道綠色屏障。馬蜂在此巢穴,螳螂、螞蟻、蜘蛛在此繁衍生息,它們一起構建起一個祥和的世界。酸棗還時刻地提醒著人們:收腳,前面就是崖畔的盡頭——從這方面考慮,酸棗樹更加可愛了呢,它尖銳不好親近的外表,反而會讓人警醒著不走錯路。
從我記事起,家家戶戶都種有蘋果樹,家家都有果園。怕牲口闖進來,父親會移栽些酸棗樹當作藩籬,酸棗樹又充當起侍衛的職責。當滿園子都是香噴噴、紅通通的蘋果時,是不是也有酸棗樹一份功勞呢。
老邁死去的酸棗樹,也會發揮著它的價值。要么立在菜園子周圍充當守護者,要么被人塞進灶膛里成為燒柴。裊裊炊煙里,酸棗樹的靈魂化作一縷青煙,身軀則化作木灰,被莊稼人撒入田地,它們以另一種存在的方式供養著農民的希望。
近年來,酸棗樹的價值被聰明的人類無限開發。嫩芽炒制成茶,據說有保健養生的功效,我嘗過,味道清香怡人,帶著鄉野清甜的氣息。酸棗花蜜,越發走俏;酸棗酒,也應運而生;酸棗木,成為根雕藝術品的新寵。一條酸棗木拐杖,是很多人饋贈老人的禮物。而酸棗仁,這味記載在《神農本草經》《本草綱目》等典籍中的傳統中藥,雖然不如人參、鹿茸、蟲草等中草藥的身份高貴,卻是無數失眠人的靈丹妙藥。
我從心底敬佩生長在鄉野間的酸棗樹。
四
到了秋天,崖畔成了農村娃采摘歡樂的果園。
記得一個中秋節的下午,我們姐弟仨去摘酸棗。高空中的一只雄鷹,就像一把大刷子,一圈又一圈在天空盤旋。偏西的太陽雖然沒了三伏天的銳氣,但依然溫熱;云彩像被火燒過一樣,擁在西天邊緣,就像一幅色彩明亮的油畫。我們無心欣賞,因為酸棗牽引著我們的味蕾。
我們不停往嘴里塞著酸棗,果核吐了一地。好運從天而降,大隊的螞蟻慌不迭啃噬著上面殘留的果肉。
摘酸棗可是個技術活,不能心急。姐姐最為心靈手巧,一只手穩穩地拽住枝條,一只手蝴蝶穿花一般采著果子,摘完了也不能粗暴,要輕輕松開酸棗的枝條,否則受傷的就是自己了。一會兒工夫,我們的口袋就鼓鼓囊囊了,在缺少零食的年代里,是酸棗給了我們純真而快樂的時光。回想起來,仿佛我們的童年都是酸甜味道的。
如今生活在城里,琳瑯滿目的時令水果看得人眼花繚亂。鄉野間的酸棗,被勤快人帶上了都市的水果攤。
我懷著幼年的念想,忍不住買點吃,吐掉棗核的那一刻,我意識到自己咀嚼的是當下的生活,回味的是久違的鄉愁,吐掉的則是不能尋回的美好時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