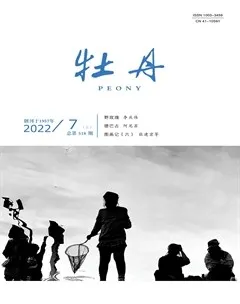大地凡草
王蘇蘭
蒲公英
在無數種草藥里,我偏愛蒲公英。小時候喜歡的是那笑臉一樣的花兒,開在早春裸露的大地上,溫暖、明凈、喜悅。少年時,喜歡它那團霧一般隨風飄散的種子,詩意伴著憂傷,像我新生的那些情愫。后來我學醫,這藥草在我手下一次次驗證著它“天然抗生素”神奇而強大的療效。我和家人們那些喉嚨痛、牙疼、中耳炎、炎性腫塊,無數次被這微苦的草棵子打敗。
大兒子兩歲時,忽一天食指腫脹,又硬又亮,一觸即爆的樣子。饒是醫生,我也嚇得不輕,滿腦子都是刀片劃過肌膚膿血四流的畫面。我去村邊地堰上翻找,剜回來三棵蒲公英和兩棵紫花地丁,洗凈,搗成糊,在兒子的食指上敷成一個綠殼。一夜不安。早上取下藥包一看,除了皮膚微有綠色,一切如常。
早年坐門診,遇見一個得了急性乳腺炎的年輕媽媽,體溫近40℃,左乳腫脹得像個小籃球,焮紅發亮,痛不可觸。住院,退熱消炎,通乳按摩,熱敷,抗生素直接三代頭孢,收效甚微。如此下去,化了膿,只有手術切開引流。
情急便顧不得許多,我叫來家屬:去剜些黃花苗和紫花地丁,洗凈拿來。好在不是冬天,草藥并不難找。我搗爛草藥給病人敷上時,心里其實非常忐忑:這算是西醫擅長的急癥,不知道中醫這慢郎中會不會真造個奇效出來。如若還不行,這一刀怕是難免。“這兩樣藥,熬濃一些,當茶喝。”
第二天一大早,家屬欣喜地跑來叫我:消多了消多了!不紅了也不疼了!
長吁一口氣。這算是中醫的又一次勝利吧……
艾
在農村,沒有人不認識艾,沒有人不用艾。
端午節的早晨,太陽沒有升起之前,村子里每一家都會有人背一捆帶露水的野艾回來。這幾乎是一種儀式,專對于這個節日的儀式。在他們看來,這一天采割的艾才算是真正的藥。北方農村的端午節不喝雄黃酒,粽子也可以沒有,但艾草是絕不能缺席的,若有了閑暇,五色線和香囊才能登場。
割回來的艾草,一小扎一小扎掛在檐下陰干,驅病的用處大于辟邪。
那時的農村,生了孩子的人家,必會煮一鍋艾水,放溫了給新生嬰兒洗浴,據說避風。以后的幾天,還要用艾水給產婦熏洗,據說不得月子病。
夏天蚊蟲多,老人們把一根艾繩燃起,一家人來便可安然入睡。
腰疼灸腰、腿疼熏腿、肚疼敷肚臍、驅寒泡腳,艾葉的諸多用途中,對我來說,止血最是印象深刻。
小時候我曾在老宅的青石臺階上磕破了頭,鮮紅的血滴答滴答打在地上,怎么也止不住。奶奶過來,讓嚇壞了的我拿小黑手捂住傷口,回身去找一把艾葉燃了,火苗剛熄,一撮艾灰按我額上,片刻間血就止住了。六七天之后,揭去一大片血和艾灰結成的黑痂,非但沒有感染,連個小疤也沒留下。奶奶和媽都覺得這是“端午艾”的神力。當然,這神力不單對我,村里每個小傷不斷的孩子都見證過。
我體寒,年年秋后便開始腰腹冷痛,去年越發嚴重,入冬大冷,不得已開始自治。晚上抓一大把艾葉,加了花椒熬水,先熏腳,水溫勉強可以放腳進去,就開始泡腳,涼了再加熱的,直至墨綠色艾水淹了腳踝。艾葉已煮得柔軟若棉,在腳邊一飄一蕩,偶爾幾根小梗在腳底硌得癢癢的,身上開始微微出汗。一周下來,通體溫暖舒泰,覺得天仿佛也沒有那么冷了。
“溫經止血,除濕驅寒,平喘鎮咳祛痰”“除濕止癢,祛風療瘡”。這些年,在我們“艾草之鄉”,成百上千畝的艾,一年三茬在肥沃的田地上自由生長,無數種改了模樣的艾草,漂洋過海去了遠方。艾,這曾經鋤之不盡的野草,不止給鄉親身體肌膚的護佑,終于以財富回報了與它們世世代代糾纏相依的人們。
清明柳
楊柳枝,芬芳節,可恨年年贈離別。
清明也折柳,卻不為贈別。
清明那天的柳枝,照例得日出之前采。門前的大柳樹,河邊的矮柳叢,那些唾手可得的枝條被隨意砍回了家,照例是掛在檐下陰干。
清明柳和柴胡一樣,可以用來發汗退燒。家里誰感冒發了燒,母親從墻上扯幾根干柳枝,撅成幾截放鍋里,添兩碗清水,放了蔥白、老姜、辣椒面兒、整棵的芫荽、鹽,熬成一碗發黃的辣湯來。一掀鍋蓋,滿屋子清苦的味道,有時還會奢侈滴上幾滴香油。一碗這樣的湯水下肚,蓋嚴了被子躺著,很快就遍身微汗,熱退自然病愈。
母親身體一直很好,高高低低五個孩子的吃穿和十幾畝地的莊稼,讓她片刻不閑。我從來沒有見過她大白天在床上躺過,只有一次例外。
那天母親從地里回來,沒有了往日的健步如飛,看上去疲憊恍惚,搖搖晃晃。母親發燒了,額頭滾燙。她強打精神做完飯,從墻上揪下一把清明柳,開始熬辣湯。家里沒有姜,也沒有芫荽和蔥,鍋里只有一大把干柳枝熬著。母親坐在灶臺前無力起身,讓我去拿了兩個干辣椒放進鍋里,就趕我去吃飯了。
母親喝了辣湯進屋捂汗。她的虛弱讓我害怕,更擔心這湯水會不會有用:沒有了蔥姜芫荽,就憑掛了大半年的干枝枝,還能治病嗎?
不到半后晌,出透了汗的母親,神清氣爽?著籃子下地了。
后來學了醫,才知道阿司匹林提取于柳樹,這解熱鎮痛的圣藥,原來就伴隨在我們左右。
紅薯葉
我的口味越來越像母親,大魚大肉遠沒有野菜讓我著迷。從春到秋,田里樹上總有我想吃的根葉花實,也總有機會拿它們給人科普。春天的豬毛菜和鬼針芽降脂清血管,后者還兼消炎。正月的茵陳護肝退黃清濕熱、四月的槐花清熱涼血、花椒芽溫胃散寒、嫩柳芽治腹瀉痢疾高血壓。“八月小蒜,香死老漢”,小蒜骨朵學名叫薤白,辛辣通脈治冠心病。山薄荷腌了吃別具風味,又祛風熱治喉嚨痛。它們不再為了充饑,是因為美味和保健作用被端上餐桌,也許,還為了懷舊。
諸多的葉子菜里,我和母親一樣,喜歡吃紅薯葉,它柔軟光滑,沒有異味,怎么吃都好吃。年幼時經常看母親大籃小籃捋回來,曬干存著。冬天,糊涂面條里有它,紅薯糝湯里有它,稠稠的粥飯被這些干葉子染成淺褐色,有一種特別的香味。紅蘿卜絲白蘿卜條吃多了胃嘈,母親就換個樣子,把干紅薯葉焯開涼拌,灑幾滴香油,我們都能吃下去大半碗。等糧食菜蔬都不再短缺的時候,母親還會大籃大籃扛回來,喂豬。
母親不知道如今的紅薯葉已經升級為“蔬菜皇后”了,她還是會掐了紅薯秧的嫩尖或葉子,炒了,或者拌面蒸了,樂此不疲。去年母親生病不怎么吃飯,問她想吃啥,說,有紅薯葉的糊涂面條。弟弟一副怒其不爭的無奈表情,我也苦笑:哪里有啊?其實,我也想念母親做的糊涂面條了,下了玉米糝,煮了黃豆、粗蘿卜條、紅薯葉,冬天里那一碗濃稠噴香的糊涂面條,暖胃,也暖心。
我想替母親辯解,趕緊去百度:提高免疫力、止血、降糖、解毒、通便利尿、催乳解毒、保護視力、延緩衰老……
看吧,它哪里只是一把野菜那樣簡單呢?
秋深了,四野風涼,大地上萬千種植物正從蒼翠走向枯黃,只待最后一場秋風將它們催眠,去冬天里做一場大夢。凡草或是良藥,都要在來年春天醒來,妝點或者救治,無限輪回,就像這片大地上的萬千凡人,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