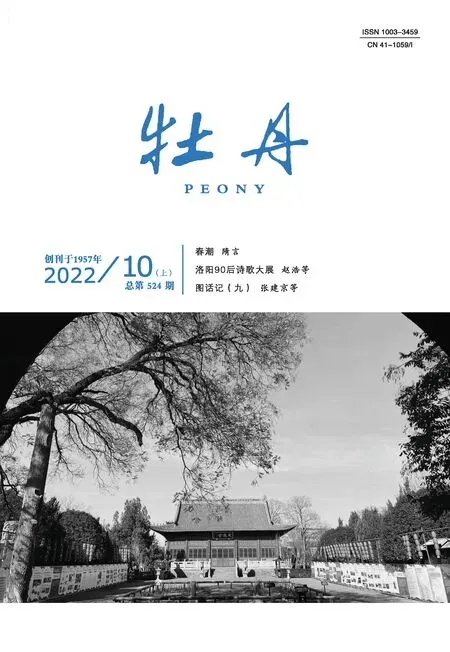悖論(外一篇)
金國泉
人是一個悖論,甚至就是一個悖論的產物,我甚至還認為,人是因證明悖論的存在而存在的。他終日撕扯著自己,左沖右突,左顧右盼,至而合縱連橫。
但人類總是撕扯得恰到好處,沖突得左右逢源,或者說不左不右,就像地球上那些因造山運動、板塊碰撞所造就的丹霞地貌、雅丹地貌、喀斯特地貌……它是那樣的圣潔那樣的人見人愛那樣的悠然自得。于是人一直生存著,人類一直存在著,世界一直存在著。
那些陶罐也是。每一口精心打制的陶罐在被打碎,又在被復活,且復活后更加精粹,即便是人工的修復,我們也仍然能窺見到,甚至能體悟到折射的力量,那些由陶罐一次次裝滿的水從遠古一路潑灑一路沉淀,一路嘆息一路歡歌。這嘆息里有浪涌,這歡歌中有淚滴。人類因此在這秘辛深含的水聲中從來不曾成為偽命題。
這樣一種恰到好處就是中庸之道嗎?不一定。當然這個“不一定”也是中庸的。中庸不是折中,不是百分之五十,或者各打五十大板。孔子曰:“鄉愿,德之賊也!”中庸因而也是由撕扯所致。
“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但孔子還是在學生的保護下離開了宋國。我在想,孔子的這種撕扯,不論其與桓魋還是其他人物進行,其結果不是左邊多一些,肯定就是右邊多一些,中庸之道因而需要不斷地糾或者匡。我數學學得不咋的,不知道這個糾或者匡概率怎樣計算,但我仍然認為這個左右對稱的概率一定是很小的。人體左右細究就不對稱,何況加上了各種力量的不均勻,材質的不均等,撕扯當然也就無法正中下懷。
不對稱便會尋求對稱,正如失去平衡便會尋求新的平衡,而新的平衡仍然是不平衡的,正如我們走路,我們邁出的每一步都是在打破平衡,尋求平衡、建立平衡,然后又打破,如此不斷循環,人因此走完小路,拐個彎便能走上大路。人的一生不過就是走走而已,路走到頭了,人生也就到頭了。我走到頭了,你便接著走,人類社會因此不斷前行,不斷更迭,不斷草蛇灰線,從未止息。
人一個人時才是自己。誰說的?不記得了,但我非常喜歡。喜歡它的真實性。但真實性不矛盾嗎?答曰真實性與悖論并不相互否定,甚至在相當的時候會畫上等號,也就是說真實性與悖論經常攜手挽袖。
但人一個人時就不撕扯不左沖右突嗎?一般情況下,人一個人時是相對安靜的。他在喧囂的處心積慮的世界里抽身走了出來,作為矛盾的一方暫時性地離開了另一方,成功地蓋上了那個潘多拉魔盒,盡管是暫時的,但他開始想一個人的事情了,甚至在做他一個人時才能做的事情。不過他的內里仍然是五味雜陳、翻江倒海,他敢于哭泣,敢于大笑、敢于竊竊私語,敢于怒發沖冠地面對某人某事,甚至可以罵得對方體無完膚。
有靜如止水的人或人的內心嗎?我敢肯定沒有,除非那潭水是死水,死水一般容易成為腐水。腐草化螢,估計腐水也能生蛆。家鄉有句俗語:水無百日孤。所以靜如止水只是一個渴望、一份寄托。
坐地日行八萬里,人類何以能止?即便是大德高僧,打坐時也仍然心心念念不忘自己怎樣才能修成正果。正果當然是除了枝蔓,剪了旁斜的結果,這樣的正果我想是不是有些光禿禿呢?光禿禿的正果肯定像石頭。石頭不是果子,無法吃進人的肚子。
人類十分渴望靜下心來,其實人類又是十分害怕靜止的。多年前就聽說,微軟總部有一處負20.3 分貝的房間,被吉尼斯紀錄評為世界上最靜的地方。任何人進入這個房間之后,沒有辦法熬過一個小時,外界的聲音無法傳進去,房間里面也沒有任何回音。人在這樣的環境中,適應一會后,就可以聽見心臟跳動的聲音,連走路時骨頭摩擦的聲音都可以聽到,讓進入這個房間的人感到異常恐怖。
人類一直是被自己反對的,所謂自我革命。我唯一不理解的是人類在自己的反對聲中居然一次次脫離窠臼,一次次更加旺盛,一次次有了自己更趨完善的編碼。像老家湖灘、田壩上的青蒿、白茅根、益母草、車前草……這些一年年枯萎一年年茂盛的草根們。我不知它們是在刮骨療傷還是在韜光養晦,但它們從不止息,石縫中、沙灘上、瓦礫處、峭壁處、大路旁……人類的踐踏也因此從不止息,真正就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再次長出來的它們仍然初衷不改,以它們的前輩為宗范,向著人類的腳印出發,向著枯萎之處挺進。
這是世界的悖論還是人類的悖論?被世間萬物浸潤并浸透了的人類用盡全力飛蛾撲火,前仆后繼。
每一次前仆后繼、飛蛾撲火都是看得見、摸得著的,是紀念品,也是一次性消費品,像炸彈只能炸一次。只要能炸的炸彈,不是啞彈,之于炸彈便都是成功的逃離,沒有遺憾。
一歲年紀一歲人,或者說一步一風景講的無疑也是這么個理。它們總是一次次成功地勘探、剪輯,一次次成功地放棄。
那么,走向悖論也是一次放棄?
每一處風景都是一個“知面”。羅蘭·巴特在他最后一篇著作《明室》中告訴我們,“知面”就是照片顯示的基本文化背景與知識框架,我們借此可以讀懂照片的內容。你沒有走到那一步,或者你還處于你看不到那個風景及其所在的位置上,你怎么會去想呢?所以我常常感到我的初衷不可靠、不著調。那最初的風景或枯萎或凋零或被人為破壞成為一處殘垣斷壁。有了殘垣斷壁便有了羅蘭·巴特的另一個概念:刺點。“刺點”總能穿越“知面”,通過殘垣斷壁蘊藏著的復雜而多樣的潛流直接刺痛人心,直接到達另一個“知面”,看到另一處風景,正如石頭里蹦出來的猴子,正如這只猴子一路降妖捉怪。
沒有不知道結果的,沒有知道結果后不一意孤行的。前途渺茫呀,但我們一直堅決地認為前途無量!始終知道人與這個世界“相看兩不厭”。
暖風熏得游人醉。我知道每一個人都是游人,每一個人都陶醉在這無處不在的春光里,每一劑藥方都在春天里游覽人生,游覽世界。我常常想為什么人類一直都喜歡贊美春天,抖音里、公眾號里……桃花紅、李花白、菜花黃……那么多果實都在秋天成熟,那么多的張揚都在冬天收斂。但人類不管不顧。
人類的這種嘴里吃著果子眼里手中摸著花的偏愛與執著讓我感到怪怪的。我在想到這個悖論時我眼里正存在一朵鮮艷而搖曳之花,甚至我想到“薰蕕不同器,堯桀不共國”的極限里去了。
我花創造我世界。但每一朵花都不是精密儀器,都不嚴絲合縫,正如羅蘭·巴特的那個刺點。相反,它總是慢慢張開,越開越大,張開的花當然瓣與瓣之間基本分開,漏洞百出,甚至就不是漏洞,而是漏掉了日月山水。像那段相聲里說的:上嘴唇碰到天,下嘴唇碰到地。對方問:你的臉呢?答曰:吹牛人不要臉。花的張開是不是花在吹牛,不好說,但它的確最后因張開而凋零而走向自己的背面。
從這方面講,每一朵花的開放都是混沌的,所謂混沌初開,似一朵朵皆沒準備好。但那些果實就準備好了嗎?也沒有,所以每一顆果實,苦的、酸的、甜的、澀的……也都在走向自己的反面,它以它的苦酸甜澀堅定地否定自己,堅定地認為自己不屬于這個世界,從而自殺式撕毀合同。
本來無一物?有物的,且何止一物!乃萬物。萬物有根系有源頭活水,但萬物都有不著調的地方與不著調的時候,于是,萬物均不斷地在那個不著調的地方與不著調的時候,走向自己的未來。未來就是背面?背面又很快成為正面,光鑒照人。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這話聽著有著真理性的辨識度,但仔細一想也是有問題的。一方人靠一方水土養著生存著,依水而居,依土而行。但人給了那方水土什么呢?至今我沒找到,且我的祖祖輩輩除了回歸到一方土地之中而外似也沒給予那方水土任何物什,是個單方面支付合同,甚至現代人一不高興,還經常單方面撕毀這份合同。這是真理嗎?規范的合同文本都不是。所以,那方水土終究會將它養育的那方人吞下去的。吞下去便吐不出來了,世界也就因此從一個悖論進入到新的悖論之中。
這是劫難嗎?但這肯定是忠告。悖論其實就是忠告,它解構一切,又被一切解構。
詩和遠方
生活不止眼前的茍且,還有詩和遠方。這里的詩不是狹義的詩歌,而是詩意,或許也不僅是詩意,而是一種詩一樣的美好與情愫,它遠遠超出了作為文本的詩歌本身。但不管怎樣,它無論如何都與詩這個大家庭脫不了干系。
為什么大家都樂意,或者認同把詩與遠方齒合起來。詩在遠方嗎?遠方就是詩的大本營嗎?有件事我記憶深刻:某次在高速路上驅車,一輛貨車從我車旁超過,別的沒看清,但我看清了那車身上赫然寫著“詩和遠方”。灰色車廂,當然那字就是灰背景了,字是紅字,波浪式的。這讓我一下子想到了這位車主的與眾不同,他有怎樣的目標?遂想追上看個究竟。我記得清楚,妻子當時嚴厲地冷笑了一聲:“詩在遠方,車禍可能就在你腳下。”妻子簡單地把遠方與車禍結合起來后,我一下子毛骨悚然,立馬放棄了追逐那個已然遠去且正在飛奔著的一車“詩”,且行且珍惜起來。
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茍且時分,茍且地偷生,茍且地行事,茍且地笑一程、哭一程。我常常由此想到了那些自殺者,他們為何在那一刻不愿意“茍且”一下呢?果真如此,便逃過了心中自動生成的那一劫——真正是一劫生存,則萬劫不復——下一步也許會生活得美妙,并詩意起來。這樣一“茍且”,似乎詩真就在遠方了。比如那個劉邦,“茍且”地“籍吏民,封府庫,還軍霸上”,便成就了一首四百年的帝王之詩,而項羽不愿意茍且,于是乎自刎烏江,自成邏輯,并出了車禍似的,讓自己的血與團隊的血一起在歷史的碾軋中自我蕩滌,獨尋寂廖。
自刎也充滿詩意嗎?也有相當多的仁人志士十分欣賞這樣的濁醪妙理,寫下“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的李清照便是一例,她詩意的定盤星是“生當作人杰,死亦為鬼雄”。但這個定盤星現代很多年輕人并不認同,“鬼雄”誰見過呢!過于虛無。他們是過于當下的那一族,于是,他們只欣賞說出那句“嗟呼,大丈夫當如是也”的劉邦以及處在這個段位上劉邦們。
我在想,劉邦所云“大丈夫當如是也”這話本身并無詩意,但它充滿著遠方,甚至就是一個直指遠方的道統。不是詩人的劉邦遵循并鉚定他自己與他一手組建起來的團隊共同策劃的遠方,一步一奮斗,既不超速,也不越界,也不違反其他交通法規,甚至在他的那輛車上也沒標個“詩與遠方”的標識,最終修成了正果,并一代著名詩人似的寫下流傳至今的《大風歌》。我感覺劉邦一定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將詩與遠方完美分離并完美結合起來的那個人,有頭有尾,頭尾相連,形成閉環。與劉邦相比,項羽那充滿著詩意的自刎是后人欣賞出來的,說真話,我對此感受到的是脊梁骨發冷。“彼可取而代之”,他說的這句話雖與劉邦那句一樣并不具詩意,似異曲同工,但終究不是一曲,工因此也就不同了。“太剛易折,太柔則卷。圣人正在剛柔之間,乃得道之本。”我不知道劉邦的后代劉安在《淮南子》中說的這句話,是在總結劉邦還是總結項羽?我只知道項羽一路斬殺,一路奮斗,違規違法地坑秦焚宮,最后也就出了交通事故,歷史這個交警自會一次性扣除他十二分,沒收駕照,永不錄用。劉邦剛柔并用,遂將遠方收入囊中,并演奏出一曲“大風起兮云飛揚”的時代強音,一路飆車。
結局就在遠方,它總是圖窮匕見地暴露一切、揭示一切。劉邦創立四百年劉氏帝業,我老想著,這個被歷史學家奉為高祖的劉季,當他從那個“遠方”回到出發點時,他胸中怎么突然就有了《大風歌》呢?“滿則溢”,我還是肯定這個句子。劉邦的詩被他自己溢了出來。也就是說每個人心中都有一首詩。劉邦的詩溢出來后,他一定還會偷偷一樂,認為自己當時不過隨口一慨,甚至他可能還在心中問自己:我當時有沒有驚出一身冷汗,嚇沒嚇著自己?歷史過往中這樣隨口一慨的例子應該不僅劉季一人。項羽的話卻是大大地驚著了他叔: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由于系隨口一慨,肯定就有些浮飄,詩意或許就藏在這浮飄之中,大多數人在行走的道路上可能忘記了自己曾做下的那個有些浮飄的標記。連標記都找不到了,結局中的那個匕首暴露出來時,可能已經銹跡斑斑。
在這銹跡斑斑中,我不知道詩是否還有存在的可能?
如此往下推,遠方當然地具有隨意性,但這種隨意性被說出來后,它便具有不可更改的歷史指向性。劉邦不可更改,項羽亦不可更改,遠方因而始終不渝地蹲守在遠方,它隨時準備與那個不忘記標記的人結合成一首詩,甚至是一首膾炙人口的那首。要實現這個根本,我想起碼要建立一條通道,要安裝一個與之對話的裝置,有了這個對話裝置,并建立一個定期對話的機制體系,我們便不至于走偏。就像那道地平線,我們每每憑著那縷光亮,為其凝神靜氣,為其策馬揚鞭,為其風塵仆仆。如此的隨意豈是一個“隨意”了得?地平線每每消失或者消解,我們必須在它露出的光亮沒消失或者消解之前一步一個臺階或者一步一個腳印地抵達。這個抵達亦不可更改,哪怕吹亂一頭白發。
一個美學常識:距離產生美。但是如果距離有些離譜,連一個點都看不到的情況下,比如遙遠的星系,連想象都無法抵達,那它還美嗎?我想應該也不是丑了。所以美有另一個常識,那就是必須有所呈現,呈現成就美。有了這樣一個常識便有了詩與遠方相連并產生出對此的向往與追求。有了向往與追求就會有“青山著意”的成色。我常常又想,項羽是成色不足嗎?剛性進行到了顢頇階段當然就起了化學反應。化學反應在我看來具有顛覆性,它已經不僅是成色的問題了,它可能踐踏一切詩性物質,甚至能讓項羽們的遠方與詩擦肩而過,并戛然而止,黯然宵遁。經年后,那宵遁之處自是荒草叢生、瓦礫成片。有多少人從此打馬路過?現代人,甚至也不僅是現代人,他們在打馬路過時仍然能從這荒草叢生、瓦礫成片中找出詩意的存在。我在想,卻原來,項羽們的詩被踐踏進了泥土,也就是說,詩是永恒與不死的,泥土始終不忘與詩結合,與詩一起生長。
常常有人問,遠方有多遠?我不知道此人問的是地理學概念不是心理學概念?但我知道,他的下一個問題是:我們什么時候能到達。我家鄉有句俗語說的是另一個理:心急吃不上熱豆腐。俗語就是彝倫。豆腐趁熱吃比冷的吃當然要香得多。但你一旦著急,那滾燙的豆腐包含著的豆汁就會咬你,咬你一嘴泡,于是你就沒法吃了,你甚至可能連那頓飯都沒法吃了。所以,我執意認為遠方是自然敲定的,而非人工設置,不可問及,不可言傳,不可胡亂激活。這樣的遠方當然地具有詩意與詩情,也只有這樣的遠方才配得上讓你為之深一腳淺一腳地行走、吟唱,并最終獨自欣賞秋水長天。
如此,遠方便是深一腳淺一腳的組合體,詩意也就分別撒落在每一個近處、每一個網格,。應該說,每一腳印都是為著遠方前行,踩下去后從那深深的腳印里綻放出來的花朵,充滿詩意與詩性。正是它悄悄地消解了遠方的濃度與酸堿度,讓遠方咸淡合適、酸辣恰當、苦甜飴心。所以遠方是一種心性,它是審美的,也是審丑的。
詩意與詩性到底是什么?現代社會許多人一直仰望、追問與追趕,我一直郁悶,盡管我寫詩寫了很長時間,對此我仍舊有夏蟲語冰的感覺。那些詩意與詩性總像那些花朵,總像從花朵里釋放出來的花香。它們或者很快凋謝,或者很快被風吹走。沒有人能真正抓住花香,并將之藏匿,獨自品嘗。我如此,大家亦如此。那詩意與詩性難道是一個偽存在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但我想說,只有果實留了下來,不為一切所動地被我們抓在手上,“桃子壓枝垂”呀!所有的果實都可能壓彎其所處的枝禾。這些不應該就是“茍且”吧?如若是,那有且只有通過這些“茍且”才能讓人類看到來年的枝禾上,再次綻放誘人的花香。
其實,花香不必抓住,將之藏匿,也并不在遠方。從這方面來說,那些花瓣中的芳香油或配糖體也是“茍且”的,它只能釋放于身邊的一小段路程,并為之照耀。我亦不敢肯定這是認知真理還是客觀真理。但無論是哪一種,它們一定是飽滿的,充滿著無盡的表達。也只有這樣的表達才能標配上那存在于每一個人胸中的詩意與詩性。而這時,遠方已然就在近處,就在腳下——我欣然感到,我們均擁有或曾經擁有。
我一直在用我的腳步丈量我的人生,一步一步,一寸一寸,從少不更事到成家立家再到現在的太陽開始偏西。我用雙腳丈量丘崗,那些黃土崗總有不斷的酸甜苦辣,我用雙手撫摸草木,那些草木中總有不盡的蝶舞鶯飛。我一直在前行,如果這世界真有苦行僧,那我們便都身處其中了。這是不是海德格爾所言“詩意的棲居”呢?
“詩意的棲居”與茍且地棲居有什么不同嗎?道在屎溺,或者說屎溺中有道。這也就不可否認“茍且”中存在著詩性。
印象中我一直沒有過如劉邦項羽那般隨口一慨,所以我的遠方之于我不僅一直模糊,而且常常要么占線要么信號弱無法接通,因而也就無法在模糊中將處于我心中的那首詩與遠方結合。當然隨口一慨本身也是模糊的。但我要說的是:我們似乎只有那個“茍且”的近處,近處當然應該是清晰的,就像小時候大晴天看到的那個清晰的湖的對岸。我那會好像還從沒到達過湖對岸,我驚訝于那對岸的村莊與我的莊子居然一模一樣,一模一樣的人一模一樣地日出日落,荷鋤帶笠,我甚至有了“豈有此理”的沖動。
每一生命都是清晰的,清晰得足以讓每一個生命最終成為一幅堅毅的剪影。我感覺我們的每一步前行都充滿著詩性。任何生命也都充滿著詩性。生命的一次性決定著生命必須全過程在詩性中展開、在詩性中表達。
表達即綻放,綻放即為詩性。
它不一定或不必在遠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