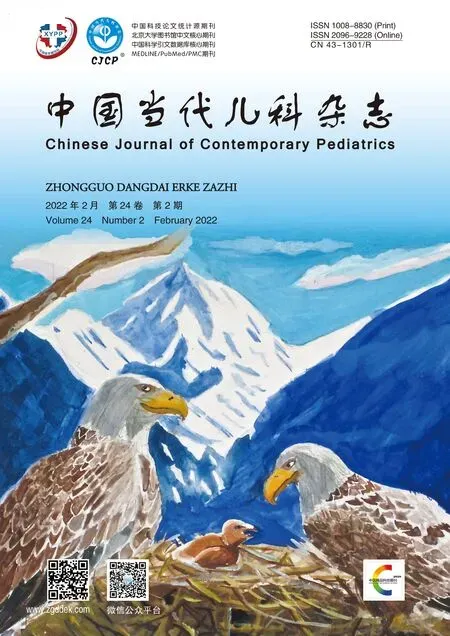兒童急性淋巴細胞白血病化療后血流感染的病原體分布與耐藥變遷分析
湛玉曉 張儉 樊彩芳 樊文娟 徐岷
(1.鄭州大學第一附屬醫院感染管理科,河南鄭州 450000;2.鄭州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心血管外科,河南鄭州 450000;3.鄭州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兒科,河南鄭州 450000;4.鄭州大學第一附屬醫院血液科,河南鄭州 450000;5.鄭州大學第一附屬醫院檢驗科,河南鄭州 450000)
急性白血病是兒童群體常見的惡性腫瘤(約占30%),其中約78%為急性淋巴細胞白血病(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ALL),病死率居兒童惡性腫瘤首位[1-2]。近年來隨著治療方案不斷改進,ALL患兒總生存率和5年無病生存率均有明顯改善[3]。然而化療對骨髓造血功能的抑制作用,使得化療后患兒感染發生率明顯升高,其中血流感染呈增高趨勢,因血流感染進展迅速,是導致急性白血病患兒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近年來關于ALL兒童群體病原體感染的相關研究較少,結果提示病原體分布和耐藥性呈區域性差異[4-7]。本研究旨在了解我院ALL患兒化療后血流感染病原體分布及耐藥特點,并了解其在研究期間的變遷趨勢,為臨床更好地抗感染治療提供依據。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
納入鄭州大學第一附屬醫院2015年1月至2020年12月收治的確診ALL并接受化療的1 090例患兒(住院4 052例次)作為研究對象。回顧性分析其中化療后發生血流感染的206例患兒(229例次)臨床資料、病原體分布及藥敏結果。229例次血流感染中,中位感染年齡5(4,7)歲。同一例患兒的重復培養結果,只提取首株數據進行分析,因真菌總體檢出較少,故本研究未做耐藥分析。
1.2 血流感染診斷標準
參照美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國家醫療保健網醫療保健相關感染的監測定義和急性醫療機構感染的分型標準中實驗室證實的血流感染診斷標準[8],即發熱>38.0℃,可合并寒戰、低血壓(收縮壓≤90 mm Hg)等,至少1套血培養出確認的病原體(如為常見皮膚污染菌,至少要求2套不同時段血培養陽性)。
1.3 分組標準
自2018年起,我院抗菌藥物臨床應用管理方案優化,建立兒童血液中心感染多學科會診機制,以此時間點為界限,根據標本送檢日期分為前3年組(2015年1月至2017年12月)和后3年組(2018年1月至2020年12月)。
1.4 血標本采集
按照《臨床微生物實驗室血培養操作規范:WS/T 503-2017》[9],感染患兒均采至少雙套培養(2瓶需氧,必要時加厭氧,總采血量4~20 mL),留置靜脈導管患兒同時抽取導管內和外周靜脈血送檢,未留置靜脈導管患兒同時抽取雙側不同部位外周靜脈血送檢。
1.5 菌株鑒定和藥敏試驗
按《全國臨床檢驗操作規程》[10],菌株的分離鑒定和細菌藥敏測試[最低抑菌濃度(minimum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MIC)值測定]均采用VITEK 2 compact全自動微生物鑒定儀器。不能用儀器法鑒定MIC值的病原體采用K-B紙片擴散法進行藥物敏感性試驗補充。藥敏結果依據2020年美國臨床和實驗室標準化協會M100標準[11]及《常見細菌藥物敏感性試驗報告規范中國專家共識》[12]判讀。質控菌株:銅綠假單胞菌ATCC27853;大腸埃希菌ATCC25922;金黃色葡萄球菌ATCC29213;表皮葡萄球菌ATCC12228;肺炎克雷伯菌ATCC700603。
1.6 統計學分析
采用SPSS22.0軟件進行數據處理。計數資料采用頻數和率(%)進行描述,組間差異比較采用χ2檢驗。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血流感染基本特征
6年間,1 090例患兒共住院4 052例次,共送檢血標本3 714份,其中陽性標本521份,血培養總陽性率14.03%(521/3 714),前3年組血培養陽性率為13.72%(206/1 502),后3年組血培養陽性率為14.24%(315/2 212),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0.205,P=0.651)。發生血流感染229例次,血流感染總發生率5.65%(229/4 052),前3年組血流感染發生率為5.16%(94/1 822),后3年組血流感染發生率為6.05%(135/2 230),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1.505,P=0.220)。發生血流感染時209例次(91.3%,209/229)患兒外周血中性粒細胞絕對計數<0.5×109/L,143例次(62.4%,143/229)患兒外周血中性粒細胞絕對計數<0.1×109/L。200例次(87.3%,200/229)患兒血流感染時留置血管導管。229例次血流感染中,97例次(42.4%,97/229)無明確感染灶,132(57.6%,132/229)例次在診斷血流感染前存在1個或多個感染灶,感染部位依次為肺部感染(39.4%,52/132)、胃腸道感染(23.5%,31/132)、口腔感染(12.9%,17/132)、肛周感染(9.8%,13/132)、皮膚軟組織感染(8.3%,11/132)、上呼吸道感染(6.8%,9/132)、腹腔感染(5.3%,7/132)、尿路感染(3.0%,4/132)及中樞神經系統感染(1.5%,2/132)。
2.2 病原體分布
共檢出病原體235株,其中革蘭陰性菌(Gram-negative bacterium,G-菌)159株(67.7%),革蘭陽性菌(Gram-positive bacterium,G+菌)61株(26.0%),真菌15株(6.4%)。G-菌以大腸埃希菌(36.5%,58/159)、肺炎克雷伯菌(28.9%,46/159)及銅綠假單胞菌(18.2%,29/159)居多;G+菌以表皮葡萄球菌(30%,18/61)、金黃色葡萄球菌(20%,12/61)及緩癥鏈球菌(13%,8/61)居多。見表1。

表1 235株ALL患兒化療后血流感染病原體分布
2.3 常見病原體的抗菌藥物耐藥性分析
常見G-菌中,腸桿菌科細菌(大腸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未發現替加環素耐藥菌株,大腸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對多黏菌素耐藥率<3%,二者對亞胺培南耐藥率<10%、對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和頭孢哌酮/舒巴坦耐藥率<20%;銅綠假單胞菌中未發現頭孢哌酮/舒巴坦、亞胺培南及多黏菌素耐藥菌株,其他抗菌藥物耐藥率均在20%以下。見表2。

表2 常見的G-菌對常用抗菌藥物的耐藥率
常見G+菌中,葡萄球菌屬和鏈球菌屬均未發現替考拉寧、萬古霉素和利奈唑胺耐藥菌株。表皮葡萄球菌對利福霉素耐藥率(22%)相對較低;金黃色葡萄球菌對復方新諾明耐藥率(25%)相對較低;緩癥鏈球菌對頭孢噻肟(12%)和青霉素G(25%)耐藥率相對較低。見表3。

表3 常見的G+菌對常用抗菌藥物的耐藥率

表3(續)
2.4 血流感染病原體分布及耐藥率變遷
前3年組檢出96株病原體,后3年組檢出139株病原體,兩組G-菌和G+菌比例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后3年組緩癥鏈球菌和真菌比例高于前3年組(P<0.05)。見表4。

表4 2組間常見的病原體分布差異比較 [株(%)]
前3年組和后3年組大腸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銅綠假單胞菌對常用抗菌藥物耐藥率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5。前3年組和后3年組表皮葡萄球菌、金黃色葡萄球菌對常用抗菌藥物耐藥率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6。

表5 2組間G-菌對常用抗菌藥物的耐藥率對比分析 [株(%)]

表6 2組間G+菌對常用抗菌藥物的耐藥率對比分析 [株(%)]
3 討論
血流感染是兒童ALL化療相關感染中最重要的類型之一,近年來血流感染發生率明顯升高,病死率高達40%[13]。
本研究中血流感染發生率5.65%,低于王真等[4]報道的8.2%。血流感染可能與化療、留置血管導管、嚴重粒細胞缺乏、黏膜炎等因素相關[14]。本研究229例次血流感染中,91.3%例次患兒在血流感染發生時處于粒細胞缺乏期,62.4%例次患兒處于嚴重粒細胞缺乏期,87.3%例次患兒在血流感染發生時留置血管導管。由于粒細胞缺乏減弱了局部炎性反應,患兒感染常不典型,發熱可能是感染的唯一征象[15]。本研究中42.4%血流感染發生時僅表現為發熱,無其他感染定位癥狀,57.6%在診斷血流感染時存在1個或多個感染定位灶,最常見的感染部位為肺部感染,其次為胃腸道感染和口腔感染,與國內相關文獻[5]報道大體一致。
福建省某醫院惡性血液腫瘤患兒合并血流感染病原體以G-菌為主(74.7%),G+菌(22.0%)次之[5]。上海某醫院ALL患兒血流感染病原體中G-菌占47.2%,G+菌占51.1%,真菌占1.5%[4]。本研究患兒血流感染病原體中以G-菌為主(67.7%),其次為G+菌(26.0%)和真菌(6.4%)。不同醫療機構病原體分布存在差異,原因可能為:(1)納入的研究對象病種分布存在差異;(2)治療方案及抗菌藥物選擇存在不同;(3)抗菌藥物臨床合理應用管理現狀不同。近6年我院ALL患兒血流感染以大腸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為主,銅綠假單胞菌次之,此3種菌前后3年構成比差異無統計學意義。而后3年組緩癥鏈球菌和念珠菌比例顯著增高。緩癥鏈球菌是口腔、上呼吸道及消化道常居菌群,而念珠菌除可在以上部位定植外,在外環境亦具有強大的依附定植能力,可通過醫務人員手水平傳播[16]。相關文獻認為嚴重的黏膜炎、使用抑酸劑、抗菌藥物暴露等與緩癥鏈球菌感染相關[17-18]。希臘一項研究指出,留置中心靜脈導管、應用廣譜抗菌藥物、應用糖皮質激素、惡性腫瘤等均是兒童罹患念珠菌血癥的危險因素[19]。我院后3年緩癥鏈球菌和念珠菌增多,分析可能與化療引起口腔、胃腸道黏膜損傷有關,另外預防用藥傾向于選擇三代頭孢、氧頭孢烯類以覆蓋常見的G-菌,長期應用導致緩癥鏈球菌和念珠菌優勢生長,菌群移位引起機會致病。提醒臨床需關注化療所致的黏膜炎,加強黏膜保護,重視口腔護理。
2005~2017年中國細菌耐藥監測網數據顯示兒童碳青霉烯類耐藥腸桿菌科細菌檢出率逐年升高,由2005年3.0%增至2017年10.2%,且區域性差異明顯,如2017年5家兒童醫院中,北京檢出率最高(25.2%),山西省檢出率最低(1.0%)[6]。北京兒童醫院血液腫瘤合并感染患兒病原體分布及耐藥分析數據表明,大腸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對碳青霉烯類藥物耐藥率分別達57.7%~61.9%,67.6%~70.5%,銅綠假單胞菌對碳青霉烯類耐藥率達46.5%~50%[7]。本研究僅納入血標本,因此整體耐藥水平較低。本研究示,G-菌中,大腸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對β-內酰胺酶抑制劑復合制劑、碳青霉烯類藥物、多黏菌素、替加環素均較敏感,可作為一線經驗性治療用藥,對復方磺胺甲噁唑及三代、四代頭孢菌素耐藥率偏高,臨床需謹慎選擇。銅綠假單胞菌對常用抗菌藥物普遍敏感,未發現頭孢哌酮/舒巴坦、亞胺培南及多黏菌素耐藥菌株。G+球菌中,表皮葡萄球菌、金黃色葡萄球菌和緩癥鏈球菌均未發現替考拉寧、萬古霉素及利奈唑胺耐藥菌株。前3年組和后3年組主要的G-菌和G+菌對常用抗菌藥物耐藥率無差異,可能與后3年我院臨床抗菌用藥管理更加規范,對細菌耐藥有一定遏制作用,抑或與納入樣本量偏少,且研究時間不足有關。
綜上所述,ALL患兒化療后血流感染仍以腸桿菌科細菌為主,然而緩癥鏈球菌和以白色念珠菌為主的念珠菌屬呈增多趨勢,緩癥鏈球菌耐藥性發展較快,而念珠菌血癥臨床易漏診且病死率高,二者均需引起臨床足夠重視。同時提醒臨床應根據病原學及耐藥監測結果科學制定抗感染方案,以提高抗感染治療成功率,并減少耐藥菌的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