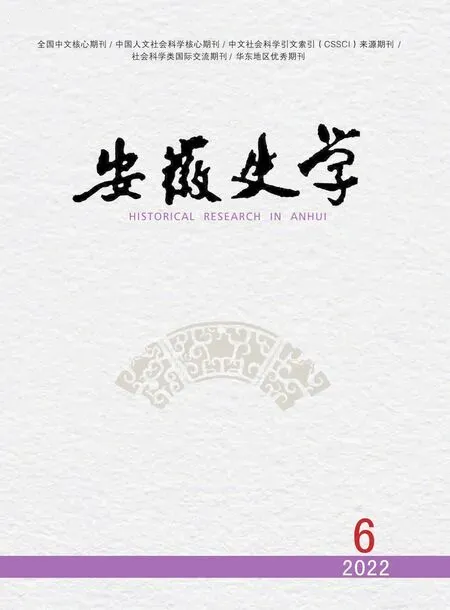明清會(huì)館的起源及其功能演變
陳寶良 周遠(yuǎn)航
(西南大學(xué) 歷史文化學(xué)院,重慶 400715)
傳統(tǒng)中國(guó)的行會(huì)源遠(yuǎn)流長(zhǎng)。然就其源頭而言,傳統(tǒng)行會(huì)只是商人之間松散的團(tuán)體,甚至是應(yīng)付朝廷徭役的組織,無(wú)固定的聚會(huì)場(chǎng)所,不過(guò)憑行以示區(qū)分而已。相對(duì)于行會(huì)而言,同業(yè)會(huì)館的崛起,則使商業(yè)團(tuán)體無(wú)論在規(guī)模上還是在組織結(jié)構(gòu)上,無(wú)不得到長(zhǎng)足的進(jìn)展。
作為同鄉(xiāng)、同業(yè)組織的會(huì)館,其名稱(chēng)雖是借用其他組織而來(lái),卻有其自身特殊的涵義。關(guān)于會(huì)館,近人何炳棣有如下定義:“會(huì)館是同鄉(xiāng)人士在京師和其他異鄉(xiāng)城市所建立,專(zhuān)為同鄉(xiāng)停留聚會(huì)或推進(jìn)業(yè)務(wù)的場(chǎng)所。狹義的會(huì)館指同鄉(xiāng)所公立的建筑,廣義的會(huì)館指同鄉(xiāng)組織。”(1)何炳棣:《中國(guó)會(huì)館史論》,中華書(shū)局2017年版,第12頁(yè)。毋庸諱言,在不同研究中,會(huì)館的定義則因關(guān)注視角差異而各有不同。有人將會(huì)館視為工商業(yè)者的行會(huì),有人把會(huì)館看作是一種同鄉(xiāng)組織;有人把會(huì)館分為一般同鄉(xiāng)人的會(huì)館和商人的會(huì)館,有人則認(rèn)為會(huì)館既可以是同鄉(xiāng)組織,也可以是同行組織。(2)相關(guān)的梳理,參見(jiàn)王日根:《明清時(shí)代會(huì)館的演進(jìn)》,《明清民間社會(huì)的秩序》,岳麓書(shū)社2003年版,第175—176頁(yè)。綜合諸家所論,大抵可以將會(huì)館歸為以下兩類(lèi):一類(lèi)是業(yè)緣性的工商行會(huì),另一類(lèi)則是地緣組織的會(huì)館。
一、會(huì)館起源蠡測(cè)
會(huì)館作為一種組織團(tuán)體,無(wú)論是同鄉(xiāng)會(huì)館抑或同業(yè)行會(huì),其起源大抵可以從傳說(shuō)與史實(shí)兩個(gè)方面加以考察。首先,就傳說(shuō)而言,其起源甚至可以追溯到遠(yuǎn)古甚至先秦時(shí)代。根據(jù)西人馬士《中國(guó)行會(huì)考》及阿維那里烏斯所編《中國(guó)工商同業(yè)公會(huì)》兩書(shū),中國(guó)的會(huì)館或同業(yè)公會(huì)的創(chuàng)始時(shí)間,遠(yuǎn)較歐洲為早。會(huì)館的起源甚至可以追溯到史前神話(huà)傳說(shuō)中的帝舜時(shí)代。一般認(rèn)為,最古老的中國(guó)同業(yè)公會(huì)組織出現(xiàn)于寧波,其章程曾言此會(huì)成立創(chuàng)始于周朝。又如在北京的“盲人會(huì)”(即三皇會(huì))中,甚至保存有漢高祖時(shí)所定的章程。這一說(shuō)法僅限于西人引述,不過(guò)是會(huì)館、公所章程的追溯之言,尚無(wú)法得到史料的印證。
其次,就史實(shí)來(lái)說(shuō),早在明清兩代乃至民國(guó)初年,很多學(xué)者將會(huì)館的起源追溯到后漢時(shí)期的“郡邸”。如朱國(guó)禎言:“會(huì)館,古郡邸之遺也。”(3)朱國(guó)禎著、何立民點(diǎn)校:《朱國(guó)禎詩(shī)文集·序·會(huì)館條約序》,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版,第421頁(yè)。在另外一則記載中,朱氏的闡釋更為詳細(xì):“漢時(shí)郡國(guó)守相置邸長(zhǎng)安,唐有進(jìn)奏院,宋有朝集院,國(guó)朝無(wú)之,惟私立會(huì)館。然止供鄉(xiāng)紳之用,其遷除應(yīng)朝者,皆不堪居也。”(4)朱國(guó)禎撰、王根林校點(diǎn):《涌幢小品》卷4《衙宇房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73頁(yè)。這一說(shuō)法,值得引起重視,可以從以下兩個(gè)方面觀之:
其一,在近人的研究中,日本學(xué)者根岸佶最早關(guān)注這一點(diǎn)。他在所著《支那行會(huì)的研究》中,將會(huì)館的起源追及漢代的“郡邸”。全漢昇引用《說(shuō)文解字》《漢書(shū)·宣帝紀(jì)》對(duì)郡邸的解釋?zhuān)C實(shí)“漢代的郡邸,確實(shí)屬于同郡官員的寄宿舍”。(5)全漢昇:《中國(guó)行會(huì)制度史》,河南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92—93、92—93、94頁(yè)。何炳棣對(duì)以上兩人之說(shuō)提出了質(zhì)疑。因早在清人惠棟的《后漢書(shū)補(bǔ)注》中,即已提出了不同的佐證,證明東漢郡邸是郡守“自為之”,屬郡守的私產(chǎn),而并非一郡的公產(chǎn)。何氏在惠棟之說(shuō)的基礎(chǔ)上,認(rèn)為“兩漢諸郡因每年上計(jì),在京師不得不有郡邸,郡邸就是各郡在京的辦事處,并不是同鄉(xiāng)組織”,因此斷言會(huì)館起源于兩漢時(shí)期的郡邸,是一種誤解。(6)何炳棣:《中國(guó)會(huì)館史論》,第14頁(yè)。
其二,就郡邸與會(huì)館的性質(zhì)而言,兩者確乎有所差異:郡邸屬于官立,通常“領(lǐng)于官”;而會(huì)館則屬于“私立”。這一點(diǎn)在明人朱國(guó)禎的記載中已經(jīng)明確道出。即使如此,將后漢時(shí)期的“郡邸”看作會(huì)館古老而久遠(yuǎn)的源頭,或會(huì)館是“古郡邸之遺也”,其實(shí)也未嘗不可。理由有二:一是漢代地方各郡,確乎在京城設(shè)有提供同郡人入京時(shí)居停的郡邸。如《漢書(shū)·朱買(mǎi)臣傳》云:“初,買(mǎi)臣免,待詔,常從會(huì)稽守邸者寄居飯食。”這種郡邸無(wú)疑具有同鄉(xiāng)會(huì)館的性質(zhì)。又《后漢書(shū)·史弼傳》云:魏劭“與同郡人賣(mài)郡邸,行賄于侯覽。”李賢注以為郡邸即“寺邸”,《集解》引惠士奇之說(shuō)亦以為如此。惟周壽昌認(rèn)為郡邸即平原郡公置之邸,猶如同郡會(huì)館。邢儀田認(rèn)為,若寺邸則屬官舍,魏劭與同郡人安能賣(mài)乎?相比之下,似周說(shuō)稍通。(7)參見(jiàn)邢儀田:《漢代的父老、僤與聚族里居——〈漢侍廷里父老僤買(mǎi)田約束石劵〉讀記》,梁庚堯、劉淑芬主編:《城市與鄉(xiāng)村》,《臺(tái)灣學(xué)者中國(guó)史研究論叢》第7冊(cè),中國(guó)大百科全書(shū)出版社2005年版,第35頁(yè)。從郡邸、寺邸可以自由買(mǎi)賣(mài)來(lái)看,郡邸顯然并非盡是官設(shè)。二是全漢昇引《三輔黃圖》元始四年長(zhǎng)安城南北所設(shè)“會(huì)市”的記載,說(shuō)明漢代郡邸除了政治功能外,尚有商業(yè)的意義,認(rèn)為“當(dāng)時(shí)共同組織設(shè)此種郡邸的太學(xué)生并不專(zhuān)去讀書(shū),還要去作買(mǎi)賣(mài),那就是各自本郡的土產(chǎn)之出售”。這無(wú)疑凸顯了郡邸的商業(yè)功能。(8)全漢昇:《中國(guó)行會(huì)制度史》,河南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92—93、92—93、94頁(yè)。郡邸的商業(yè)屬性,同樣可以從另外的史料中得到印證。如仲長(zhǎng)統(tǒng)所著《昌言》中亦云:“井田之變,豪人貨殖,館舍布于州郡。”由此可見(jiàn),豪人在“貨殖”之時(shí),在各處州郡均設(shè)有“館舍”。其中所云“館舍”,或許亦與“郡邸”有關(guān),但有待于進(jìn)一步加以證實(shí)。
會(huì)館的形成,顯然離不開(kāi)以下三大要素:一是同鄉(xiāng)的聯(lián)結(jié)紐帶;二是同業(yè)的商業(yè)紐帶;三是具體的組織場(chǎng)所,亦即所謂的館舍。現(xiàn)以此為考察的出發(fā)點(diǎn),對(duì)會(huì)館的起源做如下蠡測(cè):
其一,同鄉(xiāng)關(guān)系及其聯(lián)結(jié)紐帶。人在他鄉(xiāng),同鄉(xiāng)人組成會(huì)社團(tuán)體,堪稱(chēng)淵源有自。早在宋代的京城,已經(jīng)有了“鄉(xiāng)會(huì)”這樣的組織。南宋時(shí)期,居住在杭州的“外郡寄寓人”開(kāi)始出現(xiàn)互助活動(dòng),甚至還舉行了“社會(huì)”。全漢昇根據(jù)吳自牧《夢(mèng)粱錄》所載兩條論據(jù)斷言,在南宋的杭州,雖沒(méi)有明說(shuō)是“會(huì)館”,但從外郡人在杭州干的事情與后來(lái)會(huì)館的事業(yè)無(wú)異這一點(diǎn)來(lái)看,顯然不能否認(rèn)有會(huì)館這一回事。(9)全漢昇:《中國(guó)行會(huì)制度史》,河南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92—93、92—93、94頁(yè)。這種推測(cè)無(wú)疑很有建設(shè)性。到了明代弘治年間,常州府無(wú)錫縣在京城的官員,借助于一年四季的節(jié)日,開(kāi)始舉行同鄉(xiāng)會(huì)。此舉始于弘治六年春,邵寶因“入覲京師”,得以在顧氏所居“芹軒”與“同鄉(xiāng)縉紳諸公”相會(huì),且一起賦詩(shī)作為留念。其后,凡是元夕、上巳、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重陽(yáng)、長(zhǎng)至各節(jié),無(wú)錫同鄉(xiāng)在朝的官員20余人,無(wú)不相會(huì),亦即所謂的“會(huì)以節(jié)舉”。尤其是弘治十一年的重陽(yáng)節(jié),無(wú)錫在京官員再次聚會(huì),與會(huì)人員“人為詩(shī)一章”,稱(chēng)《重陽(yáng)會(huì)詩(shī)》。(10)邵寶:《容春堂別集》卷5《芹軒詩(shī)序》;《容春堂前集》卷13《重陽(yáng)會(huì)詩(shī)序》,《容春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45、135—136頁(yè)。明代京城官員的這種同鄉(xiāng)聚會(huì),特點(diǎn)是“節(jié)舉一會(huì),以要鄉(xiāng)盟”,顯然也是為了維系同鄉(xiāng)的關(guān)系紐帶。
其二,同業(yè)關(guān)系及其聯(lián)結(jié)紐帶。同業(yè)之行亦即所謂的行會(huì),其起源有宗教團(tuán)體說(shuō)、同鄉(xiāng)團(tuán)體說(shuō)、政府之不法說(shuō)、人口與事物之不均衡說(shuō)、家族制度說(shuō)等五種說(shuō)法。(11)全漢昇:《中國(guó)行會(huì)制度史》,第2—5、17、29—36、67—69、92頁(yè)。全漢昇較為認(rèn)同家族制度說(shuō),并將中國(guó)行會(huì)的起源時(shí)間,追溯到周末至漢代,認(rèn)為這個(gè)時(shí)期“手工業(yè)行會(huì)已有存在的事實(shí)了”。(12)全漢昇:《中國(guó)行會(huì)制度史》,第2—5、17、29—36、67—69、92頁(yè)。他認(rèn)為楊衒《洛陽(yáng)伽藍(lán)記》已記載北魏洛陽(yáng)便有這種典型的同業(yè)商店區(qū)了。此外,他借助唐人韋述《兩京新記》、宋人劉義慶《大業(yè)雜記》、元代《河南志》的記載,最終認(rèn)定,“行”的名稱(chēng)最初見(jiàn)于記載是隋代。(13)全漢昇:《中國(guó)行會(huì)制度史》,第2—5、17、29—36、67—69、92頁(yè)。至唐代,更是廣泛出現(xiàn)了各色行會(huì)組織,諸如“梨園會(huì)”“鼓樂(lè)板”等同業(yè)公會(huì),大約均始于唐代中葉。(14)彭澤益主編:《中國(guó)工商行會(huì)史料集》上冊(cè),中華書(shū)局1995年版,第76、117—118頁(yè)。宋代盡管尚無(wú)公所、會(huì)館一類(lèi)的名稱(chēng),但據(jù)《夢(mèng)粱錄》與《宋會(huì)要》記載中的“上行”“住行”之說(shuō),斷定宋代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會(huì)所,即行會(huì)的辦公地方,同時(shí)又成為同業(yè)者共同祭祀本行祖師的所在地,并將此類(lèi)“上行”或“住行”的會(huì)所,視為后世會(huì)館或公所的“前身”。(15)全漢昇:《中國(guó)行會(huì)制度史》,第2—5、17、29—36、67—69、92頁(yè)。
其三,作為同鄉(xiāng)、同業(yè)紐帶的“會(huì)館”名稱(chēng)出現(xiàn)。《帝京景物略》記載,廬陵人在順天府學(xué)宮之外設(shè)祠祭祀文天祥,稱(chēng)“懷忠會(huì)館”。(16)劉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1《文丞相祠》,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4頁(yè)。全漢昇以此為據(jù),斷定會(huì)館的名稱(chēng)最初見(jiàn)于明代。(17)全漢昇:《中國(guó)行會(huì)制度史》,第2—5、17、29—36、67—69、92頁(yè)。將會(huì)館真正出現(xiàn)的時(shí)間定于明代,這一點(diǎn)并無(wú)疑義,但若將會(huì)館名稱(chēng)斷為始于明代,并非完全準(zhǔn)確。換言之,同鄉(xiāng)會(huì)或同業(yè)行會(huì)出現(xiàn)辦公場(chǎng)所,或者說(shuō)“會(huì)館”一稱(chēng)的真正確立,應(yīng)該與元末明初直至明代中葉廣泛興起的“文會(huì)館”“經(jīng)館”“講學(xué)會(huì)館”“公館”“試館”“同善會(huì)館”等有著密切的關(guān)系。尤其是試館的出現(xiàn),更是與同鄉(xiāng)會(huì)館有著直接的淵源關(guān)系。如明末,士子到北京應(yīng)試,由旅居北京的官僚,為其鄉(xiāng)人士子集資購(gòu)產(chǎn),辟有房屋館舍,名曰“試館”,后亦稱(chēng)為“會(huì)館”,但性質(zhì)與商人會(huì)館有所不同。下面以此為線(xiàn)索,從四個(gè)方面論之:
一是“文會(huì)館”“經(jīng)館”“講學(xué)會(huì)館”與會(huì)館之關(guān)系。會(huì)館一稱(chēng),始見(jiàn)于“文會(huì)館”。早在元代,文會(huì)頗為興盛。此類(lèi)文會(huì),實(shí)則與科舉士子的關(guān)系密切。如元人謝良曾在金山西南的呂巷鎮(zhèn),設(shè)立“應(yīng)奎文會(huì)”。(18)章鳴鶴著、范棫士校:《谷水舊聞》,上海市松江區(qū)博物館、華東師范大學(xué)古籍研究所編:《明清松江稀見(jiàn)文獻(xiàn)叢刊》第1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5頁(yè)。文會(huì)之舉,通常是臨時(shí)的舉措,至元代開(kāi)始出現(xiàn)了固定的場(chǎng)所。如在湖廣岳州府就建有一亭,稱(chēng)“文會(huì)亭”,以供學(xué)者們“講磨經(jīng)史,議論斯文”。(19)張文啟:《文會(huì)亭記》,嘉靖《湖廣圖經(jīng)志》卷7《岳州府》,《日本藏中國(guó)罕見(jiàn)地方志叢刊》本,書(shū)目文獻(xiàn)出版社1992版。這種文會(huì)亭,即為文會(huì)館的淵源。
至明代,科舉士子的文會(huì)尤為繁盛,隨之出現(xiàn)了各種“文會(huì)館”,甚至“館以會(huì)設(shè),會(huì)以文名”(20)江東望:《建聚星文社館序》,江登云輯、江紹蓮續(xù)編、康健校注:《橙陽(yáng)散志》卷12《藝文志三》,安徽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18年版,第216頁(yè)。,亦即文、會(huì)、館最終趨于合流。如成化年間,蘇州府昆山縣的士大夫致仕之后,與一些在鄉(xiāng)里隱居的賢人,結(jié)成雅會(huì),稱(chēng)“斯文會(huì)”。參與者共有15人,每月舉行一次,人各賦詩(shī),又將參與文會(huì)之人繪成一圖。文會(huì)原本設(shè)有會(huì)所,因較為狹小,不能容身。至弘治初年,昆山知縣楊子器撤去一些祠廟,改建為文會(huì)館。(21)黃云:《斯文會(huì)詩(shī)后序》,嘉靖《昆山縣志》卷4《第宅》,《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本,上海古籍書(shū)店1982年版。萬(wàn)歷五年,淮安府宿遷縣知縣俞文偉,在新城南門(mén)內(nèi)設(shè)立文會(huì)館,稱(chēng)“凌云會(huì)館”。(22)萬(wàn)歷《宿遷縣志》卷2《建置志·學(xué)校》,《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xù)編》本,上海書(shū)店出版社1990年版。
明末文社“公寓”的出現(xiàn),更是足證文社、文會(huì)與會(huì)館已經(jīng)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據(jù)吳應(yīng)箕記載,“江以上”即安徽一帶文士至蘇州之后,為了參與文社活動(dòng),一至虎丘,盡管“精舍相望”,但也不得不“卜之而僦館”,以致“稅驂之費(fèi)恒苦不繼”。鑒此原因,陳名夏與吳應(yīng)箕商議,會(huì)集安徽的“同聲之友”,共同籌措資金合計(jì)銀150兩左右,買(mǎi)一所僧寮,作為文社之士的“公寓”,以便江上之士到了蘇州之后,可以有“寓屋”可居。公寓還負(fù)責(zé)文社之士的“寄餐”,以及書(shū)信往來(lái),使“郵筒不致沈絕”。(23)吳應(yīng)箕:《樓山堂遺文》卷6《虎丘公寓序》,章建文點(diǎn)校:《吳應(yīng)箕文集》,黃山書(shū)社2017年版,第651頁(yè)。
值得引起注意的是,歙縣所設(shè)各種文會(huì)館,如聚星會(huì)館、蟾扶文社、鵬扶文社及其會(huì)館,并系于“祭祀”項(xiàng)下,與春社、秋社之祭相混;聚星會(huì)館、聯(lián)云會(huì)館、鵬扶會(huì)館,又系于“書(shū)院”項(xiàng)下,說(shuō)明與書(shū)院在功能上有趨同之勢(shì)。事實(shí)確乎如此。在明代,這種文會(huì)館,有時(shí)又稱(chēng)“文會(huì)堂”,或稱(chēng)“會(huì)講堂”。正如周洪謨?cè)凇段臅?huì)堂記》一文中所言,文會(huì)堂確乎起到了精舍的作用,生員從中可以商討學(xué)業(yè)。(24)嘉靖《湖廣圖經(jīng)志》卷6《荊州府》。一般說(shuō)來(lái),明代很多地方學(xué)校的校舍建筑,除了明倫堂之外,就是東、西齋,以供生員學(xué)習(xí)與生活,并無(wú)此類(lèi)會(huì)講堂、文會(huì)堂。只有湖廣荊州府學(xué)才額外設(shè)置了這類(lèi)建筑。這當(dāng)然也是有原因的。自明代中期以后,生員的肄業(yè)乃至生活場(chǎng)所,有了一些改變。生員已不再在學(xué)校內(nèi)學(xué)習(xí)與生活,而是改而在一些公私建立的書(shū)院、精舍中生活與學(xué)習(xí)。文會(huì)堂的建立,部分適應(yīng)了這種趨勢(shì)。徽州的“斗山文會(huì)”即是典型的例證。斗山文會(huì)最初即為斗山書(shū)院,湛若水、鄒守益、耿定向、王畿等人,先后在此講學(xué)。至萬(wàn)歷年間,許穆、凌琯“請(qǐng)于當(dāng)事”,作為徽州府、歙縣士子的“文會(huì)”。(25)許承堯撰,李明回、彭超等校點(diǎn):《歙事閑譚》卷1《斗山文會(huì)錄》,黃山書(shū)社2014年版,上冊(cè),第221—222頁(yè)。
何炳棣憑其敏銳的目光,發(fā)現(xiàn)了講學(xué)會(huì)館與會(huì)館之間的淵源關(guān)系。他引乾隆《吉安府志》所記,證實(shí)明正德年間王陽(yáng)明講學(xué)青原山,有“青原會(huì)館”之設(shè)。至萬(wàn)歷年間,吉水人鄒元標(biāo)倡陽(yáng)明之學(xué),又建“九邑會(huì)館”。從此類(lèi)講學(xué)會(huì)館中,何氏得出如下結(jié)論:“本地非經(jīng)常性講學(xué)聚會(huì)的所在,也可稱(chēng)為‘會(huì)館’。在王學(xué)極盛的16世紀(jì),吉安每個(gè)屬縣都有‘會(huì)館’,而且不久都有‘公田備餼’。這雖是自16世紀(jì)初葉起江西一個(gè)區(qū)域的現(xiàn)象,但會(huì)館一名詞已被借用,亦足表明京師郡邑會(huì)館確已具有相當(dāng)長(zhǎng)的歷史,而其性質(zhì)與功能則尚未固定”。(26)何炳棣:《中國(guó)會(huì)館史論》,第17頁(yè)。但何氏認(rèn)為講學(xué)會(huì)館借用了郡邑會(huì)館之名,或許顛倒了前后關(guān)系。從上揭元代出現(xiàn)的文會(huì)館,以及明代初期、中期以后文會(huì)館、講學(xué)會(huì)館的普遍出現(xiàn)即已可知,理應(yīng)是郡邑會(huì)館借用了文會(huì)館、講學(xué)會(huì)館之名。
所謂講學(xué)會(huì)館的功能,不但有學(xué)者在其中講學(xué),而且可供學(xué)者肄業(yè)、居住。從源頭來(lái)說(shuō),此類(lèi)會(huì)館,遠(yuǎn)者為孔子聚徒杏壇,近者則為精舍、書(shū)院。在明代,書(shū)院不列于學(xué)宮,而精廬、學(xué)堂、講舍,更是“因俗為制,要在作人,非以標(biāo)異也”。(27)萬(wàn)歷《廣東通志》卷7《書(shū)院》,《稀見(jiàn)中國(guó)地方志匯刊》本,中國(guó)書(shū)店1992版。明代的講學(xué)會(huì)館,史不乏例。除了何炳棣所列之外,至少尚有如下幾個(gè)講學(xué)會(huì)館:桐城縣的“桐川會(huì)館”,其中設(shè)有崇實(shí)堂、先正堂、盡心齋、左右室、更衣所、養(yǎng)正所。(28)焦竑:《澹園集》卷4《桐川會(huì)館記》,中華書(shū)局1999年版,第829—830頁(yè)。桐城之學(xué),首倡于何采,并由耿定向、張緒發(fā)揚(yáng)光大。而桐川會(huì)館,則由耿、張二人的門(mén)人方學(xué)漸所建,其用意在于“以待四方同志之來(lái)會(huì)者”。(29)葉燦:《方明善先生行狀》;陸嘉猷:《東游記序》,均載方昌翰輯、彭君華校點(diǎn):《桐城方氏七代遺書(shū)》,黃山書(shū)社2019年版,第1、69頁(yè)。石埭的“陵陽(yáng)會(huì)館”,于萬(wàn)歷十七、十八年由畢一衡創(chuàng)設(shè)。當(dāng)時(shí)畢氏講學(xué)石埭,“一時(shí)從游者,至屨滿(mǎn)戶(hù)外”,于是擬建別館“以居之”,未成而歿,后由其弟畢一素建成。(30)焦竑:《澹園集》卷4《陵陽(yáng)會(huì)館記》,第830頁(yè)。江西吉安府廬陵縣的“西原會(huì)館”,位于西原山能仁寺之左,萬(wàn)歷十二年,由吉安府人陳嘉謨等捐金買(mǎi)地共建,題名“求益堂”。會(huì)館置有田30畝,“供會(huì)饌”。(31)萬(wàn)歷《吉安府志》卷15《學(xué)校志》,《稀見(jiàn)中國(guó)地方志匯刊》本。西安的“關(guān)中書(shū)院”,萬(wàn)歷年間為馮從吾講學(xué)而設(shè)。(32)翟鳳翥:《重興關(guān)中書(shū)院序》,《馮少墟續(xù)集》卷5《書(shū)院記》,馮從吾著,劉學(xué)智、孫學(xué)功點(diǎn)校整理:《馮從吾集》,西北大學(xué)出版社2015年版,第573頁(yè)。馮從吾即有《輔仁館會(huì)語(yǔ)題辭》一篇(33)馮從吾:《馮少墟集》卷16《輔仁館會(huì)語(yǔ)題辭》,《馮從吾集》,第322頁(yè)。,足證關(guān)中書(shū)院又稱(chēng)“輔仁館”。桐城縣樅陽(yáng)鎮(zhèn)的“輔仁會(huì)館”,原本為布衣童定夫的講學(xué)之處,由其弟子“醵金為建”。至天啟三年,錢(qián)澄之之父繼承講席,并與童心鑒“倡率同志,一遵昔規(guī),以每月十三日會(huì)于館所”。(34)錢(qián)澄之:《田間文集》卷22《童翁鄣石墓志銘》、卷29《先考敬修先生鏡水府君行略》,黃山書(shū)社1998年版,第440、549頁(yè)。
綜上可見(jiàn),明代的會(huì)館,有時(shí)實(shí)指士子聽(tīng)講、肄業(yè)的場(chǎng)所。會(huì)館有時(shí)又稱(chēng)“經(jīng)館”,如東莞人任柱,在出任舞陽(yáng)縣知縣時(shí),曾創(chuàng)設(shè)“五經(jīng)館”,“以教邑之多士”。(35)湛若水:《湛甘泉先生文集》卷18《五經(jīng)館》,《四庫(kù)全書(shū)存目叢書(shū)》影印清康熙二十年黃慨刻本。相同的例子也見(jiàn)于六安州。如當(dāng)?shù)赜幸凰鞍埠?huì)館”,位于六安州西南,由州同知鄧向榮構(gòu)筑;又有“青云會(huì)館”,在州學(xué)宮前右,屬于知州楊際會(huì)的生祠。這兩所會(huì)館,均有“諸生肄業(yè)于此”。(36)萬(wàn)歷《六安州志》卷2《營(yíng)建志·學(xué)校》,《日本藏中國(guó)罕見(jiàn)地方志叢刊》本。此外,明代的會(huì)館,有時(shí)又指書(shū)院、社學(xué)。以書(shū)院為例,如寧國(guó)府宣城縣,有一所“同仁會(huì)館”,位于西門(mén)內(nèi),始建于萬(wàn)歷年間,每月一會(huì),府縣官員、薦紳、父老、子弟“講學(xué)歌詩(shī),或具館谷”。(37)嘉慶《宣城縣志》卷8《學(xué)校》,《稀見(jiàn)中國(guó)地方志匯刊》本。“法華會(huì)館”同樣具有書(shū)院的性質(zhì),位于湖廣嘉魚(yú)縣,最初是由法華寺改建,后在寺廟的西南隅建堂,“翼廊辟門(mén),除路,厥制煥如,厥觀偉如”。(38)尹相:《法華會(huì)館志》,乾隆《重修嘉魚(yú)縣志》卷6,《稀見(jiàn)中國(guó)地方志匯刊》本。以社學(xué)為例,廣東惠州府興寧縣有一所會(huì)館,原在城北。萬(wàn)歷十八年,惠州府推官王棟署理興寧縣知縣時(shí),買(mǎi)民居鼎建,與社倉(cāng)、社學(xué)相連。(39)崇禎《興寧縣志》卷2《學(xué)校》,《稀見(jiàn)中國(guó)地方志匯刊》本。這段史料被放置在“社學(xué)”目?jī)?nèi),顯然這一會(huì)館具有社學(xué)性質(zhì)。
二是“公館”與會(huì)館之關(guān)系。公館又稱(chēng)“賓館”,究其設(shè)立之意,原本不過(guò)是為官員因公外出提供歇息之所。如明代寧夏城內(nèi),有“皇華館”,在城南五里,靠近大路之東,宣德八年,由慶靖王朱栴所建,“以為迎接詔書(shū)之所”。(40)胡玉冰、孫瑜校注:正統(tǒng)《寧夏志》卷上《公宇》,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出版社2015年版,第33頁(yè)。在潞安,同樣有一所“皇華館”,作為經(jīng)過(guò)“使客”歇息的賓館。館中之堂,稱(chēng)“四咨堂”。(41)程嘉燧:《松圓偈庵集》卷上《新筑皇華館記(代方方石)》,沈習(xí)康點(diǎn)校:《程嘉燧全集》上冊(c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317頁(yè)。寧國(guó)府涇縣、旌德縣之間,設(shè)有一所“仰賢公館”,弘治十二年南畿巡撫彭禮下令修建,最后由寧國(guó)知府、涇縣知縣建成。公館有大廳、左右?guī)俊?42)楊守阯:《碧川文選》卷5《寧國(guó)府涇縣仰賢公館碑記》,張壽鏞輯:《四明叢書(shū)》第26冊(cè),廣陵書(shū)社2006年版,第16414—16415頁(yè)。
自明代中期以后,公館的性質(zhì)開(kāi)始出現(xiàn)了轉(zhuǎn)化,甚至帶有會(huì)館的性質(zhì)。主要體現(xiàn)在以下兩個(gè)方面:一則公館有時(shí)亦稱(chēng)“會(huì)館”。如在寧國(guó)府,設(shè)有“三府會(huì)館”,從其設(shè)立的目的來(lái)看,顯然屬于寧國(guó)、徽州、池州三府的公館,“凡有公務(wù)于三郡者,皆得以棲止焉”。(43)鄒旸:《三府會(huì)館記》,萬(wàn)歷《寧國(guó)府志》卷13,《稀見(jiàn)中國(guó)地方志匯刊》本。二則公館與書(shū)院之間出現(xiàn)了一種互動(dòng)趨勢(shì)。一方面,公館成為地方學(xué)校生員肄業(yè)的場(chǎng)所,進(jìn)而帶有書(shū)院的性質(zhì)。如嘉靖年間,福建龍溪縣知縣林松憩息于“金沙公館”,見(jiàn)到諸生周一陽(yáng)、陳科選等人在此肄業(yè),于是,就將公館改為書(shū)院。(44)林希元撰、何丙仲校注:《林次崖先生文集》卷10《金沙書(shū)院記》,廈門(mén)大學(xué)出版社2015年版,下冊(cè),第391頁(yè)。又福建建寧府公館,在府城內(nèi)從化坊。成化七年,由通判李明建,作為清理軍政之所,后改稱(chēng)“東甌書(shū)院”。(45)黃仲昭修纂:弘治《八閩通志》卷40《公署》,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下冊(cè),第164頁(yè)。另一方面,書(shū)院有時(shí)又可轉(zhuǎn)變?yōu)楣^。如福建泉州府同安縣的文公書(shū)院,始建于元至正十年,至明代,“書(shū)院鞠為府館,人有遺恨”。(46)林希元撰、何丙仲校注:《林次崖先生文集》卷10《重建文公書(shū)院記》,第386—387頁(yè)。
三是“試館”與會(huì)館的關(guān)系。會(huì)館有時(shí)又被稱(chēng)為“試館”,大抵源于京城會(huì)館為公車(chē)舉子提供便利之故。究試館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南朝時(shí)期的“貢計(jì)館”,“在建康縣東二里洲子岸上,諸州府秀才選舉,皆憩此館”。(47)趙彥衛(wèi):《云麓漫鈔》卷6,中華書(shū)局1958年版,第92頁(yè)。
何炳棣從方志中勾稽出諸多的府城試館與省垣試館,但或許囿于所檢多為清代方志,除了最早建立于明季的南昌樂(lè)平試館外,其他均為清代所建試館,如廣東順德于乾隆時(shí)期在廣州城外建立的“邑館”,湖南邵陽(yáng)道光四年在長(zhǎng)沙建立的“試館”。(48)何炳棣:《中國(guó)會(huì)館史論》,第34—35頁(yè)。其實(shí),入明以后,不僅京城設(shè)有諸多試館,而且在很多地方,同樣也設(shè)有為士子提供便寓的試館。一般說(shuō)來(lái),在明代各級(jí)考試中,除了中央的會(huì)試與各省的鄉(xiāng)試有專(zhuān)門(mén)貢院之外,各地提學(xué)道舉行的童試,通常只是臨時(shí)搭棚,并無(wú)專(zhuān)門(mén)的試館。至明代末年,也陸續(xù)出現(xiàn)了這類(lèi)試館,或稱(chēng)“校士館”,或稱(chēng)“試士館”,或稱(chēng)“弘文館”。如溫州府校士館,即“督學(xué)使者所駐以校六庠者也”。(49)王叔杲著、張憲文校注:《王叔杲集》卷9《校士館記》,上海社會(huì)科學(xué)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237—238頁(yè)。此外,崇禎十五年,在浙江嚴(yán)州府建德縣,就建有“試士館”一所。(50)康熙《建德縣志》卷2《營(yíng)建志》,《稀見(jiàn)中國(guó)地方志匯刊》本。崇禎年間,知府鄭瑄在浙江嘉興府設(shè)立“弘文館”,其實(shí)也屬于督學(xué)道校士的試館。(51)康熙《嘉興府志》卷5《公署》,《稀見(jiàn)中國(guó)地方志匯刊》本。
試館與會(huì)館的關(guān)系頗為密切。閩縣人程樹(shù)德云:“京師之有會(huì)館,肇自有明,其始專(zhuān)為便于公車(chē)而設(shè),為士子會(huì)試之用,故稱(chēng)會(huì)館,自清季科舉停罷,遂專(zhuān)為鄉(xiāng)人旅京者雜居之地,其制已稍異于前矣。”清代閩縣人陳宗蕃說(shuō):“會(huì)館之設(shè),始自明代,或曰會(huì)館,或曰試館。蓋平時(shí)則以聚鄉(xiāng)人,聯(lián)舊誼,大比之歲,則為鄉(xiāng)中來(lái)京假館之所,恤寒畯而啟后進(jìn)也。”(52)李景銘:《閩中會(huì)館志》,程樹(shù)德、陳宗蕃序,轉(zhuǎn)引自王日根:《明清時(shí)代會(huì)館的演進(jìn)》,《明清民間社會(huì)的秩序》,第181頁(yè)。另一條史料也說(shuō):“各省會(huì)館,莫盛于京都,原為鄉(xiāng)會(huì)場(chǎng)寓考而設(shè)。”(53)《江南會(huì)館義園征久錄》卷4《會(huì)館落成公議條規(guī)》,清刻本。針對(duì)此說(shuō),何炳棣提出了質(zhì)疑。他認(rèn)為,明代會(huì)館“大都為已仕之人暫居聚會(huì)之所,尚非試館性質(zhì)。近人有謂會(huì)館專(zhuān)為同鄉(xiāng)參加會(huì)試之人而設(shè),故曰會(huì)館之說(shuō),亦欠正確。”(54)何炳棣:《中國(guó)會(huì)館史論》,第17頁(yè)。其實(shí),何氏之說(shuō),也并不全面。崇禎年間的《帝京景物略》,就有關(guān)于會(huì)館起源的明確記載:
嘗考會(huì)館之設(shè)于都中,古未有也,始嘉、隆間。蓋都中流寓十土著,游閑屣士紳,爰隸城坊而五之。臺(tái)五差,衛(wèi)五緝,兵馬五司,所聽(tīng)治詳焉。惟是四方日至,不可以戶(hù)編而數(shù)凡之也,用建會(huì)館,士紳是主,凡入出都門(mén)者,藉有稽,游有業(yè),困有歸也。……繼自今,內(nèi)城館者,紳是主,外城館者,公車(chē)歲貢士是寓。(55)劉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4《嵇山會(huì)館唐大士像》,第180—181頁(yè)。
細(xì)繹上說(shuō),已明確道出明代會(huì)館分為兩種:一是內(nèi)城的會(huì)館,由縉紳所主,成為同鄉(xiāng)仕宦的寓居之所;二是外城的會(huì)館,則為舉人、歲貢生所寓之處。前者為同鄉(xiāng)會(huì)館,后者則可歸入試館。
從具體的史實(shí)來(lái)看,京城會(huì)館寓居人員,確非僅僅限于仕宦之人,而是各色士人薈萃,尤其是鄉(xiāng)、會(huì)試之士子。關(guān)于此,史料有如下記載:
京師為萬(wàn)方輻輳之地,風(fēng)雨和會(huì),車(chē)書(shū)翕至,彩纓紆組之士于焉云集景從。遇鄉(xiāng)會(huì)試期,則鼓篋橋門(mén),計(jì)偕南省,恒數(shù)千計(jì),而投牒選部,需次待除者,月乘歲積,于是寄廡僦舍,遷從靡常,欲珠薪桂之嘆,蓋伊昔已然矣。時(shí)則有寘室宇以招徠其鄉(xiāng)人者,大或合省,小或郡邑,區(qū)之曰會(huì)館。(56)《京師休寧會(huì)館公立規(guī)約》,民國(guó)十一年重訂本。
仔細(xì)分析這段記載,同樣可以證明會(huì)館為以下兩類(lèi)人員提供了寓居的方便:一類(lèi)是仕宦官員,包括“投牒選部,需次待除”的官員,亦即“彩纓”之士;另一類(lèi)是科舉士子,包括參加鄉(xiāng)試、會(huì)試的士人,亦即“紆組”之士。清初人施閏章在論及京城宣城會(huì)館時(shí),除了“以會(huì)邑之游宦往來(lái)者也”之外(57)施閏章:《施愚山集·文集》卷11《宣城會(huì)館記》,黃山書(shū)社1992年版,第227—228頁(yè)。,也明確說(shuō)自己至京城參加博學(xué)鴻儒考試,先是僦屋寓居,后入寓會(huì)館。(58)施閏章:《施愚山集·補(bǔ)遺一·試?guó)櫜┖蠹視?shū)十四通之六》,第127頁(yè)。至于清初人汪琬所記,認(rèn)為會(huì)館的寓居人員,除了“貴自仕宦”之外,而且“下訖商旅”,并“寓敦睦救恤諸遺法于其中”,更是將會(huì)館與同鄉(xiāng)商人聯(lián)系在一起。(59)汪琬:《鈍翁前后類(lèi)稿》卷25《文稿十三·序三·代青陽(yáng)館規(guī)序》,李圣華箋校:《汪琬全集箋校》,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10年版,第2冊(cè),第569—570頁(yè)。
四是“同善會(huì)館”與會(huì)館之關(guān)系。明代末年,作為慈善組織的“同善會(huì)”,也開(kāi)始設(shè)有公所,并稱(chēng)為“會(huì)館”。如嘉興府嘉善縣的“同善會(huì)館”,崇禎十四年由陳龍正設(shè),以思賢書(shū)院舊址改建而成。(60)光緒《嘉興府志》卷24《養(yǎng)育》,《中國(guó)地方志集成》本,上海書(shū)店出版社1993年版。入清以后,同善會(huì)館繼續(xù)存在。如在婁縣楓涇鎮(zhèn),就設(shè)有同善會(huì)館,在鎮(zhèn)南均安橋北,乾隆二十年由全鎮(zhèn)士民公建,有房屋20余楹。咸豐十年,毀于火。外有市房6楹,在米篩橋北,改為“公所”。(61)許光墉、葉世熊修輯:《重輯楓涇小志》卷2《志建置·義建》,上海地方志辦公室編:《上海鄉(xiāng)鎮(zhèn)舊志叢書(shū)》第6冊(cè),上海社會(huì)科學(xué)院出版社2004版,第26頁(yè)。
二、會(huì)館的正式形成
當(dāng)然,同鄉(xiāng)組織立有會(huì)館、公所,究竟始于何時(shí),顯然存在著爭(zhēng)議。明人沈德符論會(huì)館云:“京師五方所聚,其鄉(xiāng)各有會(huì)館,為初至居停,相沿甚便。”(62)沈德符:《萬(wàn)歷野獲編》卷24《畿輔·會(huì)館》,中華書(shū)局2004年版,第608頁(yè)。此雖道出會(huì)館之功能,但尚未點(diǎn)出其出現(xiàn)的時(shí)間。一般認(rèn)為同鄉(xiāng)會(huì)館始于嘉靖、隆慶年間,更為確切的記載是嘉靖三十九年。如《帝京景物略》即有以下之說(shuō):“嘗考會(huì)館之設(shè)于都中,古未有也,始嘉、隆間。”(63)劉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4《嵇山會(huì)館唐大士像》,第180頁(yè)。又萬(wàn)歷十四年,許國(guó)在為京城歙縣會(huì)館所撰的碑記中,也僅模糊地記載歙縣會(huì)館的創(chuàng)始時(shí)間為“嘉靖季年”,進(jìn)而認(rèn)為經(jīng)始于嘉靖四十一年十二月,落成于嘉靖四十二年十二月。鄭濤曾為《歙縣會(huì)館錄》撰寫(xiě)序言,時(shí)間為嘉靖三十九年。(64)徐世寧、楊熷續(xù)錄,徐光文、徐上墉重錄:《重續(xù)歙縣會(huì)館錄·續(xù)修會(huì)館錄·節(jié)存原編記序》,(香港)大東圖書(shū)公司1977年版,第13頁(yè)。此外,歙縣會(huì)館中有題為“崇義”的匾額,清人徐光文在按語(yǔ)中,也說(shuō)嘉靖三十九年題于菜市中街,后移置新館。日本學(xué)者和田清在1922年即引《帝京景物略》之說(shuō),加藤繁亦采納此說(shuō)。仁井田陞及楊聯(lián)陞先后根據(jù)道光十四年《重續(xù)歙縣會(huì)館錄》所保存的原序,認(rèn)為會(huì)館最早創(chuàng)設(shè)于嘉靖三十九年。由此可見(jiàn),將會(huì)館創(chuàng)設(shè)的時(shí)間定為16世紀(jì)中葉以后,似已成為定論。(65)何炳棣:《中國(guó)會(huì)館史論》,第14—15、15—17頁(yè)。
毫無(wú)疑問(wèn),這一說(shuō)法存在著可疑之處。同鄉(xiāng)會(huì)館真正出現(xiàn)的時(shí)間,并不會(huì)晚至嘉靖末年。西人馬士在《中國(guó)行會(huì)考》中認(rèn)為,早在明初,已有確切的證據(jù)證明,在北京開(kāi)始設(shè)有江蘇會(huì)館。(66)彭澤益主編:《中國(guó)工商行會(huì)史料集》上冊(cè),第76頁(yè)。這一說(shuō)法,不知出自何種記載。何炳棣借助于兩種史料,將會(huì)館起源的時(shí)間,追溯至永樂(lè)年間。其一是民國(guó)十八年《蕪湖縣志》記載,北京前門(mén)外長(zhǎng)巷上三條胡同的蕪湖會(huì)館,是蕪湖縣人工部主事俞謨于永樂(lè)年間所建。其二是清初《閩小紀(jì)》所載一則關(guān)于林璧的軼事,證明在嘉靖初葉以前,亦即15世紀(jì)后半葉,福州京宦已在北京建立福州會(huì)館。(67)何炳棣:《中國(guó)會(huì)館史論》,第14—15、15—17頁(yè)。王日根借助乾隆《浮梁縣志》與同治《重修廣東舊義園記》兩種史料,證實(shí)以下事實(shí):在永樂(lè)年間的北京,出現(xiàn)了浮梁縣人吏員金宗舜鼎建的浮梁會(huì)館,以及禮部尚書(shū)王忠銘等人所倡建的廣東會(huì)館。(68)王日根:《明清時(shí)代會(huì)館的演進(jìn)》,《明清民間社會(huì)的秩序》,第178頁(yè)。
根據(jù)已有史料,再綜合何、王二家之說(shuō),可知同鄉(xiāng)會(huì)館最早出現(xiàn)于明永樂(lè)年間。但在嘉靖末年以前,僅有零星關(guān)于會(huì)館的記載。至嘉靖末年之后,會(huì)館趨于勃興,且可以得到更多的史料佐證。如據(jù)呂作燮的勾稽,嘉靖年間,南京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兩所會(huì)館,分別是福建莆田的文獻(xiàn)會(huì)館,以及廣東潮州會(huì)館。(69)呂作燮:《南京會(huì)館小志》,《南京史志》1984年第5期。福建福清在北京的福清會(huì)館,始于嘉靖末年。葉向高記載:“福清之有會(huì)館,始于嘉靖之季。久之浸圮,其地亦湫墊,往來(lái)不便。吾鄉(xiāng)人謀欲更之,乃相與醵金,買(mǎi)宅一區(qū)于城之西隅,飭以為館。”(70)葉向高:《蒼霞續(xù)草》卷4《重刻福清會(huì)錄序》,明萬(wàn)歷刻本。在北京,尚有莆田會(huì)館,“館之樓上祀莆城隍”。(71)姚旅:《露書(shū)》卷13《異篇上》,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08頁(yè)。史載,萬(wàn)歷四十一年十二月初七日,北京莆陽(yáng)會(huì)館旁“人家生豬,一頭一口四眼四耳,項(xiàng)以下分兩身,身為雌雄,生已即死,懸以示人”。(72)姚旅:《露書(shū)》卷10《錯(cuò)篇下》,第244—245頁(yè)。這則史料足以證明,北京的莆田會(huì)館至晚在萬(wàn)歷四十一年就已創(chuàng)設(shè)。徽州府休寧縣在北京的會(huì)館,“始自明萬(wàn)歷間,經(jīng)營(yíng)草創(chuàng),規(guī)制未閎”。(73)《京師休寧會(huì)館公立規(guī)約》。青陽(yáng)會(huì)館,創(chuàng)設(shè)于“前明萬(wàn)歷中”,且刻有《館規(guī)》30則。(74)汪琬:《鈍翁前后類(lèi)稿》卷25《文稿十三·序三·代青陽(yáng)館規(guī)序》,《汪琬全集箋校》第2冊(cè),第570頁(yè)。浙江湖州在京城的會(huì)館,位于玉河橋之東,原先屬于休寧會(huì)館的舊址,創(chuàng)自萬(wàn)歷二十六年,并訂有《會(huì)館條約》。(75)朱國(guó)禎著、何立民點(diǎn)校:《朱國(guó)禎詩(shī)文集·序·會(huì)館條約序》,第421—422頁(yè)。萬(wàn)歷年間,北京尚有延陵會(huì)館,位于順城門(mén)內(nèi)的石虎胡同。(76)計(jì)六奇:《明季北略》卷19《董心葵大俠》,中華書(shū)局1984年版,第348—349頁(yè)。陜西三原縣在北京有兩所會(huì)館,“諸宦游、計(jì)偕、權(quán)子母人往往入都,即暫寓其中,如抵家舍,甚便焉”。至崇禎四年,陜西涇陽(yáng)也開(kāi)始在北京創(chuàng)設(shè)會(huì)館,位于正陽(yáng)坊。(77)王徵著、林樂(lè)昌編校:《王徵集》卷16《創(chuàng)建涇陽(yáng)會(huì)館記》,西北大學(xué)出版社2015年版,第298頁(yè)。據(jù)陳舜系記載,崇禎八年他充任里長(zhǎng)解送黃冊(cè)進(jìn)京時(shí),寓居于嶺南會(huì)館。同行者有袁州府推官吳鼎元,因浮躁而改調(diào),也赴京補(bǔ)銓。(78)陳舜系:《亂離見(jiàn)聞錄》卷上,李龍潛等點(diǎn)校:《明清廣東稀見(jiàn)筆記七種》,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8頁(yè)。可見(jiàn),在崇禎八年之前,京城嶺南會(huì)館即已創(chuàng)設(shè)。此外,崇禎年間北京尚有山會(huì)會(huì)館,為紹興的同鄉(xiāng)會(huì)館,館址為太監(jiān)諸升的故宅,位于長(zhǎng)安右門(mén)之外受水塘。(79)劉若愚:《酌中志》卷22《見(jiàn)聞瑣事雜紀(j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99頁(yè)。
三、會(huì)館的功能及其演變
從會(huì)館的起源、形成來(lái)看,明清會(huì)館的功能及其演變存在著以下幾種趨勢(shì):一是從文會(huì)館、講學(xué)會(huì)館等向同鄉(xiāng)會(huì)館的轉(zhuǎn)化。這一轉(zhuǎn)化過(guò)程關(guān)乎明清會(huì)館的起源,理應(yīng)加以重新關(guān)注。二是從同鄉(xiāng)會(huì)館向同業(yè)會(huì)館的轉(zhuǎn)化。這一轉(zhuǎn)化過(guò)程體現(xiàn)為會(huì)館從鄉(xiāng)緣轉(zhuǎn)向業(yè)緣。三是會(huì)館名稱(chēng)呈現(xiàn)多樣化的變化趨勢(shì)。這一趨勢(shì)足以證明會(huì)館在功能上得到了更好的拓展。在此略去第一種轉(zhuǎn)化不論,就后兩種會(huì)館功能的轉(zhuǎn)化稍作討論。
(一)從同鄉(xiāng)會(huì)館到工商會(huì)館
在明清會(huì)館的形成及其演變歷程中,商人除了是同業(yè)會(huì)館、公所的熱心支持者之外,又開(kāi)始參與同鄉(xiāng)會(huì)館的建設(shè)。相關(guān)的例子頗多,僅引下面四例加以說(shuō)明:一是北京的歙縣會(huì)館,在嘉慶十九年重修會(huì)館之時(shí),捐款人除了在京紳士、京外諸公之外,又多了茶商、姜店兩類(lèi)人。其中茶商在這次捐款中,共計(jì)有73人,姜店則有錦春號(hào)、錦新號(hào)兩家。(80)徐世寧、楊熷續(xù)錄,徐光文、徐上墉重錄:《重續(xù)歙縣會(huì)館錄·續(xù)錄新集》,第51—53頁(yè)。二是設(shè)于廣西省城的全浙會(huì)館,目的是“以為鄉(xiāng)之仕宦、游幕、商旅之初蒞者解鞍息肩之所”。(81)董秉純:《春雨樓初刪稿》卷6《廣西省垣全浙義園序》,《四明叢書(shū)》第14冊(cè),第8742頁(yè)。可見(jiàn),商人同樣可以得到同鄉(xiāng)會(huì)館的庇護(hù)。三是清代北京的鄞縣會(huì)館,即為鄞縣商人共同籌集資金所建,進(jìn)而供士人至京城參加會(huì)試,可以“解鞍息駕”,“無(wú)賃僦之勞,獲如歸之樂(lè)”。(82)董秉純:《春雨樓初刪稿》卷1《創(chuàng)建鄞縣會(huì)館碑記》,《四明叢書(shū)》第14冊(cè),第8673—8674頁(yè)。四是會(huì)館、公所大多附設(shè)義園、善堂,從而成為一種慈善團(tuán)體。如在四川,浙江會(huì)館就設(shè)有貞節(jié)堂,并附設(shè)恤嫠局,恤嫠名額,“官場(chǎng)十名,幕場(chǎng)十名,商賈十名,共三十名”。(83)《浙江館貞節(jié)堂恤嫠局引》,《浙江館恤嫠局章程清冊(cè)》,清刻本。上述四條材料說(shuō)明,會(huì)館同鄉(xiāng)人員的組成,除同鄉(xiāng)籍官員、幕僚以外,尚包括商賈。這足證同鄉(xiāng)會(huì)館與商人會(huì)館正趨于合流。
商人會(huì)館在明代已經(jīng)出現(xiàn)。入清,更趨繁盛。如在蘇州,建于山塘橋西的嶺南會(huì)館,就為萬(wàn)歷年間由廣州商人建立。東莞會(huì)館,亦始建于天啟五年。還有岡州會(huì)館,俗稱(chēng)扇子會(huì)館,清康熙十七年義寧商人建;東齊會(huì)館,清順治間膠州、青州、登州商人建。(84)顧祿:《桐橋倚棹錄》卷6《會(huì)館》,《蘇州文獻(xiàn)叢鈔初編》,古吳軒出版社2005年版,第611—612頁(yè)。自清中期以后,商人設(shè)立會(huì)館的勢(shì)頭更趨迅猛。如南廒在蘇州閶門(mén)外,為水路要沖之區(qū),凡南北舟車(chē)、外洋商販,畢集于此。各省大賈,自為居停,設(shè)會(huì)館,“極壯麗之觀”。(85)蘭常安:《宦游筆記》卷18,清乾隆十一年刻本。尤其至清末,由于商人到處貿(mào)易,有些在貿(mào)易之地僑居,或聯(lián)同業(yè)之情,或敘同鄉(xiāng)之誼,會(huì)館、公所紛紛崛起。這種會(huì)館、公所,有些為同業(yè)團(tuán)體,如上海的香雪堂,為滬幫鮮肉行的公所;點(diǎn)春堂,為福建汀州、泉州、漳州三府業(yè)花糖洋貨各商在上海建立的公所。(86)民國(guó)《上海縣續(xù)志》卷3《建置下·會(huì)館公所》,收入《地方志·書(shū)目文獻(xiàn)叢刊》,北京圖書(shū)館出版社2004版。在江陰縣,亦分別有綢布業(yè)集裕公所、衣業(yè)錦云公所、錢(qián)紗公所等。(87)民國(guó)《江陰縣續(xù)志》卷3《公所》,《中國(guó)地方志集成》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有些為商人的同鄉(xiāng)團(tuán)體,如清末的上海,有徽寧會(huì)館、泉漳會(huì)館、潮州會(huì)館、浙紹公所等,均是各地同鄉(xiāng)商人所建。而在有些地方,如四川成都的公所設(shè)立,既有同鄉(xiāng)商人之集合體,如西江公所、黔南公所等;亦有同業(yè)之組織,如酒坊公所、醬園公所。(88)根據(jù)傅崇矩記載,清末四川成都之公所,應(yīng)該分為三類(lèi),除了上面所列之同鄉(xiāng)商人公所、同業(yè)公所之外,尚有光緒三十二年在各街設(shè)立的“講理公所”及其他諸如“學(xué)務(wù)公所”“警務(wù)公所”“勸業(yè)公所”“戒煙查驗(yàn)所”“候?qū)徦薄傲?xí)藝所”等。與前兩類(lèi)公所屬于民間組織不同,第三類(lèi)公所屬于官方組織,所以傅崇矩將其列入官立各局所內(nèi)加以敘述。當(dāng)時(shí)成都之公所,分為城內(nèi)與城外兩類(lèi),設(shè)于城內(nèi)者共計(jì)14個(gè),設(shè)于城外者共計(jì)3個(gè)。參見(jiàn)傅崇矩編:《成都通覽·成都之會(huì)館公所》,成都時(shí)代出版社2006年版,第22—23頁(yè)。當(dāng)然,商業(yè)同行雖以行會(huì)為通稱(chēng),而且辦事機(jī)構(gòu)多稱(chēng)會(huì)館、公所,但確實(shí)又與傳統(tǒng)的會(huì)社關(guān)系非淺。換言之,商業(yè)各行亦有結(jié)成會(huì)社之例。如清代湖南武岡之零星京貨店,就專(zhuān)門(mén)合成一會(huì),稱(chēng)為“仁義會(huì)”;長(zhǎng)沙之西幫衣店,共設(shè)七會(huì),其中“軒轅會(huì)”“福佑會(huì)”兩會(huì),屬于店?yáng)|之結(jié)會(huì),而“福主”“福勝”“福興”“福生”“福慶”五會(huì),則屬店伙、客師之結(jié)社。(89)《湖南商事習(xí)慣報(bào)告書(shū)·商業(yè)條規(guī)》,《中國(guó)工商行會(huì)史料集》上冊(cè),第247—248、259、263、265、273—274、287、324、385頁(yè)。按:湖南長(zhǎng)沙靴鞋鋪所設(shè)之“孫祖會(huì)”,名稱(chēng)源自該行之祖師孫祖。此會(huì)始于乾隆四十八年,最初是在乾元宮合祀孫祖。至咸豐初年,在樂(lè)心巷建立孫祖廟之后,改為在乾元宮、孫祖廟兩處辦會(huì)。
尤堪注意者,除商人會(huì)館、同鄉(xiāng)會(huì)館之外,明清兩代,尚有手工工匠、農(nóng)民、仆人設(shè)立的會(huì)館與行會(huì)。清代蘇州的棉染織業(yè)手工工匠,為了增加工資和反對(duì)場(chǎng)主無(wú)故開(kāi)除工人,紛紛成立會(huì)社組織,以與場(chǎng)主抗衡。如雍正元年,踹匠“糾集拜把,商謀約會(huì)”;七年,踹匠又“拜把結(jié)盟”。(90)《雍正朱批諭旨》第42冊(cè),北京圖書(shū)館出版社2008年版,第76頁(yè)。與此同時(shí),踹匠還設(shè)有會(huì)館,如康熙時(shí),“結(jié)黨創(chuàng)立會(huì)館”。(91)江蘇省博物館編:《江蘇省明清以來(lái)碑刻資料選集》,生活·讀書(shū)·新知三聯(lián)書(shū)店1959年版,第40頁(yè)。清代的佃農(nóng)亦開(kāi)始創(chuàng)設(shè)自己的會(huì)館,如康熙五十二年,江西興國(guó)佃農(nóng)創(chuàng)為“會(huì)館”,“遠(yuǎn)近傳關(guān),每屆有秋,先倡議八收七收有差,田主有執(zhí)原額計(jì)租者,即號(hào)召多人,碎人屋宇,并所取攫入會(huì)館”。(92)同治《興國(guó)縣志》卷46《雜記》,收入《中國(guó)地方志集成》,江蘇古籍出版社1996版。農(nóng)民創(chuàng)設(shè)會(huì)館,以作為保護(hù)自己利益的組織,顯然受到商人、手工工匠的影響。又據(jù)西人馬士《中國(guó)行會(huì)考》,時(shí)至清末,在上海的仆人中也開(kāi)始出現(xiàn)行會(huì)組織。在上海1905年12月18日暴亂期間,作為起義計(jì)劃的一部分,所有家庭的仆人在各自的時(shí)間和地點(diǎn),離開(kāi)他們的外國(guó)主人。由于暴亂過(guò)早地舉行,計(jì)劃沒(méi)能貫徹到底。然而,根據(jù)后來(lái)仆人對(duì)其主人的陳述可知,“如果給了通知,即使他們不愿意,但也不得不服從通知的要求而離開(kāi)”。(93)彭澤益主編:《中國(guó)工商行會(huì)史料集》上冊(cè),第73、112頁(yè)。可見(jiàn),城市中的仆人行會(huì)同樣對(duì)其成員行動(dòng)具有約束性。會(huì)館作為同行的組織機(jī)構(gòu),原本是城市的產(chǎn)物,農(nóng)民會(huì)館的出現(xiàn),足以證明明清時(shí)期商品經(jīng)濟(jì)已相當(dāng)發(fā)達(dá),并開(kāi)始向農(nóng)村滲透。
(二)會(huì)館名稱(chēng)的多樣化
在明清時(shí)期,作為一種同鄉(xiāng)或同業(yè)組織,會(huì)館、公所僅僅是最為常見(jiàn)的名稱(chēng)。若是細(xì)究之,其名稱(chēng)堪稱(chēng)千姿百態(tài)。據(jù)清末《湖南商事習(xí)慣報(bào)告書(shū)·會(huì)館》記載,當(dāng)時(shí)湖南的會(huì)館,若是按省份加以區(qū)分,分別有江西的“萬(wàn)壽宮”,福建的“天后宮”,廣東的“嶺南會(huì)館”,江蘇的“蘇州會(huì)館”,安徽的“徽州會(huì)館”“太平會(huì)館”。此外,湘潭有“七幫”之目,常德有“三堂八省”之稱(chēng)。若是按營(yíng)業(yè)加以區(qū)分,則有錢(qián)鋪及雜貨、綢緞業(yè)的“財(cái)神殿”,藥材業(yè)的“神農(nóng)殿”,屠戶(hù)一行的“桓侯廟”,酒館行業(yè)的“詹王廟”。(94)彭澤益主編:《中國(guó)工商行會(huì)史料集》上冊(cè),第73、112頁(yè)。
由此可見(jiàn),除了會(huì)館、公所之外,上面所引述的舉凡“宮”“殿”“廟”之類(lèi),實(shí)則與會(huì)館、公所無(wú)異,均可歸為會(huì)館、公所的別稱(chēng)。其實(shí),明清時(shí)期的會(huì)館,很多與廟、祠合一。如蘇州的鎮(zhèn)江公所,位于小武當(dāng),為乾隆年間鎮(zhèn)江商人在大士庵的基址上建成。建成以后,仍供奉普門(mén)大士,由僧人主持香火。蘇州的磨坊公所,亦位于小武當(dāng),為乾隆五十五年在陸羽樓的基址上改建而成,供奉馬牛王神像,故又稱(chēng)馬牛王廟。(95)顧祿:《桐橋倚棹錄》卷6《會(huì)館》,《蘇州文獻(xiàn)叢鈔初編》,第612、611頁(yè)。此外,明清會(huì)館之中,多設(shè)有宗教神殿。即以在蘇州的商人會(huì)館為例,如嶺南會(huì)館,中設(shè)天后殿、關(guān)帝殿;東齊會(huì)館,中設(shè)關(guān)帝殿;全晉會(huì)館,有關(guān)帝殿;翼城會(huì)館,有關(guān)帝殿。(96)顧祿:《桐橋倚棹錄》卷6《會(huì)館》,《蘇州文獻(xiàn)叢鈔初編》,第612、611頁(yè)。
下面以湖北漢口為例,對(duì)會(huì)館之眾多別名加以梳理。有稱(chēng)“殿”者。如“三皇殿”,為藥材行幫公所,始于清順治十三年;又“老漢義殿”,為循禮坊肉業(yè)公會(huì),始于清康熙六年。有稱(chēng)“庵”者。如“新安準(zhǔn)堤庵”,為徽州商人商業(yè)公所,始于清康熙七年;又“法云庵”,為五金礦砂業(yè)會(huì)議之所,始于清道光十一年。有稱(chēng)“廟”者。如“覃懷藥王廟”,又名“懷慶會(huì)館”,為藥商公所,始于清康熙二十八年;又“關(guān)帝廟”,為山陜旅漢商業(yè)建筑,又稱(chēng)“山陜會(huì)館”,始于清康熙年間。有稱(chēng)“書(shū)院”者。如“新安書(shū)院”,其實(shí)就是徽州會(huì)館,始于清康熙三十四年;又“凌霄書(shū)院”,實(shí)則糧行公所,始于清同治年間。有稱(chēng)“宮”者。如“萬(wàn)壽宮”,實(shí)為商家營(yíng)業(yè)之所,始于清康熙年間;又“仁壽宮”,其實(shí)就是江西臨江會(huì)館。有稱(chēng)“閣”者。如“魯班閣”,實(shí)則工匠集合之所,始于清康熙年間;又“孫祖閣”,又稱(chēng)“鞋業(yè)公所”,始于清乾隆年間。(97)彭澤益主編:《中國(guó)工商行會(huì)史料集》上冊(cè),129—147頁(yè)。按:在傳統(tǒng)中國(guó)社會(huì)中,“廟”并不僅僅是宗教信仰的標(biāo)志,有時(shí)更是有著共同宗教信仰的地方社會(huì)組織。如清代廣東各鄉(xiāng)普遍流行一種“香火廟”,有些甚至經(jīng)費(fèi)相當(dāng)充足,每年的利息,“少至數(shù)百金,多至數(shù)千金”。這些公共經(jīng)費(fèi),大致用于以下兩類(lèi):一是“父老鄉(xiāng)人宴饗之用”,二是“留作爭(zhēng)訟之需”。參見(jiàn)余治:《得一錄》卷10《粵東啟蒙義塾規(guī)條》,《官箴書(shū)集成》第8冊(cè),黃山書(shū)社1997年版,第623頁(yè)。
再以湖南行會(huì)為例,公所或公會(huì),有時(shí)又稱(chēng)“祀”。如邵陽(yáng)紙燭行公會(huì),又稱(chēng)“福佑祀”;武岡之染紙作坊的同行組織稱(chēng)“梅葛祀”;武岡之衣店,則稱(chēng)“軒轅祀”。(98)《湖南商事習(xí)慣報(bào)告書(shū)·商業(yè)條規(guī)》,《中國(guó)工商行會(huì)史料集》上冊(cè),第314、328、383頁(yè)。按:行會(huì)組織稱(chēng)“祀”,其得名顯然來(lái)自行業(yè)成員之共同祭祀。換言之,一個(gè)行會(huì)組織,同時(shí)可以構(gòu)成一個(gè)祭祀圈。由此而來(lái)者,則是行會(huì)組織稱(chēng)“福”。如湖南益陽(yáng)煙匠之行會(huì)組織,始自清乾隆年間的“永年福”,參見(jiàn)《中國(guó)工商行會(huì)史料集》上冊(cè),第434頁(yè)。或稱(chēng)“公司”。如清光緒年間長(zhǎng)沙之煙店,就成立了“煙稅公司”;光緒三十二年,重慶之瓦窯業(yè),亦設(shè)有“瓦窯公司”。(99)彭澤益主編:《中國(guó)工商行會(huì)史料集》上冊(cè),第426、563頁(yè)。
此外,亦有稱(chēng)“堂”者。如清代山西澤州府梨園行,為了支應(yīng)官差,專(zhuān)門(mén)設(shè)立了“五聚堂”,府屬各縣戲班均可以寓居于此,同時(shí)也是梨園行的行業(yè)會(huì)所。堂中設(shè)立班頭一人,支應(yīng)差務(wù),以便公私兩便。在五聚堂中,祭祀行業(yè)之神,正中為“開(kāi)元皇帝”,即唐玄宗李隆基,是梨園行的祖師爺;左祀“三官”,是為了祈禱賜福;右祀“財(cái)神”,則是為了祈禱多富。此外,尚附祭大王、咽喉、山神。(100)《五聚堂紀(jì)德碑序》,馮俊杰編著:《山西戲曲碑刻輯考》卷9,中華書(shū)局2002年版,第469—470頁(yè)。
(三)會(huì)館功能的演變
商業(yè)會(huì)館、公所,或?yàn)橥瑯I(yè)會(huì)館,或?yàn)橥l(xiāng)商人公所,雖也帶有同鄉(xiāng)會(huì)的性質(zhì),但與明清兩代通行的同鄉(xiāng)會(huì)館稍有不同。同鄉(xiāng)會(huì)館與商業(yè)會(huì)館相較,至少有兩點(diǎn)不同之處:一是同鄉(xiāng)會(huì)館的商業(yè)色彩極為淡薄,有些甚至禁止在會(huì)館內(nèi)進(jìn)行與商業(yè)有關(guān)的活動(dòng)。如當(dāng)時(shí)規(guī)定,會(huì)館只是衣冠薈萃之地,“不得寄存貨物,粘貼招牌”。(101)《上湖南會(huì)館傳書(shū)》卷6《新議章程》,清刻本。二是從這些會(huì)館的寓館條規(guī)來(lái)看,也不是同業(yè)或同鄉(xiāng)商人的會(huì)議之所,而只是為鄉(xiāng)、會(huì)場(chǎng)寓考而設(shè),即為同鄉(xiāng)應(yīng)試士子、選官士紳提供方便。如清代北京休寧會(huì)館的《館寓條規(guī)》就規(guī)定:會(huì)館只為應(yīng)試及需次者而設(shè),此外概不得與;鄉(xiāng)試、會(huì)試、候選、候補(bǔ)均以文書(shū)為憑,若無(wú)文書(shū),以及不是應(yīng)試的生監(jiān),就不得寓于會(huì)館。休寧本籍紳士,可以寓館;若為寄籍,就必須詢(xún)明鄉(xiāng)村、姓名,確有證據(jù),方準(zhǔn)寓居。寄籍久遠(yuǎn),須同縣京官力保,若無(wú)保人,就不準(zhǔn)寓居館內(nèi)。(102)《館寓條規(guī)》,《京師休寧會(huì)館公立規(guī)約》。
清代北京,同鄉(xiāng)會(huì)館林立。據(jù)現(xiàn)存的會(huì)館條例、章程來(lái)看,較為著名者有:休寧會(huì)館,始建于明萬(wàn)歷年間,至清乾隆時(shí)重建。(103)北京休寧會(huì)館的始建乃至沿革狀況,可詳見(jiàn)《京師休寧會(huì)館公立規(guī)約》。河南全省會(huì)館,共有七處:中州東館,在騾馬市大街路北;中州南館,在米市胡同南頭路西;中州新館,在丞相胡同北頭路東;嵩云草堂,在達(dá)智橋東頭路北;嵩陽(yáng)別業(yè),在騾馬市大街路北;中州鄉(xiāng)祠,在上斜街路北;河南會(huì)館,在粉房琉璃街路東。(104)《京師河南全省會(huì)館管理章程》,民國(guó)元年修正本。河間會(huì)館,乾隆年間由舒成龍創(chuàng)建。(105)關(guān)于北京河間會(huì)館創(chuàng)設(shè)及沿革,可詳見(jiàn)《河間會(huì)館錄》,清刻本。安徽會(huì)館,定有公議條規(guī),光緒十二年九月重訂規(guī)條。(106)安徽會(huì)館重訂條規(guī),詳見(jiàn)《京城安徽會(huì)館存冊(cè)》,清光緒十二年重訂本。浙閩會(huì)館,民國(guó)四年重訂章程。(107)參見(jiàn)《重訂浙閩會(huì)館章程》,清刻本。江西會(huì)館,道光二十九年公定條例。(108)《江西會(huì)館紀(jì)略·條例》,清道光二十九年訂本。上湖南會(huì)館,議有章程,定有傳書(shū)。(109)參見(jiàn)《上湖南會(huì)館傳書(shū)》,清刻本。又根據(jù)光緒年間人李虹巖的詳細(xì)記錄,當(dāng)時(shí)各省在北京的同鄉(xiāng)會(huì)館,已達(dá)382處(110)李若虹:《朝市叢載》卷3《會(huì)館》,北京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46—62、146頁(yè)。,并呈現(xiàn)以下幾個(gè)特點(diǎn):一是會(huì)館或稱(chēng)“試館”,大抵保留了會(huì)館起源時(shí)的稱(chēng)謂;二是會(huì)館除了原先的老館之外,又分別出現(xiàn)了新館,于是同鄉(xiāng)會(huì)館有老館、新館之別;三是同一地域在北京不止一處會(huì)館,有些甚至有兩處或更多處的會(huì)館;四是從某種角度上說(shuō),鄉(xiāng)祠同樣具有會(huì)館的功能;五是有時(shí)往往同鄉(xiāng)與同業(yè)合而為一;六是縣亦開(kāi)始在京城設(shè)立會(huì)館;七是以山西人所設(shè)會(huì)館居多。
至于工商會(huì)館、公所的數(shù)量,其實(shí)與經(jīng)濟(jì)和商業(yè)的繁榮程度密切相關(guān),亦存在地域差異。明清兩代,會(huì)館、公所大多集中于北京、南京、蘇州、杭州等經(jīng)濟(jì)發(fā)達(dá)的城市,自清末乃至民國(guó)時(shí)期,上海、漢口等開(kāi)埠城市,逐漸取代北京等傳統(tǒng)城市,成為工商會(huì)館、公所最為集中的城市。據(jù)成立于民國(guó)元年的會(huì)館公所聯(lián)合會(huì)調(diào)查,當(dāng)時(shí)漢口約有200個(gè)工商會(huì)館、公所。(111)彭澤益主編:《中國(guó)工商行會(huì)史料集》上冊(cè),第130、76、90—91頁(yè)。又據(jù)民國(guó)十二年出版的《上海指南》,當(dāng)時(shí)上海共有工藝公所58個(gè),商業(yè)公所117個(gè),此外還有新成立的農(nóng)業(yè)團(tuán)體、工廠聯(lián)合會(huì)以及商務(wù)運(yùn)輸公會(huì)151個(gè),三項(xiàng)所加,總數(shù)已達(dá)326個(gè)。(112)阿維那里烏斯:《中國(guó)工商同業(yè)公會(huì)》,《中國(guó)工商行會(huì)史料集》上冊(cè),第128頁(yè)。反觀北京,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jì),在清代末年,僅有商人會(huì)館8個(gè),分別為文昌會(huì)館、長(zhǎng)春會(huì)館、顏料會(huì)館、藥行會(huì)館、仙城會(huì)館、煙行會(huì)館、安平公所、正乙祠。(113)李若虹:《朝市叢載》卷3《會(huì)館》,北京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46—62、146頁(yè)。到了1928年,北京所有工商行會(huì)均已屬總商會(huì)統(tǒng)轄,總數(shù)亦僅有55個(gè)。東北的哈爾濱,據(jù)民國(guó)十一年出版的《哈爾濱指南》,在哈爾濱總商會(huì)之下,僅有12個(gè)工商公所,分別為濱江縣商會(huì)、銀行公會(huì)、錢(qián)業(yè)公會(huì)、雜貨商公會(huì)、油業(yè)公會(huì)、運(yùn)輸公會(huì)、風(fēng)船公會(huì)、糧業(yè)公會(huì)、當(dāng)商公會(huì)、火磨公會(huì)、木商公會(huì)、工業(yè)維持會(huì)。(114)阿維那里烏斯:《中國(guó)工商同業(yè)公會(huì)》,《中國(guó)工商行會(huì)史料集》上冊(cè),第128頁(yè)。這大抵顯示了在會(huì)館功能演變過(guò)程中,工商會(huì)館所呈現(xiàn)出來(lái)的區(qū)域轉(zhuǎn)移態(tài)勢(shì)。
余 論
盡管會(huì)館的定義有所歧義,但會(huì)館的出現(xiàn),顯然還是源于以下兩方面的原因:一是“會(huì)館為崇祀鄉(xiāng)賢之地,春秋祭祀”。(115)《江南會(huì)館義園征久錄》卷4《公訂會(huì)館木榜條規(guī)》。換言之,會(huì)館是一種同鄉(xiāng)會(huì)組織,原為鄉(xiāng)、會(huì)場(chǎng)寓考而設(shè),目的無(wú)非是“為奉祀事而聯(lián)鄉(xiāng)誼,且便于會(huì)議”。(116)《江南會(huì)館義園征久錄》卷4《會(huì)館落成公議條規(guī)》。就此而論,西人馬士在《中國(guó)行會(huì)考》中,將同鄉(xiāng)會(huì)館的主要特征定義為“其全部成員都是來(lái)到外地的同鄉(xiāng)官吏和同鄉(xiāng)商人”(117)彭澤益主編:《中國(guó)工商行會(huì)史料集》上冊(cè),第130、76、90—91頁(yè)。,大抵把握住了同鄉(xiāng)會(huì)館的底蘊(yùn)。二是明清時(shí)期,由于商人力量的崛起,在商業(yè)繁華之處設(shè)會(huì)館,聯(lián)鄉(xiāng)誼,團(tuán)結(jié)同行。關(guān)于此點(diǎn),日本東亞同文會(huì)編《中國(guó)經(jīng)濟(jì)全書(shū)·會(huì)館及公所》有詳細(xì)討論,引述如下:“蓋會(huì)館、公所者,所以固團(tuán)體,重信義,為商業(yè)之機(jī)關(guān)也。且清國(guó)自古以農(nóng)立國(guó),崇本抑末之說(shuō),深中于人心。官之于商,刻削之而已,困辱之而已,凡商情之向背,商力之盈虧,置若罔聞,不有會(huì)館公所以維持之,保護(hù)之,欲求商業(yè)之發(fā)達(dá),豈不難哉。”(118)彭澤益主編:《中國(guó)工商行會(huì)史料集》上冊(cè),第130、76、90—91頁(yè)。
會(huì)館又是一種群體組織。它的設(shè)立,“乃依群為結(jié)合,特大群中之一小群而已”。(119)《山西湖廣會(huì)館章程·序》,清刻本。所以,會(huì)館又與會(huì)社團(tuán)體關(guān)系頗密。在清代,京城、外省各官,通常以“同年”“同鄉(xiāng)”“同僚”為紐帶,在每年春初宴集一次,俗稱(chēng)為“團(tuán)拜”。(120)清人陳兆侖以“團(tuán)拜”為題,作詩(shī)一首,云:“登場(chǎng)傀儡漫相嗤,肅肅班行演舊儀。云路飛騰凡幾輩,苔苓氣誼重連枝。一舟人海歡相集,百里雷封慎所司。忽向歌筵縈昔夢(mèng),春明逐隊(duì)少年時(shí)。”參見(jiàn)潘煥龍:《臥園詩(shī)話(huà)》卷6,高洪鈞編:《明清遺書(shū)五種》,北京圖書(shū)館出版社2006年版,第239頁(yè)。團(tuán)拜之會(huì),通常由值年一二人承辦,開(kāi)筵演劇(121)關(guān)于會(huì)館中所設(shè)供團(tuán)拜或祭祀演戲之用的戲臺(tái),西人瑪高溫有如下描述:“其最引人注目的部分,是為敬神而演戲的園庭,它的一端是一個(gè)戲臺(tái),另一端是神龕圣祠;環(huán)繞戲臺(tái)的圍欄上,那些有身份的人邊看戲,邊聊天,邊飲宴;下面露天場(chǎng)地則免費(fèi)提供給一般公眾享用。”參見(jiàn)瑪高溫:《中國(guó)的行會(huì)》,《中國(guó)工商行會(huì)史料集》上冊(cè),第8頁(yè)。,費(fèi)用多達(dá)數(shù)百兩銀子,稍次者亦必?fù)竦貢?huì)飲。究其原因,還是因?yàn)榫煹卮笕吮姡?jīng)年不謀一面,不過(guò)借此得以聚晤,聯(lián)絡(luò)友誼。外省亦然,其團(tuán)拜多聯(lián)合商界共同舉行。(122)徐珂:《清稗類(lèi)鈔·師友類(lèi)·以團(tuán)拜聯(lián)友誼》,中華書(shū)局2003年版,第3594頁(yè)。在會(huì)館中,每年亦定期舉行“團(tuán)拜會(huì)”“追祭會(huì)”“懇親會(huì)”,聯(lián)絡(luò)鄉(xiāng)情,追祭鄉(xiāng)賢。如北京的休寧會(huì)館,每年春秋二季,即四月與十月,分別舉行團(tuán)拜會(huì),“招集正副會(huì)員,并臨時(shí)來(lái)京之鄉(xiāng)人,以共敦鄉(xiāng)誼”;而在清明、中元節(jié),又行追祭會(huì),“招集正副會(huì)員,親詣義園祭拜”。(123)《京都休寧會(huì)館公立規(guī)約》。而北京的河南會(huì)館,每年陽(yáng)歷四月間,開(kāi)一次懇親會(huì),“公宴同鄉(xiāng),以期聯(lián)絡(luò)鄉(xiāng)誼,并報(bào)告各館所有出入款項(xiàng),及籌議各館進(jìn)行整頓事宜”。(124)《京師河南全省會(huì)館管理章程》。
同鄉(xiāng)、同業(yè)組織的名稱(chēng),大抵可分為以下兩類(lèi):一為會(huì)館,一為公所。前者屬于同鄉(xiāng)的集合,后者屬于同業(yè)的集合。同業(yè)的未必同鄉(xiāng),但同鄉(xiāng)多半同業(yè)。(125)《清季上海地方自治與基爾特》,《中國(guó)工商行會(huì)史料集》上冊(cè),第182頁(yè)。揆之明清同鄉(xiāng)會(huì)館的實(shí)況,其同鄉(xiāng)的概念,既可以是同省,亦可以是相同的府、州、縣。即使是在相同縣份的同鄉(xiāng)會(huì)館中,同樣不乏來(lái)自外縣之人的熱心捐款。換言之,“同郡異邑”亦即同府不同縣的人,允許加入會(huì)館。如明代在北京建立的歙縣會(huì)館捐款錄中,列有三名外邑之人,分別為:方邦度,戶(hù)部郎中,婺源人;潘懷,揚(yáng)州府通判,婺源人;黃騰宇,績(jī)溪人。為此清人徐光文專(zhuān)門(mén)作按語(yǔ)云:“以上三人皆外邑輸資入館。此同郡異邑入館之始也。”(126)徐世寧、楊熷續(xù)錄,徐光文、徐上墉重錄:《重續(xù)歙縣會(huì)館錄·續(xù)錄前集·捐款錄》,第21頁(yè)。這一點(diǎn)顯然頗值得關(guān)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