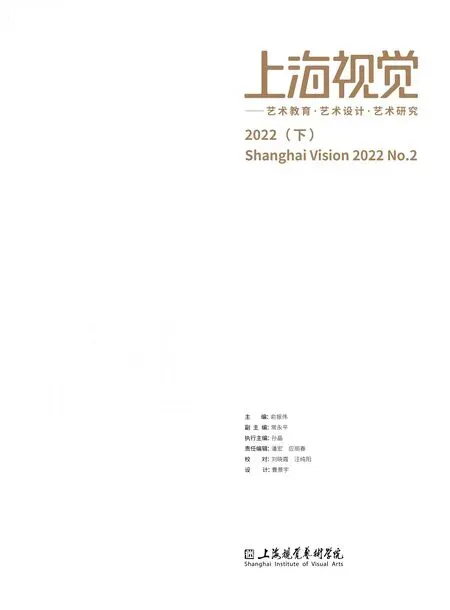基于 “景觀社會” 理論的 “奇觀電影” 之殤
方景鋒 吳春集
(上海視覺藝術(shù)學院,上海 201620)
一、“奇觀電影”:新電影范式的興起
電影被稱為第七藝術(shù),是一種綜合藝術(shù)形式,囊括文學、戲劇、音樂、舞蹈、表演、美術(shù)等多種藝術(shù)要素,其藝術(shù)特色更加復雜更加多樣。電影與戲劇、文學關(guān)系十分密切,早期電影深受戲劇影響,帶有明顯的戲劇特點,其戲劇性和情節(jié)因素十分突出,表演、語言對白也顯得非常重要。尤其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拍攝的黑白電影,它們更像是文學作品的視覺再現(xiàn)。因此,戲劇性、文學性曾經(jīng)是早期電影的內(nèi)核,以敘事為首要目標。
隨著電影的發(fā)展,在敘事電影之外,“奇觀電影”的新范式逐漸發(fā)展起來,并占據(jù)了主導地位,成為主流電影。所謂“奇觀電影”,就是電影中“非同一般的具有強烈視覺吸引力的影像和畫面,或是借助各種高科技電影手段創(chuàng)造出來的奇幻影像和畫面及其所產(chǎn)生的獨特的視覺效果”[1]。好萊塢電影就是奇觀電影的受益者,為了吸引觀眾,好萊塢的導演們利用航拍、斯坦尼康等設(shè)備拍攝出平滑流暢又動感十足的運動鏡頭;利用三維動畫技術(shù)制造出了各色虛擬角色(如:機器人、外星人、變異人、神魔鬼怪)、各種奇幻場景;利用短鏡頭切換制造出了緊張激烈、扣人心弦的快節(jié)奏敘事方式;利用藍屏摳像數(shù)碼合成技術(shù)合成出極具視覺沖擊力的唯美畫面。憑借高科技技術(shù)手段,好萊塢制作出了一部又一部的“奇觀電影”,使得好萊塢電影風靡全球。世界上票房最高的電影《阿凡達》就是好萊塢電影的代表作品,導演詹姆斯·卡梅隆利用最先進的三維動畫技術(shù),創(chuàng)造出了潘多拉星球的魔幻世界。雖然觀眾清楚電影世界是虛構(gòu)的,但在幻像面前,在視覺奇觀的吸引下,觀眾還是完全沉浸在虛構(gòu)的世界中不能自拔。
“奇觀電影”的概念源于法國哲學家德波。德波提出了“景觀社會”的概念,在德波看來,“景觀”是新的社會批判理論的關(guān)鍵詞,這是指一種被展現(xiàn)出來的可視的景象,也意指一種主體性的、有意識的表演和做秀[2]。
德波的理論為女性主義電影理論提供了理論基礎(chǔ),20世紀70年代以來,在結(jié)構(gòu)主義、符號學、精神分析、意識形態(tài)、解構(gòu)主義、后結(jié)構(gòu)主義的理論盛行下,西方女權(quán)主義嶄露頭角,女權(quán)主義電影理論成為女權(quán)主義運動的一個重要分支,把電影放在女權(quán)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下去研究,因此女權(quán)主義電影理論采用的研究方法不是美學,而是結(jié)構(gòu)主義符號學、精神分析學、意識形態(tài)理論、解構(gòu)理論、敘事學研究等研究方法。女性主義電影理論深刻闡釋了好萊塢電影影像所泄露出的男性欲望和侵略心理,其批判的縝密性和有力程度遠遠超出了單純的女權(quán)范圍,成為對電影制作和電影理論的全面反思和質(zhì)疑,為電影研究帶來了新的靈感和啟迪[3]。
女性主義電影理論的代表:勞拉·穆爾維(Laura Mulvey)(圖1),1975年發(fā)表在英國《銀幕》雜志的文章《視覺快感與敘事電影》(Visual Pleasure and Narrative Cinema)提出了電影中的“奇觀”現(xiàn)象。穆爾維依據(jù)精神分析學說,認為“奇觀”與電影中“控制著形象、色情的看的方式”相關(guān),電影鏡頭代表的是男性凝視的目光的觀點。《視覺快感與敘事電影》一文是女性主義電影理論的奠基之作,為電影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

圖1 勞拉·穆爾維
勞拉·穆爾維提出,“奇觀電影”拋棄了戲劇藝術(shù)所擅長的敘事手段,而強化了電影所特有的視覺藝術(shù)手段,即:無意識構(gòu)建觀看方式和觀看快感的諸種方法。尤其是好萊塢電影,好萊塢風格(以及所有受其影響的電影)的魔力充其量不過是來自于它對視覺快感游刃有余的操縱,這雖然不是唯一的因素,但卻是一個重要方面[4]。雖然穆爾維并不是在為奇觀電影搖旗吶喊,但奇觀電影的發(fā)展壯大確實使得電影藝術(shù)更具視覺吸引力和娛樂化,促進了電影商業(yè)化的發(fā)展,這也可以視為“奇觀電影”對電影發(fā)展的貢獻。
正如美國哲學教授道格拉斯·凱爾納在《波德里亞:一個批判性讀本》中所指出的“奇觀(spectacle)”所造成的廣泛“娛樂”迷惑之下[5],“大多數(shù)”會偏離自己本真的批判性和創(chuàng)造性,淪為“奇觀(spectacle)控制”的奴隸[6]。由于強調(diào)“視覺奇觀”,有時便不可避免地弱化了電影的敘事性。由于過分追求“視覺奇觀”,有時甚至導致忽略了故事的合理性,出現(xiàn)大量不符合事實邏輯的情節(jié)點。
張藝謀導演的電影《懸崖之上》最終也未能避開這一陷阱。
二、《懸崖之上》:“奇觀電影”之殤
張藝謀早期導演了《紅高粱》《大紅燈籠高高掛》《菊豆》《秋菊打官司》《一個都不能少》等現(xiàn)實主義影片,運用民族文化符號,如:紅高粱、紅蓋頭、花轎、顛轎歌、祭酒神、四合院、京劇、紅燈籠等民族元素,不斷地創(chuàng)新與探索,創(chuàng)造出有著濃郁東方文化韻味的獨特電影美學風格,成為了第五代導演的一面旗幟。
在早期電影中,張藝謀也在作品中展示了很多具有高度東方寓意的文化奇觀,比如染坊里的人性覺醒與掙扎(《菊豆》),西部高粱地里的狂野激情(《紅高粱》),北方大院中內(nèi)卷的命運悲歌(《大紅燈籠高高掛》)等,這一方面滿足了西方人對中國文化的獵奇心理,另一方面也因為其中或隱或顯的“后殖民主義”傾向遭到批判。
20世紀90年代后,張藝謀開始走商業(yè)化電影道路,拍攝了《英雄》《十面埋伏》《滿城盡帶黃金甲》《長城》等商業(yè)大片。商業(yè)電影制作資金充足,充分利用現(xiàn)代先進電影特效技術(shù),加入更具視覺沖擊力、感染力的觀賞性、娛樂性元素。受此影響,張藝謀的導演風格發(fā)生明顯變化,從充滿人文關(guān)懷的敘事電影開始走向強調(diào)視覺沖擊力的“奇觀電影”。為了迎合觀眾的口味,這個時期張藝謀的電影更加注重視覺快感,故事節(jié)奏快、鏡頭畫面信息量大、充滿科幻色彩的武術(shù)動作設(shè)計、獨特的構(gòu)圖等電影美學特點。不過,張藝謀的電影依然保留了其主旋律電影、文藝電影的一些影子,融合形成了一種新的電影美學特點。
近幾年,在中國年輕一代電影人的努力下,中國電影發(fā)展有了新的趨勢,有學者稱之為“新主流電影”[7]。受“新主流電影”的影響,張藝謀執(zhí)導拍攝了《懸崖之上》(圖2)。

圖2 《懸崖之上》海報
影片改編自小說《懸崖》,故事發(fā)生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后,地點是中國東北哈爾濱。講述的是從蘇聯(lián)受訓歸來的四位共產(chǎn)黨特工,奉命執(zhí)行“烏特拉”秘密行動,因為叛徒的出賣,深陷險境,如立懸崖之上。關(guān)鍵時刻,共產(chǎn)黨安插在特務內(nèi)部的臥底周乙發(fā)揮關(guān)鍵作用,與敵斗智斗勇,經(jīng)歷各種驚心動魄的秘密行動,最后勝利完成任務的故事。
《懸崖之上》故事發(fā)生在白雪茫茫的東北地區(qū),因此整部影片都是黑白色調(diào)的交響,暗示著光明(共產(chǎn)黨)與黑暗(敵人)無處不在的斗爭,形式與內(nèi)容完美統(tǒng)一。影片既有讓觀眾感動落淚的悲壯場景,也有為國為民的民族大義。立意積極向上,政治站位高,有熱血有情懷,演員演技細微且精湛絕倫,畫面唯美震撼且具有視覺沖擊力,精準營造“歷史原貌”,清晰詮釋和彰顯了時代的主流精神,具有重大的愛國主義教育意義。影片警示國人:今天的和平生活來之不易,我們要感恩那些拋頭顱灑熱血的革命前輩,好好珍惜當下,不辜負革命前輩用犧牲換來的和平生活。為了更好地還原故事的艱苦環(huán)境和真實的歷史事件,導演堅持實景拍攝,沒有使用三維動畫技術(shù)制作場景,而是實景搭建了一個哈爾濱街道和內(nèi)部建筑,使得影片視覺上更加真實可信。
總體而言,這部影片仍然可以歸諸“奇觀電影”范疇,是一場畫面唯美的視覺盛宴。但影片沒能脫離“奇觀電影”與生俱來的魔咒,過分強調(diào)“奇觀”帶來的視覺快感,忽略了故事合理性,弄巧成拙,成為“奇觀”的奴隸。
三、殤在何處:視覺效果與敘事邏輯
(一) 尺度過大,血腥畫面過多
“視覺奇觀”強調(diào)視覺沖擊力,為了達到這一效果,影片中血腥畫面過多,尺度過大,比如雪地里的正面擊打、砍手、砸擊頭部的飆血鏡頭,還有刑場爆頭的血腥場面,雖然使用了蒙太奇技巧,但仍然會給觀眾帶來不適,尤其對青少年來說過于暴力。一方面是為了追求奇觀效果而過于追求視覺沖擊力,另一方面因為是主流電影,需要滿足不同年齡段的觀眾,暴力鏡頭不應以成人觀眾為尺度要求,應該以最低年齡段觀眾適合度為宜。
(二)節(jié)奏過快,導致劇情不明
奇觀電影的另一重要特征是:極快的敘事節(jié)奏,極具視覺沖擊的震撼場面。鏡頭剪輯快與故事節(jié)奏快構(gòu)成了奇觀電影的典型形態(tài)。傳統(tǒng)敘事電影那種娓娓道來的敘事模式已不再適合于當代觀眾的觀賞需求,為了加快故事節(jié)奏,導演有時會簡化甚至省略次要情節(jié),花更多的時間篇幅強調(diào)重要情節(jié)。但簡化不當就會造成故事不清不明的問題,弄巧成拙,敘事性被肢解,從而喪失了整體性和邏輯性。
《懸崖之上》也做了不少簡化處理,起到了非常不錯的效果。如共產(chǎn)黨特工張憲臣(張譯飾演)被俘后,用曲別針撬開手銬逃走,雖然導演并沒有用畫面直接交代曲別針是周乙(共產(chǎn)黨臥底,于和偉飾演)給張憲臣的。但導演用一個特寫鏡頭拍攝曲別針,做了一個視覺上的強調(diào),足以讓觀眾想象到:曲別針是周乙偷偷給張憲臣的,這種處理堪稱經(jīng)典,既增強了懸念感,又加快了敘事節(jié)奏。
然而另外幾處簡化處理則非常不妥當,甚至讓觀眾感覺迷惑。敵偽警察廳長(倪大紅飾演)得知一本書是地下黨的密碼本,于是在書店安插特務日夜看守,等待特工來自投羅網(wǎng)。張憲臣早就料到敵人會利用這一點抓捕自己,于是男扮女裝來到書店,在敵人嚴密看守的情況下把書偷走,拿到了密碼本。這原本是觀眾十分期待的精彩橋段,也是考驗導演能力的一場重頭戲,但導演卻把劇情省略了,一筆帶過。張憲臣僅僅從書架旁邊經(jīng)過,隨后書就不見了,只剩下了書的封皮。從頭到尾觀眾并沒有看到張憲臣接觸到書,令觀眾非常遺憾和迷惑。
張憲臣離開書店后,已經(jīng)遠離事發(fā)地,并恢復男裝,像普通路人一樣走在大街上。但特務在大街上搜查時,看到張憲臣,就立馬認出他,火速展開追擊。特務是憑什么辨認出已經(jīng)恢復男裝的張憲臣的(因為觀眾是全知視角,知道是張憲臣偷的書,但此時的特務是不知道的),完全不符合正常邏輯。
在特務安排的住處,女特務準備了兩份有毒的咖啡,并提醒臥底周乙,不要弄錯了有毒咖啡。周乙悄悄替換了咖啡,讓其中一個特務喝有毒咖啡。結(jié)果出現(xiàn)了三人暈倒的后果:男特工楚良(朱亞文飾演)、女特工王郁(秦海璐飾演)、男特務(李乃文飾演)全都暈倒。女特務見狀產(chǎn)生了懷疑,周乙解釋是男特務自己喝錯了咖啡。女特務居然相信了周乙,沒有繼續(xù)追著問下去。明明準備了兩杯有毒的咖啡,怎么可能有三個人暈倒,這么明顯的數(shù)字漏洞,正常情況下訓練有素的特務,怎么會不產(chǎn)生懷疑。 為了吸引觀眾設(shè)置懸念,但忽略了懸念的合理性。
(三)期待落空:中途更換主角
勞拉·穆爾維認為,在奇觀電影中女性作為“奇觀”吸引觀眾,而男性是作為推動故事發(fā)展、促成故事的主導者。為了商業(yè)利益和明星奇觀效應,在影片宣發(fā)階段過度宣傳影片男主角—頂流明星張譯,觀眾對此充滿期待。但實際上張譯(圖3)只是影片前半部分的主角,影片后半部分主角更換成了臥底周乙(于和偉飾演,圖4)。

圖3 《懸崖之上》男主角:張憲臣

圖4 《懸崖之上》男主角:周乙
影片后半部分,臥底周乙在敵人內(nèi)部與特務周旋,主導其他同事順利完成了“烏特拉”任務,完成任務后還全身而退,沒有暴露自己的身份;又順利救出兩個女特工:王郁和小蘭;把張憲臣和王郁兩個失散多年的孩子找到,交給了王郁,影片結(jié)尾還親自清除了共產(chǎn)黨的叛徒。周乙可謂是得到了主角的所有光環(huán),是全片最關(guān)鍵角色,而張譯飾演的張憲臣幾乎沒有起到什么積極作用,還拖了周乙的后腿。這種設(shè)置給觀眾造成了巨大的心理落差。觀眾是帶著對張譯的期待走進電影院的,所以影片看到一半時,觀眾失去了一直跟隨著的主角,這既是追求奇觀電影所帶來的設(shè)計(隱瞞觀眾,制造懸念),也是奇觀電影所帶來的敗筆。
中途更換主角是電影中的大忌,而為了迎合觀眾,真正的奇觀設(shè)置,應該是讓張譯這個主角堅持到最后,不斷給觀眾驚喜,這一點電影《風聲》就做得更好。
(四)女性角色:設(shè)計理念游離
勞拉·穆爾維提出,在常規(guī)敘事電影中,女性的出現(xiàn)是奇觀中不可或缺的因素,但女性角色在視覺上的出現(xiàn)往往會阻礙故事線索的發(fā)展,在觀看色情的時刻凍結(jié)了動作的流程[8]。與電影中男性主角不同,“奇觀電影”中的女性則是男性凝視下的視覺與色情符號。女性形象在電影中是作為被動者、被窺視者而出現(xiàn)的,她是作為一個奇觀、超脫于敘事之外、純粹的被看的客體。女性自身便理所當然的成為了“花瓶”。
《懸崖之上》中的兩個女特工便是這樣的“花瓶”,她們魅力四溢,被展示,被性感化。在“烏特拉”任務中沒有起到任何作用,完全的陪襯,到故事的后半部分兩個女角色好像消失了一樣,完全離開了劇情。因此,兩名女特工完全是為了吸引觀眾的眼球而強行加入的角色,這樣的設(shè)置造成故事非常不合理。真實的戰(zhàn)爭時期,女性情報人員為了掩人耳目,一般會與男性情報人員扮演成情侶夫妻一起行動,以減少別人的懷疑。在特殊情況下,還可以利用女性的柔弱來做掩護,獲得其他人的同情心,來達到完成任務的目的。影片中明顯沒有利用女特工的這些特點,為了博得眼球給女特工設(shè)計夸張的打斗動作,女特工小蘭通過敏捷的身手,還成功拯救了兩次男特工,強行加入的動作必然不符合邏輯,顯得兩個男特工非常不稱職,甚至有點無能。
在火車站的一段戲中,特務已經(jīng)知道了共產(chǎn)黨特工要在哈爾濱下車,開始檢查去哈爾濱的車票。小蘭(共產(chǎn)黨女特工)為了能安全離開火車站,躲避特務的盤查,不得已跳下火車,扭傷了腳,走路一瘸一拐,途中被一個特務追上,小蘭反抗,開槍將對方擊斃。小蘭的槍聲在寒冷的冬夜里特別刺耳,根據(jù)常識,聲音在冬天氣溫非常低時會傳出去很遠。但附近眾多追蹤的特務,居然全都沒聽到槍聲來抓小蘭。小蘭更是在一瘸一拐的情況下,最后順利離開了火車站,到了哈爾濱。這段戲在故事中的作用顯得非常多余,是強行為女角色加戲的結(jié)果。
四、結(jié)語
“奇觀電影”順應時代發(fā)展需求,以觀賞性的圖像化、動作化為視覺主題,突出視覺快感,強化畫面視覺沖擊力,為電影藝術(shù)的進步提供了新的范式。但“奇觀電影”不能因強調(diào)“奇觀”而淡化甚至弱化敘事,不能中了“奇觀電影”與敘事電影二元對立的魔咒。更不要弄巧成拙,讓“視覺盛宴”淪為“視覺疲勞”。
電影應給人以啟迪,洗滌、凈化心靈,告訴我們?nèi)绾胃玫厣睿A我們的精神世界。“奇觀”要為敘事服務而不是凌駕敘事之上,其表達重點是講好故事,強調(diào)故事內(nèi)在邏輯,注重人物塑造。一味強調(diào)“奇觀”而忽視故事合理性,即使提供了一場視覺盛宴,也會因為失去了故事內(nèi)核而難以成為經(jīng)典之作。